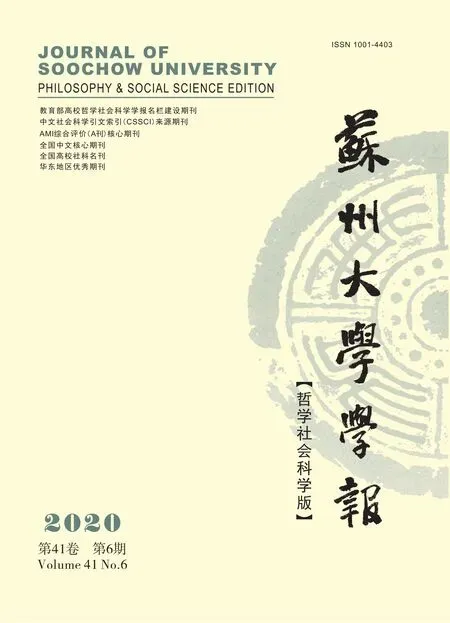论清代桐城诗歌总集的体派意识与文学权力互动
史哲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桐城夙为诗国,戴名世云:“江淮之间,士之好为诗者莫多于桐。”[1]32桐城诗派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基本已被学界承认,但其构成、风格、演化诸多内容依然存在可论之处。应注意到,近年来明清诗歌总集的整理与研究逐渐得到广泛重视,而清代桐城一地辑纂地方诗歌总集不少,就目前知见,有潘江《龙眠风雅》六十四卷(续编二十八卷),王灼《枞阳诗选》二十卷,文汉光、戴钧衡《古桐乡诗选》十二卷,徐璈《桐旧集》四十二卷等数部(1)除此以外,还有如吴希庸、方林昌《桐山名媛诗钞》十一卷,专录明清桐城女性诗人诗作,参见史哲文、尚丽姝《论〈桐山名媛诗钞〉与明清桐城女性诗学伦理观念》(《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3期);姚觐阊辑《桐城诗萃》三十二卷,仅存目;又有民国时桐城人吴复振,字健吾,著有《续桐旧集稿》一卷,毁于“文革”。(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925页)。,这些诗歌总集折射出的桐城体派观念、文化态度、诗学成就以及文学史书写尤其值得关注,许结、周成强等学者对具体单部总集如《龙眠风雅》《桐旧集》已有一定讨论(2)详见许结《〈桐旧集〉与桐城诗学》(程章灿主编《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从〈桐旧集〉到〈耆旧传〉》(《文献》2011年第3期),周成强《论桐城诗歌选本的编纂思想及其诗学特征——以桐城诗歌总集〈龙眠风雅〉为考察文本》(《求索》2013年第3期),潘林《〈龙眠风雅〉的诗学传统》(《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不过将清代桐城诗歌总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尚付之阙如。早有学者认为:“总集的作用在许多方面往往构成文学发展的契机。……影响一代风气;确立一种美学传统;促进文学流派的形成;抟聚出一些文学史概念,从而对文学史的构建发生重要影响。”[2]这对考察桐城诗歌总集颇有启发。
一、诗以地著:以地域总集透视姚门之外的“桐城诗派”
桐城派以文闻名,但谈及桐城诗派须首要明确的一点是,桐城诗派是桐城之诗派还是桐城派之诗派。前人有两个经典观点为人熟知:一是吴汝纶《姚慕庭墓志铭》所说:“桐城自方侍郎苞以义理文章为学,流风渐被,文无工拙,制行一准宋贤,君其选也。……至姚郎中乃以诗法教人,其徒方植之东树,益推演姚氏绪论。自是桐城学诗者,一以姚氏为归。”[3]213吴汝纶认为桐城诗学以姚鼐为始创,方东树承之,将桐城诗派的正祖归于姚鼐,但仍强调方苞古文地位在先,意在表明文派在先,此论影响颇深;二是钱锺书续其父之论认为桐城诗派应自姚范始,“桐城亦有诗派,其端自姚南菁范发之”[4]364,又称“惜抱以后,桐城古文家能诗者,莫不欲口喝西江”[4]365,“亦有”一词显然含有与古文之桐城派相比照的让步意味,从而以此阐明桐城诗派的构成人员为桐城古文家,诗学以江西为尚的观点。当代不少学者或尊钱氏之论,以姚范为诗派嚆矢,或认姚鼐为祖师,以姚门四弟子为中坚,今人大部分论述基本不出这两种观点。(3)可参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严迪昌《清诗史》、朱则杰《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吴功华《桐城地域文化研究》、周兴陆《桐城亦有诗派》(《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卢坡《姚范:桐城诗派的先导》(《华夏文化论坛》2013年第2期)、叶当前《论桐城诗派的两条诗学路径》(《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论著。也有学者认为戴名世为桐城诗派的先声,详见许总《论戴名世与桐城诗派》,陈宇俊、马亚中《试论戴名世对桐城诗派的影响》,等等,但相比姚氏之说处于少数。
姚氏叔侄为桐城派重要人物无疑,姚鼐实为文派祖师:“古文而有‘桐城’一派,据之史实,乃肇开自姚鼐。‘桐城三祖’之名,系姚门弟子所追崇,今之论者径称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云云,系昧于史实作随意不根之谈。”[5]但诗派是否同样如此?细察钱锺书先生关于桐城诗派观点的关节有三,一是“自姚南菁范发之”,二是“惜抱以后”,三是“莫不欲口喝西江”。从第一个关节来说,自清立国至姚范活动的乾隆年间,已有百余年时间,其间是否能说姚范之前桐城无诗派之实;第二个关节,是否姚门之外不属于桐城诗派;第三个关节,钱氏将宗宋诗家局限在“桐城古文家”内,那么“桐城古文家”是否尽尚宋风。显然,这三个关节都值得推敲。我们不妨以潘江《龙眠风雅》(4)潘江辑《龙眠风雅》前有嚆矢,顺治五年(1648)潘江与方授着手纂《龙眠明诗选》,后因潘江遵母命参加科举,未能成书。后至顺治十七年(1660)左右,钱澄之与姚文燮欲采辑桐城之诗,但在集名上发生分歧,钱澄之认为应名曰“诗存”,“存者,存其略也,严之也”,姚文燮则主张称“诗传”,“传者,传其详也,宽之也”,二人未达成一致意见,遂又搁置,这次编纂潘江也曾参与,姚文燮有诗《柬潘蜀藻》,自注云:“余有《龙眠诗传》之选,搜集先贤遗编,蒙蜀藻多授藏本。”又十余年后,潘江另名曰“风雅”,寓意“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潘江《龙眠风雅全编》第1册,彭君华主编,黄山书社2013年版)与王灼《枞阳诗选》为观察对象,在当地诗歌总集中可窥得另一个“桐城诗派”。
潘江(1619—1702),桐城人,字蜀藻,一字耐翁,号木厓,潘氏“与海内名流相结,主盟坛席者三十余年”[6]219,著述颇丰,但多遭清廷查禁,其《龙眠风雅》初编成书于康熙十七年(1678),与续编前后花费四十三年之久,用力最深。合计收桐城诗人五百五十三人,诗作一万四千八百七十四首。《龙眠风雅》以桐城名山龙眠山为题,所录诗家或序以年齿,或以相近身份各划群体,是清初桐城重要诗歌总集。实际上,毛奇龄在《龙眠风雅序》里已说:“予思江左言诗,首推云间。近代闻见,颇称钱氏。当夫黄门崛兴,与海内争雄,一洒启、祯之末驵狯余习。而其时齐驱而偶驰者,龙眠也。故‘云龙’之名,彼此并峙。”[7]279明末清初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夏允彝等人组成的云间诗派在文学史上自有体派盛名,而毛奇龄直接将“龙眠”与“云间”并论,称“云龙”二者“齐驱而偶驰”,呈现出彼此对峙的局面。从观念认同的意义上而言,桐城诗派似已先于桐城文派发轫。
清代以降,桐城诗派亦并非仅为桐城古文家所专有,姚氏之前,桐城实有诗派的自觉意识。康熙十六年(1677)陈焯撰《龙眠风雅序》云:
予观古今诗格之升降,系乎时,不系乎地。自唐殷璠有《丹阳集》,刘松有《宜阳集》,黄滔有《泉山秀句集》,于是,诗始以地著矣。汴宋立江西之派,而推黄鲁直为宗;南宋立蒲阳之派,而称林艾轩为长,于是,以地著者,又因以派分矣。顾《丹阳》诸集自储光羲数人外,其诗多踳驳不传。严羽卿力辟江西为旁门。刘后村欲自异于蒲阳,有“英豪忌苟同”之句。繇是言之,诗固不得以方隅侈胜乎?然非所论于龙眠也。……龙眠之名卿硕士,与四方分坛立墠者未尝不声光相接,而坚守朴学,一以正始为归者,固自如也。[8]序6-7
陈焯,字默公,号越楼,桐城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著《涤岑诗集》,辑《宋元诗会》。他先梳理诗歌与地域的关系源流,称唐代《丹阳集》《宜阳集》等诗选问世后“诗始以地著”,至两宋黄庭坚、林光朝后“以地著者,又因以派分矣”,举地域中又有流派分别。陈焯对往昔地域诗派的追溯,并非故作攀附之语,实则在于佐证自己的论点,他在列举众家后,引出“诗固不得以方隅侈胜乎”的设疑,随即话锋一转,“然非所论于龙眠也”,从而自江西、蒲阳一线连至龙眠,道出桐城已有地域诗派之实的观点。
如果说,清初陈焯是在观念上肇启桐城自有诗派的初步认同,那么另一位诗人王灼所辑《枞阳诗选》则从一镇之地明确了清代桐城在姚氏之外的诗派形态。《枞阳诗选》成书于道光十七年(1837),录明末至清嘉庆年间桐城县枞阳镇诗人一百五十家,诗作二千一百二十余首。桐城耆宿马树华在《枞阳诗选定本序》中云:“国初田间钱先生经学文章,声名在天下矣。及海峰刘先生归老居之,以诗、古文辞导引后进,从之游者,多磊落英俊之士;先生殁后,私淑其教者,相继而起,风规未坠。……(王灼)自田间下逮近今,得二十卷。”[9]1马氏点明枞阳人钱澄之、刘大櫆二人是清代桐城诗坛旗帜。王灼则明确以钱澄之作为《枞阳诗选》的首卷诗家,选诗八十八首,刘大櫆选诗最夥,占二卷一百八十七首,除此二人之外,枞阳不乏名家,如方文以“嵞山体”著称于时,在此集中选诗一百零七首。
马树华又说:“乾嘉之间,则有王丈晴园、朱君歌堂、张君勖园,所谓枞阳三君者也。晴园年最长,亲受业与海峰。”[9]1此处所叙王灼、朱雅、张敏求三人号为“枞阳三君”,据方宁胜《桐城科举》又称“枞川三俊”,却长期掩不得发。此“枞阳三君”皆师从刘大櫆,实有声名,略述于下:王灼,字悔生,一字明甫,号晴园,又号滨麓,《桐城文学渊源考》评价王灼:“大櫆在桐城门人,以灼为最,大櫆亦极称许。……诗亦沉雄雅健,卓然为一大宗。”[10]127王灼对桐城派承上启下以及阳湖派的流衍不无贡献,曹虹评价道:“在张惠言与刘大櫆之间,王灼起到了类似于纽带的作用。”[11]117朱雅,字歌堂,号芥生、岑南,“师事刘大櫆,受诗古文法,又与王灼、吴定等相切劘尤工,诗真能得师传”[10]131。张敏求,字燮臣,号勖园、卜崖,“师事刘大櫆,受诗古文法,其为诗藻缋百态,穷极博丽,声色皆善”[10]133。同时,选诗数量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诗人在当地的诗歌成就,除了王灼为辑者列卷末,《枞阳诗选》选朱雅诗一百一十一首,选张敏求诗八十一首,亦为数众多。试举三人诗作一观:
澎湖泱漭隔风潮,釜底游魂敢自骄?合饬戎兵歌六月,讵多干羽被三苗。旗翻鳄雾晨阴晦,燧骇蛟宫夜动摇。天上楼船横海出,汉家将是霍嫖姚。(王灼《闻台湾贼警》)[9]308
金风吹落九门霜,直北天寒雁几行。辽海飞云人倚剑,燕山斜月客思乡。关河入望愁无际,砧杵谁家捣正忙?逆旅不堪仍吊古,昭王台畔草茫茫。(朱雅《秋日旅怀》)[9]247
天阔浮云暮,城高纵目愁。风声连大漠,海气暗幽州。边塞难为客,关山畏及秋。素衣缁已尽,还向帝京游。(张敏求《登天津城楼》)[9]256
由是可见,三人诗作雄健激荡,欲追唐人气韵,与江西瘦硬生新之法迥异,也就意味着从刘大櫆到“枞阳三君”形成了与姚氏“口喝西江”所不同,却又拥有完整诗学师承的桐城诗人群体。
位居“姚门四杰”之列的刘开在《张勖园明府诗序》内更为全面地阐论了王灼、朱雅、张敏求三人的诗学倾向和桐城之诗派概念,他首先认为:“自海峰先生卜居枞江,以风雅导启后学,而枞阳诗派遂盛于桐城。”[12]551在姚氏之外,以刘大櫆为发端与中枢,“枞阳诗派”已兴盛于桐城;其次认为:“当吾时而得见者三人,其始则王悔生学博,其继则朱芥生孝廉、张勖园明府。……夫诗至近日难矣,海内之好尚与吾桐之趋向亦互有得失,所胜于世人者,大体雅正风气遒上耳。然吾桐之近为诗者,所造亦不一焉。以吾所见三人论之,力追往哲,得其精华,而七言短章尤为超绝,盖悔生之所得也;雄健瑰丽,调悲节壮,盖芥生之所得也;高秀雄阔,跌宕生姿,而情韵深婉,盖勖园之所得也。”[12]551表明该诗派存在稳定成员和诗学师承,主要代表人物“枞阳三君”王灼、朱雅、张敏求三人诗风虽然各异,但是皆师法刘大櫆;尤应关注的是,刘开认为:“三君并崛起,枞阳扬声江表,使后进有所观感,吾桐之诗派共遂盛矣乎。”[12]551从刘开的叙述来看,枞阳一镇之地,已然成为桐城的诗学乃至诗派核心,所以刘氏才明确称其为“吾桐之诗派”。王灼、朱雅、张敏求三家诗风宗尚“雄健瑰丽”“跌宕生姿”,绝非宋调,有别于姚门“口喝西江”,显然,此时此地的“桐城诗派”不属姚氏闬闳,却既有诗派之名,又有诗派之实,岂非另一个“桐城诗派”?
梅曾亮诗云:“是时文派多,独契桐城诗。”[13]562可见,通过研读桐城诗歌总集,桐城诗派并非杜撰而成,而是一个与桐城文派并行不悖的诗歌体派,桐城诗派在清代文学史中得以成立,不唯外部诗家称道使然,更为重要的是桐城本土诗家的内部认知将诗派观念逐渐确立。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回答之前钱锺书先生关于桐城诗派观点中的三个关节问题,首先,桐城有诗派无误,但在姚范之先已有诗派自觉意识。其次,姚鼐在桐城派所处地位固然未可否认,但是回到彼时现场,姚门之外尚有以海峰为始,上追田间,“枞阳三君”为核心的“桐城诗派”。最后,通过阐述可知派中多有诗文兼备者,从风格上看并非皆“口喝西江”。所以,从桐城诗歌总集来看,与其说“桐城亦有诗派”,倒不如说桐城自有诗派。
二、选诗之心:桐城诗歌总集的文学权力互动
桐城诗歌总集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文学权力的表现。诗歌总集在与文学史关联过程中具备特定的文学权力,曾有学者从命名上指出总集有权力支配的作用与内涵:“总集之名,无论是‘总’还是‘集’字,本身已意味着某种汇聚整合的权力。”[14]文学权力是学界已有概念,国内不少学者如朱国华、戴燕、程章灿、张德建等人在西人葛兰西、阿尔都塞、福柯、布尔迪厄等人基础上从本土语境出发各有论述,大致意指文学与权力之间的离合状态以及文学在自身话语体系中所具备的支配力量。总集相对于别集具有不同价值,这里意在强调诗歌总集在多重权力语境下汇聚、选裁、再创作与经典化诗派、诗人、诗作等过程中体现出文学权力的行使态势。
首先,应注意到桐城诗派所纂诗歌总集对官方政治权力的反映,我们知道,清代官方层面统一选辑“御纂”“御选”诗文总集,或未冠以类似名称但明显受到官方权力影响所纂的总集,意在树立旗纛,以一代文风服务一代政治。如《御选唐宋诗醇》《皇清诗选》等总集试图以御选诗学的范式来印证清廷权力上的统一,以诗歌的雅正风貌来呼应盛世的伟丽气象。《皇清诗选序》云:“圣治纯熙,崇文劝学,一统之化,肇造方新,而海内诗教,遂已跨越前世,振古希有。……本朝风雅之盛,将人尽折衷是书,其为传世尚可量欤?”[15]10-11庙堂之外的诗家也不免有切身体会,汪志伊坦言明清两代政治权力对诗人创作的干涉以及诗作对政治环境变迁的直接反映:“明世诸公,生逢世乱变起君父之间,身当家国兴亡之际,故其诗愤而多感,踔厉悲凉,使读之者犹想见其遭时多难,而其发乎忠孝,旁魄勃郁不能自已之心,百世下如或遇之。圣人受命海内,又安臣民、袭福愿,靡不称以是,士大夫作为颂歌,类皆承流布德,润色朝庙,畅乎昌明,岩穴之士乐今而称古岁,时俦与讴歈愉愉,无复悲愤激烈之意。”[16]3-5诚然,世俗权力地位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反映在总集选人顺序排列上,清代不少诗歌总集也以科第官爵尊卑为先后依据,不过,时人参与辑纂桐城诗歌总集时已有清醒认识并试图反拨。为《龙眠风雅》作序的陈焯在给友人书信中说:
近见纷纷操选政者,大约以爵位之崇卑为篇次之多寡先后。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一部有韵之缙绅便览,非诗也。”[17]298
潘蜀藻即潘江,陈焯引潘江之语,指斥当时诗歌总集以权力地位选人的弊端。文学是否应保持自身本位,在陈焯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陈焯素与潘江友善,《龙眠风雅》也暗蕴此义,实际上反映出清人以文学本位对威权观念的阻拒心态。
那么,《枞阳诗选》中所标彰的诗派宗主刘大櫆虽备受本地诗家推崇,其地位却在清人诗家的主流评价中名实不副的问题,按照这一角度来思考似也不难理解。刘大櫆之所以在彼时未得到所谓“主流文坛”普遍重视,一方面由于其终生布衣,与一般以科名官位为依据的评价标准不符;另一方面,其思想亦有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悖之处,吴孟复《续枞阳诗选序》明确指出:
文直而诗曲,文之不能达者,诗可以宛曲达之。因举海峰“团圞一门内,弟寒兄不知。深宫狎阿保,而悯百姓饥?”是无君论也,是民权宣言也,当雍、乾文网极密之时,是文集中不可以质言者也。其锋芒之锐,与黄宗羲、唐甄相较,殆有过之。[18]54
吴孟复认为诗可以道文不可道之语,表明诗有别于文的特殊权力意味。刘大櫆科场蹭蹬,又以诗刺讽清朝统治,个人的文学权力固然得到行使,但与帝王的政治权力相比终究不可同日而语。是故在雍乾威权之下,刘大櫆难以被官方接纳,其文学地位受到牵连不能说与之没有关系。然而,方文即云:“布衣自有布衣语,不与簪绅朝士同。”[19]482个体声音即便微弱,也拥有对抗威权的力量,清人对位尊方显诗著的观念早有不平之鸣,如清初王士禛执诗坛牛耳,但时人郑性(1665—1743)为友人沈渔庄忿然道:“今以渔庄之笔,使其置身廊庙,鼓吹休明,正自不减渔洋,顾乃蹭蹬蹇伏于江湖闾里间,有渔洋之诗而无渔洋之位,海内之人未必遽宗之如渔洋。”[20]607文学对于政治权力存在疏离与拒斥,然而文学又存在自身的独有权力,所以,桐城文人面对刘大櫆的遭遇也应存在不平之意,故《枞阳诗选》等诗歌总集在与官方意识形态角力之间,选政之人于选诗与评诗中行使文学权力,努力为文学史保留了以刘大櫆作为清代桐城诗派宗师的如实评价。
其次,桐城诗歌总集中以选人选诗影响文学观念,进而对文学史构建施与影响。放眼整个清代,从地方性诗歌总集到全国性诗歌总集,文人辑纂诗歌总集蔚然成风,一方面反映地域与时代的诗歌成就,一方面又影响一代文学的走向。潘务正认为,清初“诗歌总集的大量出现为宗唐诗风在康熙诗坛占据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21]72,表明清代诗歌总集与文学史潮流的演变确有关联。而二者关联中的关键要义,毋庸置疑,正是总集选人选诗对诗派、诗人、诗作的传播流衍以及经典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依然以桐城诗派为例,前文所述桐城诗歌总集以刘大櫆为诗派宗师,除了行使有别于政治约束的文学权力,显然也意在将其经典化。而至晚清桐城派名宿张裕钊选施闰章、姚鼐、郑珍三家合为《国朝三家诗钞》,隐隐含有将三人作为清初、清中期及晚清诗家代表的用意,一循曾国藩观点:“姚姬传氏自述其作诗之旨在熔铸唐、宋,然以余观之,独七律为最工耳。……国朝诗集行世,无虑数百家。章章炳著,为世所传述者,亦无虑数十家。然其卓然自立,不愧古人,独此三家而已。”[22]211姚鼐诗学地位的经典化与此不无关涉,从而客观上将刘大櫆的经典地位解构。同样地,桐城派末期另一位名家吴闿生则在《晚清四十家诗钞》又试图塑造范当世在桐城诗派中的地位,吴闿生的弟子曾克端撰序文指出:
覃及胜清之末,肯堂范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忧时愤国,发而为诃诗,震荡翕辟,沉郁悲壮,接迹李杜,平视坡谷,纵横七百年间无与敌焉,洵今古以来不朽之作也。自范先生没,当世负盛名者多能与范先生同源一趣。而轨辙较近、感发较切,示天下学诗者所从入之途,固莫捷于是矣。此吾师北江先生选录近代四十家诗之微意也。[23]27
有学者曾撰文对此集的文学权力表现有清楚认识,吴闿生的编纂行为“是一个叠合了‘权势转移’的文学发展过程”[24]。不唯桐城诗派,清代不少诗派的文学史构建也有赖于时人辑纂诗歌总集的权力话语,如岭南诗派得益于《广东诗萃》《粤东诗海》《岭南群雅》的反复标举,常州诗派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黄景仁、杨伦、吕星垣、徐书受等人在钱维城《毗陵七子诗》的推重之下得以扬名海内,毕沅就说:“近今毗陵钱文敏公以沉博宏丽之才,提倡后学,一时异才辈出,指不胜屈,而七子为最著,惊才绝艳,均齿齐名。”[25]92充分说明诗歌总集的辑选方法与内容对文学史书写的塑造力量。文学经典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而总集的选编内容即是逐渐积淀的具体方式,文学权力看似难以触摸,却确实左右了文学史的演进。
最后,桐城诗歌总集存在诗与史的权力互动。一方面,明亡清兴,自钱谦益辑《列朝诗集》,以诗歌总集高标“以诗存史”大义,黄宗羲进一步提出“以诗补史之阙”,表明文学权力与史官权力二者合一的倾向。清人纂诗歌总集也有强烈的诗史自觉意识,如《遗民诗》《清诗铎》《道咸同光四朝诗史》等。桐城诗歌总集同样具有此功能,如由文汉光、戴钧衡所辑《古桐乡诗选》十二卷,于道光二十年(1840)刊行,收录桐城县北乡诗人一百七十七家,含闺秀四人,方外四人,诗作一千一百零七首,因北乡为古时桐国、桐乡所在,故以古桐乡名之,笔者所见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本。文汉光在《古桐乡诗选》中将采诗与述史相联系:
既欲辑一乡之诗,则生长是乡,上下数百年间,苟有可传,必宜博采兼收以彰之人世,顾欲有所别择于其间,则隘而不广也。夫古者天子巡狩至列国,命太史陈诗以观民风,而列国必采之都鄙、征之闾巷以献,都鄙闾巷者,诗之所自出也。后世之诗,无当民风,故采诗之典不行,而其抒写胸次,发挥才藻,固足以考人才之兴衰,证世风之轮替也。[26]文书2
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所说诗歌总集诗史互动表现文学权力的内涵,更为深层次地体现在总集编者通过一定的价值判断辑录或不辑录某人诗作进而塑造其人的历史定位,这便是以诗章阐史笔之义。如徐璈《桐旧集》以家族姓氏为序,至桐城阮氏仅录阮鹗、阮自华、阮自嵩、阮之钿、阮湛五人,却不录阮大铖之诗,唯独在阮湛诗后按语中提到阮湛之父阮之釬“至性孝友,为人沉毅,有大节,不慕荣利,不喜见要人。族人石巢官大司马,公不因之仕进”[27]101。石巢即为阮大铖号,此处按语一字一句莫不似在讥刺大铖。
徐璈还有意选录反映阮氏族人忠烈高节的事迹与诗作,如阮之钿“殉节卒”[27]98,其《题壁诗》云:“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勉哉杀身成仁,无负孝廉方正。”[27]99阮大铖虽官居高位,文采过人,但品行奸佞,首鼠两端,素来为人不齿,观上引按语以及所选诗篇的意旨,不难发现《桐旧集》努力将阮氏族人与阮大铖分割开来,以彰示诗歌总集的以诗塑史之意。徐璈在春秋笔法中体现出的文学权力颇可体察,其实,诗并非史,其特殊价值有别于简单的纪事陈述,而是在于以诗歌特有的情感审美旨趣对人物事件蕴意褒贬,这才是诗有别于史的权力所在。
在文学史不断消解与形塑的过程中,文学权力或隐伏或显露,而诗歌总集的力量尤为值得关注。就桐城诗家而言,一方面,桐城派门人编《龙眠风雅》《枞阳诗选》《古桐乡诗选》《桐旧集》《桐山名媛诗钞》等地方诗歌总集以彰显地域诗家自身文学权力;另一方面,又如刘大櫆《历代诗约选》《五言正宗》《七律正宗》《唐人万首绝句钞》、姚鼐《今体诗钞》、张裕钊《国朝三家诗钞》、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等以选本试图表达文学主张或塑造桐城名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清代是诗歌总集辑纂的鼎盛时期,同时又是台阁与草野离立的高峰时代,在清人所辑纂的桐城诗歌总集内展现的政治与文学、缙绅与布衣、诗章与史笔多方角力互动的局面具有独特意义。
三、以集显派:桐城诗歌总集对桐城诗派流衍的意义
学者吴孟复曾说:“前年,复与钱仲联先生及舒芜兄弟同游浮山,拜密之墓。舒芜言:‘文派’之外,更有‘学派’;钱先生则谓‘诗派’比之文章,似尤足重。孟复则谓:诗也,文也,学也,三者既区别而又相联系,学为之根,而诗为之华。”[18]54就文学史研究的共识而言,一个诗派特别是地域性诗派的形成,或在当时已有体派观念的觉醒与诗人同声共气的聚合,或是彼时自身并未有体派的自觉意识,而由后世对风格类似群体的追认。在对体派的确认定义方面,前者的优先级应高于后者,即文学体派发展过程中的自我认同是更为明晰而关键的指标。我们说桐城早有诗派认知,而并非在姚范、姚鼐时才形成一个桐城诗派,这一话题表述不单意味着对桐城地域文学成就的肯定,而是在文学现场对桐城在清代已出现一个地域文学共同体的如实呈现。常有人在文学研究中说要回归文学现场,那么体察地方诗歌总集大概可以相对准确地回到当时的“现场”中去,因为由当地文人所辑的总集很大程度上可以将时人的文学观念与立场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保存下来。我们通过对桐城地方诗歌总集的研读,一方面可以从当时文人视角与观念审视桐城诗派,另一方面可以发现桐城地方诗歌总集的价值所在。
首先,清代桐城诗歌总集在先后承续上具有重要意义。清代桐城文人多次纂修地域诗歌总集,各总集一脉相承,体系完整,延续有清一代。徐璈《桐旧集引》指出:
国初以来,搜辑遗逸,编录韵章,若钱田间、姚羹湖、潘蜀藻、王悔生诸先生《诗传》《诗选》《龙眠诗》《枞阳诗》之类,皆为总集佳本。第其书或未经锓梓,或已镂板而渐就毁蚀,其诸家专集亦大半湮落无可收拾。[27]9-10
如若地方没有文学承传意识,桐城诸人必不会多次裒辑总集以显示成就,不断继起的编纂行为正体现出桐城诗学的自觉认同。于是徐璈决心延续这一传统:“余不敏,浮沉薄冗,无所酬能于世,而言念曩者俯慨方来,窃欲效施、阮诸公辑《宛雅》《广陵诗事》之意,赓续钱、王诸先生之绪,采萃乡邑先辈诗章并言行之表见于他书者,寸累尺积,汇为若干卷,颜曰《桐旧集》,以蕲流示来兹,永言无敦焉。”[27]9又如其后的《古桐乡诗选》例言说:“吾桐诗人渊薮,前之选本有潘征君江《龙眠风雅》,版已销毁,本少流传。近则徐明府璈复为《桐旧集》之编,表微阐幽,二君子先后同志。……昔者王学博灼居枞阳,有《枞阳诗选》,聚奎、钧衡生长北乡,因仿学博之例,辑成此编。”[26]例言1文汉光、戴钧衡细数前人所辑总集,表明四部总集的继承关系,桐城诗派的理念也自会镌进桐城诗歌总集的辑纂过程当中。
其次,各桐城诗歌总集重视认定诗派渊源传统,宗派意识明确。桐城古文家有选辑总集的传统,如方苞辑《古文约选》,姚鼐辑《古文辞类纂》,戴钧衡、方宗诚辑《国朝桐城文录》,萧穆辑《国朝桐城文征》等将桐城文法显扬于世,对桐城派赓续作用深远,方东树云:“姚姬传先生纂辑古文辞,八家后于明录归熙甫,于国朝录望溪、海峰,以为古文传统在是也。”[28]235而桐城诗家同样认识到总集之于诗派的价值。诸诗歌总集上溯文统渊源以反映诗学传承,如《桐旧集》称“自齐蓉川给谏以诗著有明中叶”[27]1,以明人齐之鸾(1483—1534)为桐诗发轫,而张敏求于《古桐乡诗选》序内将时间继续向前推进,指出“永乐以还,人才蒸起,蔚然焕然”[26]张序1,认为明初桐城诗文成绩已见滥觞。诚然,上溯至永乐之时不能说明诗派的成型时间,但是从明代桐城的诗学演进接武而下,这一脉络未可否认。
其实,除了《枞阳诗选》,《桐旧集》也认为,在清代桐城诗家心中,刘大櫆才是桐城诗派成型的宗师。徐璈《桐旧集》编纂时间较晚,至咸丰时方刊出全书,理应受到姚门之“桐城诗派”影响,不过姚莹《桐旧集》序文认为清代桐城诗派的宗师还应归为刘大櫆:
康熙中,潘木厓先生是以有龙眠诗之选,犹未及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翁起而继之,然后诗道大昌。盖汉、魏、六朝、三唐、两宋以至元、明诸大家之美无一不备矣。海内诸贤谓古文之道在桐城,岂知诗亦有然哉![27]1
黄华表直接认定:“望溪终身未尝作诗,海峰始以诗教弟子。故桐城文派,推始于望溪,诗派则自海峰。”[29]清代桐城诗派至刘大櫆堂庑始大,非一家之言。如果说,前文马树华《枞阳诗选》序文以刘大櫆为桐城诗派宗师人物,不排除是因王灼为海峰弟子的恭维之语,然而,身为姚门弟子的姚莹在《桐旧集》中将刘大櫆、姚鼐二人认定为桐城诗学的核心人物,其中又特地指出刘大櫆“出而大振”,姚鼐不过“继之”海峰,可见桐城派成员认定刘大櫆才是振起桐城诗派的津梁宗师,实则在于对文学现场的如实记录。
再次,各桐城诗歌总集反映清代桐城诗派盛衰变局。各总集积淀诗家,从而促进桐城诗派发展。当我们历数清代桐城地方诗歌总集的辑纂者,从明清之际的钱澄之、姚文燮、潘江到清代的王灼、徐璈、文汉光、戴钧衡、姚觐阊等人,他们接续辑纂的行为,是将桐城地域诗人与诗歌逐步经典化的一种方式。毛奇龄也预见到潘江编纂《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编》的价值:“木厓著书等身,其所为诗,久为海内所诵扬,然犹兢兢乎不忘先烈,而具为搜讨。今之所为后,即后之所为先也。”[7]279在光绪三十二年本《枞阳诗选》序中,方恪勋也说:“《枞阳诗选》,余曾假阅一过,读其诗想见其人,惜余生后时,不得与诸先生览山光、眺江景,饮酒赋诗于一时。”[30]序1可以想见,当刘大櫆、姚范、姚鼐乃至后来的刘门弟子、姚门弟子及再传弟子诵读桐城诗歌总集时,未尝不为个人诗学素养的向心生长乃至桐城诗派群体的日益繁盛埋下了原发地域的文学种子。也正是因为如此,与前代其他诗派有别的是,《龙眠风雅》《龙眠风雅续编》《枞阳诗选》《古桐乡诗选》《桐旧集》等桐城诗歌总集的编纂历程与桐城诗歌创作状态交织一体,更重要的是,与桐城诗派的形成路径基本呈现出并行的轨迹,反映出桐城诗派自我认同的成熟过程。
事实上,桐城文人也试图通过反复刊刻总集来挽救诗派颓势。据前人记载,仅《枞阳诗选》一部总集,即于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二十年(1840)和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后七十年间分别镂版付镌三次,特别是最后一次距离清王朝寿终正寝仅余五年时间。彼时桐城派已渐羸弱,此次刊印未尝不暗蕴桐城派仍欲回顾历史成就,重现昔时四海文名的意图。方恪勋在第三次刊刻《枞阳诗选》时已认识到:“吾乡诗文之盛,非复当日。于是刻诸先生之诗,俾使后生小子读之以为兴起之一助云尔。”[30]序1然而,重复刊印旧本而无新纂总集,正表明在王朝衰败的阴影显露之下,桐城派逐渐落幕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最后,还应注意到,各诗歌总集具有在家族层面促进桐城诗派发展的意义。清代“桐城世家之昌盛,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令人瞩目,对创立桐城诗派、桐城文派、桐城学派意义非凡”[31]各宗族热衷编纂本族成员诗歌总集,这一现象在桐城尤为集中,如方观承《述本堂诗集》、方于榖《桐城方氏诗辑》、马树华《桐城马氏诗钞》、周方林《周氏清芬诗集》、姚永概《桐城姚氏诗钞》等多种宗族诗歌总集相继问世,呈现地方文学的繁荣面貌,正如清人所说:“盖家谱与诗略,人物文章世相表里,交藉为不朽盛事甚哉。”[32]11这些宗族诗歌总集属于家集,家集与家谱共同构建出文学世家的系谱。
在此背景下,清代桐城各地方诗歌总集的辑纂体例,在以生卒时间作为排列依据的普遍规律之下,存在从以相似身份为分类标准向以宗族姓氏为分类标准的转变。清初桐城诗歌总集以相似或相近的身份划分群体类型,据今人整理《龙眠风雅全编》前言所述,多以科举身份、同门身份、职位身份、行为身份、血缘身份等进行归总,《枞阳诗选》基本依循《龙眠风雅》前例,至《桐旧集》则已完全以各姓宗族分类,以辈分排序,“分姓列卷,其间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序”[27]11,严格遵循以宗族姓氏为排列顺序的体例,所以苏淳元在《校刊桐旧集后序》云:“今几二百年,诗家辈出,而卷帙浩繁,或有选辑一乡一族之诗,而合邑通选未有续其事者。”[27]5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桐城地方诗歌总集与宗族诗歌总集二者间呈现从双向并行到同向交叉的变化面貌,这一转变是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的相互作用所致,表明家族观念逐渐对桐城文学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关涉到桐城派发展。我们当然不否认桐城诗歌总集仅收录当地诗家似有拘墟乡里之嫌,不过桐城文化世家对桐城诗派建构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所以,清代桐城文人不断辑纂地方诗歌总集,在展现诗作的功能之外又与诗派演进扭合一体,将当时文人创作面貌与成就凝聚在梨枣之内,并不因后世接受理念的改变而发生偏移,进而从一定程度上完善文学史的书写。
四、结语
总之,姚范、姚鼐的诗学传承是清代桐城诗派的重要开创门径之一,不过并非桐城诗派的唯一正宗,在清代桐城诗歌总集内详细记录了刘大櫆及其门人所确立的“吾桐之诗派”,不仅创于姚门之外,诗法宗尚也有所异趣,是桐城诗派中不可忽视的另一支力量。而清代桐城诗歌总集的价值又不局限于此一点,《龙眠风雅》《枞阳诗选》《古桐乡诗选》《桐旧集》等总集累代传续、探赜渊源,既反映桐城诗派盛衰变局,又从家族层面影响桐城派发展。诗人辑纂桐城诗歌总集在以文学应对威权中或顺应或阻拒,在选人选诗中左右文学史书写以及以诗歌干涉影响现实与历史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文学权力。
方东树曾在《古桐乡诗选》序文内溯源诗歌总集的发展历程:“选诗为总集,盖有权舆,正考父辑《商颂》,其后孔子本之以删《诗》《书》,自汉以来刘《略》、班《志》、阮《录》递显,集遂专部而为之一名。至于萧梁,而其体备。至于李唐,而其号繁,或以体分,或以代断,或以地别。”[26]方序1表明总集在文学发展史中的丰厚内容与重要地位。然而,清代包括近代文人大量自发辑纂清人诗歌总集相比以往又富有其独特性,辑纂本身是一种书写与创作,并通过创作行为呈示文学内在力量,这种文学内在力量正是在树立经典与打破经典过程中促使文学史动态演进的内因。进一步说,我们通过研读总集文献,可以理解与评价一个地域、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学现场与文学成就,从而在阐释文学活动形态和文人创作经验上展现出其应有价值,而观察数量宏富的清代诗歌总集,恰能赋予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