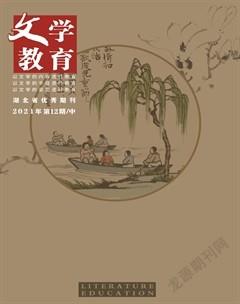自由与纯粹
夏甜 王钻清
在唐诗中出现的“自由”所表达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一种正面的价值诉求。我从香港诗人云影的系列生命诗中感受到她不仅传承了这种传统,而且呈现现代性意义的自由形态,正是这种自由滋养了她诗歌的纯粹。她顺从语言哲学回归感觉人类学,并且诗意地寻觅自由的必要条件;她以审美的高远精神境界即以显隐相统一的整体观——即从高远处、以整体观看待日常事物的心灵开放又自由地诗性表达,完成诗歌文本的纯粹。
我们如何从“泛化”的哲学史观看唐诗中的“自由”观念呢?我们发现,在唐诗中出现的“自由”所表达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一种正面的价值诉求,主要涵义表现为:对身心、情感上不自由状态的不满;对政治上、官场上不自由的反抗;同时,指向一种与个人自主的目的性相关的自由意志;指向一种与宗教的解脱生活相关的自由意志。从唐诗的角度来看,部分诗人把“自由”当作自己所追求的一种正面价值,在整体上都表现了对自由感获得的肯定。这种身为人的要求和追求成为文人(或言知识分子)的基本素质。我从香港诗人云影(原名史云彦)的系列生命诗中感受到她不仅传承了这种传统,而且呈现现代性意义的自由形态,正是这种自由滋养了她诗歌的纯粹。
一.以灵魂书写方式诗性地走向宗教
我们知道,自由是文学家的天性。在诗人云影的身上,她的一部分诗歌始终寓居着“两个诗人”:她身为现代人带着先进性和未来性,以诗人之名要求自己所写的每一首都尽力给诗歌带来一个新的定义,以显出对诗的新的理解;同时,她以另一个诗人的身份用许多首诗来复活诗的最古老的定义——凭借生命的悟性和语言的智慧来达成某种神秘的契约。我从她的诗集《必要条件》里读到这样的诗学实践效应。从她后来的诗中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她的诗以“一种化为行动的神学”的姿态让诗歌抵达生命深处和时间深处——即“一个寻求神恩的灵魂的个人遭遇”。
云影在仅有四句的《拉雪兹神父公墓》一诗里,将日常生活秩序神圣化,并且有从怀疑到信仰的跳跃;正如诗云:“四野空寂/拉雪兹神父公墓在雨水聚集之处”。我仿佛看到一个带着中原文化并混合多元文化的人间旅行者来异域巴黎,找寻灵魂的归宿或感染别样文化之美。在雨水聚集之处,她的灵好象从“空寂的四野”降临随即运行在水面上。换句话来说,一个四维或七维宇宙里的人在三维世界里生长的模样或者如同公墓里的神父,或者就像探访者本人,他们都在思考自身的存在——即活人或死人的灵与肉在四维甚至更高维度里,与时间共存可能是具象的。正如诗云:“巨大的静谧之中,一朵蒲公英忘记飞行/守墓人摇起铜铃,人间才起风”。这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穿越时空旅行,并且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重新发现上帝——上帝在时间之外,以时间和空间之和,赋予人间有趣的灵魂——即“一朵蒲公英忘记飞行”,同时在没有出路的世界徒生希望——即“守墓人摇起铜铃,人间才起风”,以此让人爱上终将压垮自己的虚无主义。
读到这里,我仿佛看到诗人坐在电脑前书写的情景,让我感到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她那探索、追寻、触及某些不可知的情境包括风土的或心灵的行为都是一种旅行;而且她的欲望以表现在身体上和表现在灵魂中的两张面孔呈现,或许此刻她静下心来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自己,或许她保持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傲清高又以包容的姿态跟现实的世俗握手言和。从她的其他诗文中,我看出她有过消沉或幽怨或崩溃,但是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她可能在寻找自愈的良方。比如,她在《喜悦》中如是表达:“光从这里进入/把这崭新的清晨缓慢地带入永恒之地”。又如,她在《我们说起雪》中写道:“雪花并非凭空而降,她有宿命的去向/倘若一片雪花释放出来的热忱还不够决绝/再叠加另一朵”。一个如此热爱生命的人跃然纸上,一个纯粹的灵魂诗意地取道“宿命的去向”,并且努力做好自己。
二.顺从语言哲学回归感觉人类学
云影的诗同样印证“人类的思维过程充满了隐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提示我们如何认知隐喻。隐喻这一修辞手段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标志。而现代隐喻理论明确地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认知现象,人类的思维过程充满了隐喻。语言中的隐喻只是这种认知活动的反映和手段之一。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符合语言常规的语言现象。从言、象、意三者关系来看,贯穿了从现象学、解释学到分析哲学和科学理论的各种哲学思潮,从根本上带来了知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全新革命。其实从分属于“欧陆人文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两大传统中的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语言观与维特根斯坦的日常语言学的语言哲学来思考,我们发现人与世界、语言与人、文学与世界等诸多关系在言、象、意上可以找到鲜活的例证。比如,云影的《西贡的黃昏》有云:“窸窸窣窣的脚步声像迟疑的风,傍晚很轻/一定还有更轻的什么,躲在灌木丛”这种感兴的诗性表达构成了“言、象、意”三者关系的完整融合。难得的是作者打破常规语言,顺应心灵感应并以艺术感觉捕捉一瞬间的感受,如此走进微妙和神秘:“蚂蚁奔向它的巢穴,猫穿过枯叶/影子幽居在第九只耳朵”“细小的声响相爱着/霞光灌满她们的眼睛”我们从中读出了一个诗意的自由人那隐秘的世界。似乎可以到此为止,可是诗人让一个人的魂灵在隐喻中自由地飘荡:“一个突然哭起來的人/被风拣中,掀起,被风擦亮”。以上状物抒怀,令读者抚摸诗意的纯粹。更令读者震惊的是诗人以终极关怀的言说拆射语言那有如黑与白这两种高贵颜色的色彩语言之光,进而完成一种语言哲学。诗云:“死亡无法带走这绝妙的晚空/不会太久”。从这首诗中可以感受到:精神生命涉及终极关怀、慈悲之心、隐喻、象征等等这些都表明了语言哲学的转向。
从上述例诗中还可以看出:其实文学是常常作为知识的反面而存在。或许云影明白这一点。她受一种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潜意识等)的牵引在写,而且她顺从感觉经验来构造语言,同时找到了共鸣的途径即语言上的沟通和理解,正如《逻辑哲学论》中的最后一句話:“语言走多远,现实就开展多远。”或者暗合了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世界不是由事物构成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事实是判断,判断是一个语句、一个句式;也较好地诠释了维特根斯坦观点:问题不在词语、不在观念,而在于句子。在于句子的表达语义。比如,云影在《命名术》中写道:“我越来越满足于眼前的事物/鸢尾,紫背兰,马蹄,白掌,忧伤的华尔兹/阳光接踵而至/这方寸之地,云与影/草木庇荫,河水奔涌”这么纯粹的诗句把大自然的物和现代文明的艺术置于有如交响乐般的和谐的语境中。可是作者转折任凭内心的情结滑向另一个语境:“后来,我把不可捉摸的东西叫做命运/把花槽里的雏菊叫做梦/它混迹于众多绿色之中/瞪着清澈透亮的眼睛”。如是从哲学视角处理感觉问题。这是怎样的命名术——其诗以诗意的语言传达感觉的人类学某种神秘和旨意:“妹妹,我有悲伤,无以名之”。
我们知道,感觉学所探究的是诸多感知模式领域的多样性之整全性。她的诗《植物的一生》完好地成就了这一文学范式。诗云:“多年来,我一直在模仿一棵古橡树/我知道沉默,隐密,荒芜,悲戚/我称之为根须,眼睛,嘴唇,骨骼中的大海,潮汐”这样在语感驱驶下将通感流动地导引出来。接下来,诗人让身体的感觉性成全诗歌语言的敏感性:“昨夜,我的眼睛长出/叶子,身体生出根须/大海涌进胸口,海鸥沿著手指盘旋/低鸣——”。这样的艺术处理是对知识的反动,但是它完成了感觉人类学的某种哲学命题——如是以哲学人类学的诗学实践求索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诗人更进一步地从人之外的宇宙走进人的内宇宙:“没有哪一片阴影能覆盖我们/明亮来自内部”。这隐喻贴切地或者说恰到好处地表现人所感知的内外宇宙,这是存在主义哲学所说的此在,也是相遇哲学所表示的人与物相遇过程中才产生存在的意义。然而诗人更加深入时间深处和内心深处以及人与万物的生命深处:“这刹那的狂喜/让我终于完整——作为植物的一生/重新开始”。如此完整性的诗性表达或者说优质的诗歌结构令读者感受得到,诗人对情绪的把控恰到好处,诗的整体感跟自我生命的完整合为一体,从外在到内在,从古老到此在,写出了人伦的社会学意味和时间的空间化。
三.诗意地寻觅自由的必要条件
这么说吧,自由就是把外在的、被迫的必然性,通过认识,转化成为自觉自愿的内在的必然性。可以说,自由人便是自愿服从宇宙必然法则,自愿按宇宙自然法则行事之人。罗素指出,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说:“虽然我们要服从自然的威力,然而我们仍然有自由意志,并且在某些限定之内,我们乃是我们自己命运的主人”。伊壁鸠鲁的思想告诉我们,在科学研究——科学认识的“自然威力”即必然性必须“服从”之外,我们还有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的自由领域。
对于自由,诗人的表达方式是别样的。云影在《一种生活》中起兴就定下了整首诗的基调:“我们没有坐下來等一场日落/我们迎着斜阳走下山坡”。这是一种自由意志支配的行为。作者任凭诗性的感觉自由地游走:“芒草明净,巨石杂错/黄昏绵绵不绝/奔涌成黄金的河”。一种语境随着有质感的诗意语言铺展成一幅画,画面呈现自由的氛围。于是,“当我们追赶着夕阳踏上一面陡峭的山坡/漂浮成石头和云朵/我们同时接受了那炫目中的失重,灌木丛的刺痛/尽头的墓群,无边的寂静/我们沉默,不是因为美如此壮阔”。这是怎样的人间与陰间啊!或许诗中的“我们”作为自然人也成了大自然的一部分——这种物我观表达一种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即活人也好、死人也罢,人的身心回归大自然是自由的完美表现。接下来,一种自由人的诗意栖息在灵动的语感中从自然界飞入社会界:“穿过这毛绒绒的密林,村落/穿过一朵花的紫色/我们飞翔着,没入滚烫的灯火”。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烟火和人气——诗中的“我们飞翔着”——让自由突现在超验的领域,让人之为人的深层本质和尊严之所在力透纸背。云影在《芒草》中放纵个人的自由意志:“仿佛一直白下去/就能滑进消失的爱中”“听我说,芒草,不要回头”。一个自由人的有趣灵魂拥抱着“爱”这还不够——那个找到了自由的必要条件的“我”发出人间的呼声:“不要回头”。这样的存在状态源于人是自由的,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呼唤折射出人性的弱点即人同时恐惧和逃避自由。诗人在《赤柱的海》中用灵敏的语言和混合的感觉描述生命感动和生命冲动:“令人心碎的爱情,在我们之间/我们成为彼此的容器和镜子/万物混沌,它是明亮的/照见花朵翻飞的瞬间”。接下来,作者由起、承到转折,巧妙地结构诗歌,表现一种生命智慧:“我不能在一场绝望中站得太久/我在轻盈的跳跃中,练习坠落/并非一切都尽如人意/人群仍络绎不绝地奔赴未知之地”。正如康德所说,人有两重性:一重是自然方面,一重是自由意志方面。我们在这首诗中感悟到:自然方面的属性受因果必然性支配——比如诗中的“我们”那男女之欲;倒是此诗还写有另一方面即独立自主、自我决定的生命形态:就像此刻,“一只鱼鹰飞向它的海心/而海水,在深蓝中敞开/亲爱的,我们承受它的冲击/聆听它的歌声/在波浪和波浪之间,拿不定主意/是该遗忘,还是珍藏”。这里用多重意象组合来表现现代人那繁复的生命动态和复杂的精神世界,用健康又精致的诗意语言曲径通幽地建筑一种富于美感的诗歌结构,自然地促成语言与生命的同谋,抵达必要条件的隐秘之处。
云影的诗整体性风格突出表现为“自由下的纯粹”,也就是她对美的态度表现为或为美而美,或把美深入到日常生活中去并实现美的现实化和艺术的生活化。她以审美的高远精神境界即以显隐相统一的整体观——即从高远处、以整体观看待日常事物的心灵开放又自由地诗性表达,完成诗歌文本的纯粹。
(作者单位:湖北荣怀学校;广东省深圳市西部水源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