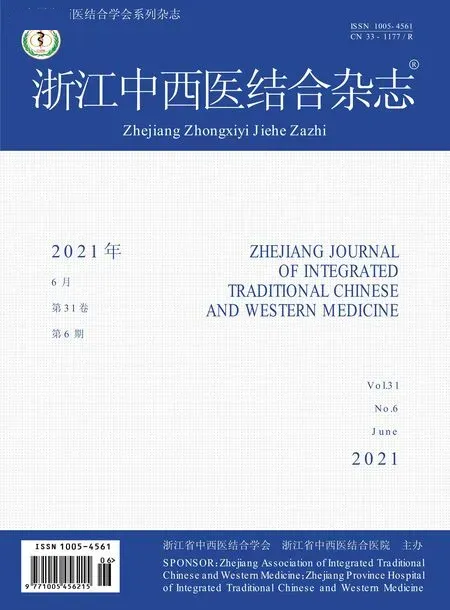浅谈《瘟疫论》学术思想对疫病治疗的价值
牟 新
吴有性,字又可,生于明末清初。当时社会动荡,瘟疫横行,吴又可总结自己和众多医家治疗瘟疫的经验和教训,著成《温疫论》,开创了一套瘟疫的辨证论治方案,成为“温疫学派”的创始人,为后世治疗急性传染性疾病和流行性疾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料。现将吴又可《瘟疫论》中关于瘟疫治疗的学术思想初步总结如下。
1 瘟疫起病与传播途径
瘟疫的病因,吴又可在《瘟疫论》序言中说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所有人对于一种新的疫病均不具有免疫性,都可罹患,因此具有较强的致病性。究其发病原因,既往以为非其时有其气,容易变生瘟疫,其实不然,气候变化的年份很多,而爆发瘟疫的较少。有的年份疠气较重则出现大面积流行,有的年份疠气较轻则出现散在病例或者小范围爆发。疠气也有明显的地域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19,COVID-19)等均有明显的地域聚集特点;此外,疠气一般不会持续终年,而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有轻重的差别。
2 伤寒与瘟疫的区别
吴又可在《瘟疫论》中对伤寒和瘟疫的区别论述颇详,他认为伤寒和瘟疫无论在感邪途径、传变方式还是治疗方法上均有很大不同。伤寒必有感冒之因,多因感受寒邪而发,伴有四肢拘急,恶风恶寒,然后头疼身痛,发热恶寒,脉紧无汗为伤寒,脉缓有汗为伤风;而瘟疫初起,突觉寒战,紧接着出现高热。此乃邪气太盛,格阳于内,阳气不能达表而温煦,故可见恶寒和四肢厥冷。而阳气一旦冲破束缚,则里外皆热,至于仅发热而不恶寒者,是阳气未被郁滞,环绕在肌表所致。伤寒触之即发;而瘟疫多为即发,但或有少部分因饥饱劳碌或焦思气郁触发,如“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就其治疗结局,伤寒治疗后,一汗而解;而瘟疫发汗不能缓解,但终解以战汗。区别在于伤寒邪在表,“其在皮者,汗可发之”,而瘟疫初起邪在膜原,后可入胃,非发汗所宜。瘟疫的汗出而解是战汗,与伤寒之汗法不同,更类似于半表半里少阳证服用小柴胡汤之战汗。就其传染性来看,伤寒多不传染人;瘟疫能传染人。伤寒之邪是“表受”,自体表皮毛而入,多侵袭足太阳膀胱经;瘟疫是“上受”,自口鼻入,多侵袭手太阴肺经。二者不同之处还在于传变过程,伤寒从外及内,太阳-少阳-阳明;而瘟疫由上及下,口鼻-膜原-胃,二者入里均入于胃,殊途同归。伤寒发斑则病情加重;时疫发斑则病情缓解。伤寒发病时比较急,症状较重;而瘟疫初起症状不重,或渐加重,或忽然加重。伤寒和瘟疫的治疗方法,也多有不同。即叶香岩《外感温热篇》中所论“辨营卫气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与伤寒大异也”。所以就治疗而言,伤寒的“汗法”是方法,而瘟疫的“汗法”是目的。伤寒初起,邪尚在体表,当以解表为先;瘟疫初起,邪在膜原,当以疏利为主。伤寒之邪传于阳明,瘟疫之邪出于膜原之际,均可使用白虎汤类方,二者均可传变至胃,故后期均可使用承气汤类方。
3 瘟疫病机和治疗
3.1瘟疫病机 关于瘟疫的传变途径和部位,书中有明确的论述:“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所谓横连膜原是也。”此段论述确实是书中之精华所在,发古人之未发,启迪后来者治疗思路。说明瘟疫的传染途径均从口鼻而入,即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居多,这和现代认识一致。其后叶天士又发挥之,认为“温邪上受”,细究之,除口鼻外,还包括眼结膜、口唇黏膜,即主要是头面部染病。
口鼻染邪而入于膜原,膜原又称“募原”,泛指膈膜或肠胃之外的脂膜。“募原”最早见于《内经》,《增订通俗伤寒论》言:“膜者,横隔之膜,原者,空隙之处,外通肌腠,内近胃腑,即三焦之关键,为内外交界之地,实一身之半表半里也。”认为膜原部位在横膈之膜和其空隙之处,位于半表半里[1]。对于邪伏膜原的传播途径,吴又可指出,邪自口鼻可以直接传到“膜原”,“白苔润泽者,邪在膜原也”为其典型舌症[2]。
瘟疫之邪初居于半表半里之膜原,其传有九,或从外解或从内陷。出表则表散于三阳经,可见太阳、少阳、阳明之经证;入里则直入于胃,可有高热,便秘,腹泻等消化道症状。出表者,又以轻症之太阳居多,所以早期可有“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的症状。
3.2瘟疫治疗 瘟疫初起,病邪位置在膜原,邪不在经,阳气被邪所困,不得伸展,故而发热,如汗之,则必腠理开而阳气外泄,也就是“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故不可汗。不可早下,并非不可下,早下邪不在胃,下之徒伤胃气。故透达膜原的达原饮,其中槟榔、厚朴、草果仁三味主药芳香辟秽攻伐,知母、芍药、黄芩、甘草后四味作调和。从表出而走三阳经者顺,为愈也,根据三阳经不同的经证而分经用药,如柴葛解肌汤之太阳羌活,阳明之葛根、白芷,少阳之柴胡,此即“三消饮”之意。轻者可快速自解,重者必从汗解,但不能发汗,此即赵绍琴教授之“汗是目的,不是方法”。邪不出三阳经,仍在膜原,继续予以达原饮。外邪适离膜原,欲表未表,宜白虎汤。此即叶天士所谓“到气才可清气”,白虎汤在邪溃结开,邪气分离膜原时适用,有“脉长洪而数,大渴复大汗,通身发热”之阳明气分热证。邪入于胃,此谓内陷,舌苔由白见黄,外邪从表入于里,黄色乃脾土之色,需从下而解,故承气汤。瘟疫除了常规传变以外,也有“一日之间,而有三变”的快速传变,如见白苔如积粉,服达原饮;舌变黄色,伴胸膈满痛,加大黄下之;午后加重,伴有舌变黑生刺,急投大承气汤。舌苔的变化在瘟疫治疗中有重要价值,根据舌苔的变化随时调整治疗药物。如果表证里证同在者,务宜承气先通其里,里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能汗解。切不可先解表,此即温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之意也。
书中多次强调“下法”的重要性,且多次出现“下后”“再下之”“更下之”“更宜下之”的字眼,说明瘟疫应该在正气未损伤时及时攻下。应下之主证很多,但要抓住“舌黄、心腹痞满”,即可予达原饮加大黄下之,在瘟疫的治疗中,下法是治疗手段,也即“承气本为逐邪而设,非专为结粪而设也。必俟其粪结,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甚至很多患者大便溏泄,始终没有结粪,也要及时使用下法,此即“通因通用”。因此“下是方法,不是目的”,要和早期疏利而汗解的治疗方法相区别,“汗是目的,不是方法”。
如果下后苔刺已清,反发热者,是邪气郁结已开,正气暴伸于肌表而致,是邪去阳复的表现,恰似炉底通透,火热上炎。此时的发热是把体内郁结日久的邪热发散出来,无需多虑。但应和邪欲出膜原时发热的白虎汤证鉴别,主要是舌苔和腹满等症状的区别。此时可选择柴胡清燥汤,方由柴胡、黄芩、陈皮、甘草、花粉、知母组成。方中柴胡、黄芩解表清里,透达膜原,花粉、知母清其余热,生津养胃,佐以陈皮理气和中,甘草和药。诸药合用,透达膜原,解热生津。
从上可知,吴又可《瘟疫论》对时疫的认识较为深刻,在感染途径、传变方式、与伤寒治法的异同等方面论述详尽,尤其是其瘟疫之邪居于“膜原”的学术思想和对应的方剂达原饮,对后世瘟疫的治疗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