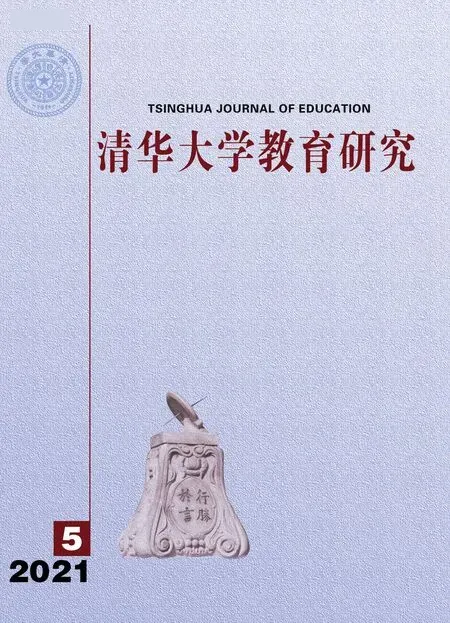高等教育监管的理由、困局与新视野
姚 荣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纵观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治理的演变历程,“监管”(regulation)长期以来被视为大学自治的对立面而存在。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民主宪政运动与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影响,高等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特殊组成部分,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的监管。当前,国家开始试图与控制其他政府投资的公共服务一样,控制高等教育子系统。传统上,以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为由拒绝外部监管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和挑战。为了确保高等教育监管获得更多支持,监管者不得不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监管提供正当理由。而反对监管的人们,则通过揭示高等教育监管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效应(1)Josh Stearns,“The Harmful Effects of Federal Regul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 46,no.2(2017):303-312.,批判高等教育监管的失灵现象。毋庸置疑,在高等教育监管已经深入影响到大学日常运作与管理的21世纪,如何审慎看待与解答高等教育监管何以正当、何以失灵以及何以超越监管迷思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为此,本研究旨在从公共管理与法律的视角,审视高等教育监管的正当理由、现实困局及其变革路径。
一、监管何以正当:高等教育监管的理由
高等教育监管的法理证成,要求对监管的正当理由予以充分论述。通常而言,高等教育通常被视为一个独立的领域。“高等教育机构比典型的公共部门官僚机构具有更大的自治权,甚至被称为‘独立’部门。”(2)伊安·奥斯丁,格伦·琼斯.高等教育治理——全球视野、理论与实践[M].孟彦,刘益东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99-101.在高等教育领域根深蒂固的学术和机构自治的观念,支持将高等教育和其他领域相区分。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等教育监管的转变正在使大学和健康保健部门等其他公共部门组织之间形成越来越多的相似点。尽管不同国家的水平有所不同,但政府正在制定政策,旨在通过更接近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方式‘引导’高等教育和大学。就像其他公共机构一样,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经常被看作‘国家的生物’,且它们的法律结构和治理模式都纳入本国的法律框架中”(3)伊安·奥斯丁,格伦·琼斯.高等教育治理——全球视野、理论与实践[M].孟彦,刘益东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 99-101.。从深层次而言,高等教育监管的正当理由,根植于高等教育的自治属性与公共属性之中。作为独立领域与公共领域的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监管提供了自治维系、权利保护以及责任导向等三种可能相互冲突的正当理由。
(一)基于维系自治的高等教育监管
大学自治为高等教育监管设置法律乃至宪法上的界限,是高等教育有别于其他公共领域的特殊性所在。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大学自治被视为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国家在管制及执行面向上的管制要求,常立刻碰触到学术的界限。”(4)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4-128.例如,在德国,由于《基本法》第5条第3项保障学术自由基本权利,因此与学术相关的国家决策程序应顾及基本权主体(包括大学)的自主性。合作原则作为一种缓和的平衡模式,有助于学术能适应国家的规范。(5)Hans-Heinrich Trute,行政法学中的治理概念——以大学为例[J].王韻茹等译.中正大学集刊,2012,(2):241-291.基于此,当前以德国、法国以及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开始放弃“程序性管制”的传统,进一步强调大学的自治地位,拓展大学的自治权限。当然,“以自治为名”的高等教育监管改革,同时要求增强大学的公共责任尤其是绩效责任。(6)Jürgen Enders et al.,“Regulatory Autonomy and Performance: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Re-visited,”Higher Education 65,no.1(2013):5-23.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传统上,英美法系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治似乎更加“纯粹”。通常而言,它无需通过国家管制与大学自治的双重结构,达成所谓的“历史的妥协”。通过特许状或大学章程保障大学自治权限,以远离国家的监督,构成英美法系的特色。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民主宪政浪潮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高等教育监管在英美法系的发展显得更加激进。权利保护与公共责任的双重诉求,促使大学逐渐从具有广泛自治权限的学术机构转变为受监管的法律实体。
当前,在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大学自治都开始被解读为一种受监管的自治或“监管型自治”(regulatory autonomy)。(7)Ibid.据此,大学自治仍然是高等教育监管不可回避的关键议题。在从自治走向治理的时代,赋予大学自治以新的内涵,不仅是高等教育监管的正当理由,更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工具”。例如,英国政府在赋予学生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Students,OfS)广泛的监管权限时,也明确其有义务维护高校的自治。根据2017年颁布的英国《高等教育与研究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HERA)的规定,学生事务办公室成立,该机构被赋予了广泛的高等教育监管权限。(8)Dennis J.Farrington and 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120-145.与此同时,该法律也明确作为监管者的学生办公室有义务维护高等教育提供者的自治。具体而言,《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强调高等教育提供者享有以下自治权限:通过有效、适当的方式自主进行日常管理;自主决定课程内容和教学、管理、评价方式;自主制定教师选拔、任命、解聘标准并付诸实施;自主确定招生标准并实施。(9)王雁琳.英国大学治理现代化和教育中介组织的变迁[J].比较教育研究,2019,(11):27-33.
(二)基于权利保护的高等教育监管
伴随着大学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师生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权利革命”的爆发,基于权利保护的高等教育监管开始兴起,国家作为法治守护者的角色不断强化。实际上,在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公共领域,监管与权利保护往往是紧密相连的。以美国为例,随着各类民权和反歧视法(civil rights and non-discrimination legislation)适用于学院和大学,联邦高等教育监管开始强化教育与就业领域的反歧视措施。(10)David E.Bernstein,“Antidiscrimination Laws and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A Skeptic’s Look at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Notre Dame Law Review 94,no.3(2019):1381-1415.基于联邦政府开支权(Spending power)的影响,受联邦财政拨款资助的高等教育机构,不仅有义务遵守接受资助的每个计划的技术要求,还必须遵守适用于联邦资助计划的各种民权要求。这些要求是联邦支出政策的主要重点,其旨在将实质性的社会目标纳入教育政策,并使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成为明确的国家优先事项。作为资助的条件,民权保障的监管诉求,是通过将权力下放给管理联邦资助计划的各个联邦部门和机构(如联邦教育部民权办公室)来实现的。具体而言,四部联邦法规禁止在接受联邦财政资助的教育计划中存在歧视,包括: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第六章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或国籍的歧视;1972年《教育修正案》第九条(Title IX)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1974年修订的1973年《康复法案》(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第504条禁止歧视残疾人;1967年《雇佣年龄歧视法案》(The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Act,ADEA)禁止基于年龄的歧视。(11)James T.Koebel,“Facilitating University Compliance Using Regulatory Policy Incentives,”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44,no.2(2019):160-208.除了反歧视以外,正当程序、隐私权、知识产权等权利,也都受到高等教育监管的有力保护。例如,《家庭教育权利和隐私法》(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FERPA)作为保护学生教育记录隐私的联邦法律,由家庭政策合规办公室(Family Policy Compliance Office,FPCO)负责实施,适用于根据美国教育部适用计划接受资金的所有学校。类似的,在英国,基于权利保护的高等教育监管,也与制定法密切相关。(12)Charles J.Russo,Handbook of Comparative Higher Education Law(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Education,2013),135-154.以2004年颁布实施的《高等教育法》(the Higher Education Act,HEA)为例,该法第13条授权建立一个实体机构,负责处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高校学生申诉事务,即所谓的“指定经营者”(designated operator)。作为指定机构,独立裁决者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Independent Adjudicator,OIA)的成立,使得视察员(visitor)处理高等院校内部纠纷的终局裁决权被终止,视察员的职责范围被极大缩小。相应的,学生作为教育消费者的权益保障状况得到改善。(13)Dennis J.Farrington and 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498-507.通过OIA制度的设置,英国为学生的权利救济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渠道,而申诉数量的持续增加,表明了学生作为“消费者”心态的转变。(14)Barbara A.Lee and Mark R.Davies,“No More Business as Usual in Higher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and U.K.Faculty,”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40,no.3(2014):499-542.
当然,除了英国与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以外,基于权利保护的高等教育监管,在大陆法系也表现得尤为明显。(15)姚荣.当大学与法律相遇:高等教育法律研究的全球图景[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1):101-110.例如,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对《基本法》第5条第3款、第33条第5款的宪法解释,保障教师的职业安全免受绩效竞争机制引入所可能产生的侵害。诚如奥托·霍瑟(Otto Hüther)与乔治·克鲁肯(Georg Krücken)所言,“尽管存在着以更加个性化和绩效导向的方式为教学和研究提供资源以及由此改变大学教授薪资结构的强烈趋势,但这种改革因其可能对教师的基本权利构成侵害,进而受到强大的宪法约束。毋庸置疑,学术自由是德国《基本法》所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联邦宪法法院需要为教授的讲学和研究提供最低限度的经费配备和资源保障。除了最低限度的资源保障以外,宪法也旨在为教授提供足够的薪资。2012年,联邦宪法法院宣布现行的教授薪酬方案违反《基本法》第33条的规定,因为没有额外工资的定期工资被认为是不足的。”(16)Christine Musselin et al.,“Hierarchy and Power: A Conceptual Analysis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New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s in German Universities,”European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3,no.4(2013):307-323.
(三)基于公共责任的高等教育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及高等教育全球竞争加剧的影响,国家开始基于公共责任逻辑要求大学承担透明、廉洁、优质、诚信、创新等一系列责任,高等教育监管的责任导向持续增强。为此,“在高等教育治理改革领域,政府不断调整或重新设计政策”(17)Giliberto Capano,“Policy Design Spaces in Reforming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Dynamics in Italy and the Netherlands,”Higher Education 75,no.1(2018):675-694.。基于责任导向的高等教育监管,旨在减少政府的控制,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通过大学自治与公共责任之间相互勾连,激发大学的创新活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增进大学的透明度与科研诚信。例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法》修正案,明确了其认可的认证机构的认证标准,促进了认证的“联邦化”,增强了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间接控制”。与此同时,《拜杜法案》《阳光法案》等法律的颁布实施,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了创新、信息公开等一系列要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阳光法案》服务于一系列具体目标,包括学术诚信、财政稳健、财务监督、组织的效率和效能,以及决策程序和结果的公正。由于目标涵盖广泛,《阳光法案》几乎影响到高校运行的各主要方面,包括:董事会评议与发展,校长搜寻与甄选,人事政策,研究与知识产权议题,预算决策与资源分配,投资与金融控股,商业谈判与交易,大学附属基金会,体育运动等等。
而在英国,201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法》对大学的透明、创新以及竞争导向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例如,新设英国科研与创新委员会(United Kingdom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作为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资助机构,旨在加强学术与商业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繁荣。与此同时,该法案还要求所有大学公开招生录取环节的详细信息,提高高等教育数据资料的透明度,以此打破目前种族、性别及家庭背景等隐形壁垒,从而实现高等教育领域的“透明革命”(transparency revolution)。(18)刘强,刘浩.当前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与发展方向——基于《高等教育与科研法案》的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8,(8):78-85.类似的监管措施,也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具体而言,2003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支持法案》(Higher education Support Act2003,HESA)要求接受联邦拨款的高校履行一系列公共责任,包括:财政可行性、质量、公平对待学生、合规等。此外,2011年成立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旨在采取基于风险与标准导向的监管模式(standards and risk-based model of regulation),增强政府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监管。当然,除了对于质量的监管之外,追求更大的透明度,也使得澳大利亚大学面临着深刻的监管挑战。鉴于大学作为公共当局(Public Authorities)或政府机构(Government Agencies)的法律地位,《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与《公共利益披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 2013)等法律被适用于接受公共拨款的大学。(19)Sally Varnham et al.,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aw(Sydney: The Federation Press,2015),64-79.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将高等教育视为公共服务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更加关注大学的公共责任。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纷纷放弃基于“程序性管制”的传统监管方式,通过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合同关系、任务导向型的经费配置模式改革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形塑监管型治理(regulatory governance)模式,重新诠释大学自治的公法内涵,以实现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20)姚荣.德国大学自治公法规制的经典内涵与现代诠释[J].高等教育研究,2017,(10):90-99.对此,有学者指出,在不涉及国家担保义务的情形下,“去管制化”意味着在维持脉络调控(Kontextsteuerung)的前提下,去除过度的管制,以减轻大学所承受的行政科层的负担,并促使大学的相关决定更透明、更迅速。(21)杨国赐,胡茹萍.大学创新转型发展[M].台北:高等教育出版,2016.1-17.换言之,“去管制化”旨在通过为大学“松绑”,拓展大学自治权限。与此同时,强有力的大学自治主体,被国家赋予了比以往更多的公共责任与期望。
二、监管何以失灵:高等教育监管的困局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就被视为独特的公共领域与相对独立的自治领域而存在,大学被赋予了作为公共机构与自治机构的双重法律地位。基于高等教育的多元色彩与复杂属性,如何审视与界定国家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难解的谜题。从监管法理学的角度而言,自治维系、权利保护与责任保护作为高等教育监管存在的三重正当理由,彼此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和法理基础。然而,高等教育监管中生动复杂的监管实践,又无时无刻不在告诫人们,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监管,存在诸多悖论、矛盾与困局。从深层次而言,大学自治、公共责任与权利保护三者之间相互冲突乃至不可调和的关系,使得高等教育监管时常遭遇失灵。这种失灵既包括权利主张引发的自治负荷与他人权利受损问题,也包含公共责任强化所带来的“监管恐慌”(regulation panic),还包括基于大学自治的不同解读所引发的争论。
(一)追求大学的透明度与学生隐私权以及大学自治之间的冲突
对大学公共责任的强调,总体表现为绩效责任与透明度两个方面。与绩效责任的强调往往与资金拨付挂钩不同,透明度的追求往往来源于信息公开相关公法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在美国,“无论公立大学的自治权(由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如何正规,另一些因素总能对它们产生干预。例如,在许多州,关于公共机构会议公开和信息自由的《阳光法案》,已经扩展到能使公立大学的正常工作陷于瘫痪的地步”(22)Michael K.McLendon and James C.Hearn,“Mandated Openness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A Field Study of State Sunshine Laws and Institutional Governance,”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77,no.4(2006):645-683.。对此问题,克利夫兰的研究提出,“当这些法案适用于公立学院和大学时,对社会构成三难困境。高等教育中的强制性公开在三个理想但往往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之间造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即确保公共问责、保护个人隐私权以及赋予组织实现公共目的所需的自主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张力。更为棘手的是,《阳光法案》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带来了更广泛的成本问题。根据《阳光法案》建立人力、法律和组织系统来回应媒体和公众的询问的成本可能很高,尤其是在组织机构复杂、庞大且知名度很高的州和公立高等教育机构”(23)Ibid.。类似的由追求大学治理的透明度所引发的监管困境也出现在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学者海伦·弗莱明(Helen Fleming)感慨道,“澳大利亚的大学,面临着不断扩张的监管环境。作为公共机构的大学,不得不将透明度的要求纳入大学运作的各个方面。有关监管导致大学自治或学术自由受到侵害的辩护和批判,似乎不再有影响力”(24)Sally Varnham,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law(Sydney: The Federation Press,2015),64-79.。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教师权利以及大学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强化大学绩效责任的重要途径。尽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一直试图通过调适,缓解对大学的监管压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仍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官僚式的决定”。在英国,将学生作为高等教育服务消费者的主张,与教师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乃至大学公共使命之间的冲突愈发凸显。大学知识的商品化,意味着大学信任秩序的瓦解和教师专业判断权的式微。以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后由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替代)的教学评估为例,其中心标准似乎是教师是否提供了客户(即学生)期望获得的课程。(25)Dennis J.Farrington and 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454-461.与英国的状况类似,美国“教授在保护学术同一性方面的传统角色越来越受到挑战,因为大学和大学管理者愈加重视学生对教授和教学的看法。通过将教与学的关系替换为市场营销的词汇(例如学生作为消费者的隐喻),市场化的话语重构了公共对话的能力,从而促进了市场逻辑在高等教育中的实施。学生消费者隐喻的制度化伴随着人们对教育的思考方式的转变,从成为更具有知识的人的过程转变为购买教育产品(分数或学位)。公众将高等教育作为投资并关注其实际价值,高等教育机构通过采取‘让公民获得选择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这一举措,以此为学生提供世界一流的服务和价值”(26)Barbara A.Lee and Mark R.Davies, “No More Business as Usual in Higher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or U.S. and U.K.Faculty,”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40,no.3(2014):499-542.。
与英美法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消费者导向不同,大陆法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兴起则根植于关于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诉求之中。(27)姚荣.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规制及其启示——基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J]高等教育研究,2018,(12):86-97.对此,公法学者倾向于认为,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对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干预方式,其正当性的获得必须基于比例原则的严格检视。实际上,德国联邦宪法法院2016年作出的大学课程认证裁定案,正是基于这一宪法层面的考量。(28)Christian Jasper,“Die Zukunft der Akkreditierung von Studiengängen,”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DÖV)70,no.1(2017):911-913.毋庸置疑,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扩张,与教师的学术自由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大学自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张关系。对此,波尔(Harry de Boer)与恩德斯(Jürgen Enders)开展的一项实证研究就指出,新型监管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自治受到了强烈的限制。大学对公共财政资金的长期依赖、国家与大学之间订立的绩效协议以及国家对大学的多重责任要求等因素,使得大学将长期在政府规则和期望的阴影下行动。实际上,给予大学更多的自治权并不意味着政府影响力的减弱。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表明政府开始采用新的方式(包括质量保障),对大学组织行为实施影响和控制”(29)Ivar Bleiklie et al.,Managing Universities Policy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from a Western Europea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Palgrave Studies, 2017),57-83.。
(三)大学创新责任的强化与教师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经典学术价值观之间的抵牾
高等教育监管对大学创新责任的呼唤,旨在推动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然而,高等教育商业化和学术劳动力转型等因素的融合对学术自由构成了威胁。大学通过提高学费和代理新商品(从专利到高管教育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进行自我调整,导致其公共身份和使命被忽视。为支持这种创业方向而制定的机构政策,往往会在“创新”的幌子下,对学术自由造成寒蝉效应。越来越多的大学放弃了研究型大学的公共目标,追求有争议的工作的学术自由权利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创业的野心。(30)Samantha Bernstein-Sierra and Adrianna Kezar,Intellectual Property, Faculty Rights and The Public Good(San Francisco:Jossey-Bass,2017),11-23.以美国为例,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对学术自由的威胁尤其严重,因为越来越多的临时教师既没有宪法保护,也没有合同保护。终身教职教师也不能幸免于此,因为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也发生了变化。随着雇佣范围内的雇佣工作的所有权被转移到大学,教师的知识产权和教学、研究自由受到严重侵犯。当前,平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利益(包括:公众的使用,大学努力创新并寻求新的资金来源,教师对其工作和作品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自治权利开始面临更多的法律干预。概言之,强调知识产权交易与转化的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既导致高等教育越来越走向封闭乃至陷入“信息封建主义”的泥淖,又加剧了教师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
(四)大学内部管理自治强化与学院治理传统之间的矛盾
为了强化大学的公共责任,保护师生权利,高等教育监管往往从两个方面强化了大学的管理自治权力。一方面,增强大学的管理自治权,采用更具企业化特征的法人治理模式,提高大学的治理能力,提高大学的办学效率和质量,以便于大学在高速竞争的全球市场中做出反应和采取行动(31)伊安·奥斯丁,格伦·琼斯.高等教育治理——全球视野、理论与实践[M].孟彦,刘益东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19-21.;另一方面,在变动的监管环境中,为了完成政府的监管要求,高校必须设置相应的机构,以规避合规风险。(32)姚荣.告别自治:合规时代的美国大学治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3):75-88.这两种状况在大学管理中都普遍存在。对于前者而言,它旨在批判大学学术自治的自我封闭性,强调大学更加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例如,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和各州《高等学校法》的修订,均强调增强校长与院长的权力。而在日本,2014年《国立大学法人法》《学校教育法》的修订,进一步拓展了校长的权限,削弱了教授会的权力范畴。诸如此类的改革措施,都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思路,即通过强化大学自治权限尤其是管理者的权力,重新定义大学使命,激活大学创新能力,削减办学成本。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亚等英美国家,大学也正在经历着向公司治理转变的过程。“现代大学正在以绩效评估、战略规划、绩效预算、绩效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和审计文化为特征的组织文化背景下进行治理。换言之,通过采用一系列公司的管理体系,大学加强了内部等级。相应的,大学治理也面临着传统治理模式与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张力问题。”(33)伊安·奥斯丁,格伦·琼斯.高等教育治理——全球视野、理论与实践[M].孟彦,刘益东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19-21.对于后者而言,政府监管对权利保护的关照,使得大学合规义务增多,并导致管理人员增加。受此影响,教师在大学治理中的作用持续下降。应该认识到,法律工作量增加和风险管理敏感性的提高,也可能导致学术机构内部的紧张局势加剧,因为它们要应对治理方面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有时会导致对学院治理模式的质疑(34)Sally Gunz and Marianne M.Jennings, “University Legal Counsel: The Role and Its Challenges,”Notre Dame Journal of Law, Ethics & Public Policy 33,no.1(2019):177-220.。
三、监管何以走出困局:高等教育监管的新视野
相比于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领域,高等教育领域的政府监管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价值整合难题。高等教育监管在自治、权利与责任之间客观存在的紧张关系,使得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高等教育监管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都存在不满。当学者基于学术自由和教师自治批判高等教育监管时,政府可能更多地抱怨自己精心设计的监管策略缘何难以奏效甚至不被理解。毋庸置疑,在大学内部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高度分化、权利高度觉醒的21世纪,国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监管变得异常复杂而充满风险。“尽管学术遵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监管机构与法院必须明白,管理一个一直以来不受监管的机构,是一个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接受和应对国家对大学的监管和立法。只有当法院、政府和高等教育系统都接受这一现实时,合作才可能发生。”(35)Amy Gajda,The Trials of Academe:The New Era of Campus Litigation(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229-257.
(一)采取更加“精明”的高等教育监管策略
如何避免基于权利保护与责任导向的高等教育监管,导致大学自治陷入规范“负载”乃至监管恐慌,是高等教育监管变革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科学界定高等教育监管的合理水平,如何重新设计高等教育监管的机制和策略,进而走向更加“精明”的高等教育监管。目前,高等教育监管合理水平的确定,存在两种基本思路。其中,英美国家的思路,是建立基于风险的市场型监管体系,增强政府监管强度与大学自主办学风险之间的匹配度。例如,在美国,应对联邦合规压力的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是利用风险告知策略(Risk-Informed Strategy)。风险告知策略要求所有大学都遵守教育部制定的“基准规则”(baseline rules)。只有当初步评估表明财务稳定性或大学学术质量等存在风险时,才适用其他法规。总体而言,这种改革策略将减轻表现良好且财务稳定的大学的合规负担。(36)James T.Koebel,“Facilitating University Compliance Using Regulatory Policy Incentives,”Journal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aw 44,no.2(2019):160-208.在英国与澳大利亚等国家,高等教育监管也开始强调监管的风险导向,当高等教育机构被判定为“低风险”时,政府的监管强度将被相应降低。反之,政府监管的强度和等级将随之“提高”。(37)苏锦丽.高等教育机构品质保证制度与实践:国际观与本土观[M].台北:高等教育出版, 2015.143-168.与此不同,在评估型国家的脉络下,欧陆国家旨在基于国家与大学之间合同关系的确立,促进教育行政监督与大学自治之间的协商合作。在德国、法国与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政府往往会根据大学履行合同约定义务的具体表现,适时调整政府财政拨款以及后续的监管措施。(38)巫锐,皮尔·帕斯特纳克.德国高等教育“合约管理”模式的经验与启示——基于柏林洪堡大学七版目标协定文本的比较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0,(1):126-133.
除了科学界定监管合理水平之外,高等教育监管改革需要强化不同监管机制与治理模式之间的优化组合,丰富高等教育监管的“工具箱”。与传统的“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不同,“后规制国”语境中的合作监管描述了一种面向治理时代的监管图景。它探求“控制过程中的多样性,这些过程利用到了除科层制与国家法律以外的控制机制,尤其是在社会或社群规范实践、在组织环境下的竞争机制,以及设计所能控制行为的能力。在每种情况下,科层结构或者国家法律可能在控制体系中发挥着部分作用,但不再具有垄断地位”。(39)科林·斯科特.规制、治理与法律:前沿问题研究[M].安永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89-92.高等教育监管应促进科层(立法)、社群(共同体)、竞争(排名、拨款机制)以及设计等为基础的不同监管模式的“混合”。(40)同上.卡帕诺(Giliberto Capano)对学界关于高等教育监管的既有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确定了四种类型的监管模式:官僚化管制、程序化管制、远距监督以及自我监管。其中,每种监管模式都有特定的政策工具。(41)Giliberto Capano,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do its Job.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ance Shift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Public Administration 89,no.4(2011):1622-1642.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复杂性,要求监管者针对不同的事项与议题,设计差别化的监管模式,实施不同的政策工具。
(二)增强对高等教育监管机构的监管
作为一项合作事业的高等教育监管,不仅要求政府设计更加“精明”的监管策略,还强调司法审查对教育行政监督权的法律控制,以增强监管的透明度。对此,托尼·普罗瑟(Tony Prosser)提出监管机构的可问责性应该通过程序化(proceduralization)的公法规制、议会监督(scrutiny)和司法审查来保证。(42)托尼·普罗瑟.政府监管的新视野:英国监管机构十大样本考察[M].马英娟,张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0.7.毋庸置疑,当司法卸除对政府裁量权的约束职责时,政府公权力必然会不断蔓延和扩张,以至于打破合作与平衡的底线。例如,在美国,司法对行政机构规则的广泛尊重,创造了一个广泛且呈指数增长的行政合规规则体系(administrative compliance rules)。(43)Josh Stearns,“The Harmful Effects of Federal Regul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Journal of Law & Education 46,no.2(2017):303-312.为此,有学者指出应根据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等法律加强对联邦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非立法性规则的约束,引入“通知-评论”(notice and comment)程序,增强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44)R.Shep Melnick,The Transformation of Title IX:Regulating Gender Equality in Education(Washington: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2018),13-23.类似的,英国法院要求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会(HEFCE)与学生办公室(OfS)等法定的规制者,履行自然正义原则与越权无效原则等公法基本原则的约束。(45)Dennis J.Farrington and 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120-124.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TEQSA)被要求遵守普通法上的程序正当与自然正义原则。(46)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Review of the impact of the TEQSA Act on the Higher Education Sector,” https://www.dese.gov.au/quality-and-legislative-frameworks/review-impact-teqsa-act-higher-education-sector.当然,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对高等教育监管的法律控制也开始引起关注。尽管基于德国高等学校作为国家设施或公营造物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政府之间内部关系的传统,法院往往拒绝介入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公法争议,但是,围绕高等教育认证活动的开展,依旧引发了一起宪法诉讼案件。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2016年的“大学课程认证裁定案”中,根据《基本法》第5条第3款的规定判决北威州关于高等教育认证的法律违宪。该判决认为,北威州的法律规定侵犯了学术自由基本权利。随后,德国各州文教部长会议(KMK)出台了认证新规,以应对联邦宪法法院作出的裁定。(47)Christian Jasper,“Die Zukunft der Akkreditierung von Studiengängen,” Die Öffentliche Verwaltung(DÖV)70,no.1(2017):911-913.应该认识到,大陆法系国家的公法学界和实务界对高等教育监管的改革措施一直抱有审慎的怀疑态度,认为其可能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构成侵害和威胁,并据此要求立法者在高等教育监管(如质量保障、目标合同等)机制的设计中,加强学术自治力量的充分参与。
(三)提升高等学校的机构能力
高等学校作为自治主体,能否积极主动地履行自我监管的责任,以实现自治、责任与权利三者在大学内部治理变革中的有机整合,是作为合作事业的高等教育监管最终走向成功的关键所在。基于此,高等教育监管的思路,应从调整外部监管的强度,转向更加强调作为被监管者的内部能力,推动高等学校的良法善治。(48)罗伯特·鲍德温等.牛津规制手册[M]. 宋华琳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136.通过机构能力的强化,高等学校作为负责任的自治主体的角色和功能逐渐明晰,而外部监管则更多扮演辅助性、引导性的角色。当前,以英国与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了以风险预防与管理以及校内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为核心的法律规划(legal planning)体系(49)William A.Kaplin et al., 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19),163-182.,增强了高校利益冲突管理、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以及协商治理体系等基础性制度的建设。(50)Dennis J.Farrington and David Palfreyman,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1),789-807.而在大陆法系国家,高校的机构能力建设根植于自治与自律的传统,且更加重视大学治理合议本质的凸显。诚如德国学者施密特·阿斯曼所言,大学是“传递行政责任以及自由基本权利保障的媒介,而不是国家行政机关用以贯彻其实质决定的工具”(51)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M].林明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4-128.。换言之,大学作为国家与教师、学生之间沟通的媒介,其大学自治的强化应顾及教师与学生的权利保障(52)高亮.论高校教育惩戒权的构造与限制——兼评高校疫情防控中教育惩戒权的运行[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0,(6):13-22.,同时担负起特定的公共责任。为此,单纯以贯彻政府意志或教授自治的观点来审视大学作为公法人的机构能力建设,都缺乏可行性。(53)姚荣.新公共管理语境下大学自治权限分配的公法争议及其解决[J].重庆高教研究,2020,(2):72-90.相反,基于合作原则,激发大学自我监管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国家与学术、学术与行政、学术与经济的合作,则是更为符合学术法规律的变革路径。(54)杨国赐,胡茹萍.大学创新转型发展[M].台北:高等教育出版,2016.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