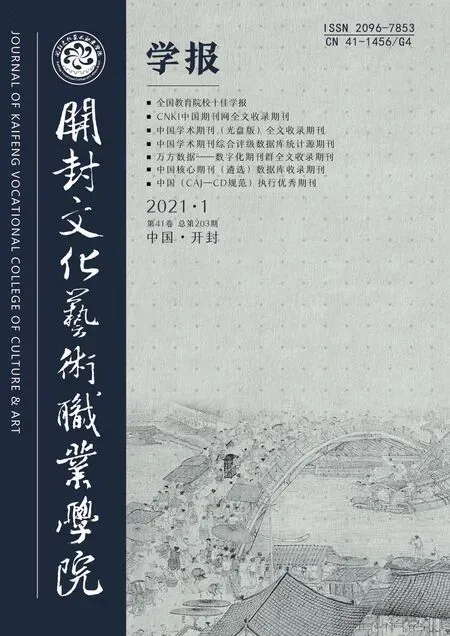论昆剧中的写意、诗意与禅意
——以新版《玉簪记》为例
杨娟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一、现代审美下的写意
(一)写意的舞美
新版《玉簪记》第一折《投庵》中陈妙常于乱世逃难来到女贞观,一方面是得到了庇佑,另一方面是要遵从佛道,洗净尘世的杂念欲望。这一折的舞台背景仅女贞观三字,配以草书经文、佛像,这样的安排既突出女贞观远离尘世之特点,又不失佛道的庄严肃穆,其中奚淞先生的白描佛像空灵之中有博爱的慈悲。笔墨的线条、素描的留白,这些舞台背景都极富写意性,不经意间就把观众带入戏梦之中。另外,舞台颜色以灰色为主,加入演员纯白的服装,有一种青莲出尘之感。陈妙常投庵的入道仪式上,12 位道姑在幽幽的诵经声中持云帚飘然出场,陈妙常在道姑的群舞中披上写有“净”字的白衫,这暗合了中国戏曲源于祭祀歌舞,极具仪式感,又有朝圣意味。随着故事的发展,之后的每一折都延续第一折的写意风格,变幻莫测,亦真亦幻,仿佛一杯幽香的清茶,清透之中韵味无穷。再如,《秋江》一折背景不是用景,而是用董阳孜先生的狂草写出的“秋江”二字。飘逸洒脱,如江水澎湃,符合《秋江》一折潘必正与陈妙常离别之时情感的爆发,这种写意高雅含蓄,既符合现代简约的审美标准,又继承了传统文化的以简写繁、以点代面,韵味无穷。
(二)写意与青年观众
写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深深熔铸在中国戏曲的唱念做打、一招一式、一本一折中。戏曲表演中一个简单的程式性动作、戏曲舞美中一处简单的设计都蕴含着丰富的意义,需要观众认真体悟。昆曲尤甚,其唱腔讲求一唱三叹,表演动作柔美舒缓,舞美设计意蕴无穷。昆曲更加追求“以无胜有,以简胜繁”的写意性美感呈现,也对观众的耐心与审美态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消费社会的背景下,新媒体日益普及,青年观众群体更倾心于快餐文化,如综艺节目、短视频、娱乐新闻等,这种审美习惯与昆曲的美学表达“格格不入”,昆曲舞台自然就“门庭冷落”。“要解决好表演程式产生的时空假定性同习惯于影视直观的青年观众之间的心理默契;调适好昆曲写意性强,往往抒情压倒戏情,青年观众则又期待故事性观赏心理的矛盾;避免青年观众因昆曲精致典雅舒缓的舞台节奏而有心理疲倦感,让青年观众对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感兴趣,产生共鸣。”[1]白先勇先生及其制作团队,以现代审美重新演绎昆曲名作《牡丹亭》。新版《玉簪记》也去粗取精,去掉原剧中繁杂陈旧的装扮、舞台布置,采用极简色调,如陈妙常与潘必正的妆容便结合现代彩妆理念,突出青春气息。再如众道姑知道必正与妙常二人的情事后,相互议论这一新奇事件的这场戏中,众道姑的服装设计极具特色,白衫水袖上点缀些许桃红,别出心裁且恰当地反映出众道姑当时的心情,她们在旁观必正与妙常的“大胆行为举动”,心中也萌发出对爱情的向往,但又十分羞涩。这样微妙而又复杂的青春少女心理就用这一色彩搭配巧妙地表现了出来,含蓄且韵味无穷,能够引起观众的无尽遐想。这样青春而又有些许调皮的色彩设计符合现代青年观众的审美体验,不再呆板沉闷,赋予传统故事以灵动质感。另外,舞美方面加入现代灯光设计。例如,《秋江》一折中,主光给到正在江上小舟追赶潘必正的陈妙常身上,突出了主要人物,这一点符合当代青年的审美习惯,也不与传统的程式相冲突,是个大胆的突破尝试。新版《玉簪记》保留戏曲写意性,与观众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同时又适当地融入一些现代元素,照顾青年观众的审美经验,使之既能够与本剧产生心灵共鸣,亦能真正感受典雅昆曲之雅韵。
二、诗意的穿针引线
(一)诗意的贯穿
《琴挑》一折以琴传情,古琴典雅优美,必正与妙常在美好的月色下初探情意。二人各自借琴声与曲调来诉说心中的爱意,表达自己对眼前之人的真挚情感。这时候的情意是含蓄的、充满诗意的,每句曲调与曲辞都是那样优雅与动人。在良辰美景中,夜色寂寂,琴声幽幽,此折如抒情诗般借景物来描写剧中人物内心,同时借助动作展现两人内心的情思涌动。必正听到妙常凄凄寂寂的琴声,顿生爱慕,便借切磋琴艺表达情意,必正道:“雉朝雊兮清霜,惨孤飞兮无双。衾寡阴兮阳,怨鳏居兮徬徨。”[2]78妙常道:“烟淡兮轻云,香霭霭兮桂荫。叹长宵兮孤冷,抱玉兔兮自温。”[2]78琴曲清淡真雅,又含蓄蕴藉,充满诗情画意。此折的诗意与写景、抒情、叙事三者相结合,更好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路线与情感深度,“兴到而不之致、气到而不之豪、情到而不之忧、意到而不之浓”[3]。
《偷诗》一折更是以诗为主要对象来展开必正和妙常二人的情感交流。其细致的曲辞把两个年轻人对爱情向往又羞怯畏惧的心理表达得真切自然。妙常把对必正的情意、对爱情的想象及自己的忧思用诗句表达出来;而必正的月夜偷诗则是对妙常的心意初探,他是那样渴望爱情,渴望去了解妙常的真实情意,所以趁妙常睡着之时偷诗探情意,随即便由妙常的诗而坚定了自己对爱情的信念。
(二)诗乐的渲染
《玉簪记》的美渗透在水墨晕染的诗意中,其中诗化的不仅仅是文辞、舞美,也有剧中的音乐。昆曲本身是一种充满了古典音乐的艺术,但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它也是依附古典文学,并由其发展演变而来的,南北曲是其基本组成单位。而“曲”是由一种韵文文体发展而来,它代表了中国古典诗乐文化的典范。这种诗乐文化体现在精致优雅的曲辞和空幽悦耳的唱腔、配乐中。新版《玉簪记》巧妙地用千年古琴九霄环佩来伴奏,古琴的声音清幽典雅,融合了唐诗的韵律、宋词的清丽、元曲的世间百态,演绎出传奇的浪漫诗情。
例如,《投庵》一折中妙常初入佛门,在寂寂琴声中出场,使这一戏剧情境立即充满了佛道的空灵神圣之感。《琴挑》一折中古琴更是占据了主要角色,必正与妙常二人以琴为中介,互诉衷肠,但又是那样含蓄,充满诗情画意。该剧的古琴演奏者汪瑛瑛曾谈到古琴对于必正和妙常感情交流的重要作用,“潘必正抚琴:‘雉朝雊兮清霜,惨孤飞兮无双。衾寡阴兮阳,怨鳏居兮徬徨。’我运用了撞、剔、挑、劈、勾、双弹、散音、按音等古琴指法,把潘必正有恃无恐,调戏、挑逗陈妙常此时轻浮的心思表达出来。陈妙常抚琴:‘烟淡兮轻云,香霭霭兮桂荫。叹长宵兮孤冷,抱玉兔兮自温。’在实际演奏中,我充分运用了挑、拨、抹、勾、一指双音、抓起带起、泛音等古琴的指法,把陈妙常此时孤单、凄凉和幽怨的心情展示出来。”[4]典雅而充满抒情性的音乐很好地烘托了气氛,净化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这种音乐是诗意的、纯净的,它和现代嘈杂的流行音乐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充分吸取传统音乐精华之后的诗化创新。
新版《玉簪记》的音乐基于深厚的古典文化,在现代审美标准之下,对传统大胆突破。古琴伴奏创新之处在于突破昆曲管弦丝竹的呢喃优雅,而多了几份庄重与神圣。这份庄重与神圣能使观众肃然起敬,融入戏剧情境,进入必正与妙常的诗意爱情世界。二人以琴传情,以诗达意,曲辞如诗句般美丽雅致。例如【懒画眉】:“粉墙花影自重重,帘卷残荷水殿风。抱琴弹向月明中,香袅金猊动,人在蓬莱第几宫。”[2]57句子整体渲染出浓浓的浪漫气氛。正是这种诗意的渲染,提升了整出戏的审美水准,使它不仅是戏曲,更是诗乐。音乐本身是一种抽象的艺术,不能触摸,也不能看见,只能靠听觉去感受、想象,但在可观的戏剧情景中,它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和感知,观众会结合具体的戏曲人物、故事演绎去联想。古琴清幽典雅的乐音充满了诗情,因此它变作一种诗乐,拥有崇高的功能,成为这出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传递情感这一功能上,音乐艺术是超越其他艺术形式的,声音可以传递情感,感化人心,使人们产生心灵共鸣。诗本来是一种表达和抒发情感的艺术,它与音乐结合后便成为诗乐,表情达意的色调便更加浓郁了。在新版《玉簪记》中,这种诗乐贴切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的微妙感情,并为之增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三、禅意中的净俗统一
(一)《投庵》的净与空
《投庵》的主题虽然是净与空,但是也为陈妙常与潘必正的一见钟情埋下伏笔。《投庵》开场是道姑的群舞,这一段舞蹈配以清幽的古琴乐,向观众展示了佛道之地的肃穆与清净,极具仪式感。道姑群舞,刻画出“投庵”的环境,从而烘托出陈妙常接下来的生活环境以及所要面对的道观人生,空寂之中又有些许悲凉。接着背景由女贞观变为董阳孜先生的手抄佛经,道姑群唱“风扬幡影,寂寂香初定,三宝皈依醒,还祈海晏河清”[2]12,唱词尽显禅意。这里既突出了爱情的萌芽与纯粹,又是对色空的解读。这种色与空的对立亦是必正和妙常心理矛盾的原因所在,妙常在佛门净地需四大皆空,而见到必正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本心,这种矛盾心理导致她既爱又不敢爱,进而衍生出后面的每一折故事。妙常欲迎还拒,必正小心翼翼却又真情难禁,致使后来得了相思病,便引出《问病》一折,“问病”,实则“问情”。二人从互探心意,到最后表露真情,完成了由色空对立到二者合一的转变。戏剧中的色空对立,是矛盾所在,也是故事发展的动力源泉。“原本色空并不异,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是佛教对于人世一切存在物发出的冷峻判断语,是至真不误的命题。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纵说千万句也未必发挥得透彻,而真正理会到个中究竟的人,当然也就受用不尽。”[5]“懂得‘色空空色’的道理,才会明白,何以佛菩萨一方面要破除我执与法执,另一方面又并不要人们鄙视或放弃这个世间,而是积极地参与人生。”[6]所以,虽是在女贞观,但妙常与必正的爱情并不违和,反而是对色空的更好解释。《投庵》为后来妙常对必正的感情转变作出铺垫,陈妙常为躲避战乱来到女贞观,这不是烦恼的终结,而是烦恼的开始。女贞观对于陈妙常仿佛是杜丽娘的寂寞闺阁、崔莺莺的高墙大院,束缚着陈妙常萌动的情窦,但是陈妙常正值青春,束缚与压抑越久,就越渴望尘世爱情,所以才有了《琴挑》中妙常大胆与必正琴曲传情,《秋江》中妙常与必正难舍难分。
(二)《琴挑》《秋江》的尘与情
《琴挑》作为必正与妙常初定情意的重要一折,是寂寂清道观的缠绵琴声,是互诉衷肠的尘世真情,是色空之色。在此折中,两人以琴曲传情,必正唱古诗词、弹奏古琴曲,含蓄委婉地表露对妙常的心意,这使得妙常既羞涩又不忍拒绝,于是二人便借琴音表达心声。这是尘世情爱的真切表现,在必正的引导下,妙常琴声、人声皆染凡尘,由此也更加敞开心扉,大胆表达真情。这里的爱情是纯粹而自由的,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这种尘世的真情与佛家的净空并不对立,因为它同样纯净,纤尘不染,是圣洁的。这样的爱情是自然而温情的,有佛家的慈悲,是对禅意的精深解读,并不是浅层面的四大皆空。这也表明《秋江》中的离别不是悲情,而是深情,这里没有《汉宫秋月》的冷寂与孤苦,有的是佛家的大悲悯、大慈悲。
《秋江》的背景是写意而简约的狂草,不是江水,也不是寂寥秋景,传递出无限的激情。狂草的气质与妙常在风浪中追赶必正的心情相符,妙常与必正的感情在离别的一刻完成了大爆发,此刻两人的心如江水般波涛汹涌。《秋江》的编演很符合此刻的戏剧情境,是对尘与情的完美诠释,也是对《投庵》净与空的呼应。
“高濂所处的时代是从嘉靖末年到万历中期,而这段时期正是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而此时的中国也迎来了一场高扬人性欲望的人文思潮。”[7]167《玉簪记》描写道观中的爱情与世俗欲望,男女纯真自由的爱情冲破封建思想以及戒律清规的牢笼,“反映出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7]167。这种爱情与世俗欲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琴挑》与《秋江》两折中,这两折也使全剧的情感达到高潮。
结语
新版《玉簪记》以现代美学观念,完成写意的完美传达,诗意的真挚表现,启发观众去理解戏曲的象外之象,并加入禅宗美学,使观众在陶醉于昆曲美之余,又能净化心灵,得到禅学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