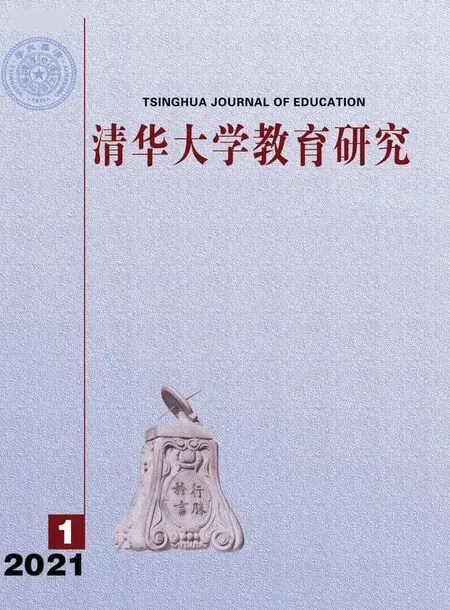新时代的教育学研究
杨 锐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今天这个时代,今天的中国和世界,要求我们有新的认识和理解,这是我们做好教育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学基础,因此,我想讨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当下时代的特点及其要求,二是我们的认识,最后落实于我们应该如何做教育学研究。
关于第一点,我想借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描述眼下的世界形势。当前的国际形势的确是乱象丛生。其实在2019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欧洲各国民粹主义高涨,以及刚刚结束的极度分化的美国总统选举。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实质上大体一致。虽然直接原因看上去是利益之争,但实质是西方社会特点所致。对非西方的态度,尤其是对我们的围堵实际是延续了其百余年来的传统。在美国,从19世纪的马汉(Alfred T.Mahan,1840-1914)到近年过世的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 1927-2008)和在位不到一个月的蓬佩奥(Mike Pempeo, 1963-),学界政界,一脉相承。反映的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对于其他文明的霸道和敌视。
种种现象因新冠疫情而变得复杂化,也更加昭然若揭。至少有几点可以观察到:首先是几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力量成为强弩之末,恶化现象及虚伪性暴露无遗,很大程度上已失去自我调试和修复的能力。其次是在其处于发展困境之时,仍强烈拒绝学习和尊重他人。相反,甚至变得更为激进,更具侵犯性。再次是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精英阶层,这是个很大的提醒:我们需要对于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先进文明文化做进一步审视。这一点很重要,也很不容易。我们由于后发,加上长期西式教育的熏陶,有意无意地用其经验和做法做参照,甚至为标准,思想上形成了定势,甚至为其所控制,即文献中所谓的被俘虏了的头脑(the captive mind)。我们必须从这种思想奴役中解放出来,必须清楚他人没有也不愿意为我们发展给良策,答案只有我们自己去找,也只有自己才能找得到。
至于第二点,让我引用18世纪初英国杰出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论批评》中的名句“一知半解,最为危险”来开始。现时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性。动荡对于我们不完全是坏事,不确定更意味着机遇。我们不是当前控制这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力量。我们希望变,利用变以成就自己。对于我国学界而言,晚清以降,尤其“五四”以来,我们的知识体系由经史子集,转向以现代学科分类为典型特征的西方知识体系。伴随着的是我们价值的失落,即杜维明先生所说的华人的集体失忆(collective amnesia),也就是对自己民族传统的不了解。一谈及传统,我们所想到的只是古代。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我们多数的高校毕业生读古文比读英文更难,与历史文化传统割裂。由于我们对自己了解不深,就难以真正了解西方。更由于我们对西方一知半解,便无法彻底了解自己的民族和社会,形成恶性循环。
这种双向的不了解已成为常态。在喧闹斑驳的眼下去盲目凑热闹,去求变,跟着感觉走,努力适应所谓的趋势和大势,不知道该坚守什么。当不知道守护什么的时候,你怎么求变?你变成什么?不就是做为浮萍而随风飘吗?!但风多是从西方吹过来的。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没有鉴别能力,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了解不深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最大内伤。在教育学领域表现得很突出。因为不了解自己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批判吸收的能力。
关于第三个方面,希腊的箴言说,认识你自己。那么如何认识自己呢,我们常以为的自己其实不是自己。讲得严重些,有时候,我们就像柏拉图洞穴之喻中的囚犯。表面上看,我们的政策文本是中文写的,讲的是我国的目标和实施策略。但细究起来,从看问题、发现问题的角度,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几乎全是西式的。注意:不是西方理论和方法不可以借用,而是不能简单地借用,因为它们都是建基于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经验之上的。如果过于依赖它们的话,我们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都很可能会失去效用。然而,只要打开我们的社会科学教科书,在叙述各种理论家观点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人的名字。这一点在内地如此,在香港、澳门更加如此。教科书中对于本土理论的吸收不足严重误导我们的青年学生。
比如,我们的语言教学,尤其对外汉语教学,用的是英语世界二语习得理论,几乎完全依赖。所有华人社会的学生,在国际数学和科学竞赛中的成绩都远远好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学生,但权威的数学科学教育理论观点却是西方的。就连我们在农村教育、特殊教育和迅速普及义务教育方面的成就让世界刮目相看,但做起学问来,依赖的理论框架几乎全是西方的。再次声明:不是西方理论方法不可用。相反,利用我们的经验,正好是对它们加以修正的机会,既发展了自己,又为世界学术发展作贡献。但由于头脑不知不觉间受他人控制,加上对自己社会的一知半解,导致我们的研究低质量,既缺乏实际效果,更谈不上国际影响力。这不仅是教育学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内地学界,我所供职的港大也是如此。
使得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从根本上区别于我们的古代社会,西方文化和价值已经进入到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等在内的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今天,西方知识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我国社会比作一个晶体球的话,对之加以解剖就会发现,其构成从里到外的每一部分都已经是充满中西内容。这一点在理论(theoretical)和方法(epistemological)两个方面,都对我们如何观察社会和从事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要求我们应特别谨慎地使用将中与西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思维。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学术界都没有对其加以关注。
当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看到,一方面是我们的社会和教育问题,另一方面是西方理论,而且只有相对较好的研究者才会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于不知不觉间将两者置于两端,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社会是中国式的,使用几乎完全建基于我国传统社会特征的理论总结,对我们当下的社会及其问题加以描绘和指代。殊不知,北京丰台区的任何一所小学语文教学,无论是在教材编写理念,还是其所推崇的教学方法和评价理念都已受到西方理论的深刻影响,与传统社会中的理念和做法,虽然不可言毫不相干,至少是已经大相径庭。丰台区如此,海淀区呢?清华附中和人大附中呢?
我再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曾几何时,华人学习者(the Chinese learner)研究风靡国际。这一研究本身的确是极好的选题,完全可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作出重大贡献。然而,它最后却不了了之。理论上没得出什么,对实践的影响也甚少。究其原因,就是研究者包括大量的华人和非华人,对华人社会的不了解,所以无法捕捉到真正的复杂状态。一讲到华人社会,就是儒(Confucian),看不到除儒之外,广而深的其他思想,如道和释,还有墨家、法家等。同时,各种思想又是在不断变化的。例如,儒家思想内部有不同派别,而且它们一直都在变化。所以生硬武断地讲华人学习者深受甚至仅仅受儒家文化影响,当然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不可能抓到问题的实质。
到此时此刻,这种关于华人学习者的文献仍在大量增长,尤其在西方校园之中。试想我们今天在海外念书的孩子,他们有多儒(Confucian)呢?而且文献中所讲的儒的特点多是依据我国古代社会而总结出来的,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这些特征并不准确甚至已经过时。根据这些特征来分析今天华人学习者的特色,是硬加在这些学生身上去的,不是他们真正的状况。实际上,这些孩子从小所受教育一直都是西式的,在主要内容上如此,在理念上更加如此。所以他们所受教育与西方孩子的教育虽然有区别,但没有那么大,更不是深受古代中国特点或儒家文化影响所致。这就是为什么那些研究挠不到痒处、缺乏针对性的原因。其对实践和理论都不能有所成就。
所以,那些口口声声谈中和西的人,往往是弄错了,至少是不尽妥当。可是,由于我国学术体系的规模很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自成体系。因此,有不少人几乎完全无视西方当代学术话语,闭门造车。殊不知其思想和理论仍是受西方控制,只是表面上表现得很“中国”而已。这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正是那些现在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学界和学人所乐意看到的。他们处于舒服的状态,不急于改变现状。简单而具体地讲,当代学者该如何走出困境?就是务必重视西方学术话语,但却不为其所左右。在熟悉西方话语的同时,加深、加快对自己社会的洞察了解。唯有此,才能真正做好中国教育研究工作者的本职工作,并因此而发展我们的理论和实践,从而增强我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进一步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
——评《批判教育学的当代困境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