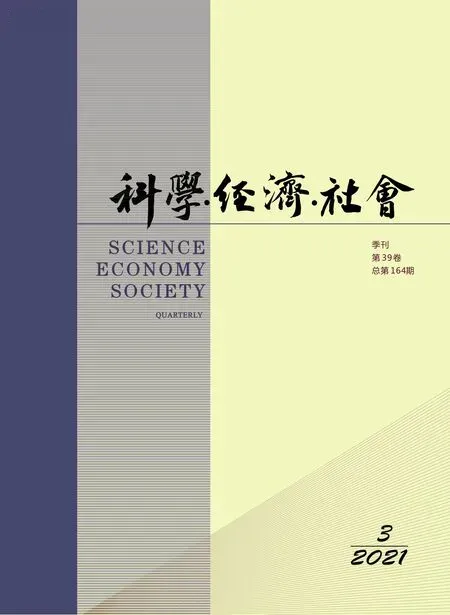跨越数字鸿沟 共享数字福利
——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进路
余 露
随着全球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加,“数字鸿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鸿沟之一,而且还在随着技术的持续加速进步而变得日趋尖锐。数字鸿沟让不平等扩展到数字领域,而且使得社会领域中本已存在的不平等以更加隐匿的形式发挥作用,带来了社会分裂的风险。如何跨越“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福利就成为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本文将细致厘清“数字鸿沟”,探究弥合数字鸿沟之赋能进路的实质和困境,进而引入一条全新的进路,即“差异进路”,让每一个体如其所是地进入到数字领域、成为其成员,真正实现数字福利的共享。
一、“数字鸿沟”及其风险
“数字鸿沟”(the Digital Divide),顾名思义就是指个体在数字领域存在的或表现出来的差异和隔阂。这一概念最早见于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一份研究报告,后来被诺里斯(Norris P.)、阿特维尔(Attewell P.)、范迪克(Van Dijk)等学者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并逐渐获得了更为丰富但精准的内涵。确切地说,“数字鸿沟”指人们基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在接受、获取、使用数据和技术的机会、倾向和能力上存在的差异。
“数字鸿沟”是个多维概念,它有着宽泛的含义,而且这些含义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发生动态的变化。首先,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数字鸿沟”会呈现出不同的含义和层次。当聚焦于差异的内容时,“数字鸿沟”可区分为“是否可及”“是否能用”“用到何种程度”三个层次。“是否可及”大致相当于阿特维尔所谓的“第一道鸿沟”①保罗·阿特维尔旗帜鲜明地区分了“第一道数字鸿沟:接入”和“第二道数字鸿沟:电脑使用”(Attewell,P.,“The First and Second Digital Divides”,Sociology of Education,2001,Vol.74,No.3,pp.252-259)。,它关注数字基础设施(网络、智能手机和电脑)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对个体可及(accessible)。不可及,既可能是因为缺乏网络连接或连接网络的设备,也可能是因为个体对技术缺乏兴趣或刻意保持距离②这受益于范迪克对于“精神接入”(mental access)和“物质接入”(material access)的区分(Dijk,V. J.,“A Framework for Digital Divide Research”,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2,Vol.12,pp.1-2)。。“是否能用”和“用到何种程度”都关乎阿特维尔的“第二道鸿沟”,即个体使用技术以及从技术中获益的能力。但“是否能用”更强调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而“用到何种程度”则更强调能力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它吸收了拉涅达(Massimo Ragnedda)的思想。在《第三道鸿沟:数字不平等的韦伯式分析进路》中,拉涅达将“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的离线回报”层面的差异称作“第三道鸿沟”,他旨在借此分析“谁从互联网中受惠最大”[1]15。“用到何种程度”仍强调个体数字能力的差异,但却将侧重点落在能力的实现上,这部分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机和电脑越来越智能,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越来越友好等),数字能力有无的界限很容易被打破,技术可及却完全缺乏使用和获益能力的个体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少。更为重要的是,“用到何种程度”才确实地彰显了数字领域的不平等,也让我们看到了赋能进路的不足(见第二部分)。
当关乎差异的范围时,“数字鸿沟”可区分为“全球鸿沟”“国内鸿沟”和“局部鸿沟”三个层次③这受益于诺里斯的讨论,他认为“数字鸿沟”包括全球鸿沟、社会鸿沟和民主鸿沟三个层次(Norris,P.,Digital Divide:Civic Engagement,Information Poverty and the Internet Worldw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tity Press,2001)。同时,这也受益于罗尔斯关于“全球正义”“国内正义”以及“局部正义”的讨论(Rawls,J.,Justice as Fairness:A Restatement,Kelly,E.(ed.),London: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1)。。“全球鸿沟”将视野放诸全球,探究发达国家或地区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数字领域的差异。“国内鸿沟”则以国家疆域为界,探讨一个国家内部“数字有产者”和“数字无产者”之间的差异。“局部鸿沟”则聚焦于国家内部的某一具体共同体或联合体,关心共同体或联合体内部成员因不同影响因素所呈现出的数字能力的差异,比如一个家庭中,老人可能因为年龄而在数字能力上处于劣势地位。
当探究差异产生的因素时,“数字鸿沟”则表现为“地区沟”“年龄沟”“性别沟”“城乡沟”“学历沟”等诸种形式。以“性别沟”为例,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Pérez)在《隐形的女性:揭露为男性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中指出,数字技术领域以男性数据为“默认设置”,严重缺乏女性的相关数据,使得女性处于一种“隐形”状态之中——她们的需求得不到或者得到较少的考虑,比如语音识别软件对女声的识别度远低于男声[2]。而2020年引起大众哗然、媒体和学界热议的“大连老人乘地铁被拒”事件则是“年龄沟”(“灰色数字鸿沟”)的实例。
其次,“数字鸿沟”是梯级的(scalar)而非离散的(discrete)概念。“数字鸿沟”彰显的并非是数字技术“可及”与“不可及”以及数字能力“拥有”与“缺失”之间的二分(进而导致的两极分化),而是强调接入和使用信息技术的不同程度的分级,这恰如道德哲学对于行为善恶的评价处于一条连续的、梯级的折线之上(至善的、较好的、好的、坏的、糟糕透顶的等)①这受益于梯级后果主义的讨论(Sinhababu, N.,“Scalar Consequentialism the Right Way”, Philosophical Studies,2018,No.175)。。我们可以对比如下情境: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在办公室随时利用高速网络获取信息、进行研究;中国某东部大学的学生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点外卖;中国某西部小镇的年轻夫妻偶尔在打印店老板的帮助下给子女下载并打印练习题;津巴布韦未受教育的且居住在贫困地区的老人没有数字设备,难以接触、获取数字信息。即便如第四类情境,一切不利条件使得其中的个体成为了四种情境的最不利者,甚至典型的“数字弃儿”,但他/她仍具备极大的可能性进入到数字领域,虽只是“边缘人”而已。前三类情境更是鲜明地展示了“数字鸿沟”的“梯级性”,这也正是上文区分“是否能用”与“用到何种程度”的重要理由。
无论从何种维度来理解“数字鸿沟”,它都展示了个体在数字领域的差异,这些差异让不平等以全新的形式、在全新的领域展开,又加深了传统的不平等,不仅对数字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也对社会领域产生了负面影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正如肖恩·杜布拉瓦茨(Shawn DuBravac)所言,“数字鸿沟这个词描述的是技术产品使用者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身边的事物数字化,而且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数字鸿沟的风险和影响也随之提高。”[3]99
首先,数字鸿沟让不平等进入到数字领域,阻碍个体的发展、甚至威胁个体的生存。缺乏或有限的数字技术接入以及从使用数字技术中获取利益的能力和技能,都会将一部分人排除在数字领域之外,让他们成为“数字弃儿”或“数字边缘人”。但在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接入、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对于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它关联着绝大多数的经济机会,也是人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必要手段。数字弃儿或边缘人因无法获取经济机会而将处于越来越弱势的地位,且不说大数据时代的“经济蓝海领域”都与数字技术紧密关联,就连普通的就业机会都对数字技能有基本的要求。同时,随着实体社交网络遭到虚拟社交平台的冲击,数字边缘人可能会因无法进入到文化生活中而遭遇情感危机和精神伤害。极端情况下,数字弃儿甚至面临着生存的危机。罗杰森(Simon Rogerson)指出,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间,有人极可能因缺乏数字接入而得不到关于疫情的及时通知,让自己的生命陷入危险当中[4]。
其次,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不平等,并使其以一种隐匿的形式发挥着作用。那些本来就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体,由于数字技术不可及或在数字领域较为弱势的地位,在大数据时代将遭受进一步的歧视。以“性别鸿沟”为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女性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范围溢出婚姻、家庭和职场,人脸识别、智能招聘、金融授信等数字领域的场景“皆存在广泛的算法性别歧视案例,性别不平等已经深入到了各类算法系统之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社会性别观念也已经演化成算法的内在机制,不仅放大了人的歧视,而且固化为体制化和规范化的机器秩序,还有可能产生变异,造成新的不平等。”[5]
再次,数字鸿沟使得数字领域的不平等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交叠在一起,形成恶性循环,带来了社会分裂的风险。我们的线上行为只是更广的社会角色、兴趣、期待和看法的延展,社会领域中关于性别、城乡、地区、种族等的刻板印象会以更加夸张的方式在数字领域得到增强,比如,2015 年谷歌的自动识别系统将黑人程序员的自拍照贴上了“大猩猩”的标签。更糟糕的是,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会以隐秘的形式体现在数字领域,“技术被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人们认识到,社会群体可能会朝着自己的目的塑造技术,而不是由技术的特性决定使用和结果。”[6]50算法歧视便是明证。社会领域的不平等进入数字领域,并在技术的影响下进一步延展、深化甚至变异,使得一部分弱势群体生存环境更为艰难,让社会陷入承诺压力过大的风险之中,进而使得社会合作危机重重。依罗尔斯之见,面对承诺压力过大的情况,人们往往会做出两种方式的反应:一是变得愤愤不平,并在必要时候采取暴力行动去反抗;二是同社会日渐疏离,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离群索居、愤世嫉俗[7]128。为了避免出现承诺压力过大的情形,我们必须尽力弥合数字鸿沟、减少数字领域的不平等,凝聚社会共识,维持社会稳定。
二、赋能进路及其困境
数字鸿沟是个体在接入、使用数字技术以及从中获益的能力方面的差异,据调研发现,这些差异实际上是由数字技术的使用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优劣位置所导致的。数字领域的不平等与社会领域的不平等交叠在一起,“数字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差异意义上的不平等,同时,它也彰显着个体背后的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比如资源的分配、获取和使用技术的机会、训练数字技能的成本等。”[8]
基于此种认识,现有试图弥合数字鸿沟的努力都采取了赋能进路,致力于培育越来越多合格的“数据或技术的使用者”。大体而言,这一进路有两方面的举措。一是,主张国家和社会发挥作用,努力减少接入层面的物质差异。这一举措实则是各国的共识,我国就一直致力于推进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全覆盖以及互联网普惠,实行网络扶贫行动。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我国“贫困地区通信‘最后一公里’被打通,截至2020 年11 月,贫困村通光纤比例达98%”[9]。二是,强调数字教育的功效,鼓励社会和家庭对个体进行数字技能培训,让个体获得或提升使用数字技术的动机和能力。以“灰色数字鸿沟”为例,中外学者无一例外地强调“数字反哺”。尼克尔等人在调研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后,强调无论老年人身处何种环境之中,“都必须有机会学习使用互联网,并被教授这些技能。”[10]而面对“大连老人乘地铁被拒”事件,我国学者也纷纷呼吁要给予老年人技术操作层面的指导以及情感层面的鼓励。
究其根本,赋能进路就是要赋予每个个体以“数字身份”——“数据或技术使用者”,让个体能够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到数字领域,进而减弱社会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对数字领域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平等承认政治之普遍主义进路在数字领域的体现。
普遍主义政治(a politics of universalism)是现代政治的典型形式,它强调所有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以及相应的平等资格和权利。普遍主义政治主张赋予个体平等的公民地位及与其相称的对待,决不允许出现二等公民,无论是缺乏公民权和选举权的情况,还是因为经济的贫困导致大部分公民权无法践行的情况。普遍主义政治“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它完全‘无视’公民间的差异”[11]38-39。
正如普遍主义政治赋予个体以平等的公民身份,赋能进路试图赋予个体以平等的“数字身份”,主张所有个体都可以成为合格的“数据或技术的使用者”,都应该享有接入、获取、使用数据的平等资格和权利。这一进路致力于让每个个体都有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公平机会”,数字领域的“形式平等”得以实现。“截至2020 年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 亿,较2020年3 月增长8 540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较2020 年3 月提升5.9 个百分点。”[9]我国网民数量的持续增长以及互联网的日渐普及,至少表明“第一道鸿沟”正在弥合、“第二道鸿沟”也具有了弥合的可能性。
但是,赋能进路也不可避免地遭遇了普遍主义政治的困境。泰勒指出,普遍主义政治至少会遭遇两类指责。一是无视差异就无法让公民那些现实的身份认同的价值得到承认。将所有人视作无差别的公民,是将“人们强行纳入到……虚假的同质性模式之中,从而否认了他们独特的认同”。二是无视差异也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它实质只是一种冒充普遍主义的特殊的文化霸权,“其结果是只有少数民族的文化或受压抑的文化被迫采取异化的形式”,因而,普遍主义政治并不能达成其反对歧视的目的,却只是让歧视以含蓄的和无意识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11]43。
赋能进路试图通过减少接入差异、激励使用动机、培养获取能力等举措,赋予每个个体无差别的“数字身份”。但是,“数字身份”可能只是“虚假的同质性模式”,给予个体无差别的“数字身份”并不会实质性地确保个体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时处于平等的地位,更无法保证个体能从数字技术的使用中获得相同程度的利益。最新研究表明,宗教和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数据或技术使用者”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接入互联网并不能确保自由和权利的多样性。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文化和宗教限制会不断地影响他对互联网的使用”[12]。
更糟糕的是,赋能进路片面地强调个体作为“数据或技术的使用者”这一数字身份,忽视了个体独特的身份认同,这掩盖了技术背后隐藏的价值设定和价值偏见,使得数字霸权以一种隐匿的方式悄然发生作用。“‘数字身份’平等一方面导致了‘自然人身份’无差别化,人在算法权力下失去了差异平等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身份’预定的背后嵌入了身份设计者的价值立场,设计者的立场歧视造成了算法对人的歧视……‘数字身份’的算法预定……以一种隐而不显的数字特权让公民走上‘数字驯化’的道路,损害了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13]上文所提及的“性别鸿沟”便是明证。由于缺乏足够的女性数据,女性的需求和渴望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在数字领域得以体现,女性在数字领域便只得时时、处处处于被歧视状态中。让女性削足适履地充当“数据或技术的使用者”,只会加深社会中本已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
三、差异进路:基于身份认同的算法
赋能进路赋予个体接入和使用数字技术的公平机会,确保了数字领域的形式平等,但它并不能实质性地保证个体在数字领域的平等,尤其无法确保个体能从数字技术的使用中同等获益。换言之,赋能进路能很好地处理“是否可及”层次的数字鸿沟,较好地应对“是否能用”层次的数字鸿沟,对“用到何种程度”层次的数字鸿沟却无能为力。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节所分析的困境外,还因为赋能进路忽视了数字鸿沟的“梯级性”。赋能进路采取了一种二元框架,着眼于数字技术的“可及与不可及”和数字能力的“拥有与缺失”之二分,故而无法解决必须敏感于梯级性的程度层次的数字鸿沟。
为了更好地弥合数字鸿沟,我们引入差异进路。据泰勒所言,现代平等承认的政治还有另一条进路,即差异政治(a politics of difference)。在差异政治看来,每个人需要被承认的恰恰是作为个体或作为群体所拥有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是他们与其他人相区别的独特性。差异政治同样反对歧视,但却认为歧视的根源在于:特定的或个体化的特质被淹没于一种“虚构的同质性模式”之中。因而,差异政治主张:要想真正地实现平等,就必须要求“以公民彼此之间的差异为基础对他们区别对待”[11]38-39。具体而言,个体应该得到两方面的承认:一是本真性承认(anthenticity-recognition),即个体被允许如其所是地生活;二是价值承认(worth-recognition),即个体受到同伴的重视和尊敬,他们的存在受到欢迎而不是谴责,他们的贡献受到赞赏而不是贬低。
采用差异进路来弥合“数字鸿沟”、实现个体在数字领域的平等,就要求我们不再仅仅将个体视作抽象的“数据或技术的使用者”,而是要让每个个体如其所是地在数字领域得到承认,他们的独特的身份认同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期待、欲望和需求都能在数字领域得到尊重和满足。首先,这要求算法设计者在进行算法设计时要虑及诸身份认同,如地域、年龄、性别、学历等,不仅在设计参数时增加敏感于诸身份认同的参数,也在数据收集和采样测试时抽取和采纳更广泛、更具代表性的数据和样本。换言之,差异进路不再要求个体将自我塑造成“数字身份”所要求的样子,而是让数字领域容纳生活中的诸身份认同。
其次,差异进路不仅仅停留在孤立地考虑数字鸿沟的单一方面,而是将其置于一种多元主义的框架之中,以多维视角去看待并处理数字鸿沟。在差异进路看来,数字鸿沟是由于各因素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导致的,正如特苏里亚(Ruth Tsuria)所看到的那样,性别鸿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影响[12]。因而,应对数字鸿沟也应该采取多维视角:我们应该假设任一身份认同在数字领域都具有价值、都应该被虑及,但同时承认并非所有的身份认同在任何情境中都具有与其他身份认同平等的价值。
最后,需要做几点澄清。第一,平等的承认是基础,无论是赋能进路还是差异进路,都是为了在数字领域实现平等。差异进路只是不满足于抽象的“数字身份”的平等,而强调诸特殊的身份认同也应以参数的形式进入到数字领域之中,让我们特定的和个体化的特质不被抽象的共性所掩盖而得到平等的承认。差异进路敏感于数字鸿沟的梯级性,希望将平等切实地落到实处。
第二,差异进路假设诸身份认同都有价值、都应该被纳入算法设计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诸身份认同事实上在所有情境中都被纳入或被同等对待。诸身份认同是否事实上被设定为影响参数或者被予以多大的权重因技术所涉领域、情境而定。
第三,差异进路较之赋能进路确实会增加算法设计以及数据收集等的负担,但这些负担并不会让人不堪重负。而且,相较于赋能进路所遭遇的困境,这些负担是可以承受之轻。
具体而言,依据差异进路,为弥合数字鸿沟,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着力。第一,倡导数字技术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设备、服务等数字援助,使各国共享数字时代红利。第二,在我国,分级分类、因地制宜地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和数字乡村建设,健全多层次的数字保障体系,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比如,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网普惠工作,实现“处处都可联网络”“人人皆可为网民”;建设公共数字终端(类似于公用电话),实现数字终端共享;敏感于多元的宗教、文化背景,普及学校数字技能义务教育,加强社会数字技能公共培训(免费或廉价的数字扫盲等),激励公民数字动机、提升公民数字素养。第三,加快信息无障碍建设,倡导设计者在进行算法设计时因情境增设敏感于诸身份认同的参数,特别是关乎民生的终端设计,强制要求其收集多元的数据、测试代表不同身份认同的样本,提升数字技术终端的易用性和可普及性,减少“数字边缘人”、消除“数字弃儿”,让全民共享数字生活。第四,倡导互助、共享精神,发挥公共服务机构、社区、家庭等的积极作用。比如,支持高水平公共服务机构对接基层、边远和欠发达地区,扩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辐射覆盖范围;鼓励社区和家庭“数字反哺”,在社区设置“老年人数字服务中心”,将家庭“数字反哺”纳入中小学实践课程等。
总而言之,基于身份认同的差异进路敏感于数字鸿沟的梯级属性,夯实了赋能的背景框架,使得由赋能进路赋予的“公平机会”落到实处,有望跨越三道数字鸿沟,实现数字福利的共享,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