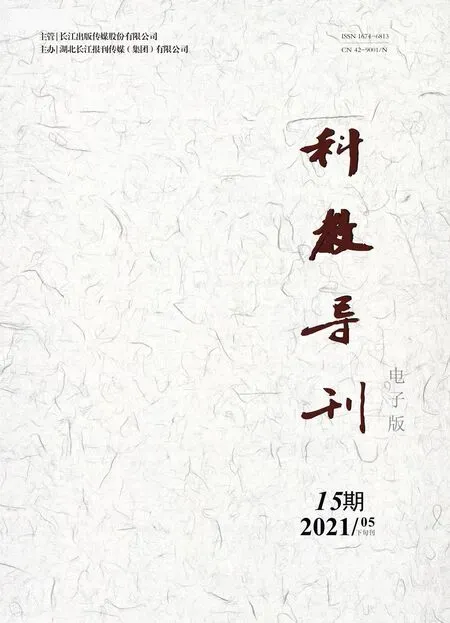透过母女关系分析《神谕女士》中的女性主体性
阎聆萱
(太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西·太原 030024)
《神谕女士》是加拿大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先前的研究大多在论证琼如何通过写作展现女性主体性,但琼的女性主体性不仅体现在写作中,还表现在她扮演女儿、妻子和情人等女性性别角色时。如果将性别角色看作性别操演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复行为,那么琼故意错误地重复这些性别角色的行为就体现了她的主体性和对性别角色禁锢的抵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操演理论适合用来探讨琼的女性主体性。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是通过重复和征引一系列性别规范的程式化行为而形成,性别主体是强制性重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性别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虚构的、脆弱的社会建构,性别角色行为在重复过程中有时会偏离原来的规则,使得反抗原有的性别角色成为可能。参考性别操演理论,本文透过母女关系,分析了琼如何反叛性地操演女性角色,展现其女性主体性。
母女关系一直是最私密和最具建设性的女性关系,母女关系的主题在女性主义文学与批评中具有重要意义。南希·科多罗认为母亲和女儿保持“原始的自恋型母婴联结”,母亲将女儿视为她的“分身”或“延续”,但是女儿在前俄狄浦斯情结结束后会从认同并依赖母亲,转而不断努力寻求和母亲的差异性和个性。
小说中琼不认同母亲灌输的女性身材、着装、言行等规范,通过颠覆性地演绎母亲及母亲所代表的父权社会规定的女性角色,彰显了自身的主体性。母女间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琼的外表,二是爱情和婚姻。琼早期将肥胖看作天赋和个性,母亲却厌恶肥胖,要求女儿减肥,变成男人眼中迷人的女性。对于婚姻和爱情,琼推崇楼姨妈自由浪漫的爱情,不为结婚而结婚;而母亲把婚姻看作终生唯一的事业,囿于家务和生儿育女,却所托非人。通过反思母亲和楼姨妈的爱情和婚姻,琼将身材和婚姻,女人的终身事业和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分割开,冲破了刻板女性角色的束缚,伸张了女性主体性。
1 身体争夺战
琼和母亲对女性美的认知迥异。母亲认为美丽的女性应该是苗条娇弱的,符合男性审美。她用苗条娇弱著称的女明星的名字命名女儿,对琼肥胖的身材、饮食习惯冷嘲热讽,企图通过把女儿送到舞蹈学校改变她,这些都体现了母亲将父权社会物化女性的思想内化为自己的言行,过分强调女性形体美,将苗条身材与美好婚姻画上等号,将女性看作婚姻市场上的商品。
身材纤瘦也有“无能”的内涵,女性纤瘦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男强女弱的刻板印象,强化了女性服从于男性的弱势地位。母亲始终保持纤瘦的身材,将婚姻看作生命的全部,屈从于丈夫,辞职在家囿于家务和养育儿女。但在丈夫看来,和男性有价值产出的社会工作相比,她的付出微不足道。母亲不仅没得到丈夫和女儿的爱和感激,反而强化了她在家中的弱势从属地位,最终在“没有出口的坟墓”中悲惨去世。
母亲不仅是男权思想的受害者,还是男权思想的捍卫者和监察员。为了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身材的要求,女性的身体一直“被规范或者被惩罚”,而规范或惩罚女性的人往往是女性自己,通过自我监督和监督他人,进一步强化了男权社会的规则。一方面,保持着纤瘦的身材,扮演“屋中天使”或者“田螺姑娘”的角色,终其一生严格要求和监督自己符合男权社会的审美。另一方面,母亲时刻监督女儿,要求女儿符合男权社会的规则。琼的肥胖违反了规则,母亲就严厉地惩罚她,不仅剥夺了女儿梦想的角色,还拒绝和琼亲近。这些对琼身体上的惩罚,也是在向琼灌输男权社会的女性行为准则。
然而琼认为肥胖是与生俱来的,赋予她一种身份认同感。琼崇拜楼姨妈,信奉18世纪“肉是美德”的美学,认为“女性的根本特征”即“软绵绵、肉乎乎、毛茸茸的一堆肉”。受到楼姨妈的启发,琼梦想成为一名歌剧歌手,肥胖但“受到爱戴和赞美”。
审美冲突引发了对琼的身体这块“争议领土”的争夺。实际上,正如卡罗尔·安·豪威尔所说,小说中有丰富的描述性段落,将她的身体详述为具象的文字,是阿特伍德作品中主张女性主体性的话语领域,重写她的身体有两种主要方法:改变身材和穿衣打扮。
琼疯狂进食,是以胖为美理念的外化,也是宣告自己对身体的主权。琼上演了“反叛时装秀”,庞大的身体故意在母亲眼前招摇。对传统时装秀的戏仿颇具说服力,彰显了琼对女性肉体美的认知,反抗了男权社会消费女性的文化。苗条的身材隐含着脆弱和女性对男性的屈从,琼大而强壮的身体则象征着力量,是击败母亲和她代表的男权势力的“唯一力量”:“我像面团一样站起来,身体在餐桌上一步步朝她(母亲)前进,至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战无不胜的。”不断膨胀的身体被比喻成危险而强大的生物,这表明琼的力量不断增强,自我主体意识越来越强。
琼还通过穿衣打扮来重写身体。琼穿着奇异艳丽的衣服,显得更加肥硕,自己也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她拒绝按照“女性化的模样”穿上制服或戏服,因为亦步亦趋会摧毁女性自主性:“为了不破坏妆容,女孩们都靠着墙站,像庙里的贡品一样一动不动”。将“女孩们”比作“庙里的贡品”,隐喻女孩在男权社会被物化,女孩自己也被男权社会的规则洗脑,自主性被牺牲却全然不知。琼拒绝穿这些服装,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身体免受父权思想的束缚,把握了身体的自主权。
后期琼减肥也是在改写身体,摆脱母亲控制。琼继承了楼姨妈给的“逃跑遗产”,但肥胖阻碍了逃跑进度:“我的大腿是巨大臃肿的,像患病的肢体,像丛林中的土著,又像无边的草原一样蔓延开来……”。琼的大腿被拟人化为令人生畏的“丛林土著”,这表明肥胖拖延了出逃计划,威胁着琼对身体的支配权。通过减肥,琼重塑了身体,而身体作为语域,也被重写,宣告琼获得了身体的支配权,增强了她的自主意识。
2 迥异的婚姻爱情观
琼和母亲的婚姻观分歧很大。母亲终其一生都在为获得并维持婚姻而挣扎,将好外表和好婚姻画等号,节食、化妆、打扮都只为了取悦男性。母亲婚姻不幸,但她认为失婚的楼姨妈更加可怜,并把她当作反面教材来教育琼。
母亲在婚姻“事业”中“富有进取心和野心”,渴望成为权倾一时的波吉尼亚人,但只能在家里施展权术,不仅把持家务,还试图控制丈夫和女儿。书中将两个靠垫比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仪式性物品”,体现了母亲对家务的绝对神圣主权。琼和她父亲的脚被物化为家具,不得不被母亲遮盖,防止破坏她的领地。
母亲的婚姻不幸福,虽然她深谋远虑地为丈夫选择职业,并为了让丈夫专心工作,独自承担了养育孩子的责任,但是丈夫不感激也不爱她,因为他们的婚姻是意外怀孕促成的,丈夫并非真心,也反感妻子的控制欲。夫妻合照中的丈夫尴尬而不悦,妻子却像拴狗的皮带一样紧紧抱着丈夫。“皮带”象征着琼母亲对丈夫的依赖和控制。无爱婚姻的另一个证据是琼母亲将合照中丈夫的头剪掉了,这象征性的死刑显示出琼母亲对丈夫的愤恨。母亲把女儿当作自己“生命的延伸”和“分身”,竭力控制着她“最后可控制的东西”,希望将琼塑造成男人眼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然而琼对性别角色有不同的理解,她通过改变身体的胖瘦,操练自己理解的性别角色,在爱情、婚姻和职业中反叛地诠释着自己的自主性。
琼的婚姻观深受楼姨妈影响,希望像楼姨妈一样独立自由,拥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楼姨妈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她喜欢拿自己开玩笑,但有时玩笑让她窒息”。笑话(joke)和窒息(choke)押韵,暗示了楼姨妈开朗外表下掩藏着悲伤,不幸但坚毅。楼姨妈在丈夫失踪后重新获得娘家的姓氏,象征她重新获得了独立女性的身份,后来成为优秀的公关负责人,经济独立并获得社会认可。琼崇拜楼姨妈,借用她的名字写小说,以此获得新身份,摆脱婚姻的束缚,获得经济独立并彰显女性自主性。
楼姨妈认为身材与婚姻爱情无关。她对肥胖的身材很满意,穿上奢华浮夸的礼服愈显膨胀,自信会有追求者“拜倒在脚下”。“拜倒在脚下”一反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优越地位,女性成为主导。楼姨妈和罗伯特的浪漫爱情也印证了身材和婚姻爱情无关。罗伯特爱楼姨妈,把楼姨妈看作“华丽的日落”,“似乎在不断扩大,温暖充满了整个房间”。 因为楼姨妈的鼓励,琼坚定了她对肉体美和女性角色概念的信心,勇敢寻求真爱。
害怕重蹈母亲的悲惨婚姻,琼拒绝被怀孕和家庭生活束缚。波伏娃认为,怀孕仅仅对已婚女性来说是光荣的,未婚先孕是禁忌和一生的阴影。母亲未婚先孕,为了挽救自己的名誉,只能与不爱她的德拉库特先生结婚,这引发了随后的悲剧。病态的母女关系使琼不愿生孩子,因为这可能重现她与母亲间紧张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琼刻意地把家务做得很糟糕,避免被妻子这个性别角色束缚住。例如,她做饭一塌糊涂,一反女性善烹调、女性服从丈夫的性别角色定位。
简而言之,琼的母亲是女性,但她的思想和行为表明她实际上是一位代理父亲,她的所思所为反映了19世纪男权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琼和母亲作对抗,颠覆性地诠释女性角色,实际上是在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刻板设定作斗争,揭示了社会性别角色、男权意识形态的虚构性,凸显了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