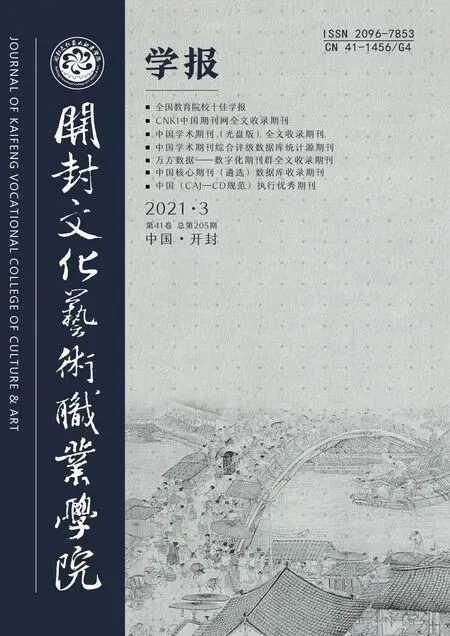我国非婚同居制度的走向探析
彭雨婷
(安徽大学 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非婚同居的语义明晰
非婚同居虽与婚姻相伴而生,但时至今日,学界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概念。有学者认为,非婚同居是包含未婚同居、不婚同居、婚前同居等各类同居关系在内的集合体[1]。也有不少学者分别从同居关系是否具有违法性、同居者的性别是否为异性等方面来试图明确非婚同居的内涵。
我国2020 年5 月28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继承了婚姻法中的传统做法,明确规定有配偶者不得与他人同居,构成重婚罪的还应接受严厉的刑事处罚。所以,在性质上,应把非婚同居和非法同居区分开来。合法性,即不得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非婚同居的应有之义。
至于同居者的性别是否限定为异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就我国而言,我国实行的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如荷兰、挪威、德国等,都已经允许同性恋者缔结同性婚姻或者登记注册为同居伴侣关系,并对其权利和义务作出法律规定。若将非婚同居的性别限定为异性,难免与世界发展趋势相脱离,也不利于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因同性伴侣同居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同居者的主观方面,是否具有婚意不应成为判断是否属于非婚同居的标准之一。无论是否以结婚为目的,只要同居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都应判断为非婚同居关系。此处的“非婚”是区别于法律婚姻之外的各种同居关系的集合,而非是主观上的“不婚”。况且,如何判断同居者的主观目的一直都是法律上的技术难题。若将“无婚意”增加为非婚同居的内涵,不仅会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和不统一,而且会增加司法实践的成本,加剧司法资源的紧张。
除以上方面外,非婚同居还应是双方共同生活且持续达到一定期间。其一,双方共同生活不仅仅需要形式上住在一起,更需要在精神、性以及经济等方面形成实质的结合。其二,同居者共同生活必须具有持续性。只有持续地共同生活在一起,才会形成较为稳固的社会关系,也才会对同居双方和其他人产生较为深重的社会影响。其三,同居者共同生活须达到一定期间。非婚同居的时间越长,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越稳固,也才越利于法律调整同居双方权利和义务作用的发挥。
根据上述分析,非婚同居应为双方持续生活达一定期间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所形成的共同生活体 。至于同居者的性别以及主观目的,则不在非婚同居的外延之内。
二、我国非婚同居关系法律现状
(一)对未婚同居的立法态度不明
我国对未婚同居的法律规制史也是立法对事实婚姻整体态度的变化史。从第一阶段对事实婚姻的绝对承认,到第二阶段有条件的承认,再到第三阶段的绝对不承认,以及第四阶段的放宽缓和,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在对待事实婚姻这一问题上的纠结与反复。
(二)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调整未婚同居关系仍然是以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和1989 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不与新法相抵触的内容作为法律依据。不仅法律规范缺失,而且作为法律依据的司法解释和1989 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条文内容也非常少。这对于引导和规范社会实践中日益纷繁复杂的非婚同居关系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是远远不够的。
(三)法律所调整的非婚同居关系范围有限
从前文所述的非婚同居制度的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法律所调整的对象都是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非婚同居关系。至于实践中,不以夫妻名义生活的非婚同居关系、同性伴侣组成的非婚同居关系都被法律排斥在门外。它们既不被法律所调整,也不被法律所保护。
(四)法律对非婚同居伴侣规定的权利和保护较少
就人身关系而言,我国目前还没有将不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的非婚同居和同性非婚同居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也就没有在立法上认可他们到底具有何种人身关系。而在财产关系方面,仅规定同居期间的财产为一般共有,但未明确此种共有的性质。在同居财产与第三人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时,如何进行处理,法律也没有提及。此外,非婚同居中的弱势群体也缺少法律的关怀与保护。照顾妇女和儿童的原则,在缺少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只能被束之高阁。而且,在同居关系解除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的归属,仍是以父母的利益为着眼点的,并没有遵循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三、我国非婚同居制度的走向
(一)积极规制的立法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事实婚姻以外的非婚同居比例升高。究其原因,有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有对结婚和离婚经济压力过大的无奈和妥协。但不论何种原因,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是——非婚同居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法律进行引导和调整。我国应该摒弃过去对未婚同居暧昧不明的立法态度,从“不保护”“不干预”的消极漠视型转为承认和限制并举的积极规制型。
(二)区别于婚姻的立法模式
通过考察和分析西方国家在非婚同居方面的四种立法模式,并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区别于婚姻的立法模式相比来说更为合适。一方面,当事人选择非婚同居,无论基于何种理由,都有追求一种不同于婚姻的生活模式的意思在内;另一方面,法律将非婚同居与婚姻区别对待,也能更好地保障我国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也正是基于此种理由,法律在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规制时不应以进行登记为要件。
(三)具体制度的设计与考量
1.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对非婚同居进行专门立法时,为了保障当事人选择不同于婚姻生活模式的充分自由,应以同居协议的优先适用为原则,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自行安排生活中的大小事务。同时,为了保护同居生活中的弱势群体,法律应规定公平原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救济和平衡,以及未成年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子女抚养权的归属[2]。
2.非婚同居形成的条件
在确定法律所调整和保护的非婚同居的范围时,可对同居主体、共同生活的期间等设定条件,规定符合条件的未婚同居才能受到法律的调整和保护[3]。例如,规定同居主体须为两个已达法定婚龄且不存在法律禁止的血缘关系的人,双方共同生活须达一定期间;也可规定,符合前述条件的双方在持续共同生活5 年后,非婚同居关系成立。同时,考虑到在育有非婚同居子女的情况下,这一时间段的要求可适当缩短至2 年或3 年。
3.对非婚同居者的权利和保护
就人身权利而言,应包括非婚同居者之间的同居和忠实义务以及不能育有子女的非婚同居家庭收养孩子的权利等[4]。而财产方面,优先适用同居协议中有关财产的约定,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基于区别于婚姻的立法模式,可适用分别财产制。在解除非婚同居关系时,对家庭事务承担较多的一方,可从对方财产中获得补助。基于非婚同居者不具有法定继承人中的配偶身份,所以在非婚同居者一方死亡后,为了保护另一方的合法权利,法律可规定先析产,然后再分割被继承人的遗产,对共同居住的住宅和生活用品,另一方同居者可优先购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