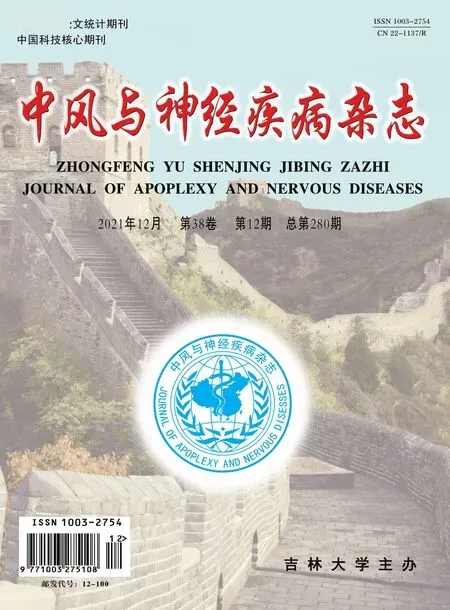隐源性卒中的病因综述
张美娟综述, 展淑琴审校
根据当前国际广泛使用的TOAST(trial of org 10172 in acute stroke treatment)分型将隐源性卒中(cryptogenic stroke,CS)定义为:经广泛的血管、血清学和心脏评估后,未归因于动脉硬化、小血管疾病或心脏栓塞的缺血性脑卒中,占所有缺血性脑卒中的20%~30%。随着医学检查技术的进步,隐源性卒中(cryptogenic stroke,CS)发病机制逐步明确。尽可能的明确脑卒中的发病原因,对于预防卒中再发,制定个体化二级预防方案极为关键。CS存在多种病因,本文就隐源性卒中的主要发病机制进行以下综述。
1 反常栓塞(paradoxical embolic,PE)与CS
PE又称矛盾性栓塞,是指静脉系统和右心房的血栓,通过心脏内的异常交通从右心系统进入左心系统,造成大循环的动脉栓塞。研究显示,PE可能是CS的发病机制之一,包括:卵圆孔未闭(patent foramen ovale,PFO)、房间隔瘤(atrial septal aneurysm,ASA)和肺动静脉畸形(pulmonary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PAVM)。
1.1 PFO 卵圆孔是胚胎时期循环血流的生理性通道,通常在出生后融合关闭,少数人出生1 y后仍未正常关闭者则称为PFO。PE中最常见的是PFO。既往研究表明,在成年人群中PFO的患病率是20%~25%[1],而在CS中PFO的患病率为40%~50%,CS患者年龄越大,心脑血管疾病危险风险越多,PFO所致脑卒中的风险就越低,因此在CS患者发现的PFO,可能是偶然的,也有可能是与卒中相关的,对此已开发出一种反常栓塞风险(RoPE)评分来估计PFO是CS的原因是与卒中相关还是偶然发现,但其指导治疗的潜力还需进一步探索[2]。PFO导致卒中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普遍公认的是“PE”[3]。当右心房压力大于左房时(如Valsalva动作,肺动脉高压),血液可出现右向左分流,右心系统栓子进入脑动脉形成栓塞,导致脑卒中,根据既往回顾性研究,PFO相关卒中主要累及皮质[4]。如上所述,由于年龄较大患者,较多的基础风险减弱了PFO在卒中的风险,因此对于55岁以上,没有通过长期心电监测来排除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的患者,将CS归因于PFO的结论可能是不可靠的[5]。
1.2 房间隔瘤(atrial septal aneurysm,ASA) 是指房间隔局部或整体呈瘤样凸向一侧心房的心脏结构异常畸形。在一项多中心研究中,接受PFO封堵的患者中有30%~40%检测到ASA[6],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访研究提示,PFO和ASA的存在是卒中再发风险增加的重要预测因子,且ASA的存在增加了PFO相关卒中的再发风险[7]。另一项研究提示,中到重度ASA可能与PFO患者的左房功能障碍有关,可产生“心房颤动(AF)样”的病理机制,进一步增加心源性血栓的风险[8,9]。另一项电生理学研究发现,伴有房间隔异常的年轻卒中患者心房易损性增加[9]。
1.3 肺动静脉畸形(pulmonary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PAVM) 是一种罕见的肺部疾病,为肺动脉和肺静脉之间的异常连接结构,形成了病理性肺内从右到左异常分流通道。这种异常损害了静脉血的常规气体交换和过滤,也被称为肺动静脉瘘和肺血管瘤。这些损伤最初由Churton在1897年描述,后来在1938年被确定与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HHT)相关[10]。一项阿根廷横断面研究表明,25%的PAVM患者有肺部症状,高达20%的患者出现栓塞并发症,是由通过PAVM的PE引起的。显著的PAVM、肺部症状和栓塞并发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11]。
2 心房颤动与CS
心房颤动(atrial fibrillation,AF):AF是缺血性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可使缺血性脑卒中的风险增加5倍[12]。根据TOAST分型,心源性卒中占所有脑卒中约25%。最新数据显示,许多CS其实是由阵发性心房颤动(paroxysmal atrial fibrillation,PAF)引起的。有研究对大血管闭塞卒中患者行血栓摘除术,并进行血栓分析表明,心源性和非心源性卒中患者的血栓成分有显著差异,但是CS与心源性卒中在血栓组织学方面却有很强的重叠性。这些发现有力地表明,CS患者的栓塞源很大可能来源于心脏[13]。另一项基因表达研究中估计心源性栓塞占CS的58%[14],但在CRYSTAL AF研究中,即使将心电监测的时间延长至3 y,AF的检出率仍只接近约1/3[15],说明心源性因素在CS中所占的比重被低估。ASSERT研究纳入了2580例年龄>65岁,且置入心脏器械的高血压病患者,这些患者既往无心房扑动或AF且未口服抗凝药,在对其进行长期心电监测,发现该试验中发生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约51%可以归因于AF。但是值得注意的是,ASSERT的后续研究发现,亚临床AF的诊断与栓塞性脑卒中事件无明显相关性,PAF的诊断并不能提供一个导致CS的确切病原学机制,该结论提示PAF可能只是促使卒中发生的众多危险因素中的其中一个,它与卒中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更为复杂的间接机制[16],具体的发病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 主动脉粥样硬化(aortic arch atheroma,AAA)与CS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大动脉慢性炎症性疾病,其特征是脂质在血管壁积聚并形成纤维组织。斑块主要成分:钙化、脂核、斑块内出血(IPH)和纤维组织。易损斑块定义为含有斑块内出血区域和/或脂核的斑块[17]。斑块内出血(IPH)在有症状和无症状颈动脉狭窄的患者中均很常见,与任何已知的临床危险因素相比,IPH是卒中一个强有力和独立的预测因子[18]。升主动脉及主动脉弓部近端易损斑块脱落可随着前向血流进入头臂干、左颈总动脉及左锁骨下动脉,导致相应脑供血发生栓塞事件,因此与CS密切相关。有研究发现,降主动脉和主动脉弓远端存在逆行血流,斑块脱落的栓子随逆行血流可到达所有主动脉上的动脉,且左锁骨下动脉邻近出口的血流返流比远端头臂干的更常见,后循环受到的影响更大[19]。与简单测量管腔狭窄相比,提供斑块易损性信息的诊断对于疾病预后诊断更为重要。磁共振影像学检查(MRI)目前被公认为颈动脉斑块负荷量化和斑块成分无创评估的最佳成像手段[20]。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检查(transesophageal echocardiography,TEE)是诊断主动脉粥样硬化的金标准,可以清晰地探查有无斑块、斑块厚度、成分及是否为易损斑块。所以临床中当颈内动脉狭窄>50%时,特别是当脑梗死的定位与狭窄的一侧不一致时,建议用TEE来排除复杂的主动脉斑块是否为脑栓塞的高危来源,因为TEE检测到主动脉血栓可能会改变二级预防策略。总之,临床上对于中老年的CS患者,经超声、影像学、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均未发现颅内、外血管和心脏器质性病变,应首先考虑主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能性。
4 癌症(cancer)与CS
随着癌症诊断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癌症存活率持续改善,中位生存期逐步延长,缺血性卒中合并有癌症的住院患者比例逐步增加。肿瘤引起卒中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可能是多因素所致,推测肿瘤患者卒中机制可能为:肿瘤后天所致的高凝状态、患者本身尤其是老年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长期放化疗损害。众所周知,由于长期卧床、侵入性操作以及药物治疗等影响凝血、血小板和内皮功能,癌症患者静脉血栓及静脉栓塞风险会增加,但美国一项基于人群的医疗保险索赔数据显示,癌症患者相较非癌症患者动脉血栓栓塞、缺血性卒中的6个月累积发生率更高,因此突发癌症的患者亦面临动脉血栓栓塞的短期风险显著增加的风险[21],考虑此时癌症活动强烈所致。另有研究表明,癌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小泡水平与高凝度的非特定标记的D-二聚体水平相关,癌细胞来源的细胞外小泡水平在癌症合并卒中组中最高,特别是在隐性卒中患者中,除此以外肿瘤类型和分期与癌症介导的高凝状态的存在和严重程度直接相关,也暗示癌症的促凝作用是这些患者卒中风险的驱动因素[22]。与非癌症患者一样,合并有肿瘤的急性脑卒中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也可合并有导致大动脉粥样硬化和小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单核细胞是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胞。另一方面,在肿瘤中单核细胞来源的巨噬细胞可作为宿主细胞以参与肿瘤炎症反应。这一事实强调了粥样硬化与癌症肿瘤过程的相似之处,癌症可能通过加剧全身炎症来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和破裂。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加速了脑卒中发生的进程[23]。一项包含17个随机对照试验的12,917名患者的荟萃分析显示,使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显著增加了中枢神经系统缺血和出血事件,风险可能因化疗剂量和肿瘤类型而异[24]。除此以外,放射是许多癌症的常见治疗方法。辐射可对血管内皮和外膜造成联合损伤,使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或缺血性卒中的相对风险增加一倍[25]。一项随访中位数26 y的研究显示,接受放射治疗的卒中风险存在剂量-反应关系,较高的辐射剂量会增加卒中的风险,对Wills环的辐射剂量是卒中的最好预测因素[26]。
5 颈脑动脉夹层(cervical ocerebral artery dissection,CAD)与CS
CAD是指颈脑动脉壁上的撕裂,血液进入血管壁,引起动管腔狭窄、血管闭塞、瘤样扩张、血栓形成或出血,导致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被认为是青壮年缺血性卒中的主要原因之一[27]。有研究显示,颈动脉夹层所致卒中,大多为动脉-动脉栓塞机制。在夹层血肿形成阶段中所引起的脑梗死,栓塞机制占主要地位。随着血肿的增大 ,管腔的狭窄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此时又有低灌因素的参与[27]。据一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显示,CAD引起的缺血性卒中患者与LAA引起的缺血性卒中患者相比,更容易出现头颈部疼痛,表现为严重的跳痛,可根据疼痛部位进行病变初步定位[28]。因此对于青年缺血性卒中患者未发现常见致病因素,尤其时合并有头颈部疼痛的患者,应考虑脑动脉夹层可能。
6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bstruci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OSAS)与CS
OSAS是最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类型,它的特征是间歇性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并伴随着白天过度嗜睡的存在。OSAS已被证明是卒中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且一项大型前瞻性多中心研究表明,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客观测量的睡眠呼吸障碍与再发缺血性卒中有关,但与死亡率无关[29]。
OSAS导致卒中的可能病理生理改变:(1)间歇性低氧血症会导致交感系统兴奋,使得血压升高、心律增快,诱发心律失常;(2)慢性间歇性缺氧同时引起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RAAS)系统的激活,活性氧(ERO)生成增加,通过激活炎症通路使血管内皮功能失调,同时缺氧会改变一氧化氮合酶的活性,致一氧化氮产生减少,最终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3)在OSAS中,由于血小板聚集、纤维蛋白原和循环儿茶酚胺的增加而出现高凝状态。这种高凝状态会在夜间达到高峰;(4)长期的高碳酸血症使得OSAS患者,脑血管自我调节能力下降和脑血管储备减少,干扰了调节大脑血流的自我调节机制,导致大脑灌注不足,增加脑缺血的风险。在呼吸暂停期间,最初脑血流量增加,但到最后下降到基线以下,产生低灌注期[30]。临床上对于CS的患者应注意是否合并有OSAS。
7 单基因遗传病(single genetic diseases)和CS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发现几种与家族性遗传相关的、导致青壮年脑卒中的单基因疾病。基因异常的识别对疾病治疗管理和遗传咨询有重要意义。常见的单基因疾病包括:伴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cerebral autosomal dom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DASIL),伴有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隐性动脉硬化症(cerebral autosomal recessive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CARASIL),Fabry病等。CADASIL是一种累及全身小动脉的非动脉粥样硬化性淀粉样阴性血管病变,主要见于大脑,NOTCH3基因是CADASIL的致病基因,基因错义突变、剪接点突变和基因片段缺失是其病理基础,NOTCH3主要表达于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s),调节其活性和功能,基因突变致血管平滑肌细胞中出现“颗粒状嗜酸物质”(GOM)沉积,导致血管平滑肌细胞广泛破坏[31,32]。众所周知在脑血流调节中,血管平滑肌对脑灌注压的动态变化发挥重要作用。CADASIL临床上其特征表现是反复的缺血发作[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或卒中],有先兆的偏头痛发作,情绪障碍,认知障碍和癫痫发作[31,32]。CARASIL也称前田综合征,是影响脑部小血管的单基因疾病,主要在日本和中国发病。HTRA1是CARASIL相关的致病基因,相关的突变导致HTRA1的蛋白酶活性降低,无法抑制转化生长因子-β家族的信号传导,导致CARASIL发生动脉病变,特征性的改变是严重的动脉硬化改变,纤维性内膜增生,内弹力板断裂,管壁透明变性,导致管腔狭窄,主要发生在穿透的小动脉,同时CARASIL的动脉平滑肌细胞(SMCs)明显丢失,最终引起组织缺血性病变的发生[32]。与CADASIL不同的是,CARASIL无淀粉样物沉积和GOM颗粒[32,33]。CARASIL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缺血性卒中或脑功能逐步恶化,进行性痴呆,过早脱发以及严重的下腰痛或脊椎变形/椎间盘突出症发作[33]。Fabry病是由于α-半乳糖苷酶A(α-Gal A)活性不足导致的一种进行性X连锁遗传性鞘磷脂代谢紊乱,通常在儿童时期出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患者会患上肾脏、心脏和脑血管疾病,并过早死亡。最新研究表明,在反复发生隐源性卒中的男性中,未被识别的Fabry病的患病率为24.3%[32,34]。临床中对于卒中发病年龄较小、缺乏常规危险因素且有家族卒中史的患者应排查单基因疾病的存在。
8 小 结
二级卒中预防的策略依赖于充分的检查以确定卒中的原因,目的是减少卒中复发的机会。临床上在除外常见的卒中危险因素后,对于仍不能确定卒中原因的患者,应积极寻找病因考虑上述可能,这对于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降低卒中复发率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