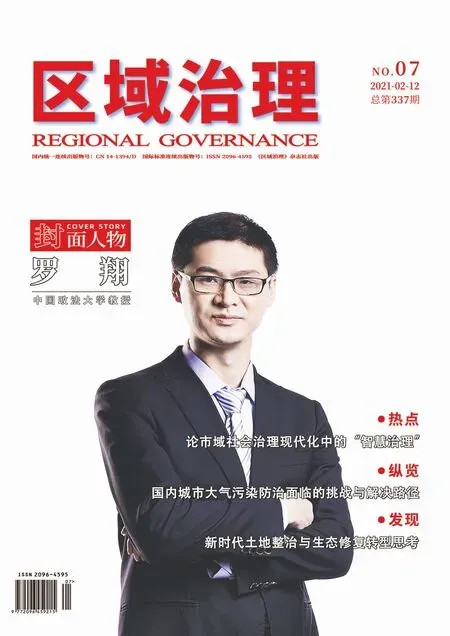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研究——重大突发事件防控的思考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许亚莉
全球化、工业化进程在不断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社会风险也日渐增多。此次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种发生在公共卫生领域的非传统的社会风险。纵观人类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疾病奋战的斗争史。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绝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最后一次公共卫生事件。“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把公共卫生风险“扑灭”在萌芽状态,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一、公共卫生风险提出及风险挑战
(一)公共卫生风险提出
何为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预防和控制疾病与伤残,改善与健康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提供预防保健与必要的医疗服务,培养公众健康素养,创建人人享有健康的社会。“公共卫生风险”是指发生不利于人群的健康事件, 特别是可在国际上播散或构成严重和直接危险事件的可能性。
(二)公共卫生风险挑战
“十三五”期间,我国公共卫生建设取得显著成绩,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2015年的76.3岁提高到2019年的77.3岁;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成功应对了像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热等突发疫情,主要传染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摘掉乙肝大国帽子;2019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10.8%等。与此同时,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公共卫生风险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传染病防控存在挑战。当前我国面临新旧传染病交织防控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是常规传染病风险。据统计2019年全国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数近2.1万人,占甲乙丙类传染病死亡总数的83%,是报告死亡数居第一位的病种。结核病年发患者数量大约为130万,占全球发病患者总数的14%,仅次于印度,据世界第二位。病毒性肝炎依然是我国法定报告传染病中报告病例数第一的乙类传染病。据估算,我国乙肝病毒感染者约7000万人,丙肝感染者约790万人,每年约33万人死于乙肝或丙肝感染导致的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另一方面是新发传染病风险。以此次新冠肺炎为例,截至2020年12月31日,我国现有确诊病例37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206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7071例。
(2)慢性病防治存在挑战。随着疾病谱的逐渐改变,慢性病成为威胁人们健康的主要“敌人”。2019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88.5%,其中心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为80.7%;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和癌症发病率与2015年相比有所上升,慢病防治对公共卫生工作提出更多新要求。
(3)食品安全管理存在挑战。食品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据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对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研究发现,现阶段食品安全面临5类风险挑战,分别是微生物污染、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质量指标不符合标准、农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和重金属污染,分别占不合格样品总量的29.6%、25.0%、16.8%、15.4%、7.6%,食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4)环境卫生治理存在挑战。环境卫生安全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近年来,北京雾霾、河南污水灌溉麦田、上海松江死猪事件、兰州自来水苯超标等环境卫生事件屡见报端,可见,环境卫生污染仍是影响我国公众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二、我国公共卫生风险治理困境分析
在众多公共卫生风险中,由于传染病传播的不确定、波及范围广、社会影响深等特点,防控难度系数最大,直接关系人民健康、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对疫情防控中面临的困境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更好的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避免疫情二次爆发。
(1)“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形势依旧严峻。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我国打赢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在前期抗疫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病毒本身的复杂性。病毒从“人传人”出现“物传人”,从“有症状”出现“无症状”,从“原始毒株”出现“变异毒株”等变化,病毒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人类对其认识的速度。另一方面我国疫情多地散点爆发,全球疫情加速蔓延。全球化带来人通、物通、信息通等便利的同时公共卫生风险也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屡屡出现入境人员、进口冷链食品和物品等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问题。(2)公共卫生专业力量薄弱。公共卫生专业力量是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有力保障。当前,公共卫生专业力量薄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卫生人才匮乏。长期以来,公共卫生人才发展平台小,薪酬待遇低,职业成就感弱等问题,导致公共卫生人才短缺问题十分突出。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2018年我国各类执业(助理)医师总数持续上涨,其中临床类别增长人数最多。与临床、中医、口腔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的稳步增长相比,公共卫生人数涨幅最慢,2017-2018年甚至没有增长。按照国家《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到2020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达到2.10人、注册护士达到3.14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达到0.83人。根据《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77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3.18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6.41人。其他医疗卫生人才已实现国家规划目标,而公共卫生人才目前每千人仅有0.64,离2020年实现0.83的目标距离甚大。二是公共卫生经费结构性失衡。在“重医轻防”惯性导向下,政府大量的财政补贴投入到疾病谱后端的医疗卫生机构,前端的公共卫生财政投入则长期不足。2002年我国在原卫生防疫站的基础上组建了自上而下的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各级疾控中心定位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由各级财政供养。因此,各级各地财政收入好坏直接影响对疾控机构经费的投入。在2017年之前,各级疾控机构尚能够通过预防体检或委托性检测收费弥补日常经费不足的部分,2017年4月国家取消或停征3项收费后,经费不足的问题更为凸显。(3)专业机构与决策机构有效沟通机制还需提高。专业机构对公共卫生风险的研判和评估是公共卫生风险决策和防控的直接依据。不同机构之间的有效沟通是公共卫生风险治理的前提。新冠肺炎疫情中暴露出的不同机构之间有效沟通机制较弱具体表现在:一是医疗机构与疾控机构沟通不畅。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早期,许多临床医生早期已觉察到不明肺炎,但由于监测系统多头管理、公共卫生风险意识不足等原因并未有效将疫情实况上报,一定程度上延误了疫情的有效监测和评估。二是疾控机构与决策机构沟通不畅。各级疾控机构隶属于同级卫生健康部门,上级疾控机构对下级疾控机构仅进行业务指导。各级疾控机构向同级卫生健康部门汇报公共卫生信息,卫生健康部门向政府部门报告信息。这种层层上报情况,效率低且信息存在走样的可能性。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早期,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组多次前往武汉调研,当地政府提供给专家组的资料有限并在汇报中表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出现感染者,感染者病症不是太重,和季节性流感差不多”。专家组通过对患者病历的监测和流行病学分析,向决策部门提供了多份调查报告,并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及临床救治中采用抗病毒治疗,然而早期这些报告并未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
三、提升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效能对策
上级领导强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查漏补缺,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强化风险意识,提前系统谋划,着力防范和化解公共卫生风险。
(1)坚持预防为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需逐步转变“重医轻防”理念。一是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入机制,重点向财政收入落后的地区倾斜。坚持“强基层、保基本、建机制”新医改方针,夯实农村卫生三级防护网,优化医疗卫生资源投入结构,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金融机构等参与建设,形成政府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机制。二是加强疾控机构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提升其核心能力建设。三是改革和健全公共卫生队伍人员培养、准入、待遇保障、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增强公共卫生人才职业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2)强化科研技术支撑,提升公共卫生风险治理效能。“科学技术,战胜疫情的关键利器”。一是加强全球在疫苗和药物研发合作。二是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科技力量,精准监测和评估公共卫生风险。三是加快推进公共卫生数字化建设,合并流感监测系统、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发热门诊等系统,建立统一的呼吸道疾病的监测系统。破除医院电子诊疗系统和传染病直报系统数据壁垒,落实临床医生疫情申报主体责任,发挥好疫情“吹哨人”作用。
(3)畅通机构间沟通机制,凝聚防控合力。完善《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专业机构在公共卫生风险预警、防控等方面的话语权。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要将公共卫生风险培训作为干部培训的必修课,强化领导干部的公共卫生风险意识和提高其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决策和治理能力。卫生健康机构系统的主要领导干部的选拔应当从具有相关学科背景的人才进行选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