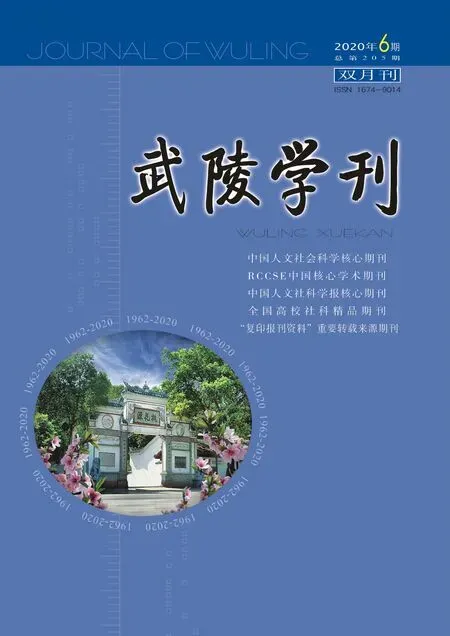在小说与诗之间
——蒋韵创作论
毛郭平
(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蒋韵,山西当代文坛杰出的女作家。1979年发表处女作《我的两个女儿》《少男少女》,响应了当时的文学主潮。1989年之后,蒋韵逐渐找寻到自己的创作风格,相继创作了《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行走的年代》等长篇小说以及小说集《心爱的树》,其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不过,蒋韵的创作与文学主潮保持着疏离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文坛上的关注度。
一、乡愁的缺失
蒋韵出生于太原,随后被送回河南开封老家,五岁时又回到太原,并在此学习、工作和生活。由于童年经验、周边环境以及女性的敏感细腻心理,蒋韵并不能完全接纳这个城市,太原在其心里只不过算是人生中的驿站而已,也就谈不上有认同感、归属感。为此,在她的小说中,太原并没有像其他的城市那么具有明显的标志,要么以“T城”代替,要么以北方某个省的省会,抑或是“内陆”代称。在《心爱的树》中梅巧把城东那座近千岁的古塔作为观看这座城市的视点,觉得这座城太小,并试图把暗淡灰色的小城全部涂成热烈的红色;《北方丽人》中北黄沟的人没有把“我”这个省城的“著名评论家”当回事,因为与“京城”某报的记者相比,孰轻孰重也是一目了然的;《完美的旅行》中作为外省夫妇孩子的刘钢,被带到了那座他心目中原以为世界上最大又很热闹的城市,不过,他却无法习惯这S省的省会的嘈杂、拥挤和肮脏。作为叙述者的“我”,也仅仅把“T城”与自杀或者死亡关联在一起。“T城”,或者黄土高原上的S省的省会,都有着太原的影子:无论是小说中关于东城“塔”的描绘,南城荣军医院的掠影,或者小说叙述中或多或少关于“作者经历”的互文性特征,都使得我们看到了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地与实际地域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蒋韵在《我的内陆》中还是将“T城”与太原的关系说清楚了,“我的小说中从没出现过‘太原’这样一个地名,只有‘T城’。‘T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我走进T城时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1]。那么T城的地理位置是怎样的?向北就可以走到昔日的要塞雁门关、杀虎口,这里是与丈夫李锐重新走西口的必经门户;向南则是汾河盆地,那里是小说中提及的“河谷平原”,是走向西口的出发点;向西则是著名的吕梁山区,那里是李锐当年插队的地方。在行经了T城的周边之后,作者将笔触伸向了她生活着的城市,探寻到了其中的密码,写出了生活于其中的“我的”T城——太原。
在小说家笔下,太原似乎没有辉煌的过去,这与作者诗化的想象有关。既然太原与自己诗化的城市想象之间存在着距离,那么关于太原的书写就从理想中回到了现实,与此同时太原也就不会成为她的乡愁。比如在《我的内陆》中就明确地表明,她在精神上一直游荡于这座城市之外。尽管她逐渐感受到了她的生活与这座城市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它对自己的善待与呵护,并试图在《我的内陆》中与之达成某种和解,但太原于蒋韵而言却无法满足她的精神依赖,于是,她成为精神上的漂泊者。漂泊就意味着要远走,要一直行进在路上。具体来说,《我的内陆》中的人物就是一直处于漂泊中的。林萍在父母被扫地出门前率先离家出走,与家庭划清界限,然后又从迎泽大街徒步走向了革命圣地延安,甚至走向了越南战场,以洗刷因出身所带给她的耻辱。同样,知识青年吴光因朋友出事而被牵连,于是他一直流浪,来到别人的家园,并将之作为奔向远方的驿站。当然,蒋韵对于流浪的认识源于她自身的双重背叛。当还是孩子时就完成了对家乡的背叛,因为她所居住的城市对河南人的偏见使得她努力想洗掉身上所有关于家乡的蛛丝马迹,特别是从语言上放弃了故乡。然而,又从外乡人的视角对客居之城充满了敌意和不信任,这又从内心深处背离了第二故乡。于是,有家无法回的念头充斥着她的头脑,于她而言,每一天都是漂泊的日子,也都是放逐的日子,无论是被放逐抑或自我放逐。
二、精神的漂泊
漂泊是许多作家作品的主题,林白用极致的语言表达对社会人生的体验,而蒋韵则试图通过诗意的描写来呈现社会中的人情冷暖、爱恨情仇。用诗意的方式呈现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氛围,蒋韵的小说便兼具小说的外形诗的内核。
蒋韵小说中的“漂泊”既体现在人物肉身的远足跋涉,也体现在人物精神的孤苦无依。在《行走的年代》中讲述了诗人“横行天下”的20世纪80年代,在内陆小城读中文系的文艺女青年陈香献身给了小有名气的诗人莽河,然而莽河却在汲取了这个城市的温情与爱之后远走他方,从此杳无音信。陈香执着地将两人的孩子生下来,因为孩子携带了诗人的基因。小说又给我们讲了莽河在陕北与一个从事社会学调查的研究生叶柔心灵相通,就在温柔一夜之后,第二天醒来,莽河才发觉叶柔已经远走了,于是,他开始了他的追寻之旅。莽河与叶柔在走西口的路途中相遇,然而,叶柔却因宫外孕大出血死亡。而那个文艺青年陈香在偶然翻看杂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孩子的父亲只不过是一个赝品,写《高原》的莽河另有其人,于是她试图了断自己的生命,孩子也在偶然中失去了生命。那个爱着叶柔的莽河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开始经商,继而成为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他用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来推介自己的楼盘。陈香的同事明翠将陈香的故事告诉了莽河。两个莽河与两个女人的故事作为两条并行的线索,最终在真正的莽河这里汇集在了一起,而那个假的莽河却不知所踪。《行走的年代》为我们展现了逝去的八十年代里,人们都在探寻自己向往的美好,平凡的人追寻诗人,而诗人却在远离平凡,正如作者借叶柔表达了诗人自身放逐的缘由,“从平庸的日常生活中出逃,那是诗人的本质”[2]。放逐只不过是对自己生存境遇的怀疑,于是,在放逐中寻找诗意,寻找诗人的魂灵,待真正被现实所击垮的时候,才发觉寻找本身就是一种诗,寻找的过程就是诗意不断酿就的过程。所以,生活在别处对人的牵绊,既造就着人们生活的信念,同时也给予人精神层面的苦痛,那就是总会把此处作为批驳的对象,从而注定了现代人都会行走在路上,基本上都会成为精神的漂泊者。因而,蒋韵小说中的人物固守着浪漫和诗,为之能够奉献一切,但就在面对残酷现实的同时不堪一击。他们尽管对现实有着质疑和背叛,却总是期望着现实能有一个诗意的呈现。正如已经在商业大潮中经历了起伏的莽河,其诗人身份早就被忽视了,然而,那颗诗心却总会时不时跳动起来,于是,“望海小筑”的广告语对于海子诗歌的征用,再一次表明了莽河的“诗心”不灭。这或许是蒋韵对于诗的执着,对于心灵家园的苦苦寻觅,于是,命中注定只能是一个孤独的旅人。
对于孤独的旅人而言,寻找精神的依靠或许是解决漂泊的方式。然而,在寻找的过程中,或许会增加孤独的程度,《完美的旅行》和《隐秘盛开》就为我们做了另类的描述。《完美的旅行》中,小男孩刘钢的美好记忆停留在东北的爷爷奶奶家。于是,在肮脏、混乱的黄土高原上的这个城市,刘钢执意于探寻回家的路。然而,在刘钢离家出走之际碰上了出差回来的医生陈忆珠。陈忆珠起先帮他找回父母。随后,他们通过阅读地图,借助想象,开始了自由的旅程,行程中,他们两个人成为了最好的旅伴。就在此时,刘钢的母亲与其他的妇女打破了这种美好,污秽了世间的这种纯情。然而,这并不能阻拦刘钢试图跟随陈忆珠继续旅行,但是待刘钢见到陈忆珠时却是一副残酷的场面,陈忆珠已经服药自杀。随后陈刚也远离了T城,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下落。美好的东西总是要被摧残的。这是蒋韵的“残忍”之处,也给作品带来了一抹悲情。如果说《完美的旅行》表达的是在现实面前,精神生活无法得到维系,主人公要么采取了决绝的方式了断人生、要么选择流浪的话,那么《隐秘盛开》则为我们展现了柔弱的两位女性如何面对现实的残酷,却又能坚守内心的那份执着。蒋韵在《隐秘盛开》的开篇便介绍本书与爱情有关,当然更与死亡有关,是关乎“让人疼痛至死却不能放弃的爱意”。小说开头写到了两位中国女性偶然参加了一个从巴黎到西班牙的自助旅行团,年长的女性与年轻的女性都看出了彼此的心事,于是她们相互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样,原本并不怎么美好的旅途上彼此有了精神上的伴侣。潘红霞讲述了七七级的生活,尤其是她在上大学时期面对了一个危险:“对一个人一见钟情毫无希望的爱。”[3]41那个人叫作刘思扬,是个诗人,同小说《红岩》中的“刘思扬”一样名字的人。然而她却没有将自己的内心的这份情感向被爱者表白过,甚至于别人也未必觉察到这一点。小说在叙述其成长经历时就已经交代了她的性格,“这孩子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也许,那是坚贞的狂热,是属于圣徒的品质。可她生活在俗世,这就埋藏了不幸。只不过,它隐藏得很深,不易觉察”[3]27。潘红霞在毕业聚餐之际,借着酒劲向与刘思扬共同援藏的“小玲珑”吐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并让小玲珑守护着这份秘密。米小米也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出身贫苦却为了坚守一个道德底线,即永不再花家里的钱而去拼命赚钱。不过,由于被扫黄的人抓到,米小米被南方的学校开除。巧的是,她又遇到了以前的“恩客”,这位恩客又父亲般地资助她考取了北京的大学。不幸的是她同潘红霞一样,也面对着死亡的威胁。为了爱,也为了她的妈妈,她在一个预言的鼓舞下去寻找自己的爱情,结果竟然也找到了。两个身患癌症的人,在游历欧洲的时候向对方敞开了内心的秘密,成为这趟旅行中的伴侣。不过,与米小米的幸运不一样的是,潘红霞原有可能在欧洲碰到刘思扬借以让自己内心的秘密公开,然而她却最终错过了心里所眷恋的那个诗人。潘红霞去世之后,米小米帮助潘红霞向刘思扬讨回了一个拥抱。旅途倒不见得有多少优美的风景,但这风景融入了看风景人的情致。米小米和潘红霞的经历诠释了两个时代中的女人对爱的不同理解,但她们对爱情的追求却是一样的。
三、对失去的凭吊
蒋韵不避讳谈自己是一个固执的凭吊者。之所以凭吊,是因为那些美好和珍贵的东西会失去,那些关于美好和珍贵的东西的记忆也会失去。因此,蒋韵才在她的小说中反复叙述那些关于过去、关于失去的传奇故事。在《隐秘盛开》中,“情”是最珍贵的东西,无论是潘红霞对刘思扬的那份“情”如何秘而不宣,拓女子为了爱情勇敢地做出反抗,抑或米小米去欧洲的旅途就是为了验证一份关于爱情的预言,这些都与蒋韵对于失去的思考有关。她曾指出“情”的天下始终被“法”的天下所围攻,特别是在这个欲望至上的年代,纯情的东西已经被欲望围剿得所剩无几了,以至于每个人都只剩下了一具肉身[4]232。潘红霞无法获得刘思扬的爱情,但爱是一个人的事与被爱者无关的信仰冲淡了那份遗憾;拓女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的人生课本翻看完算是埋葬了自己;米小米在经历了风尘之后,在死亡面前,也期望着爱人,期望着一颗柔软、不谙世故的心。失去并不是蒋韵凭吊的目的,她只是借失去表达那份眷恋,试图让人找回曾经的世界。曾经的世界在蒋韵这里是充满着“情”的,当然主要是爱情,尽管她曾说自己不擅长写爱情故事,但爱情却是找回失去世界的有效途径。所以她才在《行走的年代》这部小说的题记中援引了汤显祖的那句名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正如前文所说,1980年代是诗的年代,而诗是关于“情”的,没有情感何来诗?没有诗何来寄托情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是那个年代的媒介,是回到那个年代的有效方式。于是,诗人成为故事的引燃点,也成为了故事最终的灰烬。诗人莽河,是那个时代偶像的化身,他们的命运遭际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有人假借诗人的名义欺骗了别人的感情,真正的诗人却在流浪漂泊中寻找灵魂的归宿,即便根本找不到归宿;爱诗的人会爱上和诗有关的一切,甚至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洪景天);不爱诗的人也会在诗人那里找寻到一点诗情,即便是在进入物欲横行的新世纪(如楼盘售卖现场用海子的诗做广告)。这就是诗的魅力,不过,对诗的凭吊、对诗人的凭吊、对诗的年代的凭吊,源于作者对现实中诗的萎缩、诗人的柔弱和诗的年代的失去的感慨。诗的年代是一个真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最虚幻的年代,因为,诗是要远离现实的。固然,失去的总会在经历过的人那里留下一些印记,然而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看来却是传奇。其实,在传奇与旧事之间,关联起来的“情”却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所以,王德威评价蒋韵的《行走的年代》时就指出,这是一部关于“情”的考古学[5]58-63。在这部小说中,时代的浪漫与现实的狼藉之间,是情感得以无限丰富滋长的温床,也给它的受众带来了巨大的时代幻灭感与空虚感。幻灭感与空虚感固然与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有关,更重要的是那种岁月无可挽回地逝去了。于蒋韵而言,那个年代是一个有关失去的追忆,是那代人的遗产、财富,也是那代人的标记,是他们的青春之歌。不过,蒋韵更是从美好的意义、诗的高度来看待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执着、疯狂、浪漫。于是“凭吊”成为蒋韵这部小说的主色调,她冷冷地看着作品中的主人公,尽管会有时忍不住要表达自己对主人公的态度看法。所以,对失去的凭吊有蒋韵试图再次进入那个场景的欲望,她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充满了向往和眷恋。
蒋韵对“失去”的凭吊也表明了她对自己身份和经验的探寻。如果说《行走的年代》是对自己青春经验的一次重新检视的话,那么《栎树的囚徒》则是对家族故事的一次重拾。蒋韵在小时候就听自己的外祖母讲过有关家族的故事,后来长大了也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关于家族往事的记忆,加之自己对所生活城市缺乏一定的认同感,于是,自己从何而来的追问成为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重要主题。当然,这部小说充斥的都是寻找。范天菊在七岁时要在太平间找到她的乡愁,不过这是一次失望的寻找;她在十四岁的时候要去找她在大西南的二表姐范悯生。范悯生则因为父亲的入狱阻碍了她与特级英雄瞿排长的爱情进展,当瞿排长费尽气力找到范悯生的时候,她已经嫁作他人妇。范天菊的同母异父弟弟张建国,翻遍城市里所有的垃圾场,意欲寻找自杀未遂的母亲从烟囱上掉下来的那只鞋,结果,在找鞋的过程中淹死在了水库中。范天菊在舅母贺莲东的指引下,发现了母亲的出身地朴园并试图追问来历。范天菊的母亲范苏柳萌生了她的父亲到底为谁而厮杀的疑问,但这一追问却因为父亲的被杀而终止。因为她认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宿命,“父亲的血在我们血脉里留。父亲的罪恶在我们血脉里流,而他的英雄之情却荡然无存。父亲的一生真是失败到底的一生,他使所有的后代子孙和亲人沦入罪恶的渊薮,一个一个全无好下场。当我的母亲妖娆无比像成熟的果实悬挂在屋梁上时,我知道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6]。贺莲东在见到范天菊的时候,就有过一番感慨,认为就范苏柳目前的处境,是无法给范天菊讲述有关家族的故事了,因为上一代人的闭嘴,使得家族故事在上一代人的嘴上消亡了,这就使得关于整个家族的记忆在后代人那里完全消失了。贺莲东跟朴园的告别,意味着整个家族记忆的开始中断、开始被遗忘,这种遗忘既是因时代外力的强力介入所致,同时也源于这个家族的人的选择性遗忘。小说《栎树的囚徒》通过范天菊离开T城去找寻她的二表姐这样一个偶然的机遇,从此撬开了那个快要被尘封了的整个家族记忆的大门。这个记忆中,陈桂花被人剜了双眼,纵身投入伊河;段金钗不愿做阳山的最后埋葬者,生吞了芬芳的烟膏;范福生被人用黑枪射杀,当场毙命;白秀叶(小红)为救范先琴,替他挨了两枪香消玉殒;芬子在为情私奔的路途中被自己的同父异母哥哥枪杀;关茛玉历经沧桑,最后在西屋的房梁上自尽了;……这些都是不愿被人提及的故事,却在范天菊的闯入中唱完了最后一曲挽歌。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但这些往事真正能被遗忘吗?这是蒋韵的思考。
四、对现实的反思
蒋韵小说的漂泊主题有着蒋韵对诗性的追求,即要远离现实的喧闹,又要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中人物都是至情至性的,他们敢爱敢恨、可爱可恨,有一种离尘弃俗的精神,任何那种理性的说教对她(他)们而言似乎都无济于事。当然,漂泊本身与失去有着很重要的关联,如果失去了,那么就无所归依,只剩下漂泊。所以,蒋韵对于失去往往有着足够的留恋,她游走在煽情的边缘,却又不让你陷入唏嘘之中,只能让你冷冷地思索着浪漫情感支配下的现实人生。为此,她的小说中往往充满了足够的警醒与反讽。
在《北方丽人》中,那个从京城来的著名记者田平坝试图扮演一次救世主的角色,妄图解救那名被拐卖到太行山深处的贵州姑娘银鱼,通过一连串的推理和双簧表演,却无法真正改写这名女性的命运,他只好无奈地用“意外”和“惊喜”来向已经看穿他的行为的人解释他的动机。在小说中写到银鱼迎接田平坝去她家的时候,整个画面带有一种凄艳的色彩,“她换了一件鲜艳的红衣袖,甜蜜而凄伤地望着她的孩子微笑”[7]。解救被拐卖妇女是合法合情的,但这样一种方式是否真能带来女性的新生?如果是,那么银鱼一个人回到她的故乡以后,她又为什么要重新回到那个地方?这是这个短篇小说带给我们的启发,也表明了蒋韵的反思,尽管她只是在小说的末尾处才亮出那个“丽人”,那“丽人”的凄伤而微笑的眼神却使得每个人无法释怀。这里面有难以言状的情感,只是蒋韵将这个故事诗化,让内心的情感得以隐秘地盛开。蒋韵反复强调要做一个自然之子,在笔者看来,即是随心随性。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实际上是蒋韵小说中的另一个主题。她在《隐秘盛开》中描述了一群从大城市来乡下插队的知识青年找了一个启蒙对象——“拓女子”,教会她识字,让她懂得了爱情。然而恰恰是这份启蒙,开启了拓女子的另外的人生。她原本可以懵懵懂懂地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着一个平凡乡村女子的凡俗生活,然而,在受到了这些启蒙教育之后,她却走上了追求个人爱情而激烈反抗别人为她所设定的婚姻、生活的路子,最终却又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这是福是祸?我们当然可以从启蒙主义的视角来谈论拓女子的悲壮、勇敢和无奈,也会给她平添上一层悲剧的标签。但是,拓女子如何看待这些启蒙者,这些做了启蒙而全然不顾她今后生活的那些从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呢?蒋韵借助小说中拓女子的闺女米小米做了一番反思,“本来,她可以生活得很平静,嫁给我爹,一门心思过日子。……其实在农村人看来这是一桩不错的婚姻,没有什么不般配。……但是她铁了心地要爱情。我后来想‘爱情’对她而言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非现实的、浪漫的、美好的一切,和真实无关的一切——毁了她的生活”[3]183。这是米小米对她母亲遭遇的反思,认为那些象征的、浪漫的东西扰乱了她本该拥有的平静的生活。除此之外,米小米还对那些启蒙者有着一番质问,即当她妈妈孤身一人与命运抗争的时候,那些启蒙者、那些教会她识字懂得爱情的人却不知道跑到了哪里,她甚至质疑那些启蒙者在教会别人追求自身爱情的时候,她们却在与现实媾和,撇下她与生活同流合污。于是她的母亲的抗争是否真的值得成为一个需要思考的话题。这就是蒋韵的反思,虽然在她的诸多小说中充满了悖论,蒋韵一方面强烈地追忆着那已经失去的浪漫和激情,一方面却对这种浪漫和激情充满了怀疑,由此,她的反思本身便有了真正的哲学意味。我们可以从蒋韵在评价陈亚珍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时援引了陈亚珍回复她的博客的一段话,“写作是具有使命感的,仅仅是帮闲与帮忙不过是匠人而已,成不了真正的作家。……大智大勇是一个作家有能力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人类提供建设性的远景,有勇气坚持反叛意识,发出正直的呼声”[8]。
浪漫、诗性是蒋韵小说的外壳,因为,在她的小说中,浪漫与诗性是被现实与凡俗所裹挟的,也正是后者使得前者具有了悲壮美。同样地,也正是前者使得后者具有了诗性美。在《栎树的囚徒》中,当天菊的母亲苏柳爬到高高的烟囱上被当时的人当作自杀行为来围观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观风景的看客,甚至她的亲人都期望她能从上面跳下来。人们在认识和情感层面的共通性和共同性,自然符合那个年代对所有政治身份有问题的人的前提预设,而蒋韵借助于苏柳自己的回忆质疑了当时人们的共识背后的谬误性:范苏柳只不过是受到笤帚的引诱,不知不觉地爬上了烟囱,试图离天国更近一些。这种认识的不对称、错位导致了对一个事件的不同的意义解读。所以作家蒋子丹认为:“《栎树的囚徒》还写出了事件的荒诞性。……人们原来总把小说的多义性理解为一个故事被安排了种种结果,是一种结果的多义等等,显然这种理解还是表面的。我觉得,生活的多异性恰恰在于每一个处在不同地位的、不同身份的人对一个事件的不同记忆和理解。不同记忆和理解的错位造成了荒诞感,这是这部小说的高明所在。”[9]或许,蒋韵正是通过对失去、对漂泊的再现,借以表达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方法,从而写出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那么,蒋韵该如何来被命名,她又如何自我命名?
五、对自我的命名
关于蒋韵的才情和小说的艺术价值,评论者屡屡给予好评。然而,对蒋韵的命名似乎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蒋韵试图在宏大叙事的主流中找寻极容易被遮蔽了的个人感受、个人体验。她坚守着她的浪漫主义,于是小说中的人物都因为那份执着,在遭遇现实之后带了几分悲壮,遭遇现实磨砺却依旧坚守那份诗情。从生活中逃离,在流浪途中时时会翻检曾经的记忆,从而给自己的行为带来一份诗意和审美。这就是蒋韵对于创作的理解。但是,比起那些波云诡谲的文学创作方式以及献媚读者的创作思路,蒋韵的创作手法显得有些迟滞,创作内容显得有些超越现实。这样,蒋韵总是显得有些不“入流”。但这并不能掩盖蒋韵小说的价值。于是,海内外的学者试着给她命名。王德威称赞她“关心的诗,写的是小说”[5]59;王春林称赞她“赋予小说以诗的灵魂”[10];杨品则推举她是山西新时期以来女作家中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认为她的作品旨在为同龄人塑像,写家族传奇故事,采取了怀旧型的叙述视角,即“尽可能地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注重将生命感觉转化为艺术感觉,追求一种朦胧、悠远的美学效应”[11]。当无法替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坐标系找出准确的位置时,“成就大于名望”这样的美誉就显得有些含糊。
当然,蒋韵一开始就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她也曾经努力地追随过各种新的思潮,然而,就在她亦步亦趋的“追潮”过程中,她对新思潮产生了质疑,“新”的就一定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吗?写小说就一定是思潮的诠释抑或把文学变成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副本吗?或者说,我们的小说,一定要是西方某个大师的“副本文学”才有价值吗?她要写出具有灵魂的东西[12]。当然,这种质疑一直伴随着她的创作,因为她对整齐划一有着天然的警觉,她觉得洪流内一定暗含着潜流。即便是对自己创作的“个人性”的东西,她也做了一番审视,如果把每个人都强调的独特个性汇聚起来的话,那很有可能是一个“可怕的雷同和类型化的汪洋大海”[13]。她遵照自己的生命体验,她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现诗情。她与丈夫李锐沿着山西人走西口的路线进行探寻,却在天地空旷之中发现了一群沉寂的坟茔。在春天的阳光中,她能够感受着那些移民拓荒者所赠予的乡愁与前路的艰辛。她开启她的想象之旅,在黯淡的生活中找到诗意。就是说,在这个物质和欲望几乎成为人的本质的时代,她没有办法放弃理想、道义和浪漫,于是,她与这个时代有了距离感,显得有些异己,显得与这个时代的文学“格格不入”。蒋韵并非不看重别人对她的评价,但她对自己有过命名,“在我的城市里,我一直游荡着。虽说我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并且还要继续生活下去,虽说除了这个城市我再无其它的家园可言,可我仍旧是那里的一棵无根之草。没有根,自然谈不上‘根正’,别人看你,总像在看一个漂泊而来的异端。我的城市我的省份是一个著名文学流派的所在地,但我在它之外。它的麾下没有我。从一开始,我就是轰轰烈烈一群人之外的形单影只的一个。我是我自己的旗帜,尽管被高原的大风撕扯得七零八落,但破碎的旗帜也是旗。它猎猎地飘扬也自有它的一点壮烈之处”[14]。这个破碎的旗帜成为蒋韵我行我素的信念,她不愿为了向某个家族的命名而靠拢,从而改变自己,不愿放弃青春期的骚动,因而,她无法忍受理论家各种言不由衷的“多元”理论,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进化的理论。因而,蒋韵绝不愿意做某个理论家或者某种理论的“副本”,只愿做自己的先锋,即便是茕茕孑立,无人喝彩。她所赏识的是与她具有相似气质的人,正如她对山西作家成一的评价,“他离时尚很远,离浮嚣很远……他只是竭尽全力地去讲好他的故事”[15]。用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语言讲述自己的发现和体验。
这样,蒋韵并非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她是用小说的形式和诗歌的精神召唤那些曾经失散了多年的同路人,追忆那段为诗迷狂的岁月,即便是已经逝去,但还是试图回望那段夹杂在记忆深处却无法重返的行走的年代,以及行走之后所带给自己的生命裂变。
总之,蒋韵在创作中坚守自己的内心体验,无论是对家族历史的书写抑或是对同龄人故事的追述,都采用了浪漫的笔调,这使得其作品具有了诗的意蕴;同时,蒋韵还对所述之事从现实的层面进行了深入思考,这又使其创作带有小说的深沉。正是因为对内心体验的尊重,她并不追随文学潮流,而是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