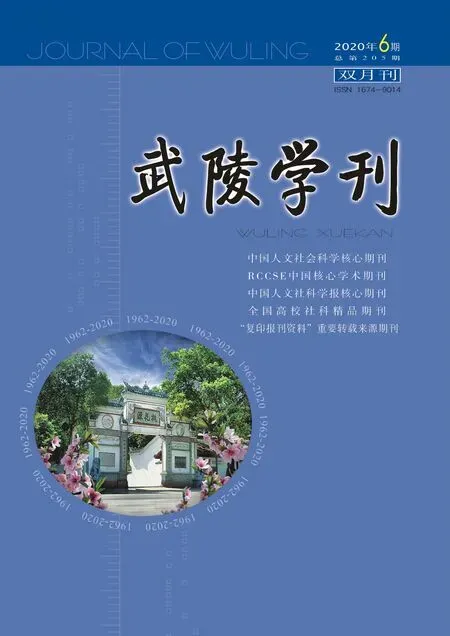查尔斯·泰勒超越“现代自我认同危机”之可能性思想探析
刘力红
(沈阳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引 言
马克思反对追求抽象的普遍性的道德主义,但是,他的哲学在本质上并不反对道德,相反,他以自己的方式全面呈现了具有现代基因的道德诉求,这种道德诉求为现代人走出个人主义的道德困境提供了可能。无独有偶,现代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也从伦理学角度阐述了这种诉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泰勒的相关思想对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以现代性语境超越由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所造成的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正是因为看到了泰勒相关研究的重要价值,有学者对他的现代自我认同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其中,何怀宏从现代认同与承认政治关系的维度揭示了泰勒现代自我认同思想的本质内涵[1],张容南从泰勒与福柯、哈贝马斯论争的角度全面呈现了泰勒的现代自我认同思想的独特性[2],邵晓光、刘岩具体分析了现代认同中的共同体认同的结构[3]。有学者则系统研究了泰勒的本真性伦理思想,其中,韩升从根本性存在的角度探讨了泰勒的本真性伦理思想[4],孟芳系统总结了泰勒本真性理想的三重内涵[5]。也有学者探讨了泰勒有关个人主义及消费社会认同危机及拯救方案的相关思想,其中,余晓玲、刘同舫认为,泰勒立足于本真性伦理的道德理想,试图从现代个人主义的困境中拯救现代性的成就[6];李世涛认为,泰勒提出了“本真性理想”的思想,希望由此克服当代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困境[7]。这些研究为我们系统地认识泰勒为超越现代自我认同危机所做的理论努力奠定了基础。
在泰勒看来,现代西方个人主义必然会产生认同危机,这是因为,在祛魅化的现代西方世界,能赋予人们以意义的基本框架降低为个人的偏好。然而,“因为框架是我们赖以使自己的生活在精神上有意义的东西。没有框架就是陷入了精神上无意义的生活”[8]24[1]。因此,个人主义的认同总是与意义危机相伴随。泰勒认为,我们只有澄明强势评估框架以建构道德空间,关照“对话网络”这一自我认同的超验条件,自觉追求“善”的叙事,才能摆脱由个人主义的自我认同所带来的现代认同危机。“超然的自我”,只有在这一宏观的道德空间中,才能摆脱自身存在的狭隘性;“缓冲的自我”,只有通过参与对话网络,追求“善”的叙事,才能打破现代性存在的隐忧[9]。
一、道德空间:自我认同的基本框架
泰勒认为,自我是处于道德空间之中的自我,其内心深处有着对道德空间的渴求。道德空间构成了人们的自我认同的基本框架,人们只有在特定道德空间中才能形成健全完满的人格。人们通过澄明强势评估框架以进入道德空间,而进入了道德空间的自我在根本上不同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中的自我。“他们是拥有前边所说的身份(或正努力发现一种)、有必要深度和复杂性的存在”[8]44,他们通过在道德空间中的自我认同来确证自身。这意味着,“在没有趋向善的某种方向感的情况下我们无法获得这个概念,正是依靠它我们每个人才本质上(即至少特别是规定我们自己)拥有立场”[8]46。因此,在现代性条件下,人们要想避免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和意义危机中,就需要确立特定的道德空间或道德框架。这在根本上是由道德与自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决定的。
道德与自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人类对过更好的生活的道德信念和追求,使人们相信其生命和完整性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应该得到尊重;另一方面,对内在于人的生命之中的何种存在应该享有特权又成为道德框架不断演进的内在动力,人们需要根据特定的道德框架进行道德判断。例如,前现代社会把人的尊严与其在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所获得的等级和地位(诸如自由公民、武士、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等)相联系的荣誉伦理看成具有重要地位的伦理。在现代社会,尊重人的完整性,就意味着尊重他们的表现力,他们拥有形成自己的见解、规定自己的生活概念以及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的表现自由。当然,这并不否认,在现代社会,荣誉伦理仍会赋予民主政治以生命力。只是与尊重人的表现力的道德框架比较起来,荣誉伦理不再居于主导地位。
由道德与自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所决定,我们对道德框架有着内在的渴求。尽管随着现代文化的“祛魅”发展,传统框架被削弱,古老的框架被摒弃,所有的框架看起来都是有疑问的。尽管被人们曾经看成是与宇宙结构一样具有本体论的坚固性的,不受挑战的绝对命令的特定的框架,在“祛魅”的现代文化条件下仿佛变成了人们能随意采取的易变的解释,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人们对框架的内在渴求。
人们的生活和判断需要建立在某种解释之上,他们不可能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生活,他们需要通过包括强势性质区分在内的框架获得有意义的生活。“被强势赋予的视界中生活构成着人类的特质,而走出这些限制也就是走出我们所认为的完整性,即未受损害的人类人格性的状态之外”[8]36,人们只有在强势的框架之中才能过有意义的生活,知道自己是谁,才可能达致人格的完满性。这是因为,只有在特定的道德框架中才能实现自我认同。“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我应赞同或反对什么。”[8]37有了这种建立在特定的道德框架上(部分地由某种道德的或精神的承诺所规定,部分地是由其所属的民族或传统所规定)的立场或认同,人们才可以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或值得赞赏的,亦即获得了一种能采取特定立场的框架。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不值得做的,什么是重要而有意义的、什么是次要而无意义的,构成了人们内在的道德空间,人类的心灵深处存在着这种对道德空间的渴求,只有在这种道德空间中人们才能获得方向感,形成自我认同。
如果离开了特定的道德空间,人们就丧失了承诺或认同,就会因为对什么是重大的事情毫无所知,从而不知所措,陷入认同危机中。所谓“认同危机”就是“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界,在其中事物可获得稳定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而另一些则是坏的或浅薄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都是固定的、易变的或非决定性的。这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经验”[8]37。更为严重的是,陷入认同危机的人不仅会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恐惧之中,而且会出现病态性的人格,他们无法判定什么对人有价值。
当然,现代人所需要的道德框架与前现代人们所需要的道德框架有着本质差别。泰勒指出,现代人所需要的认同与前现代人所需要的认同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差别在于,在前现代社会,人们需要根据普遍术语提出调整人们行为的基本的道德框架,否则,人们就会有严重的罪恶感和不可挽回的被逐感。与之不同,在现代社会,我们虽然还使用普遍术语提出诸如人的生命和完整性这些基本的道德问题,但是却不再把依照普遍术语构造所有的道德问题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充分考量有差异个体在获得道德框架方面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赋予人们方向感的道德空间必须是由强势评价或性质差别所规划的空间,通过它,我们可以获得自我认同;根据它所体现的性质差别,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方向;通过它,道德空间得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生作用。道德空间在我们生活中起作用的过程,也是我们获得现代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使我们能够判断什么对我们重要以及什么不重要,它使包括那些依靠强势评价的区分成为可能。正是我们的认同规定着我们在其中生活和选择的性质差别。当然,这样的认同,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可能的表达都更深刻和更具有多面性,因为它被看作是由给予我们根本方向感的东西所规定的生活的整体,这在根本上不同于试图描述它的抽象的道德范畴。
泰勒驳斥了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关于人们可以在没有强势评估框架下也能生活的假定,进一步重申自我是需要在道德的空间和框架中进行认同的自我。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认为,我们可以不接受任何性质差别而回答自己“是谁”的问题,从而把框架看成是我们发明的产物,认为我们没有必要澄明道德框架。然而,泰勒认为,我们探寻空间方向感、形成道德框架,并非要回答人为的、非必要的问题,并非像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那样接受先前的范畴,相反它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它属于存在于有关强势评价之善的问题空间中的人类特质,是先于所有的选择或偶然的文化变迁的。”[8]42脱离了所有框架的自然主义主体往往处在令人震惊的病理学状态之中。“这种人不知道他立足于何种根本的重要性问题之上,在所有这些问题中没有任何方向感,自己不能对它们做出回答。”[8]42他们深陷混乱之中,甚至不如那些仅仅将未经思考的微不足道的东西看得无比重要的浅薄的人。不接受区分高级和低级目标的传统框架的功利主义,在本质上对某种合理性和善的理想有着强烈的承诺,认为应当做理性上预测为幸福的事。它的弱点在于,人们往往为了适应自己身处其中的事实,从而忘掉那种强调差别的框架,其中的主体被误认为是无框架的主体。由此可见,框架并不像自然主义和功利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我们发明的产物,而是前在于我们、独立于我们的回答或无力回答的那些问题,决定我们的自我认同的基本框架。
简而言之,泰勒认为,有关道德空间的论述“是对于人类生活中可相信的界限的探讨,是有关其‘超验条件’的论述”[8]43。通过这种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是怎样使生活更有意义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使自己的生活具有意义的可能方式的界限。相反,如果我们无视这种边界,从而把不可理解的人类生活认定为正常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具有基本的道德方向构成了能回答自己是谁的人类对话者的本质特征。
二、对话网络:自我认同的“超验”条件
泰勒认为,处于道德空间中的自我认同,根本不同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对事物的认识,人们无法离开自我解释理解自我,无法离开自我认同形成的原始语境理解自我,因此经验性的对话网络,在自我认同的问题上具有了“历史性在先”的“超验”意味。人们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对话网络这一“超验”条件下才能实现人的自我认识。
具体说,自然科学对事物的认识有四个基本特征:其一,“绝对地”看待研究客体,认为客体意义不依赖于主体,而是客观地基于其自身;其二,客体独立于主体所提供的描述或解释而存在;其三,客体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把握;其四,客体可以在不涉及其环境的情况下被描述。
与之相对,自我认同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不能离开一个人的自我解释去理解自我、制定我的认同,我们只有在自觉地追求善的过程中,才能展现自我;其二,自我部分是由自我解释构成的;其三,自我解释是不能通过清晰的描述加以把握和解释的,完全的表达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试图增进对蕴藏在我们的道德和评价语言中的内容来理解,只能通过反复论证,进一步揭示意义;其四,在不参照周围其他人的情况下,自我无法得到描述,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中才是自我。自我只有在与他人的道德、精神、社会关系中才能形成自我认同,这其实已经包含在“认同”的概念之中了。因为自我认同意味着对“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它需要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在这些关系中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归结起来,在泰勒看来,无论是进行自我解释,还是通过参照他人形成道德方向感,都不能离开语言来研究自我。在此意义上,泰勒指出:“研究一个人就是研究这样一个存在,他只存在于某种语言中,或部分地由这种语言所构成。”[8]48“除非引进语言,我们就没有办法引入人格。”[8]49
自我之所以只有在由语言所决定的“对话网络”中才形成,“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在我们身上找出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10],是因为以下五方面的原因:第一,原初的语境是我们确立自信的“超验”条件。因为我们通过某种方式使用语言,并通过这种语言与他人相联系。这就形成了特定的语境,在这种原初的不可逃避的语境中,我们知道自己所意指的是什么,从而形成对自己的真正的信心。第二,原始的语境使我们能面对面地达成共识。因为人们在利用语言进行交谈时,会使谈论的某个事情成为共同的客体,从而形成我们的公共空间。语言的各种运用,建立、制定、关注和激活了“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中,通过这些为我们而存在的客体的经验,我们形成了意义的一致和判断的一致。第三,只有通过对话网络,自我才可能发现、理解自己的生活和人类生活的新颖方式。因为只有在对话网络中,我们才能既从较早的、更“初级”的观点中汲取营养,又能确立自己对已经拥有的较高的和较独立的观点的自信。第四,急剧的变化或创新也需要建立在对话网络基础上的认同。因为它要求废黜与给定的、历史性的共同体的联系,追求与由固定的善所规定的共同体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并没有割断我们对对话网络的依赖,只是被依赖的对话网络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是与历史性的共同体进行对话,而是与由固定的善所规定的共同体进行对话。个人虽然能超越同时代人的思想和视野的限制进行创新,但是,即使是对新视野的追求,也需要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人的语言和视野相联系。第五,只有通过语言的交谈,我们才能摆脱混乱。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历史共同体进行交谈以确立自己的立场,确认我相信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依赖于志趣相投的共同体(这里我们进行“谈话”的对象不仅包括活着的当代人,还包括已经死去的预言家、思想家、作家等等),依赖他们对我的观点提供无意识的证明。只有与了解我、或有智慧、或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伙伴论谈自己的感受,我们才能阐明它,走出混乱。
泰勒认为,强势的美国个人主义文化进一步证明了自我只能是处于由对话网络编织出来的道德空间之中的自我。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独立性也是被超验地嵌入对话之中的,年轻人所持的态度,本来就存在于“传统”之中。那种否定历史传统的极端个人主义,只是忘记了超验的条件和我们实际态度之间的差别,以为依赖传统纯粹是对独立的嘲笑。其实,即使在个人主义语境下,人们仍然不可能逃离在认同的原初语境中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正是原初境遇赋予了我们“认同”概念的意义,我们通过“从何处”和“向谁说话”的规定,得到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这样的认同,通常不仅与他的道德和精神的立场有关系,而且也与确定的社会有某种关系。离开他人及与他人相关的道德、精神立场、社会关系,孤立的自我或个人是不存在的。现代的个人主义把个人看作是同出身和历史给定的对话网络分开的存在,试图从其自身内引出目的、目标和生活规划,试图仅在它们“正在实现”的范围内寻求“关系”,其实质是忽视了我们被嵌入对话网络之中的事实,使个人成了跳出人类条件的采取英雄姿态的个人。然而,即使是这些英雄的个人也仍然不能摆脱塑造认同的对话网络,仍然需要针对那些在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东西与他志同道合的人进行交流,唯其如此,才能详尽阐述自己的新语言。
总之,泰勒看到了善与自我之间的关系,指出“自我”是与“其他自我”有着共同语言的“自我”,因而需要通过彼此间形成的对话网络,编织道德空间,确立自信,达成一致,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在对话网络中,通过形成追求善的叙事来认识自我,形成自我认同。
三、追求“善”的叙事:自我认同的文化形式
泰勒认为,我们只有在与善紧密相关的叙事中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过上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性质差别以叙述的形式规定着我们的认同,赋予我们生活以意义。
一方面,泰勒认为,自我是处于由“善”定位的道德空间中的自我,只有能自觉地回答自己的行为与善之间的关系,才会有方向感。其原因有二:一是,正如在物理空间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需要一张好的地图,同样,在道德空间中,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与善的,或极其重要的、或基本的东西相关联,需要一个合理的道德框架,把自己定位在由性质差别规定的空间中,这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渴望。现代人对于与善相关的方向感的渴求,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们对实现高级存在和追求永恒渴望一脉相承,只是在现代社会,它主要通过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追问表现出来。人们要追问生活是否有价值或有意义,追问它是(或已经是)充实而有重大价值的,还是空虚而琐碎的?追问我们的生活是否具有统一性?我们是否只是毫无目的和意义地虚度时光?
当然,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对何谓与善的联系有不同的理解。信仰特定宗教的人,把“接触”善理解成与上帝的联系;信奉荣誉伦理学的人,渴望名誉,避免坏名声、羞愧和耻辱;理性而自制的人,渴望使生活井然有序,难以忍受被对低等事物的渴望所吞没;肯定日常生活的某种现代形式的人,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能被诸如工作和家庭生活所推动,并进而推动这种生活;希望通过表达赋予生命以意义的人,渴望通过一种被认可的艺术或知识手段进行表达;如此等等。基于对与善联系的不同理解,人们获得了不同的道德框架,获得了自己的方向感。
二是,如同在物理空间中,我们需要知道怎样确定自己的位置一样,在道德空间中,我们也需进一步确定自己在特定的道德框架中的位置,这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无法停止对自己身在何处的关切。当我们获取更大的名誉,或在生活中引入更多的秩序,或在家庭之爱的丰厚喜悦中,在对妻子儿女的关注中,在变得更加稳固的家庭中看到生活的意义;或者在表达活动的某种形式中,认为自己努力趋向于或接近实现自己所规划的东西,我们就可以在生活中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因为此时,我们认为自己在相应的道德框架中处于恰当的位置,并对之感到满意。反之,我们就会遇到是与否的问题的触动和挑战。这种是与否的问题关注的是我们趋向还是背离自己生活的方向。如果人们认为自己背离了自己的生活方向,就会被这种感受撕裂。在被撕裂的生活状态下,人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那些把自己视为被低级的驱动力所掌控的人,那些因为不得不干一种固定的工作而感到自己不能得到真正生活的人,那些为自己莫名其妙地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感到内疚的人,那些为感受不到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伟大而烦恼的人,那些在成长中受到家长悉心呵护、却认为使家长感到充实的孩子,那些与民众的苦难、或历史的大潮、伟大的事业比较起来只是获得可怜的安逸、狭隘而又沾沾自喜的人,等等。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处于道德框架的不恰当位置、背离了自己的生活方向而感到无助。
总而言之,“我们与善相关的方向感不仅要求某种(些)规定着性质上较高的形态的框架,而且要求一种我们在其中处在何处的感觉”[8]61,即对我们来说,不仅要知道自己与什么样的善相联系,而且还要知道我们正走向何处,即是否趋向我们所认同的善。前者涉及或“多”或“少”的问题,后者涉及“趋向”或“背离”、“是”还是“不”的问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直接关涉到生活的方向。没有前者,我们就无从趋向善;没有后者,没有在必然变化和生成的某种东西,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只有当我们既知道自己处于怎样的框架中,又能获得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才可能获得方向感,形成自我认同。
另一方面,泰勒认为,我们要想使生活更有意义,就必须用叙事来把握我们的生活,这是富有意义的人类生活的另一个条件。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有最低限度的意义,为了拥有认同,我们需要趋向善,趋向某种性质差别和无与伦比的优异性,我们要把“善”编进自己生活的故事之中,进而在善的观照下叙述和把握自己的生活。这是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另一个基本条件。叙述与单纯地构造我们的生活不同,它强调的是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以及在不同的可能性之间,规划自己的生活与善之间的关联。为了知道自己是谁,我们必须通过叙述把握自己是怎么样生成的,将走向何方?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根据不同的可能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和方向,需要以“因而随后”这个形式理解自己现存的行为,这是包含在我的生活中的叙事。
只有通过回溯,追问那种我们在瞬间所意识到的完满而强烈的生活意义在对生活的叙事中所起作用,才能回答我处在道德空间的什么位置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才能找到生活意义的坐标。这是因为通过回溯,我们才知道“我们依靠我们生成为什么,依靠我们如何达到那儿的叙说,来决定我们是什么”[8]70。我们只有知道自己如何达到目的,为达到目的而付出努力,并因此获得相应的道德经验,才可能强烈而真实地感受生活的意义。例如,我们只有通过努力追求完美的状态,才能获得对那种伟大的完美状态的预先理解。我们只有通过努力去寻求善,经历失败然后获得它们,才能在此过程中塑造着道德。相反,通过一刹那间(包括陷入相信天使对自己讲话的沉迷状态的瞬间,感觉到巨大的意义的瞬间,感觉到了克服通常会压垮我们的那些困难的汹涌激荡的巨大力量的瞬间),我无法知道我达到了完善还是处于半路中?我们只有回溯,追问它对生活的叙述起什么作用,才能理解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成长和德性,在多大程度上是幻觉,从而正确认识自己在所处道德空间的位置。
换言之,自我不是洛克意义上中性的、点状的自我,而是存在于由善所决定的道德空间或特定的问题空间中的自我,在善以及确立与它的关系的过程中调整自己。因此,自我为了使现在的作为有意义,就要确立自身与善的关系,就要叙述性地理解自己的生活,就只有在故事中才能知道自己成为什么。我们可以规划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整个生命的方向规划未来的故事,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探索。没有对自己成为什么的某种理解,就不知道自己在何处或是谁。只有作为成长和生成的人,经历成熟或退化、成功或失败,才能认识自我,形成关于自我成长和生成的意识。因为自我理解不可能是瞬间的,而是有时间的深度和体现出叙述性的。只有在自我的全部生活中,甚至通过让未来恢复过去,使之成为具有目的的生活叙说的组成部分,使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才能使自我的生活有意义、有分量、有内容,即趋向某种完美。
总之,泰勒认为,我们只有在与他我的关系中,只有在理解与善的关系中才能形成自我认同。对我们来说,关键的、不能逃避的问题是确定与善的关系,以叙事的形式来理解我们的生活,努力给我们的生活以意义。建立与善的关系,叙述地理解我们的生活,是人类主体活动的不可逃避的结构性要求。叙事是我们获得现代自我认同的文化形式。
小 结
可以说,泰勒与马克思一样,都认为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自我不是抽象的自我,而是处于社会历史之维的自我,只有立足于社会历史之维的自我或人的生命存在,才能超越西方个人主义所带来的自我抽象的意义危机。二者的差别在于,他们分别从物质基础和道德追求的维度探寻了决定人们安身立命的具体条件。马克思将个人首先看成是处于社会历史经济空间的个人,认为个人只有通过适应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所决定的自由自觉的生活方式,才能在满足彼此包括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在内的整体性生命需求的基础上,确证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泰勒有关于善的道德诉求和叙事,只能在特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展开;离开了由特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条件,只能导致道德主义。马克思认为,道德由迄今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们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物质条件空谈道德理想的实现。与之不同,泰勒则将个人看成是思想道德空间中的自我,认为个人只有在追求以善为核心的叙事中,才能赋予生活以意义;物质因素只有在相应的道德框架中才会发挥作用。马克思意义上的道德诉求在本质上是启蒙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道德诉求的混合物。泰勒并非不关注物质条件在道德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他认为在价值多元、个人主义文化已经导致人的意义危机的背景下,当务之急是在道德文化领域重新塑造使人超越个人主义所带来的认同危机的框架。
对于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国家来说,物质条件仍然是影响人们道德素质提高的根本性因素,马克思基于社会历史和经济空间的道德思考仍然是我们在新时代背景提升全民道德素质的必须立足的基点。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我国大众价值选择并使其身陷意义危机的一元。在此背景下,泰勒有关自我认同的道德哲学思想,无疑为我们在道德文化领域超越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为我们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