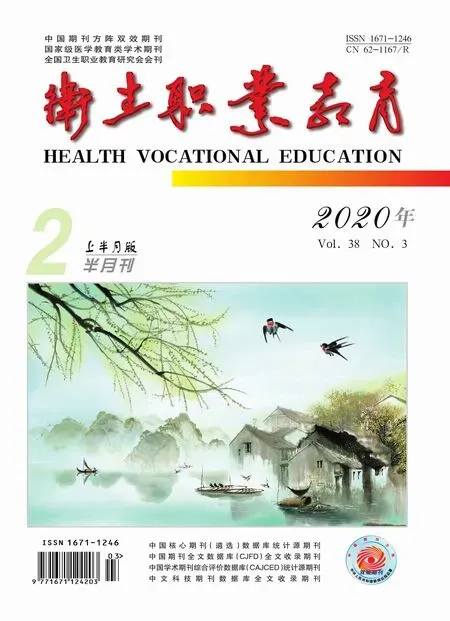医学人文伦理教育在研究生胚胎学教学中的探索
王曌华,刘玉荣,张征宇,杜宝玲,李锦新,马宁芳
(广州医科大学基础学院,广东 广州 510182)
胚胎学主要是研究从受精卵发育为新生个体的过程及其机制的学科,研究内容包括生殖细胞的发生、受精、胚胎发育、胚胎和母体关系、先天畸形等[1]。研究生阶段开设的胚胎学课程主要面向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胚胎发育的规律及胚胎学研究进展,为临床应用提供知识背景。随着科技的进步,分子生物学技术日新月异,胚胎学研究发展也一日千里,与之相伴的就是和胚胎相关的人文伦理问题。因此,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在研究生胚胎学教学中融入人文伦理教育非常必要。一方面有助于新一代医学生了解目前国际和国内胚胎学研究前沿进展;另一方面,通过了解国内外学术界的各类共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并且结合实际更好地激发对胚胎学的学习兴趣。
1 在现代胚胎学发展教学中融入国内外与胚胎学有关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基因编辑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虽然早在1987年,Ishino Y就在原核生物中发现了可以引导核酸酶进行切割的一段基因序列[2],但因没有作用机理的实验依据,因此未得到重视。直到2002年,Jansen R通过对这样的结构进行命名(称为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CRISPR)[3],该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从原核到真核,科学家通过这把基因剪刀,像编辑文字一样编辑基因,既可以切除不需要的基因或遗传物质,还允许添加所需的序列或基因。因此,从理论上,在胚胎时期对“生物的整套遗传物质——基因组”进行精确地插入、敲除和改变条件已经具备。目前这一技术在医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若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胚胎,可以预防未来后代的某些特定遗传病的发生。2015年,中山大学黄军就教授等利用CRISPR/Cas9技术,试图修改人类胚胎中可能导致地中海贫血的基因,为治疗中国南方儿童常见的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症提供了可能[4]。相关研究成果在学术杂志《蛋白质与细胞》上发表,尽管该团队使用的是医院废弃的86份异常胚胎,但论文发表后仍引发科学界的集体担心和忧虑。2017年8月,美国俄勒冈州科学家针对含有引起先天性心脏病的基因突变的人类受精卵,在实验室成功剔除了该突变基因[5],胚胎在实验室健康成长,突变的基因被修正,可以移植回母亲子宫内。虽然胚胎最终在实验室销毁了,但这意味着可以提前修改胚胎,在出生前治愈先天性疾病。2018年11月,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在中国诞生,这一新闻在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报道称,贺建奎教授用CRISPR技术这把基因剪刀,对处于单细胞的受精卵进行基因编辑,使HIV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的CCR5基因失去功能,从而使婴儿获得对艾滋病先天免疫的能力。不得不承认,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有效推动了人类胚胎学的研究。然而,和每一种新技术的应用一样,基因编辑技术同样存在着利益、风险、规则、伦理和社会影响等问题,更值得我们探讨。
目前有关于半人半动物的胚胎研究,科学家将人类胚胎的细胞注射进小鼠胎儿的脑内,结果人类细胞替代部分小鼠脑组织,此小鼠异常聪明,记忆力和认知力超群[6]。为解决器官移植问题,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在实验室将人类干细胞种植到羊胚胎,形成一个羊人结合的跨种类胚胎,其中人类细胞不到1%,羊细胞超过99%,胚胎成功存活,在实验室28天时销毁。在此之前,该实验室已经成功将人细胞注射入早期猪胚胎中。这一实验的最初目的是避免器官移植后的排斥反应,因此将部分人类细胞注射入胚胎,产生人羊或人猪胚胎,可以作为器官移植的供者。但这种生物制造过程本身就是对医学伦理极大的挑战。
2 在现代胚胎学发展教学中融入国内外与胚胎研究有关的人文伦理知识
在教学中不断强调与胚胎研究有关的人文伦理知识,是由医学生的责任以及胚胎这一特殊的对象决定的。在科学发展的长河中,科学技术和伦理道德之间的差异,总会带来难以避免的矛盾和冲突。
2.1 科技研究的不足使相关技术的副作用难以预料,因此伦理把关尤为重要
1999年美国一位18岁的鸟氨酸氨甲酰转移酶缺陷症患者接受基因治疗,结果4天后意外死亡,导致整个行业被打入冷宫长达十余年。而当时参与治疗过程的Wilson博士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自己1999年知道10年后的知识,无论如何也不会做这个试验。正是由于基础科学研究不足、人们尚未掌握人体对基因治疗可能的免疫反应就将这一技术贸然用于临床,才导致了试验失败。
而目前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对于人体安全的影响仍处在基础研究阶段,已知的安全问题如下:(1)脱靶效应:编辑了不该编辑的地方。这一缺陷极大地降低了基因编辑的安全性,也使得被编辑的胚胎面临着未知而不可控的风险。(2)基因编辑后部分胚胎是嵌合体,即只有部分细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嵌合体的胚胎在发育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以及其对后代有什么影响,仍不能完全估量。(3)技术应用过程中使用的Cas9核酸酶和sgRNA对于胚胎发育的安全性仍然未知。因此,在使用这一技术对于胚胎这一特殊对象进行改造时,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将这一技术应用于临床,无论是患有什么疾病的患者,充分告知其详情尤为重要。因为人们面对的不只是已知的益处,更多的是连研究者也完全不知的结果。
2.2 目前关于基因编辑修改人类胚胎所达成的共识,需要全体科学家共同遵守
2015年中山大学黄军就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公开发表胚胎基因编辑研究后,引发的冲突促成了相关国际伦理制约机制的建立。2015年12月,中、英、美等国共同成立了“人类基因编辑:科学、医学和伦理委员会”,并起草了报告《人类基因编辑:科学、伦理学和治理》。报告中原则上承认了胚胎基因编辑在伦理上的可接受性,但也充分强调了使用的前提,即“可以允许生殖系基因组编辑试验,但仅在要做许多研究以满足批准临床试验的现有风险/受益标准之后,仅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及在严格的监管之下才能开展”。
2018年7月英国纳菲尔德生物伦理学协会所发布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在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影响的条件下,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修改人体胚胎、精子或卵细胞细胞核中的DNA“在伦理上可接受”。
我国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印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提出“人类早期胚胎遵守14天原则”,即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他动物的生殖系统。而贺建奎教授所公布的新闻倘若为真,则打破了我国人类早期胚胎所遵守的14天原则。
纵观目前各国关于基因编辑胚胎所达成的共识,其伦理审批保护的是我们每个人“为人”的权利。在每一项科学研究开展前,伦理委员会需不断进行伦理探讨,保证最基本的人权。20世纪30年代,纳粹政权为了实现所谓的“人种优选”,颁布法律强制规定对遗传病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绝育,并最终催生了“种族清洗运动”。而今,人类胚胎编辑则是人们掌控基因的开始,先天的基因不再是无法更改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可能大大减少。试想中国古代的君主追求长生不老,而今对基因完美的追求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
虽然针对胚胎的基因编辑目前尚局限在修复有疾病的胚胎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类在自身极限上的不断突破也并非不可能。如果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好恶延伸到胚胎选择上,会带来怎样的冲突和矛盾呢?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需要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一项技术的好坏更多地取决于谁去用,怎么用。培养学生用辩证思维来看问题,对这种争论性问题学会分析利弊,避免单一角度看问题导致的片面性。
3 从胚胎发育过程和畸形胚胎处理方面探讨胚胎的生命权利
关于胚胎生命权利的探讨,首先涉及对人的生命标准的探讨,如以分娩的一刻作为生命标准,还是以父母和社会承认且由社会授予婴儿权利的时刻作为生命标准。医学伦理学认为,人的生命就是自觉和理性的存在,生命就是从分娩后的新生儿得到社会承认时开始的[7]。由此而产生的关于孕期胚胎的出生权利的讨论,一向众说纷纭。每个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但各个国家的规定也有差异。澳大利亚等国家认为非致死亡的胚胎疾病不是引产的必要指征,比如孕30周发现胎儿脑积水,即使明知出生后可能影响到胎儿智力也禁止引产。从某种程度上,这种措施可以减少父母对于胚胎的选择,但相对会增加家庭及社会养育下一代的负担。目前在我国,孕中期后的引产是严格把控的,但对于胎儿畸形的程度并没有明确划分,因此一旦出现畸形,胎儿的生命选择权全在父母。例如有的夫妻会因为胎儿孤立肾选择放弃胎儿,从理论上来讲,患有独肾综合征的胎儿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正常存活、生长发育的。所以,胚胎的生命权利需要被考虑,但是具体执行细则仍然值得探讨。
美国阿肯色州州议会通过新的法案,将胚胎视为家庭成员,也就是说女性如果要打胎,必须获得胎儿父亲的同意。该法案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如果被强奸而怀孕的女性也必须通知强奸犯才可以打胎,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对于胚胎权利的过度保护导致对于人权的不尊重。可见,胚胎的生命权利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情况下需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在教学中和学生探讨胚胎的生命权利,有助于增强其对于生命的敬畏,提高社会责任感以及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能力。
总之,在研究生胚胎学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非常必要。相较本科生,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初步医学基础知识培训,并且需要了解更多最新研究进展。授课教师通过提高自身人文素质,在教学中引入人文精神和医学伦理讨论,培养学生的高尚医德,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