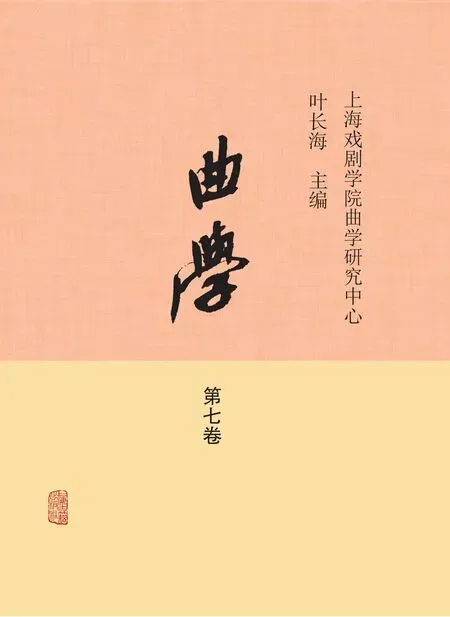南曲中的“犯调”及其与“集曲”的差异
刘 芳
关于“犯调”一词,古今词曲家都提出了“二义”说。即“犯调”同时存在两种意义,一种是“宫调相犯”,一种是“词句相犯”。如万树《词律》[江月晃重山]调下云:“词中题名‘犯’字者,有二义。一则犯调,如以宫犯商、角之类;梦窗云‘十二宫住字不同,惟道调与双调俱上字住,可犯’是也。一则犯他词句法,若[玲珑四犯]、[八犯玉交枝]等,所犯竟不止一调。但未将所犯何调著于题名,故无可考。”(1)(清) 万树《词律》,中华书局,1957年,第372页。
万树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犯有二义”的,后世很多学者也沿袭了这一观点。下举数例:
任讷《散曲概论》谈到曲中“集曲”、“联章”二体与词体的关系,云:“集曲犹词中之犯调与摊破。”(2)任讷《散曲概论》,任讷编《散曲丛刊》,中华书局,1931年,第18页。认为曲体中的“集曲”与词体中的“犯调”是性质相同的。
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之《宋代大曲与词》一节提到词之“犯调”对南北曲的影响,他举周邦彦[六丑]、[玲珑四犯],刘过[四犯剪梅花],侯彦周[四犯令],仇远[八犯玉交枝]等例,云:“此项体制,对于后世的南北曲,颇多便利之处。”(3)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68—69页。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南宋时流行以集曲的方式合成新调,也称为犯调。这不是宫调相犯,而是词调相犯。宫调相犯是运用变调变奏的方法创制新调,词调相犯则不过利用原有旧调,将其美听的乐段、字句组合成曲。”(4)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13页。
夏承焘《月轮山词论集·犯调三说》:“词中犯调有二义,一为宫调相犯,二为句法相犯。”(5)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31页。
事实上,“犯调”从唐代开始发展,一直到宋元时期的南戏中,都有相对明确和固定的音乐方面的涵义与范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或者涵盖曲体文学中的“集曲”概念。
一、 “犯调”溯源
“犯调”初始于唐代,当时又叫做“犯声”,“是指在一首乐曲中或几首乐曲连续奏唱时发生调高或调式的转变,或者调高和调式同时都有改变的情形。大体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转调’”(6)夏野《古代犯调理论及其实践》,《音乐艺术》,1982第3期,第18页。。元稹诗《元和五年予官不了,罚俸西归,三月六日至陕》写道:“那知我年少,深解酒中事。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7)谢永芳编著《元稹诗全集汇校汇注汇评》,崇文书局,2016年,第98页。其中的“犯声歌”就是说一支在曲调内部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宫调的歌曲。
至宋代,犯调理论发展得更加完善,宋陈旸《乐书·犯调》载:“乐府诸曲,自古不用犯声,以为不顺也。唐自天后末年,[剑气]入[浑脱],始为犯声之始。[剑气],宫调;[浑脱],角调。以臣犯君,故有犯声。明皇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时人以为新意而效之,因有犯调。”并注云:“五行之声,所司为正,所欹为旁,所斜为偏。所下为侧,故正宫之调,正犯黄钟宫,旁犯越调,偏犯中吕宫,侧犯越角之类。”(8)转引自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265页,注②。
再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五载:“今越调[兰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遗声也。此曲声犯正宫,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9)转引自岳珍校正《碧鸡漫志校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第7页。
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有言:“虽如此,然诸调杀声,亦不能尽归本律。故有祖调、正犯、偏犯、傍犯,又有寄杀、侧杀、递杀、顺杀。凡此之类,皆后世声律渎乱,各务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间亦自有伦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备纪。”(10)(宋) 沈括《梦溪笔谈》,岳麓书社,1998年,第246页。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从唐代至北宋,“犯调”明确指音乐角度的曲内宫调更换,并且根据不同的宫调变化程度,有“正犯”、“旁犯”、“偏犯”、“侧犯”之类。
二、 词体之“犯”
北宋年间,词体日渐繁盛,一些精通音律的词人开始使用“犯调”的手法丰富词调的创作。此时的“犯”也明确是音乐上的宫调变换,而非词调字句的连缀使用。
例如,柳永作[小镇西犯]、[尾犯]。据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自宣政间,周美成、柳耆卿辈出,自制乐章,有曰[侧犯]、[尾犯]、[花犯]、[玲珑四犯]……”(11)(宋) 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1985年,第10页。再如周邦彦作[侧犯]、[花犯]、[倒犯]、[玲珑四犯]等。
关于北宋时期文人词的犯调作品,张炎《词源》卷下评论道:“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而美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或移宫换羽,为三犯、四犯之曲,按月律为之,其曲遂繁。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词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12)蔡桢《词源疏证》,中国书店,1985年,下卷第1页。
考察《词律》、《钦定词谱》,凡北宋词作,牌名中有“犯”字的词调都是柳永、周邦彦二人创作的。由以上材料可见,北宋时期词体的犯调具有如下特征: 一、 凡是调名中有“犯”字的,“犯”都是音乐指义而非词句指义;二、 “犯调”的创作必须由精通音乐律吕的词作家完成;三、 “犯调”的创作在数量众多的北宋词创作中并不常见,属于少数现象。
到南宋时期,“犯调”之词的创作仍旧数目有限,并基本限于姜夔、吴文英、张炎等通晓乐理的文人。例如姜夔《凄凉犯》词自注云:“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夕起骚骚然,予客居阖户,时闻马嘶,出城四顾,则荒烟野草,不胜凄黯,乃著此解。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凡曲言犯者,谓以宫犯商、商犯宫之类,如道调宫‘上’字住,双调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调曲中犯双调,或于双调曲中犯道调,其他准此。唐人《乐书》云:‘犯有正、旁、偏、侧,宫犯宫为正,宫犯商为旁,宫犯角为偏,宫犯羽为侧。’此说非也,十二宫所住字各不同,不容相犯。十二宫特可犯商、角、羽耳。”(13)(宋) 姜夔著,夏承焘校,吴无闻注释《姜白石词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8页。
据杨荫浏、夏承焘等学者的考察,[凄凉犯]应当属于“仙吕调犯双调”。夏承焘云:“陆本及《花庵词选》调下有‘仙吕调犯商调’六字小注,他本皆无,当是陆据《花庵》补入。‘商’应作‘双’。”(14)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中华书局,1958年,第42页。杨荫浏云:“或疑此曲为道调犯双调,其实并无根据。本曲名[凄凉犯],序中复著‘琴有凄凉调,假以为名’云云,是‘凄凉’二字,系假自琴之宫调名称。案琴上之凄凉调为羽调;今此曲以‘么’为结音;而羽调之以‘么’字为结音者,只有夷则羽,即仙吕调;则作为仙吕犯双调,佐证似较坚强。”(15)杨荫浏、阴法鲁《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57年,第32页。
按照姜夔的说法,词的“犯调”在南宋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即所犯的两调必须保持“结音”相同。姜夔的犯调理论其实是将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中的犯调与作词的实践相结合提出来的,是适合于词体创作的词体犯调理论。姜夔只承认同主音(主音一般就是结音)的宫调可以相犯,反对不同主音的宫调相犯。如前文陈旸、沈括所言,“旁犯”、“偏犯”、“侧犯”都是“杀声不能尽归本律”的,也就是曲调结尾的音会发生变化,这种结音发生变化的宫调变换形式,在唐宋乐曲中也属于“犯调”的类别。但是在姜夔看来,这些结音变化的变换宫调的方式,在词体创作中是不可取的。姜夔对犯调理论的改进,源于词体的创作要求——词不但要受音乐旋律的约束,也要满足韵文创作的规则。具体到“结声”层面,因为词有押韵的要求,每一韵段的韵脚相同,就造成了“结声”必须要保持一致,才能够使得创作出的词调在每一韵段结束的时候,“音乐”、“字声”能够重复并统一地重复。所以,在姜夔的理论中,“犯调”是一种词体拓展的方式,并具备了比音乐理论中的“犯声”更加严格的要求,即在变化调高的同时,保持主音、结音的相同。
有学者认为,张炎的犯调理论和姜夔并不一致,如张炎云:“以宫犯宫为正犯,以宫犯商为侧犯,以宫犯羽为偏犯,以宫犯角为旁犯。”(16)蔡桢《词源疏证》上卷,第54页。又于《结声正讹》一节云:
正平调是マ字结声,用平直而去。若微折而下,则成ㄅ字,即犯仙吕调。
道宫是ㄅ字结声,要平下。若太下而折,则带∧一双声,即犯中吕官。
高宫是可字结声,要清高。若平下,则成マ字,犯大石。微高则成幺字,犯正宫。
南吕宫是∧字结声,用平而去。若折而下,则成一字,即犯高平调。
右数宫调,腔韵相近,若结声转入别宫调,谓之走腔。若高下不拘,乃是诸宫别调矣。(17)同上,第56页。
表面上看,似乎张炎否定了姜夔的看法,认为结声如果不同,则犯别调,这也是一种“犯调”。其实,张炎此处所论同样是在强调: 词体的创作中一定要注意“结声”保持一致,如果结声发生讹误,就是音乐理论中的“旁犯”、“偏犯”、“侧犯”。这些“犯”是音乐层面上可以进行的,但是在词体的创作中是不提倡的,所以张炎把这种“腔韵相近、结声转入别宫调”的做法称之为“走腔”。
根据夏野先生的研究,符合姜夔词体犯调理论的犯调形式有如下几种:
1. 正宫、越调、中吕调、高大石角,两两可以互犯;
2. 中吕宫、高大石调可以互犯;
3. 道宫、双调、仙吕调,两两可以互犯;
4. 南吕宫、小石调、黄钟宫、林钟角,两两可以互犯;
5. 黄钟宫、商调、高般涉调,两两可以互犯;
6. 大石调、正平调、双角调,两两可以互犯;
7. 歇指调、般涉调、越角调,两两可以互犯;
8. 高平调、小石角可以互犯。(18)夏野《古代犯调理论及其实践》,《音乐艺术》1982年第3期,第21页。
这其中应用最广泛的犯调当属姜夔[凄凉犯]所用的“仙吕调犯双调”,仙吕调与双调是上下四度的转调关系,相互转化比较自然,而且能保证结声相同,所以在宋元之际,干脆出现了“仙吕入双调”一大类的曲调。周维培《曲谱研究》云:“仙吕入双调的产生,与犯调有关。该宫调所辖曲多为双调与仙吕所犯后出现的新调,在长期使用中逐渐与双调或仙吕分离,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新类别。”(19)周维培《曲谱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然而到清代,很多曲家已经不明犯调的真实含义,《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干脆去掉了“仙吕入双调”一类,云:“南谱旧有仙吕入双调,夫仙吕、双调,声音迥别,何由可合?”(20)周祥钰、邹金生《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湾) 学生书局,1981年,第37页。但是在南曲中,“仙吕入双调”是长期真实存在的犯调用法,《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也云:“仙吕入双调之名,南北诸谱皆载。此名不知何,在于宫调并无是名。假仙吕宫有双调曲,是名仙吕入双调;若商调有仙吕宫调曲,即商调入仙吕调。此讹传也。”(21)傅雪漪《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1991年,第281、285页。由此可知,在明代的南曲实际创作中,“仙吕入双调”的犯调之曲十分常见,应当要追溯到南宋词的仙吕调犯双调,只是清人不明其意,反以为这是前人的错讹。
另外,我们考察南宋词人的犯调作品,宫调相犯的情形几乎都符合姜夔的说法。如吴文英《梦窗集》载[瑞龙吟],是大石调犯正平调;[玉京谣]、[古香慢]是商调犯黄钟宫;[琐窗寒]为越调犯中吕又正宫。这说明姜夔、张炎所总结的词体犯调“结声一致”理论是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南宋时期,词体中的犯调形式基本仍然由通晓音律的文人创作,而且在姜夔的推动下发展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则,即在调高转变的同时,保持结声的一致。
南宋时期词名带“犯”的调牌还有侯寘[四犯令]、刘过[四犯剪梅花]。有人认为这样的词调并非宫调相犯,而是词句相犯。如刘过[四犯剪梅花],又名[锦园春三犯],卢祖皋《蒲江词稿》有[锦园春三犯],自注由[解连环]、[醉蓬莱]、[雪狮儿]三曲合成。刘过[四犯剪梅花]同此。于是万树《词律》说:“此调为改之所创,采各曲句合成,前后各四段,故曰‘四犯’,柳词[醉蓬莱]属林钟商调,或[解连环][雪狮儿]亦是同调也。‘剪梅花’三字,想亦以剪取之义而名之,但前段起句与[解连环]本调全不相似,殊不可解。”(22)(清) 万树《词律》,第692页。
[四犯剪梅花]词如下:
水殿风凉,赐环归、正是梦熊华旦。([解连环])
叠雪罗轻,称云章题扇。([醉蓬莱])
西清侍宴,望黄伞、日华宠辇。([雪狮儿])
金券三王,玉堂四世,帝恩偏眷。([解连环])
临安记、龙飞凤舞,信神明有后,竹梧阴满。([解连环])
笑折花看,裛荷香红浅。([醉蓬莱])
功名岁晚,带河与、砺山长远。([雪狮儿])
麟脯杯行,狨鞯坐稳,内家宣劝。([解连环])
万树认为,所谓“四犯”是集了三首词调的四个部分,这三个词调应该属于同一宫调,但事实并非如此。“四犯”用于词牌名,就是指宫调变化了四次。除了[四犯剪梅花],以“四犯”为名者,还有周邦彦所创[玲珑四犯]与首调见于侯寘的[四犯令]。[玲珑四犯]如前文所说,是周邦彦移宫换羽的犯调之作。[四犯令]原词如下:
月破轻云天淡注,夜悄花无语。莫听阳关牵离绪。拚酩酊、花深处。
明日江郊芳草路,春逐行人去。不似荼蘼开独步,能着意、留春住。
其句式十分整齐,总共四个韵段,一三韵段句格一致,二四韵段句格一致,显然并非从四支词调中截取四段形成的,而是先后四次更换宫调,所以称为“四犯”。事实上,清代词学家中只有万树明确认为“四犯”是集四词调。清人杜文澜作《词律校勘记》,有按语云:“秦氏玉竹云,此调两用[醉蓬莱],合[解连环]、[雪狮儿],故曰‘四犯’,所谓剪梅花者,梅花五瓣,四则剪去其一,犯者谓犯宫商,不必字句悉同也。”(23)潘慎《中华词律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77页。
与杜文澜相同,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四犯”就是“转调四次”,如潘天宁《词调名称集释》释“四犯”云:
[四犯翠连环]四犯: 四次犯调,即指一曲中移调变奏四次,亦即转调四次,故称四犯。
[四犯剪梅花]四犯: 调名本意即以四次转调的形式歌咏折梅花。
[四犯令]四犯: 指一曲中转调四次,故称四犯。(24)潘天宁《词调名称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6页。
通过对周邦彦、侯寘“四犯”词的观察与清人对[四犯剪梅花]牌名的解读,可知“四犯”之“犯”为宫调之犯。所以在[四犯剪梅花]中,词调句式不必完全遵从[解连环]等原词句式。由上述材料亦可见,南宋词家创作的[凄凉犯]、[四犯令]、[四犯剪梅花]这三支以“犯”为名的词调,其“犯”仍然指音乐层面的宫调变化。所以,两宋时期词体的发展中,“犯调”都是由通晓音乐的文人完成的,都表示音乐调高上的变化。南宋时期的犯调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犯调之法出现了对“结音”一致的要求。其次,在进行音乐调式转变的同时也可以采用不同词调的句式,也就是说“犯调”可以仅仅变化音乐,如[凄凉犯],也可以将“犯调”和“集词”同时进行,如[四犯剪梅花]。
需要注意的是,不追求音乐调高变化,仅仅是集合不同词调的句式的“集词”形式,在南宋时期也出现了。典型者如[江月晃重山]、[南乡一剪梅]、[八音谐]。
万树将这类词也看作犯调,并认为这类“集词”是犯调的初始起源,如《词律》[江月晃重山]下注:“此后世曲中用‘犯’之嚆矢也。词中题名‘犯’字者,有二义。一则犯调,如以宫犯商、角之类;梦窗云‘十二宫住字不同,惟道调与双调俱上字住,可犯’是也。一则犯他词句法,若[玲珑四犯]、[八犯玉交枝]等,所犯竟不止一调。但未将所犯何调,著于题名,故无可考。如[四犯剪梅花]下注小字则易明,此题明用两调名串合,更为易晓耳。此调因[西江月]在前,[小重山]在后,故收于[西江月]后,犹[江城梅花引]收于[梅花引]后也。”(25)(清) 万树《词律》,第372页。
然而,万树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混淆了“犯”与“集”这两种词体变化衍生的方式。[玲珑四犯]、[八犯玉交枝]是通过变化音乐调高创制的词调,[江月晃重山]则是连缀两只词调的句子创制的新词调。王奕清的认识则更加准确,其《钦定词谱》于[南乡一剪梅]下注云:“旧谱以此与[江月晃重山]词皆为犯调,不知宋词名‘犯’者,取宫调相犯之意,如仙吕调犯商调,为羽犯商类,从来未有以两调相犯为犯者。南北曲如此者更多,其误至今犹相沿也。”(26)(清) 王奕清《钦定词谱》,中国书店,1983年,第702页。
如此,则[南乡一剪梅]、[江城梅花引]、[江月晃重山]一类将两支词调的句子集合在一起形成一支新的词调,才类似于后世的“集曲”。这种方式与“犯调”有本质区别,前者是文字角度的变化,后者则是音律层面的变化。
最明显而明确的区分就是,如果词牌名中有“犯”字,那么这首词会在调高上发生变化,如果词牌名没有“犯”字,便只是用数首调名串联在一起,或者仅仅标明所集词调的数目。清人也有注意到这一点的,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宫调发挥》云:“又有所谓犯调者,或采本宫诸曲,合成新调,而声不相犯,则不名曰犯,如曹勋[八音谐]之类是也。或采各宫之曲合成一调,而宫商相犯,则名之曰犯,如姜夔[凄凉犯]、仇远[八犯玉交枝]之类是也。”(27)(清) 方成培《香研居词麈》卷五,《啸园丛书》,光绪二年刊本。虽然方成培仍然将“声相犯”与“采本宫诸曲”都视为“犯调”,但是他注意到了这两者名称上的差异。
事实上,宋代出现了“犯调”与“集词”这两种词调变化、增衍的形式(还有其他形式)。“犯调”是在音乐的角度进行调高的变化,丰富词乐的旋律创作,进而形成新的词调,而“集词”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既有的词调进行拆解和重新组合。“犯调”的创作也可以集其他宫调词调的句式,“集词”的创作也可能集宫调不同之词。也就是说,实践中很可能出现既是“集词”又是“犯调”新词调,不过,“集词”和“犯调”这两种新调创制形式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其本质也是不同的。二者最明显的差异就是牌名,前者以“犯”为名,后者以原词名串联或提示所集词调的数目。
三、 南戏中的“犯调”
南戏所用的曲调,如徐渭所言,是“宋人词益以里巷歌谣”(28)(明) 徐渭《南词叙录》,李复波、熊澄宇《南词叙录注释》,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15页。,这些构成南戏曲调系统的词乐与民间音乐自然也有其宫调属性,也能够使用不同的宫调进行“犯调”的创作。同时,南戏也出现了大量的“集曲”作品,“犯调”与“集曲”在南戏中仍然是并行的两种新调创制方式。可以说,宋词的“犯调”是南曲“犯调”的源头,而宋词的“集词”是南曲“集曲”的源头。
在南戏中,有很多“犯调”存在,同样以“犯”为名,举例如下(29)所引曲调来自《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宋元戏文辑佚》(钱南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六十种曲》。:
1. 《琵琶记》[七犯玲珑]〔香罗带〕-〔梧叶儿〕-〔水红花〕-〔皂罗袍〕〔桂枝香〕-〔排歌〕-〔黄莺儿〕: 南吕-商调-仙吕-商调
2. 《琵琶记》[渔家傲犯]〔渔家傲〕-〔雁过声〕: 中吕-正宫(符合“结声相同”规则)
3. 《杀狗记》[节节高犯]〔节节高〕-〔鲍老催〕-〔黄龙衮〕: 南吕-黄钟(符合“结声相同”规则)
4. 《拜月亭》[忆多娇犯]([忆多娇]为越调,不知所犯何调)
5. 《拜月亭》[二犯么令]仙吕入双调(《南词新谱》云“后四句不知犯何调,故缺之”(30)(明) 沈自晋《南词新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湾) 学生书局,1984年,第798页。,从所属宫调可知当为仙吕调犯双调,与[凄凉犯]相同。)
6. 《拜月亭》[二犯江儿水]〔五马江儿水〕-〔金字令〕-〔朝天歌〕: 仙吕入双调
7. 《拜月亭》[四犯黄莺儿](《南词新谱》云“前六句皆[黄莺儿],后止三句,却云四犯,殊不可解。”却不知“四犯”与词调“四犯”同为转调四次之意。)
8. 《拜月亭》[二犯孝顺歌]〔孝顺歌〕-〔五马江儿水〕-〔锁南枝〕: 双调-仙吕入双调-双调
9. 《小孙屠》[犯衮]〔黄龙衮〕-〔风入松〕: 仙吕入双调
10. 《小孙屠》[四犯腊梅花]([腊梅花]为仙吕过曲,[四犯腊梅花]不知所犯何调)
11. 《张协状元》[犯思园]([思园春]为中吕引子,[犯思园]不知所犯何调)
12. 《张协状元》[犯樱桃花]([樱桃花]不见于曲谱,亦不知[犯樱桃花]犯何调)
13. 《子母冤家》[太平赚犯]([太平赚]为大石调,[太平赚犯]为般涉调,可能为大石调般涉调相犯。)
14. 《王祥卧冰》[风入松犯]: 仙吕入双调
15. 《王魁负桂英》[二犯狮子序]〔宜春令〕-〔狮子序〕-〔柰子花〕: 南吕-黄钟-南吕(符合“结声相同”规则)
16. 《林招得》[犯欢]〔归朝欢〕-〔风入松〕: 黄钟-仙吕入双调
17. 《罗惜惜》[四犯江儿水]〔五马江儿水〕-〔朝元歌〕-〔本宫水红花〕-〔淘金令〕-〔商调水红花〕: 仙吕入双调-商调
18. 《苏小卿月夜贩茶船》[犯声]〔双声子〕-〔风入松〕: 黄钟-仙吕入双调
19. 《苏小卿月夜贩茶船》[花犯扑灯蛾]〔扑灯蛾〕-〔花犯〕-〔扑灯蛾〕: 中吕-双调-中吕
以上曲调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宋元戏文辑佚》以及五大南戏涉及的几乎全部名称带“犯”的曲调,这些曲调无一例外都进行了音乐宫调上的变化,有的集合了两支或两支以上的曲调,如[二犯狮子序]、[四犯江儿水],有的很可能并没有集其他曲调,只是纯粹的音乐变化,如[忆多娇犯]、[二犯么令]等。由此可知,在南戏兴盛初期,“犯调”仍然和词体的“犯”一样,是从音乐出发的。有部分犯调保持了宋词犯调结音相同的特征,但也有一些犯调宫调变化、结音不同,可见姜夔提出的犯调规则,在南戏的实际创作中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守。
不过,犯调和集曲在名称上的界限还是非常清晰的,调名带“犯”的,都是曲中宫调有变化的,而曲牌是牌名串合的,则只是异调词句的串联,有可能属于同一个宫调。除了在南戏中的犯调符合这样的规则,在明代中晚期制定的一些曲谱,如《旧编南九宫谱》、《增定南九宫曲谱》、《南词新谱》中,基本上所有牌名带“犯”的曲调都是在曲内宫调有转换的。如: [二犯月儿高]、[二犯桂枝香]、[安乐神犯]、[普天乐犯]、[花犯红娘子]、[马鞍儿犯]、[普天乐犯]、[尾犯](即柳永词)、[四犯泣颜回]、[渔家傲犯]、[二犯香罗带]、[五更转犯]、[二犯五更转]、[六犯新音]、[二犯排歌]、[二犯山坡羊]、[水红花犯]、[梧桐树犯]、[三犯集贤宾]、[四犯黄莺儿]、[二犯孝顺歌]、[柳摇金犯]、[二犯江儿水]、[二犯六么令]、[五供养犯]、[二犯五供养]、[二犯朝天子]、[清商七犯]、[七犯玲珑]、[六犯清音]等。
这些犯调,有的也采用了“集曲”的方式,但是宫调发生了变化,如[四犯泣颜回]〔泣颜回〕-〔刷子序〕-〔泣颜回〕-〔剔银灯〕-〔石榴花〕-〔锦缠道〕,宫调为: 中吕-正宫-中吕,同时还符合姜夔所说的“结声相同”要求。再如[三犯集贤宾]〔簇林莺〕-〔啄木儿〕-〔四时花〕-〔集贤宾〕,宫调为: 商调-黄钟-羽调-商调。
而有的南曲犯调只是在一支曲调的基础上变化宫调,如[普天乐犯],《南词新谱》注云:“新查注犯中吕”;[渔家傲犯]《南词新谱》注云:“新改订犯正宫”;[六犯新音]注云:“南吕过曲,首犯商调。”
由此可见,在明代中期以前,在南曲实际创作中,“犯”的概念相对比较清晰,主要是指一曲之内宫调发生变化,并且对结音没有太大要求。
与此同时,南戏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集曲,集曲不以“犯”为名,牌名通常以数曲牌名串联而成,或者标明集曲的数目。这类集曲中,既有宫调变换者,也有同宫集曲者。举例如下:
异宫集曲:
1. 《琵琶记》[风云会四朝元]〔五马江儿水〕-〔桂枝香〕-〔柳摇金〕-〔驻云飞中吕过曲〕-〔一江风〕-〔朝元令〕: 仙吕入双调-仙吕-中吕-南吕-仙吕入双调
2. 《琵琶记》[金索挂梧桐]〔金梧桐〕-〔东瓯令〕-〔针线箱〕-〔懒画眉〕-〔寄生子〕: 商调-南吕
3. 《琵琶记》[啄木公子]〔啄木儿〕-〔醉公子〕: 黄钟-双调
4. 《拜月亭》[莺集御林春]〔莺啼序〕-〔集贤宾〕-〔簇御林〕-〔三春柳〕: 商调-黄钟
5. 《王祥卧冰》[五团花]〔海榴花〕-〔梧桐花〕-〔望梅花〕-〔一盆花〕-〔水红花〕: 中吕-商调-仙吕-商调
6. 《吴舜英》[二红郎上小楼]〔福马郎〕-〔水红花〕-〔红衫儿〕-〔北上小楼〕: 正宫-商调-南吕-北中吕
7. 《孟月梅写恨锦香亭》[三十腔]〔绣带儿〕-〔大胜乐〕-〔梁州序〕-〔三学士〕-〔女冠子〕-〔懒画眉〕-〔五更转〕-〔琐窗寒〕-〔十五郎〕-〔贺新郎〕-〔狮子序〕-〔香遍满〕-〔香罗带〕-〔红衫儿〕-〔绣衣郎〕-〔针线箱〕-〔浣溪沙〕-〔东瓯令〕-〔大迓鼓〕-〔阮郎归〕-〔一江风〕-〔梧桐树〕-〔孤雁飞〕-〔金莲子〕-〔太师引〕-〔刘泼帽〕-〔柰子花〕-〔刮鼓令〕-〔生姜芽〕-〔节节高〕: 南吕-道宫-南吕-黄钟-仙吕-南吕-黄钟-南吕
8. 《孟姜女送寒衣》[琐窗乐]〔大圣乐〕-〔琐窗寒〕: 道宫-南吕
9. 《崔君瑞江天暮雪》[红狮儿换头]〔红衫儿换头〕-〔狮子序〕: 南吕-黄钟
10. 《崔君瑞江天暮雪》[金梧歌]〔梧叶儿〕-〔淘金令〕: 商调-仙吕入双调
11. 《崔护觅水记》[惜英台]〔祝英台〕-〔惜奴娇〕: 越调-双调
12. 《崔护觅水记》[沉醉海棠]〔沉醉东风〕-〔月上海棠〕: 仙吕入双调
13. 《张浩》[番马舞秋风]〔驻马听〕-〔一江风〕: 中吕-南吕
14. 《陈巡检梅岭失妻》[六幺儿]〔六幺令〕-〔梧叶儿〕: 仙吕入双调
15. 《陈巡检梅岭失妻》[锦庭芳]〔锦缠道〕-〔满庭芳〕: 正宫-中吕
16. 《董秀才遇仙记》[薄媚衮罗袍]〔衮衮令〕-〔薄媚衮〕-〔皂罗袍〕: 南吕-仙吕
17. 《刘孝女金钗记》[五团花]〔赏宫花〕-〔腊梅花〕-〔一盆花〕-〔石榴花〕-〔芙蓉花〕: 黄钟-仙吕-中吕-正宫
18. 《刘盼盼》[金风曲]〔四块金〕-〔一江风〕: 仙吕入双调-南吕
19. 《蝴蝶梦》[梁州锦序]〔梁州序〕-〔刷子序〕-〔锦缠道〕: 南吕-正宫
20.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集莺花]〔集贤宾〕-〔黄莺儿〕-〔赏宫花〕: 商调-黄钟
21. 《韩彩云》[驻马击梧桐]〔击梧桐〕-〔上马踢〕-〔驻云飞〕: 商调-仙吕-中吕-商调
22. 《宝妆亭》[沙雁拣南枝]〔雁过沙〕-〔锁南枝〕: 正宫-双调
23. 《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金络索]〔金梧桐〕-〔东瓯令〕-〔针线箱〕-〔解三酲〕-〔懒画眉〕: 商调-南吕
同宫集曲:
1. 《琵琶记》[琐窗郎]〔琐窗寒〕-〔贺新郎〕: 南吕
2. 《王祥卧冰》[渔灯花]〔渔家傲〕-〔剔银灯〕-〔石榴花〕: 中吕
3. 《孟月梅写恨锦香亭》[孝南枝]〔孝顺歌〕-〔锁南枝〕: 双调
4. 《林招得》[香罗怨]〔香罗带〕-〔一江风〕: 南吕
5. 《崔君瑞江天暮雪》[渔灯花]〔渔家傲〕-〔剔银灯〕-〔石榴花〕: 中吕
6. 《许盼盼燕子楼》[渔家灯]〔渔家傲〕-〔剔银灯〕: 中吕
7. 《陶学士》[解酲歌]〔解三酲〕-〔排歌〕: 仙吕
8. 《董秀才遇仙记》[雁过锦]〔雁过声〕-〔锦缠道〕-〔雁过声〕: 正宫
9. 《董秀才遇仙记》[摊破锦缠雁]〔摊破第一〕-〔锦缠道〕-〔雁过声〕: 正宫
10. 《贾似道木棉庵记》[香五娘]〔香遍满〕-〔五更转〕-〔香柳娘〕: 南吕
11. 《赵普进梅谏》[三花儿]〔石榴花〕-〔杏坛三操〕-〔和佛儿〕: 中吕
12. 《刘盼盼》[忆花儿]〔忆多娇〕-〔梨花儿〕: 越调
13. 《刘盼盼》[蛮牌嵌宝蟾]〔蛮牌令〕-〔斗宝蟾〕: 越调
14. 《蝴蝶梦》[破莺阵]〔喜迁莺〕-〔破阵子〕-〔喜迁莺〕: 正宫
15.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花堤马]〔石榴花〕-〔驻马听〕: 中吕
16. 《锦机亭》[双蕉叶]〔霜天晓角〕-〔金蕉叶〕: 越调
17. 《薛云卿鬼做媒》[山虎蛮牌]〔下山虎〕-〔蛮牌令〕: 越调
18. 《韩玉筝》[绣太平]〔绣带儿〕-〔醉太平〕: 南吕
19. 《韩寿窃香记》[渔灯雁]〔渔家傲〕-〔剔银灯〕-〔雁过声〕: 中吕
20. 《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临江梅]〔一剪梅〕-〔临江仙〕: 南吕
21. 《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香归罗袖]〔桂枝香〕-〔皂罗袍〕-〔袖天香〕: 仙吕
22. 《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醉罗袍]〔醉扶归〕-〔皂罗袍〕: 仙吕
由以上曲调可知,在南曲中,“犯调”和“集曲”是两种出发点不同、但实际操作中有类似形式的新增曲调方式。可以用下表描述:

上表中“以一支曲调为基础犯调”、“利用多支曲调犯调”、“集异宫曲调”“集同宫曲调”四种情形在南曲中同时存在,但是在南戏中,“犯调”和“集曲”的界限还是相对清晰的,至少从牌名就可以看出不同。但是,由于一些“集曲”和“犯调”在形式上都表现为多支曲调的串联结合,因此,明代后期的曲家便逐渐混淆了犯调和集曲的概念。
四、 明清曲家对“犯调”与“集曲”的混淆
在宋词与南戏的实际创作中,“犯调”与“集曲”的实践运用是相对清晰的,如上文所论,即名称带“犯”的词曲调主要从音乐出发,以变化曲调的音高为目的,可能串联两只或以上曲调,也可能并不涉及其他曲调;而名称不带“犯”字的词曲调,只是将两支或以上曲调名称进行巧妙合并,是从不同曲调的句格连缀出发,以“联曲”为目标的曲调变化。在“集曲”的过程中,可能也发生曲调音高的变化,也可能不发生。明代早期的曲家也明确知晓“犯”的涵义,如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在“商黄调”下注释云:“此系合犯,乃商调、黄钟宫各半只或各一只合成者皆是也。”(31)(明) 蒋孝《旧编南九宫谱》,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台湾) 学生书局,1984年,第42页。
蒋孝之后,王骥德对其中的区别尚能明晰,只是已经开始使用“犯”字指代曲调之间的拆解连缀之法,如《曲律》对“犯声”“犯调”的论述云:
而又有杂犯诸调而名者,如两调合成而为[锦堂月],三调合成而为[醉罗歌],四五调合成而为[金络索],四五调全调连用而为[雁鱼锦];或明曰[二犯江儿水]、[四犯黄莺儿]、[六犯清音]、[七犯玉玲珑]……沈括又言:“曲有犯声、侧声、正杀、寄杀、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乐典》言:“相应谓之‘犯’,归宿谓之‘煞’。”今十三调谱中,每调有赚犯、摊犯、二犯、三犯、四犯、五犯、六犯、七犯、赚、道和、傍拍,凡十一则,系六摄,每调皆有因,其法今尽不传,无可考索,盖正括所谓“犯声”以下诸法。然此所谓“犯”,皆以声言,非如今以此调犯他调之谓也。(32)(明) 王骥德《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8、60页。
王骥德认为,宋代的“犯”指的是音乐音调相犯,其法不同于明代的曲调相犯,且已经不传。这两种曲调变化方式,由于存在一些模糊的交集,即犯调中的“利用两只异宫曲调的连缀实现调高变化”与集曲中的“不同宫调的曲调相连缀”在形式上完全一致,所以从王骥德开始,研究曲学理论的曲家已经混淆了二者,开始用“犯”字意指“曲调连缀”这种形式了。如李渔《闲情偶寄》云:
曲谱无新,曲牌名有新。盖词人好奇嗜巧,而又不得展其伎俩,无可奈何,故以二曲三曲合为一曲,熔铸成名,如[金索挂梧桐]、[倾杯赏芙蓉]、[倚马待风云]之类是也。……凡此皆系有伦有脊之言,虽巧而不厌其巧。竟有只顾串合,不询文义之通塞,事理之有无,生扭数字作曲名者,殊失顾名思义之体,反不若前人不列名目,只以“犯”字加之。如本曲[江儿水]而串入二别曲,则曰[二犯江儿水];本曲[集贤宾]而串入三别曲,则曰[三犯集贤宾]。(33)(清) 李渔《闲情偶寄》,《李渔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说明李渔已经错误地认为[二犯江儿水]和[三犯集贤宾]是因为串入了别曲而被称为“犯”,事实上[二犯江儿水]之“犯”是仙吕双调之间的“犯”,而[三犯集贤宾]是商调、黄钟、羽调之间的犯,如果不涉及调高的变化,曲名不应当使用“犯”字。
对于集曲是否能够使用异宫曲调,清人也十分困惑,吕士雄《南词定律·凡例》云:“凡诸谱所犯之曲,或各宫互犯,或本宫合犯。细查诸谱,不无异同。且其定句间或参差,或犯同而名不同者,诸论不齐,各相矛盾,难于定准。”(34)(清) 吕士雄《南词定律》,续修四库全书175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7页。而清代一些曲家更认为“犯调”只适宜用同宫曲调连缀,不适合用不同宫调之曲进行音乐声调上的变化了。如查继佐《九宫谱定总论》云:“犯者,割此曲而合于彼曲之谓。别命以名,此知音者之能事。然未免有安有不安,不若只犯本宫为便,一犯别宫调,必稍有异。或亦有即犯本宫而不甚安者,宜审慎之。”(35)任讷《新曲苑》,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176页。
甚至有研究词曲的理论家认为只有曲调有“犯”,词调无“犯”,并且曲调的“犯”不能够“犯别宫”,如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云:
曲调可犯,而词调不可犯。词就本旨,而曲可旁求。然曲可犯,而不能创;词可创,而不可犯。则知词律不若曲律之严。……割此曲而合彼曲,采集一名命之,为犯调。知音者往往为之。然只宜犯本宫,若犯别宫,音调未免稍异。即犯本宫亦不甚安者,均宜斟酌。(36)(清) 黄图珌《看山阁闲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1页。
出于对“犯”字涵义的困惑不解,《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干脆取消了“犯调”一词,将曲体中“曲调相集”的现象统一命名为“集曲”,认为:“词家标新立异,以各宫牌名汇而成曲,俗称‘犯调’,其来旧矣。然于‘犯’字之义实属何居?因更之曰‘集曲’,譬如集腋以成裘,集花而酿蜜,庶几于‘五色成文、八风从律’之旨,良有合也。”同时,《九宫大成》编者认为,集曲是曲体文学的新做法,词体中并无此法,云:“唐宋诗余,无相集者。后人创立新声,乃有集调,嫉青妒白,去真素远矣。顾有其举之,亦所不废。”(37)周祥钰、邹金生《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第46页。由以上几位曲家的论述,可见“犯调”的概念在清代的模糊与讹变。
不过,也有少数曲家明白“犯调”的“犯”是音乐层面的变化,而并不是曲调之间的穿插连接。清无名氏《曲谱大成》即云:
犯者,音之变也,亦调之厄也,作者勿论本宫他调,须先审其腔之粗细,调之高下,板之疾徐,务使首尾相顾,机轴自然,补接无痕,抑扬合度,则音不觉自变,调不觉暗移,人巧极而天工错,始为无弊。……此所谓犯,皆以声律言,非此曲犯彼曲之谓也。(38)李晓芹《〈曲谱大成〉稿本三种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0页。
然而,“犯调”与“集曲”在清代的曲学理论中,基本上处于模糊、讹误的状态。如上述曲家所论,有学者认为“犯调”就是“曲调相犯”,宫调则可以同、可以异;有学者认为“犯调”所用的曲调最好是同一种宫调。原本在南曲创作实践中界限比较清晰的“犯调”和“集曲”二者,由于曲学理论家自己的认识问题被混淆,以致后人几乎都将“集曲”作为“犯调”的两种形式中的一种了。
总 结
“犯调”和“集曲”两种调牌的增衍、变换形式都起源于宋词,并于南曲中得到了继承、应用与发展。无论是在宋词中或是在南戏实际使用的南曲中,“犯调”、“集曲”二者都是有明确界限的。“犯调”从音乐旋律出发,进行调高上的变化,排名中标出“犯”字;而“集曲”从曲文出发,进行句格上的串联,牌名用所涉及的诸牌名串合而成。“犯调”中包含了一支曲调的音高变化与多只曲调连缀造成音高变化两种情况,而“集曲”中也包含了“同宫集曲”和“异宫集曲”这两种情况。由于在某些情况下“犯调”与“集曲”的表现形式几乎一致,所以明清时期的词学家、曲学家逐渐混淆了二者的内涵与区别。一些词曲家错误地认为“犯调”包含“音乐相犯”、“词句相犯”两种,一些曲家甚至认为“犯调”只是不同曲调的词句连缀,还应当保持宫调的统一,这已经完全颠覆了“犯”的本意。可见研究词曲音律之学,还是要回到实际的作品、曲调,观察真实的情形,避免发生如明清曲家一般的概念模糊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