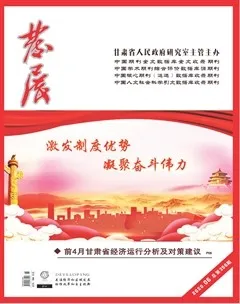新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的优势
在新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既可以解决现行《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中对商法概念的“加入不足”与“过度加入”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突显商事主体身份地位,规范商业行为的同时扩大中国“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商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近年来中国商业以崭新的姿态步入人们的视野,再加上“优化营商环境”等一系列扶持商业发展的政策出台与实施,中国的商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刚表决通过的《民法典》标志着中国民商法领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针对现有“民商合一”体系下产生的弊端,商法学界有关制定《商法通则》的呼声日益强烈。《商法通则》是指在现有《民法总则》以及未来《民法典》统领的前提下,结合商事行为的特殊性、易变性、发展性等特点,将商事行为中的共性抽象概括出来进行汇编,形成以“商事主体、商业行为、商事登记、商事账簿、商业监管、反不正当竞争”等商法总论的概括性规定,并在商法领域发挥优先于民法规则、原则、习惯等直接调整商事活动领域的作用,从而打破过去“民商不分”与“民商混同”带来的弊端以及在实务中产生的按照“民法思维”审理和裁判商事案件引发的与商法理论知识、“商事思维”的冲突和矛盾。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既有其因与时代发展相衔接而产生的独特优势,也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商法体系,从而推动中国商业持续向好发展,使得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形象矗立在国际舞台,融入国际商业的发展潮流当中。
在当前中国因“民商合一”以及传统法学教育中重视民法、忽视商法、以民法思维处理商事案件等具体模式带来的弊端中,《商法通则》的出现无疑有利于解决这种阻碍中国商业发展的问题,打破传统思维上的桎梏,与“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紧密配合,带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详言之,其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商法通则》的制定可以克服《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对商法概念“加入不足”所带来的弊端
在现有的《民法总则》以及全国人大刚刚表决通过的《民法典》中,有关“主体”的章节着重对民事主体进行了介绍,商事主体则存在于“法人”与“非法人组织”这两章当中,但商事主体包括商个人、商法人、商事合伙以及其他商业形式中的各种主体,并不限于民法中规定的法人与合伙,且《民法总则》与《民法典》中的合伙,主要指的是民事合伙,而商事合伙则单独规定在《合伙企业法》中,因而从主体上说,《民法总则》《民法典》存在“加入不足”。而从客体、法律行为、法律责任等方面来看,不论是《民法总则》,还是《民法典》,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按照民法上常见物、行为的种类来概括客体的范围,按照民事主体注重“意思表示”的原则来规制所谓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责任”。但在商事领域,商业活动需遵从“商事交易迅捷”“注重效率”等商法上特有的原则,因而在上市交易中,商主体不会过分关注交易对方的内心真实意思,而主要通过交易对方的行为来推定其目的和意图,这被称为商法上的“外观主义”。至此,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原则在商事交易领域显然不能适用,倘若在商事领域过分关注此原则,商事交易的效率将无法保证。此外,由于商事主体在以上方面较之民事主体的特殊表现,商事特别法也往往赋予他们较多的义务与较重的责任,而反观现行民法,在法条中并没有对商事主体的责任作出特别规定,在就造成在责任领域的“加入不足”,起不到督促商主体合法经营的作用。
二、《商法通则》的制定有利于克服现行《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中对商法概念“加入过度”而带来的“民商混同”麻烦
如前所述,现行《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在部分章节过度将商法概念纳入,造成部分章节民法概念与商法概念相混同,使得“民法商化”,不利于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例如,在“法人”一章,《民法总则》援引了大量《公司法》的条文,使得法人这一概念完全商化,并在其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而众所周知,法人除了公司这一种最典型的形式外,还有社会团体法人、机关法人等多种形式,排除以公司为代表的所谓“商法人”外,其余应归入到“民法人”当中。而在《民法总则》中的规定几乎将公司法中的基本制度原则通通纳入,不仅使得现有企业、公司法体系的独立性与完整性遭到了破坏,也使得本应调整民事主体的《民法总则》以及《民法典》过度商化,不利于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制定《商法通则》将“商法人”的特别规定纳入其中,对于解决现行民法体系对商法“加入过度”带来的麻烦是大有裨益的。
三、《商法通则》的制定有利于突显商事主体的地位,进一步规范商行为
在过去“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民事主体的地位得到了人们的普遍承认,但由于缺乏对商事主体法律概念的总括性规定,商事主体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在实践中很难被人们注意和认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对商事主体身份性的认同,法官倾向于从民法的角度出发,过度关注商事主体的民事地位,深究在商事交易中主体的“意思表示”,忽略商事交易的特殊性,致使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维护,甚至侵害了外商投资主体的利益。此外,由于长期不强调商事主体的特殊性,法律规定中往往给予商事主体承担与民事主体相一致的责任和义务,这就造成商事主体在从事商事活动中缺乏责任感,不能严格按照“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原则约束自己,也不能自觉按照要求办理商事登记,取得营业资格后正常合法经营,结果造成一系列消费者受害,也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为此,我国为解决这种局面,必须制定《商法通则》,通过在“通则”中确立商事主体的特殊地位,赋予其特殊权利,并且与诉讼法体系相衔接,确保商事主体在商事领域可以正常开展商业活动,在诉讼中法院可以按照商事法所固有的思维来解决处理案件,维护商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也能使得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真正享有公平公正的投资待遇,吸引“外资”进入中国。同时,通过“通则”中对商事主体规定的特殊义务和要求,以及其所承担的特殊责任来规制商事主体的经营活动。例如,将商事登记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规定在“通则”中,有利于商事主体明确知道自己应履行的义务,也利于普通消费者对商事主体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确保商事主体合法经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我国的商业发展提供“向心力”。
四、制定《商法通则》有利于响应时代的号召,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前所未有的“上升期”与“发展期”。一方面,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一系列新兴经济事物的出现以及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门越开越大,中国的商业发展需要制度和法律上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商业领域的法律制度规定不足,部分国家趁机借此为“筹码”展开对中国经济的“攻击制裁”,为中国在国际商业舞台上的发展带来了重重阻碍。十九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商业领域的制度与法律建设,他提出“优化营商环境”等新政策,全面推进企业等商事主体的“放管服”改革,这为《商法通则》等商事法的制定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值此契机,《商法通则》的出台顺应了中国商业发展的历史潮流,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必备武器,成为我国商业持续向好发展的重要支撑。
总之,新形势下制定《商法通则》,有其独特的优势,它能对我国对外开放、优化营商环境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而《商法通则》最终也会以崭新的姿态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商事主体进行商事活动的重要动力。
参考文献
[1]余 斌.《商法通则》的设计理念[J].湖南社会科学,2018(1).
[2]范 健 丁凤玲.将《商法通则》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建议[J].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5).
[3]周林彬.《民法总则》制定后完善我国商事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地方立法研究,2018(2).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