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媒体视阈下交互式电影发展研究
刁亚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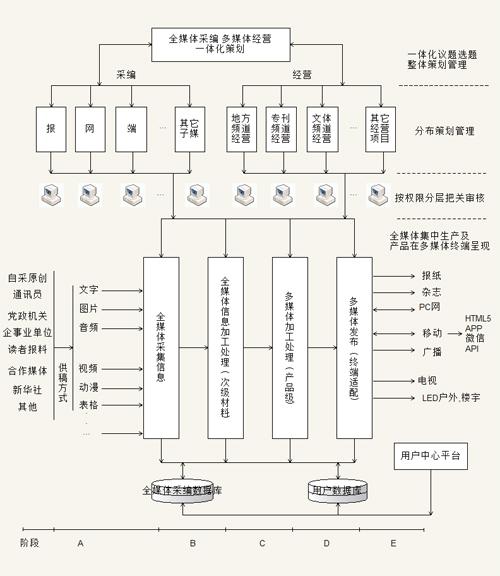
摘 要 融媒体时代,作为大众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的媒介属性、传播特性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界限也正以一种超乎预期的速度日渐模糊,甚至消弭,这些变化与交互式电影的发展息息相关。交互式电影的发展走向取决于创造者如何运用交互式电影这种表达性媒介完成受众由观影者到交互用户(参与者)的深度转换,这一目标的达成则需要实现交互式电影与其他媒介形式的融合、与游戏边界的溶解。
关键词 融媒体;交互式电影;非线性叙事;《黑镜:潘达斯奈基》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14-0112-03
随着现代信息化技术的日益成熟,媒体传播方式在适应、起步和滚雪球式的发展中不断推进,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在这股大数据变革浪潮中,媒介得到了新一轮发展,并给我们的传媒环境带来了新的变化,电影的媒介属性、传播特性也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之下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界限也正以一种超乎预期的速度日渐模糊、甚至消弭。交互式电影即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的电影产业概念,作为一种新型互动体验的形式,交互式电影通过观众自主选择性行为参与甚至影响叙事的发展,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临场感,拉近受众与电影叙事的距离,带来更加沉浸式的观影体验。由于交互式电影具有互动性强、沉浸程度深、游戏趣味濃厚等传统电影所不具备的优势,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Netflix等众多流媒体平台、影视公司探索的新方向。本文以交互式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为例,在融媒体视阈下探讨交互式电影的发展历程、发展前景及创新趋势。
1 交互电影的起源和发展
世界上第一部运用交互式技术与电影相结合手法的影片最早可以追溯到捷克电影新浪潮时期(1962—1970),在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一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名为《自动电影》(Kinoautomat)的交互影片因其与众不同的体验方式而备受人们关注。导演Vladimír Svitácek在观影席位上安装了一些选择按钮,观众可以通过按钮来选择自己所期望的情节,从而掌握故事的发展走向。虽然这部影片仅仅是通过精心构造电影脚本从而巧妙的将故事情节引向导演所安排的选项节点,制造观众能掌控结局的假象,但是其艺术性价值存在于它所制造出交互的幻觉而并非交互本身。这部电影最终也因其独特的艺术价值成为了贯穿捷克电影新浪潮的主题。《自动电影》的诞生以观众选择角度为出发点,革新了电影观看模式,同时也开辟了交互式技术与电影相融合的先河,为传统电影行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思路与创作模式。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交互式电影迎来了一个创作“井喷时期”,从2017年威尔士互动公司(Wales Interactive)发布的《晚班》(Late Shift),到2018年摘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虚拟现实体验奖桂冠的《伙伴》(Buddy VR)以及因赢得艾美奖——交互式媒体内容杰出创新奖(Outstanding Innovation in Interactive Media)而引发行业轰动的《墙壁里的狼》(Wolves in the Walls VR),再到2018年年底Netflix推出的《黑镜·潘达斯奈基》,交互式电影的制作已显得愈加成熟,创作者们运用新技术探索交互式叙事的手法也有了长足进步,观众与角色之间的真实联系也愈加密切。
大数据浪潮背景之下,数字技术的冲击和新媒体的变革导致媒介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我们无法准确的与之未来交互式电影会走上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最终会呈现什么样的形态,但不可否认的是,交互式电影的发展走向与用户在参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转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命题便是如何运用交互式这种表达性媒介完成受众由观影者到交互用户(参与者)的深度转换。在这一过程中,亲密让位于隐私,用沉浸式的梦境代替了壁炉般的银幕。这种屏幕在距离上的极远或极近也是一种制式的扩张和收缩。
2 从反馈到交互——电影受众参与方式探析
麻省理工大学(MIT)首席研究科学家格洛里安娜·达文波特(Glorianna Davenport)认为,交互式电影反映了电影的一种渴望,它想成为一种更复杂、更亲密的新事物,就像在和观众对话。她曾如此描述:“交互式电影是这样一种类型,它将电影语言及美学与一个能够实现观众反馈及控制的传送系统整合起来。”[1]相比较其他视听形式而言,交互式电影最大的亮点就在于互动性观影模式和深度的沉浸感体验。观众在观看交互式电影的过程时,往往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通过在影片关键节点处做出具有个人主观意愿的选择,以此来改变剧情的走向、从而影响到整个作品的结局,给观众带来更强的代入感。
随着各类交互式电影受众反馈的逐步深入,电影受众也日益表现出对戏剧情节发展走向发出“表达之声”的诉求与渴望,这一需求也受到了制片和发行方的重视,通过电影技术手段的革新和非线性叙事手法的运用,观众与故事情节深度交流的美好愿景也不断在实现。
2018年底,流媒体平台Netflix在圣诞特辑期推出了引发全球网友热议的交互式电影——《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从而引发了全球观影者对于交互式电影的深入思考。《黑镜:潘达斯奈基》具有多向结局的特征,按主要剧情线来划分整部影片共计有5种结局,根据所有情节支线划分的话则拥有16个主要结局,总时长5小时12分钟,叙事线索十分庞大。电影整体的情节网络所传递出的内核将《黑镜》系列的魔幻气质发挥的淋漓尽致,既具有娱乐价值也有不忽视的警世属性。影片在每一条叙事线索上都巧妙的设置了数目不一的情节点分支,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可以通过在屏幕上点选从而替主人公做出选择,实现了受众与电影叙事的深度交流。几乎与《黑镜:潘达斯奈基》同期,国内影视也对互动内容进行了有效的探索,互影娱乐与五元文化携手推出了国内首部探险互动剧《古董局中局之佛头起源》,一改观众往日默默看剧的模式,为国内观众深度通过交互技术深度参与电影故事之中提供了一种思路。
无论是流媒体巨头Netflix的实践,还是国内平台互娱科技的试水,二者在交互式电影探索拓新中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从无声电影到现在的交互式电影,电影自诞生以来已走过100余年,从科技角度观察百年电影技术的走向,不难发现其发展路向从未改变,那就是不断向实现“将梦境与现实叠合交融”这一目标迈进。从现行交互式电影传播状况看,观众对于交互式电影反馈速度的要求将逐渐拉近受传者之间的界限,而在此过程中,传播主体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反馈的时间差也将不断缩短,长此以往,受众反馈与故事情节发展走向同时发生、相互交融将是其最终将抵达的终点。
3 用户视角下的交互式电影创作
新媒体的交互性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用户与创作者的交互、用户与作品(媒介)的交互,以及用户与用户的交互[2],在交互式电影中,观众(对象)在叙事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已远超被动“观看者”的地位,逐渐成为了拥有决定故事发展走向权利的“用户”。
不论是从电影行业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受众的体验效果来看,作为交互式电影建构核心的交互技术,都不能只扮演着为新时期电影发展提供一种新的传播途径的角色。而交互式电影的发展走向取决于创造者如何运用交互式电影这种表达性媒介完成受众由观影者到交互用户(参与者)的深度转换,这一目标的达成则需要实现交互式电影与其他媒介形式的融合、与游戏边界的溶解。
《黑镜:潘达斯奈基》建立了一个故事世界和互动机制,然后将故事的进度掌握权交给参与者这个代理机构,由参与者喊出最后的“停”。这部影片是基于现代科技背景之下的电影故事,其主要内核即在于用交互性这一传播媒介表达当代科学技术和信息爆炸时代对人性的影响和重构,引发人们对于现有生活的审视和思考。
不同于普通电影在影院观看的形式,流媒体平台Netflix为此类交互式作品提供了一个能够被观众看到的平台和接纳的空间。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认为,“交互式电影要求用户去选择。每个交互应用程序都必须为其用户提供合理的选择。沒有选择,就没有互动性。这不是一个经验法则,这是一个绝对的,不妥协的原则。”[3]
由此可见,交互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可以影响我们如何思考作者、作品以及受众之间的联系及变化,其核心在于运用交互式叙事方式(Interactive storytelling)、采用非线性分叉结构的链接叙事手法以满足观众对充满可能性的观影需求,使得电影更具沉浸感和代入感,在此过程中,受众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一环。
从观众(用户)的角度出发,掌握影片故事情节的走向不仅仅是对影片故事情感的沉浸与体验,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对故事情节的多种选择、戏剧冲突发生的多种可能性的期望,是一种模拟观众在自己真实生活中选择某种自由的感受,也是一种寄托于虚拟世界可以将自己从现有生活解放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愿景。用户可以通过自己的选择来参与或改变故事情节的发展,通过交互性的结合,构建出具有一定个人主观意义的故事结局。无论是互动电影还是整个影视行业,核心都是用户及其体验,具体到作品中,如《明星大侦探之头号嫌疑人》中的互动则满足了用户的好奇心、探索欲望,增强了参与者的临场感等。
媒介的“新”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我们不应该在新事物中寻找旧事物,而要在旧事物中寻找新事物。交互式电影的尝试由来已久,20世纪末,由于时代和技术的局限,交互式电影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学术界对于交互式技术的研究并未因此停止,交互式技术的应用也在不断的扩展,例如游戏产业的运用。1985年美国Axlon公司的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汤姆·齐托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部以录像带为载体的试制型游戏机——“Interactive Television(互动电视)”。1986年,齐托等人开发了数款测试用真实影像软件,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款游戏是《犯罪现场》。《犯罪现场》是一款长约5分钟的互动解谜游戏,玩者可以随时切换镜头,以查看同一时间轴上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件。1992年,诺兰·布什内尔因不满孩之宝公司(Hasbro)对“互动电视”(NEMO计划)的搁浅,转而与ICOM Simulations公司联手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较为完整意义上的真实影像游戏《午夜陷阱》,开创了电影互动游戏先河。这款互动游戏一经上市便在日本、美国、法国等市场引发轰动,风靡一时。此后,关于电影互动游戏的探索便从未间断。1996年,Westwood Studios公司推出了一款即时战略游戏——《红色警戒》,在这款游戏中实现了以真人拍摄影像片段的形式来取代《红色警戒》游戏中的动画,该公司通过运用技术手段将电影文本与游戏文本聚合在一起,当玩家进入游戏“节点”时,便可触发影像播放条件,其聚合过程实现了技术和符码的拼贴。
从近些年来交互式游戏的发展历程反观交互式电影的创新趋势,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经验,诸如《底特律·变人》《超凡双生》《行尸走肉》《暴雨》之类的交互式游戏,其优势在于良好的沉浸体验,即通过参与文化让受众在诸多零碎片段中寻找自己行为和思维的契机,这与交互式电影的发展理念相不谋而合,这种游戏化思维对于新时期的交互式电影的借鉴与发展有着极大的好处,能够以更为隐晦的方式让受众更好地旁观与介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通过简单的剧情组合而实现粗浅的形式创新。
4 发展与挑战——交互式电影的无限可能性
从理论家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提出的“深层时间”(deep time)的角度来看,对交互式电影之新有所质疑,思考其隐含的概念、失败的开端和意外的先例,才能厘清它作为一种媒介有何作用。齐林斯基媒体考古学的方法帮助我们认识到一种媒介可以既不是新的也不是旧的,而对其最准确的理解是一种隐晦的挖掘。如果交互式电影的发展是线性的,那这就迫使我们认定接下来的10年会是交互式电影的寒冬,而当下围绕交互式电影发展的推动力都不过是赌博和玩笑,或只是繁荣期罢了。但如果我们把交互式电影看作是嵌在电影自身弹性中的一条线索,那这条线索可能会往回追溯到电影和电视的起源,又向前延展至达文波特所说的“未来的电影”。
“新”是一个扬弃的词,它很有吸引力,因为它通过尖锐的、不同的声音发出信号,争夺我们的注意力,但它同时也阻止了我们看到历史的相互联系。虽然交互式电影在新世纪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仍暴露出了诸多叙事问题,究其根本,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创作者并未找到一种令观众舒适,同时也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的叙事方法。电影的整个历史都是一系列的危机,在任何转折点,新形式都威胁着它的存在,而我们所需要进一步做的便是充分利用好受众反馈机制,利用新媒体技术不断提高受众的观影体验、提升受众对电影文本的参与性,将电影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转入深入反馈、深度交互的形态。不断扩大的电影定义及其与其他新旧媒体的关系,仍然是不断发掘交互式电影潜力的最有用线索。
在不久的将来,在融媒体技术的影响下,互动电影与交互式游戏的交流、融合也会不断加深,交互式电影的游戏性将会进一步彰显,如何让二者在保留自己叙事的独特性的同时,寻找到适用于交互式电影的新叙事体系,而不是仅仅是缺少视觉纬度探索的对话,还亟待探索。
参考文献
[1]Davenport,Glorianna.“Interactive Cinema”,In Marie-Laure Ryan,Lori Emerson and Benjamin J.Robertson,eds,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Digital Media[M].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4:278.
[2]王正中.新媒体交互叙事中的身份认同[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29-135.
[3]Chris Crawford,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Erasmatron Storytelling System[A].Narrative Intelligence[C].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2003:189-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