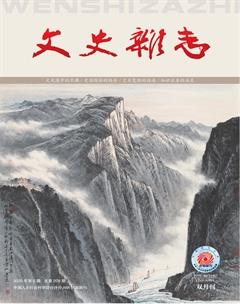读《管锥编》札记二则
黄硕
一
钱锺书《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九十三》论繁钦《与魏太子书》“凄入肝脾,哀感顽艳”句,云后句“久成批尾家当,四字并列为品藻词汇”,并随手谑评况蕙风《蕙风词话》以“拙不可及”释“顽”字,为“读破句有省”,可“终身不易”。钱氏之文字刻薄,亦可谓“终身不易”,抑其可爱处,适在此欤?
钱锺书对“哀感顽艳”的解释:“顽,艳,自指人物,非状声音;乃谓听者无论愚智美恶,均为哀声所感,尤云雅俗共赏耳。顽,心性之愚也;艳,体貌之丽也,异类偏举以示同事差等,盖修词‘互文相足之古法。”其引《礼记·坊记》:“君子约言,小人先言”,谓“君子约则小人多,小人先则君子后”;又引《左传》宣公十四年申舟之言“郑昭宋聋”,谓“‘郑昭则宋目不明,‘宋聋则郑耳不闇”。各举一事而对以相反,示小人喋喋争言,宋之昏聩。“曰‘顽,则艳者之心性不‘顽愚也;曰‘艳,则‘顽者之体貌不‘艳丽也。”
若顽、艳二字真作名词解,而又如钱氏所言意近“雅俗共赏”,即形容音乐、文章悱恻哀怨,感人至广,则有两种可能。其一即类似于“事无巨细”,“人无长幼”这种语法。后两字对举,而表示全部客体,“巨细”即概括所有事,“长幼”即概括所有人。如是,“顽”“艳”则应是反义词,方能叩其两端。“艳”在《说文·丰部》里的解释“好而长也”,即“又美又高”之意。至繁钦时或许引申出“文辞华美”之意,今语尚有“惊才绝艳”,即用此意,也或许没有。“顽”,在《说文·页部》:“顽,头也。从页元声”,意思是尚未劈开的木头。至繁钦时已有顽固、愚笨等意思。
钱氏既认为这两字“自指人物,非状声音”,那与“艳”相对者,应为丑、陋、佝之类。这与上文所言的“顽”字诸意不合;而与“顽”相对的大约是“灵”(今语尚有“冥顽不灵”)、“黠”“狡”之类,这又与“艳”诸意不合。故“哀感顽艳”估计并不是“事无巨细”这种语法。其二即钱氏所言的“同类等差”,他所引二例,也属此类。依此“互文相足”的模式,则与“顽”所对者并非“艳”,乃是行文中所省略的“灵”。通俗来解释,即:蠢人都被感动了,聪慧的人还用说么?然若如此,则“艳”字无着落,总不能说:好看的都感动了,丑的还用说么?在对音乐、文学的感悟上,美丑并非衡准。所以仍然解不通。
而钱氏既言“同类等差”“互文相足”,且举例以证,表明这第二种模式;又言“曰‘顽,则艳者之心性不‘顽愚也;曰‘艳,则‘顽者之体貌不‘艳丽也”,把“顽”“艳”两字相对,又似以为此词为第一种模式。前言后语,自相枘凿,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邪?
读《管锥编》,常叹钱氏读书之博如沧海,心思之细若毫芒;亦每病其“简单问题复杂化”,若此处所谓“顽者不艳,艳者不顽”者。单论此句,既曰“顽”,即固显其“顽”,其艳与不艳,乃至瞽与不瞽,聋与不聋,则非所虑也。艳亦如是。钱氏所言,几近平地生波矣。
二
钱锺书论《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综合孔疏與俞正燮的意见,以为“尚”“犹”二字同义连用,表示强调,且援后世诸踵袭之例,以证其来有自。窃以为,若把这用法翻译成白话文,再系之于不见经传者名下,必被斥为累赘。何以出自古名家之手,就仿如锈铁镀了金,非但不须遮盖,竟反而亮起来了呢?若视钱先生之说为归纳古文义例,自无不可;若以欲摹习此等用法为荣,则似为古人误矣。
鲁迅尝言“作文秘诀”,只有三句话: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我的理解是:作文章,必先损,而后能益。一句话能讲明的,绝不说两句。删去一些字词,而句子不显得挤,则所删者必为浮词。如上文中“尚”与“犹”叠架于句中,即殊无谓。必以“郑重”“强调”为辩,亦谬矣。若欲强调,所务者当在练字,而不在凑字。好比雕刻木头,一把刀就够了;觅不得刀,纵有十把剪子,又何益?而我所谓“损”,即在强调语言的精准,即强迫自己“觅刀”,久之或可至不觅自来之境。而妄图以堆垛补足文意,只能是词肥义瘠。比如现在有些人写东西,总爱加些“没有之一”“仅此而已”之类的话。你没说“之一”自然就没“之一”,何必加了“之一”又自我否定曰“没有之一”呢?而且这也正是鲁迅所谓“粉饰”“做作”。
写文章只需凭心去写,骄娇之气损而又损,文字精益求精,写到不动声色,自然是好文章了。
(题图: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