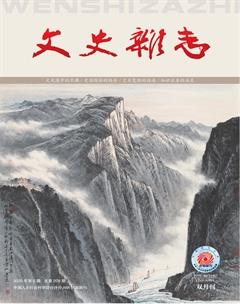敦煌“变文”数量词的文化效应
刘火
弁 言
虽然《辞海》(商务印书馆,1978年)有“数词”“量词”词条,也就是说官方认定了“数词”与“量词”在汉语词类分类学上的成立;但这一认定似乎并非“铁定”。之前,《语法修辞讲话》(吕叔湘、朱德熙著,1952年)把数词归入形容词类,没有量词条。后来,通过20世纪50年代汉语语法的讨论、研究、推广、普及,语文界在第一部(依英语语法为蓝本的)具有现代汉语语法意义的《马氏文通》(1898年)的基础上,在词法和句法上对数量词大致已经有了统一的说法。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数词”与“量词”是否完全成立,依然没有定论。王力说:“数目字,归入形容词,不自成一类”;“量词,为单位名词,也不自成一类”(《现代汉语讲座》,1981年)。《汉语造词法》(任学良著,1981年)是一部专门论及汉语造词规律的著作,但有关数量词造词的论述,却少得可怜;只在“并列”式谈及到两个词:“一二”和“再三”(而且,此两词也不属数词)。另一语法学家俞敏也认为“量词是名词的一个附类”(《现代汉语讲座》)。直到“汉语知识讲话”系列丛书出版,才列有专门的著述《数词与量词》(胡附著,1984年)。之前,王力和俞敏两先生的看法,与《马氏文通》几近一致,都受到英文语法的影响。在英文语法里,“量词”基本上是一个“黑洞”;也就是说,英语没有“量词”一说。主要以英文语法模式编纂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就只有数词(Numeral)词条,没有量词词条。但是,在现代汉语里,“数词”与“量词”则广泛存在,特别是具有汉语词汇词法学意义的“量词”,是汉语的一个独具“个性”的存在。或者说,量词作为语法学意义的单独词条,在今天看来,也不再是问题。数量词的运用,不仅具有语言学意义,还具有文化意义。
现在来看一看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唐代(包括五代)“变文”[1]里的数词与量词。
“变文”是敦煌石室重要的发现之一。“变文”的研究是敦煌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何谓“变文”?笔者在《“变文”命名考》(2019年)里说:“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石室从王道士处带走的24箱唐人写本(另有5箱绘画本)里发现一种佛经讲经的特殊形式:既是散文的又有韵文的佛经讲经文本。”郑振铎在1932年,将此独特的文本样式正式命名为“变文”(之前有其他名字,譬如“俗讲”等)。郑指出这是既不同于佛经的散文,也不同于佛经的偈,更不同于中土的先秦至唐的散文和韵文,这“是一种新发现的很重要的文体”(《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年)。郑振铎因称它为“变文”[2]。变文从1907年自敦煌流出海外、散落民间,中经海外(法、英、俄、日等)的抄写摄影和民间收集,直到草创时期的研究和向民众介绍,终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第一个研究期即初创期。此后,进入20世纪50年代,《敦煌变文汇录》(周绍良著,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民、启功、曾毅公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上、下两集)等相继出版。“科学春天”之后,20世纪80年代,相继出版了《敦煌变文集新书》(潘重规编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敦煌变文集补编》(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影印彩版)等。本文所举“变文”的数词与量词均来自《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敦煌变文集》(上下集,1957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三种的初版一印。
数 词
一
在古代汉语里,一、三、六、九,既有确指也有泛指。一,則往往意谓为“大”“全”“都”“满”或“极尽”。
确指:玉环锡杖一条(《庐山远公话》)、贱妾只生一个子(《汉将五陵变》)、藏隐一食停一宿(《捉季布传文》)。
泛指:一依前计具咨闻(《捉季布传文》)、一依处分不争论(同前)、一去三途更不回(《地狱变文》)。
全部:佛为一切众生(《妙法莲花讲经文》)、一切大从皆(《双恩记》)、一切人皆看(同前)。
二
二与两,有时通用,有时有区别。当独说“二”是数词时,往往说“两”。
入他汉界,早行二千里收兵却回(《李陵变文》)、一入虏庭,二千余里(同前)。
两三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一句两句大乘经(《八相押座文》)、点头微笑两眉分(《捉季布传文》)。
三
确指:三乘五姓远流通(《维摩诘经讲经文》)、流泪两三行(《欢喜国王缘》)、一沾两沾三沾酒(《八相押座文》)、三年不食胸前乳(《季布诗咏》)
泛指:三三五五总波涛(《季布诗咏》)。
特指:佛教语:三宝(佛、僧、经)、三昧(定、正受、等持)、三界(欲、色、无色)、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恰如人得真三昧(《维摩诘经讲经文》)、纲罗割断抛三界(同前),“三明”(见“六”字条)。[3]
四
“四”,在汉语词汇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4]由“四”字打头的双音节词在《辞源》(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里共收132个、三音节词42个、四音节词34个,为《辞源》以数字打头收词最多者之一。除数词确指外,有专用的佛教用语、儒家用语等。
确指:但将一领毡来,大钉四枚,医之立差(《叶净能诗》)、钉之内四角(同前)。
特指:佛教语。四流(见、欲、有、无明)、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弘(度一切众生、断一切烦恼、学一切法门、证一切佛果)等。一志修行绝四流(《维摩诘经讲经文》)、四弘愿力难相并(《维摩诘经讲经文》)。
五
确指:仿佛也高尺五(《燕子赋》)、是五百文金钱上(《不明变文》)、五百个童男五百个童女(同前)。
特指:佛教语。五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四邻愤怒传扬去,五逆名声远近彰(《故圆鉴大师二十四孝押座文》)。
六
确指:六尺之躯何处长(《季布诗咏》)、此时只要六字便答了(《唐太宗入冥记》)。
特指1:六铢(古钱币一种,古衣服一种)。百宝冠中若瑞霞,六铢衣上绕光彩(《维摩诘经讲经文》)。
特指2:佛教语:六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世尊作号名曰大目连,三明六通具解(《目连变文》)/六镮(锡杖之一种)。解执六镮他界外(《维摩诘经讲经文》)。
“六镮”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7年)未收,《辞源》未收,“在线汉典”未收。(按:在线汉典是今收词最丰的在线词典,六字头的词共收229词条,但无“六镮”。)锡杖有六镮、八镮、十二镮之别,六镮为常见。“六镮”一词并非生僻,如宋人郑侠赠友诗的诗题即《六镮助潮士钟平仲纳官辄辞赠以诗》,诗中有“六镮聊助君,鹭股难广献”“急取慎勿辞,六镮如六万”等。
七
确指:七十二战(《前汉刘家太子传》)、有七人先来(《韩擒虎话本》)。
特指:佛教语。七圣(信、戒、惭、愧、闻、施、慧)。信之七圣财之无胎(《维摩诘经讲经文》)。(另,七圣法指唐代从西亚传入拜火教的神幻术。)/七珍(佛教器物,供佛所用)。世上七珍之宝偏除现在贫病(《维摩诘经讲经文》)。/七重。佛教语,即位列七重,即须弥山下,第七重海外、第八重海里(《妙法莲花经讲经文》)。
八
确指:每日八人齐来(《韩擒虎话本》)、八水三川入掌内(《王昭君变文》)、四时八节眼前无(《盂兰盆经讲经文》)。
特指:八难(在地狱难、饿鬼难、畜生难、长寿天难、边地难、聋喑哑难、智辩聪难、在佛前佛后难)。三乘五姓远流通,八难四生令离苦(《维摩诘经讲经文》)。
九
确指:九年之中(《前汉刘家太子传》)、九龙吐水早是议(《悉达太子修道因缘》)。
特指:九种,佛教语。九种陌上为佳瑞,一国人中作吉祥(《维摩诘经讲经文》)。
十
确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韩擒虎话本》)、□国现有十硙水,潺潺流溢满□渠(《张义潮变文》)、贱奴念得一部十二卷(《庐山远公话》)、是时三十佳人齐至厅前(同前)。
特指:佛教语:十方(即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又乃梦中见十方诸佛(《庐山远公话》)/十果,佛教语(即信心、念心、回向心、达心、直心、不退心、大乘心、无相心、慧心、不坏心)。当当来世界,十地果圆,同生佛会(《庐山远公话》)/十劫(指特定的一段时间长度)。与心往彼救时,胜得十劫财施(《维摩诘所说经讲经文》)。
百、千、万
确指:其人问一答十,问十答百,问百答千[5](《汉将王陵变》)、餐百字之珍膳,敕赐赤斗钱二万贯(《李陵变文》)、陵下散者,可有千人(同前)、酝五百瓮酒,杀十万口羊(《王昭君变文》)、一树死百枝枯(《孔子项托相问书》)、天地相却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里(同前)。
泛指:除“百”确指外,“千”“万”“亿”都可以泛指,即指“全部”“众多”或“所有”。地僻多风,黄羊野马,日见千群万群(《王昭君变文》)、单于重祭山川,再求日月,百计寻方,千般求情(同前)、空留一冢齐天地,岸兀青山万载孤(同前)、受罪既旦夕不休,一日万生万死(《目连变文》)、喜欢之心万万重(《妙法莲花经讲经文》)。
序数
汉语的序数词从何时开始,并不太清楚。[6]但是敦煌变文里给我们提供了序数的完整谱系。这就是现藏原苏联符卢格的《十吉祥》:
文殊师利,此云妙德。正梵语云“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何以名为妙吉祥,此菩萨当生之时,有十种吉祥之事。准文殊吉祥经云云。且弟一……;弟二……;弟三……;弟四……;弟五……;弟六……;弟七……;第八(案,惟“第八”用的是今天通用的序數词“第”,其他皆作“弟”)……;弟九……弟十……。有此十般希(通今“稀”)奇之事,所以名为妙吉祥菩萨……。只缘是事多欢喜,所以名为妙吉祥。
佛教西来进入中土,充实或者说改造了中原的传统文化;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通过译经带来了汉语词汇(甚至语法)的极大变化。白话和简体字的出现,大约在公元1世纪到9世纪、特别是7世纪到9世纪的300年间,是汉语演变史、发展史和汉字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包括本文涉及的变文的数词与量词的出现。从译经的书面语到口语,再由如变文一般的说唱的口语又返回到书面,两两碰撞与交流交融,逐渐或最后形成了汉语发展史的两个方向:其一,汉字的简化以不可逆的速度加快(参见拙文《汉字的痛与逆——西夏文、徐冰的天书与流沙河的复繁》2016年,《简化字真的不讲理吗?》2018年);其二,口语成为书面语最有活力的语言来源。《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共收录外来词10000余条,主要来源有三个:一、公元1世到9世纪的佛教语,二、18世纪开始的英语、法语、俄语、德语,主要是英语,三、19世纪开始的日语。这三个方面的外来语的进入,使由外语转译的词汇不断涌现,许多至今依然鲜活并且常用。如“觉悟”(梵语)、“米”(法语)、“汉堡包”(英)、“纳粹”(德)、“阶级”(日)等。《汉语外来词词典》在1984年之前所收录的10000余条外来词中,佛教语和日语为最多,前者为中古时期,后者为近代时期。前者的背景为唐的海纳百川,主动接受外来文化(俗语为“西天取经”);后者则因近世清朝闭关和自大造成与世界迅猛发展的极大落差而受辱,包括文化的落伍,以致19世纪后期被迫降身向西洋和东洋学习。日语以平假名的方式“大规模”地转输进汉语。[7]仅从外语转译成汉语来看,这两个时期,正是古代中国和近现代中国与外国交流程度最为深广的时期。虽说一为主动,二为被动,但由于外来文化就本文角度讲是外来语的进入,这便成就了汉语的新生与发展。佛教语里的大量的数词,在转译成汉语后被植入进汉语,与汉语原来的数词一道,构成汉语词汇与其他语言(物别是印欧语系)相区别的一个显明特点。汉语数词特别是形成了定式的数字词汇,以及它们的特定所指,成为汉语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应该看到,有唐一代,伴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佛教的词汇便自然成为汉语词汇的一部分。“变文”的口语化及口语书面化,更加快了它丰富汉语词汇的速度,如以“四”字带头的词。《辞源》共收四字词汇208条(包括双音节、三音节、四音节以上等),其中佛教语词汇收22条。这一数据远远超过本土宗教道教2条的词汇量。[8]
量 词
量词,是汉语词汇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一个重要显著特征。在先,中国语言学界最早一批接受英文语法的语言学家,自赵元任开始,大都不赞成量词这一说法,认为量词只是名词的一个附类。从量词的词性上看,大都也确实如此。譬如“万载”“万年”里的“载”与“年”就是名词;但它们在数词后面,却不再具有名词的全部含义,而具有一种对数词起到比较或限定的作用。这一比较与限定,即是量词的语法能指与所指。即便是古汉语,量词不仅存在,而且量大。前文已述,中国语言文字,在唐宋,是白话文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变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见证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变文”,量词是丰富的。
一、个、個、箇
感得八个人,不显姓名,日日来听。(《韩擒虎话本》)
相公前世作一箇商人,他家白庄也是一個商人。(《庐山远公话》)
个,是汉语量词里使用最频繁之一的词。几乎所有数词后面都可以跟“个”。个,不见于《尔雅》,也不见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收箇,许慎释“竹枚也,从竹固声”。段玉裁注“竹曰个、木曰枚”。箇,从字意来讲,是竹经人工之后的一种材料;从字形来讲,是一象形与指事相结合。从“箇”到“個”再到“个”,我们看到汉字的简化历程。“个”不见于19世纪末出土的甲骨文,“个”收于《甲金篆隶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8年),出自于西汉的武威简。(奇怪的是《甲金篆隶大字典》无“箇”“個”字条;《尔雅》“释草”“释木”都无这两字。)如果是这样,东汉的许慎应当是看见过“个”的,但《说文解字》没录。从“变文”看,个、個、箇三字义相似或相等,足见西汉时的偶尔简化已在唐时较为通常了。从而,我们看到白话文于量词的广泛使用。
二、量词独立使用
三尺白刃。(《汉将王陵变》)
人执一根车辐棒。(《李陵变文》)
更若为人十只矢。(同前)
现有十硙水。(《张义潮变文》)
不知江海有万斛之船。(《王昭君变文》)
附马赐其千匹彩,公主子仍留十斛珠。(《同前》)
收夺得驰马牛羊二千头疋。(《张义潮变文》)
(案,“头”“疋”两量词并用,实为罕见。)
锡杖一条(《庐山远公话》),即“一条锡杖”。
每人纳绢一疋(《李陵变文》),即“一疋绢”。
大哭号啕泪千行(同前),即“千行泪”。
赤斗钱二万贯、紫磨黄金一万铤(同前),即“二万贯赤斗钱”“一万铤紫磨黄金”。
三、名词与量词合二为一
雕弓每每换三弦。(《汉将王陵变》)
大战曾经数十场。(同前)
既是今日当值……何不巡营一遭。(同前)
四、特例
百般放圣谩依着,千种为难为口粮。(《譬喻经变文》)
“百般”“千种”看似是已约定俗成的俗语或白话(也为佛教语转换),但并非专用词汇。“般”或“种”可结构成“千般”“万种”。可见,“般”与“种”具有量词属性,即量词不为它之前或之后的数词所限定。
数词量词集成举例
敦煌变文,是汉语口语大规模进入汉语书面语的一个重要诱发端口和平台。从上述举证中,我们已可以看到,数量词特别是量词的大量使用,乃是口语的放大与讹变,也是口语转换为书面语的途径之一。上述举证大都在某一特定的单句,下面的举证为一散一韵。
散
昔时大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婆罗门僧,教学八万个徒弟,善惠为上座。六年苦行,八万伽他之偈,并五部佛心,无有不识,无有不会。善惠却往还不,和尚又遗三般物色:一、是五百文金钱,二、五百文金舍勒,三、五百个金三故。过大雪山北面,言道王舍大城,有一大笛长者,常年四月八日,设个无遮大会,供养八万个僧:并是盲聋喑哑,无数供养。八万个僧,各布施五百文金钱,五百个金舍勒,五百个金三故。善惠四月八日,至到王舍大城,到是大富长者宅内,四部僧众齐坐念诵。善惠发四弘盛愿,言道四部僧众,……善惠却问僧众:“大雪山南面,有一梵志婆罗门僧,教学八万个徒弟,曾闻不闻?”四部僧众却道:“之闻。”“八万个徒弟,上坐善惠,曾闻不闻?”“曾闻。”“既若知闻,某乙便是善惠。”四部僧众,便请为上坐。常年四月八日发愿,旧上坐数年发愿。……其大愿给孤长者,心中大悦,遍布施五百个童男,五百个童女,五百头牸牛并犊子,金钱、舍勒、三故,便是请佛为王说法。……给孤长者启王:“王园计地多少?”“其园八十顷。”……请佛园中说法。千二百五十人俱听法。……世尊到来,不用者七珍八宝,则要莲花转巽。有一个小下女人族逐水如而来,瓶中有七支莲花。便善惠言道:“娘娘卖其莲花两支,与五百文金钱。”……善惠却便发心供养,一支两支便足,不用广多。……七支莲花都与善惠,同其一会,到第二日早去。世尊到来,善惠便是供养如行。世尊取其莲花两手如把,五支僻着,一面与行,两支僻着,一面与行。(《不知名变文》)
韵
……欲知百宝千花上,恰似天边五色云。……佛愿慈悲度弟子,学道专心报二亲。……千般锦绣铺床坐,万道殊幡室里悬。……锡杖敲门三五下,胸前不觉泪盈盈。……独自抛我在荒郊,四边更无亲伴侣。……耳边唯闻唱道念,万众千群驱向前。……守此路来经几劫,千军万众定刑名。……烟火千重遮四门,借问此中何物罪。刀山白骨乱纵横,剑树人头千万颗。……七分这中而获一,纵令东海变沧田。……手中放却三楞棒,臂上遥抛六舌叉。……一过容颜总憔悴,阿娘既得目连言。……十恶之惩皆具足,当时不用我儿言。……力小那能救慈母,五服之中相容隐。……左右天人八部众,东西侍卫四方神。……(《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不知名变文》是一篇缺漏和错讹甚多的短文(只有散文没有韵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有散有韵),是韵多过散的一篇长文。不过,两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为数词、量词(还有序数词)最为密集的变文。它可以看作是变文数词、量词的汇总范本。从两范本可以看到本文所持的观点:无论数词还是量词,在敦煌“变文”已经十分成熟,而且运用已经手(书面)口(口头)如一。它除了为白话文的成长提供了生存平台和生长空间外,也为汉语的词汇提供了增长平台和空间。通过这一数词、量词的汇总范本,我们还可以看到(或者猜到),变文以散韵相间、说唱并举,又通过抄经者的努力,使佛教成为一个在中土影响极深的文化现象。它同时也表明了宗教从庙宇从僧侣从知识精英走向了大众和民间。由这些数字带头的词构成了有别于原来文化的不同的文化特点。由此也可以说,由这些佛教的专门词汇所建构的话语权力(Discourse Power),不仅侵占了本土宗教道教的领地,还削弱了从汉开始建立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与儒家文明为主导地位的汉文化与汉文明。它甚至让儒家文明里的某些元素(如善、如劝善等),成为佛教感化众生或者寻找自我安慰的言语(Speech)能指(Signifier)与所指(Referent)。就当时看,外来文化、外来文明的进入并非洪水猛兽。自汉至唐,尤其是唐,就佛教东传以来,外来文化与外来文明成為庙堂与江湖、知识精英与大众平民共生共长的需要。[9]在这一文化和文明的衍变里,如此多的数词和量词为大众所接受、所运用,彰显出这一语言现象和言语(Parol)文本(Text)强大的内在力量。而且,这些词汇直到今天,依然深入骨髓地植入在汉语的机体和血液里,依然展示着它们的话语权力。[10]
不过,我却遗憾地发现,像《汉语白话史》(徐时仪著,2007年)这样的当代语言学著作,虽然讨论了变文在白话文进程中的作用,却没有讨论在此过程的重要元素之一的数词与量词;甚至于被视为敦煌变文字义研究的重大成就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蒋礼鸿著,中华书局,1960年),亦无涉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虽然讨论和辨析了敦煌变文里的约800个词,却无一关涉到数词与量词。[11]可见,敦煌“变文”的语言学研究尚有空白和空间。这样来看,仅就变文来讲,语言学(除社会语言学外)的文化研究似乎更具空间。当然,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注释:
[1]今天我们看到的“变文”,绝大部分来自20世纪初敦煌石室的发现。“变文”这种散韵结合的文体,在后来的宋元戏曲等里能够见到。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3年写成,初名《宋元戏曲考》)里列举宋元戏曲数百种,所列名录中,虽然没有佛经的影子,但是他在所引《都城纪胜》(大约成书于公元13世纪)时讲,宋带有戏曲因素的“说话”共有四种:一小说、二说经、三说参请、四说史书。可见,“说经”在宋时,尚有一席之地。
[2]据《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变”首见唐人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周绍良据此称“《目连变》之名始见于此”。但这并不妨碍“变文”一名为郑振铎所首次命名。因为“变”与“变文”毕竟有区别。
[3]《春秋·襄公十一年》春正月作三军。“左注”: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公注”:三军者何,三卿也。作三军。……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汉语以数字打头的词汇,历史悠久,且源远流长。佛经汉译,则极大地放大了汉语的这种构(造)词法。
[4]《尚书》第一篇《尧典》便出现“四岳”(四方诸侯)一词。汉语以数字打头的缩略词,是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质。就在《尧典》里,有“二生”“三帛”“五典”“五礼”“五玉”“五端”“五刑”“五器”等。
[5]“问一得N”句式,源于《论语·季氏》——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与此句式相近的还有“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此可看出本土的儒家文明在融会外来文明时所展现的本领。
[6]鸠摩罗什(343—413)译的《般若波罗蜜金刚经》,是佛经汉译影响最广的一部佛经。此经共5000余字,分32篇。分篇都用“第”表序数,如“法会因分第一”“一体同观分第十八”“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也许,“第”这一序数词,就源自佛经汉译。
由《墨子·七患》也可看到序数的发端。其无序数词,用语尾助词表达——“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一患也;二患也;三患也;四患也;五患也;六患也;……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見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
《论语·公冶长》还提供了另一种序数的表达(无序数词,无语尾助词,用语前助词排列)——“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礼记·中庸》还提供了“其次”这样的序数样式。
[7]《汉语外来词词典》在“C”目里,收外来词近200个,日语外来词就有36个。依词典词条的汉语拼音顺序为:财阀、财团、采光、参观、参看、参照、策动、插话、茶道、常备兵、常识、场合、场所、成分、成员、承认、乘客、乘务员、宠儿、抽象、出版、出版物、出超、出发点、出口、出庭、初夜权、处女地、处女作、创作、刺激、催眠、吋、错觉等。这些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词,语(词)源竟然不是汉语词汇(至少不是现代汉语词汇),而是来自日语。
[8]《辞源》录四字头佛教词汇有:四天(四禅天)、四生、四苦、四相、四众(四部众)、四尘、四轮、四辈、四谛、四摄、四人天、四梵天、四天王、四分律、四食诗、四论宗、四面八方、四弘誓愿、四律五论、四十二章经。
录四字头道教词汇有:四大、四虚。
[9]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灭佛发生在佛教东传中国化的唐代。“会昌(公元845年)灭佛”的原因很是复杂,但主要一方面来自唐武宗崇尚道教(这是唐王的传统),另一方面,来自僧侣们的势力壮大以及恶行扰乱了唐朝政权与天子的声威和安全。
[10]五四经典作家散文如鲁迅的《朝花夕拾·后记》:“研究这一类三魂渺渺,七魄茫茫的学问,是很新颖,也很占便宜的。假使征集材料,开始讨论,将各种往来的信件都编印出来,恐怕也可以出三四本颜厚的书”;韵文如郭沫若《凤凰涅槃》,其中“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就用了五次。此两例都来自佛教文化和佛经转译词汇。
[11]《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讨论了“千次”“一向”等词,但这些词的词面的“数”和“量”的词,并非数词与量词之义,而是变文里的专用词汇。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