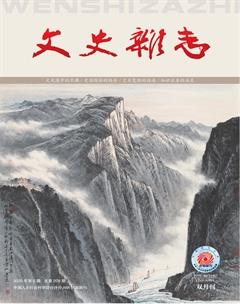与流沙河的君子之交
冯广宏
2019年11月23日下午3时45分,流沙河与世长辞,享年88岁。
按道家的规矩,不看生,不看死,没有去参加追悼会,而是照老家的习惯,凡得知至亲好友的噩耗,总要甩碗以表痛悼——由老伴找来一只特大的碗,往地上一摔,摔个粉碎。
我自迁居成都城南翠云庭后,有时拉着手推车到長寿路菜市场买食品。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上午,我买了东西往回走,忽然看到许久未见的流沙河,正坐在长寿南路新开的杏林药房门口一排长椅端头。这不奇怪,他家就在附近的“名仕公馆”里。我高兴地挨着他坐下。他一把抓住我的左腕,紧紧不放,用嘶哑的喉音问候寒暖。我以为他偶感风寒,以致声带受损,便让他不要出声,只听我一人倾诉。流沙河露出快慰的神色,紧抓我手静听我洋洋洒洒地讲述考证《山海经》地理的过程。我先批判当代研究者声称找出了不少能够开发的经中物产,可是产地在如今哪省哪县,却没有个说法,那又有什么实用价值呢?鄙人不才,试图补上这一课……我讲得眉飞色舞,发现他儿媳(或保姆)正推来摩托等待拉他,便扯他起身。他发觉我背部异常佝偻,竟低音关切道:“你背怎么了?”我说在“本命年”,从一个市场的旋转楼梯上“后空翻180度”摔往地上所致。他遂露出惊讶的眼光打量。我则夸他腰杆挺直,定然长寿,继而目送他上车去往医院。殊不知此时他已罹疑似喉癌,而这次相聚正是人生旅程中的永诀!
开始知晓“流沙河”这个名字,应该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报纸上,他的大作《草木篇》被点名为一株“大毒草”,谓“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从此便给扣上“知名右派”的帽子。他后来在所在单位的四川省文联监督劳动。据他说,那时只有小他10岁的川剧团女演员何洁看上了他,送来不少安慰。可是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6年,“大批判”开始掀起燎原大火,四川急急跟风,到处寻找“三家村”“四家店”。老右派流沙河再一次“猫吃糍粑——脱不到爪爪”,由民兵押回老家城厢镇(属于金堂县)“劳动改造”,主要项目是拉大锯——将完整的圆木解剖为板材,与一位熟手合作,一人在上,一人在下,不断将锯片啮入,化为木屑纷飞。这全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没有取巧的途径,虽然秋凉,仍然要打赤膊,并不像儿歌“拉锯,扯锯,家婆门前唱大戏”那样轻松。可是三个月后,何洁却跑来看他,提出要和他结婚!他俩背着门外的民兵,到派出所去登记。工作人员虽然知道“流沙河”的反动大名,但一问姓名,女名“何洁”,男名“余勋坦”,便十分麻利地开具“结婚证”,毫无留难。就在1966年农历七月初七中国情人节那天,他们花了10元人民币顺利成婚,老母亲做了红烧肉佐餐,成为6年拉锯生活中的特大喜庆——提起这一过程,流沙河咯咯直笑。
他有首“怨而不怒”的诗——
纸窗亮,负儿去工场。/赤脚裸身锯大木,音韵铿锵,节奏悠扬。/爱他铁齿有情,养我一家四口;/恨他铁齿无情,啃我壮年时光。/啃完春,啃完夏,晚归忽闻桂花香。/屈指今夜中秋节,/叫贤妻,快来窗前看月亮。/妻说月色果然好,明晨又该洗衣裳,不如早上床!
1978年底,四凶既灭,艳春将至,流沙河调回四川省文联,担任《星星》诗刊编辑,与何洁住在东风路文联的一间资料室里。到了科学园林百花齐放的1979年4月,四川科普作家协会在周孟璞等人的倡导下成立,编起《科学文艺》杂志来,八方征稿。流沙河因为夜晚看到了“不明飞行物(UFO)”,就写了一篇《会飞的大铁环》。当时我也凑热闹,按格律体写了《科学幻想诗》6首,登在杂志上。那时写作的人不多,有一天科普作协召集作者们聚会,我和流沙河、刘兴诗、闵蔚儒恰巧同坐一桌,一问年龄,居然发现4人同岁,都是1931年生——属羊,分外高兴。当时闵蔚儒是出版社编审,创办了《文明》杂志,大大咧咧;刘兴诗是地质学院讲师,与童恩正、王晓达、叶永烈号称“四川科普四杰”,自视甚高;只有流沙河和我比较低调,每次开会便更加谈得来。他比我小4个月,常戏称我为“大哥”。
流沙河对汉字情有独钟,常常冒出一些奇思妙想,进行解读。说老实话,他对汉字结构确实提出不少新见解,完全另辟蹊径,功劳不小;后来还出版《流沙河认字》一书,走的是宋代王安石《字说》的一路,完全不理《说文解字》那一套。我这人思想比较保守,内心并不赞成他走那条路,但并没有对他表白,更多的是钦佩他的新奇头脑。当时,我下功夫研究都江堰史,对于《华阳国志》上描述古都江堰“壅江作堋”疑惑不解,就按“右文说”对这个“堋”字进行考证,最终发现上古都江堰的形状,应该像广西灵渠那样的“飞鸟形人字坝”,蜀语便叫做“堋”,近代英国人称为“迷宫堰”。我把这一发现写出稿本寄给流沙河,他很快就回了信:“蒙赐大作稿本两册,当即放下工作,拜读一遍,较之读诗,收获大多矣。你对‘堋字的解释,我很赞成,提供一个旁注。”他说英文“bund”(堤岸、码头、江边道路)似乎就是“堋”的音译,“供你一笑。握手并致谢了!”这使我眼界大开,其时当在1984年。
他的夫人何洁(普照寺居士,法名圆果)经常在都江堰盘桓。那里的市委书记徐振汉主编《青城文荟》双月刊时,延请她担任实质性的“副主编”,于是征稿的担子便压在这位瘦瘦小小的文学女史肩上。1989年9月,流沙河来信替何洁向我约稿:“恳求你写一些水利文化,有关都江堰市的普及之作,知识性与趣味性兼顾的最好,她想同你见面详谈”;还留下电话号码。
何洁其人极富人情味,不厌爬上狭窄的5楼楼梯来到寒舍,原原本本讲述刊物的稿件要求,还很快与我们一家子亲如家人。后来凡有替流沙河传书带信的任务,都由她上下狭梯出入蜗居。我简直过意不去,跟着让膝下子女代表我到流沙河家去问候、道谢。那时,我赶快写了篇《都江堰之谜》加以应命,10月12日流沙河就来了信:“广宏兄:大作拜读,何洁嘱我代她致谢”,“请勿停笔”;“何洁还说,大作富有智趣与文味,避免了专业性的枯燥与艰深,很好”。这番鼓励使我信心百倍,一口气写了10几篇刊登在《青城文荟》上。徐振汉主编非常高兴,说:“冯广宏的文章看起来不打脑壳!”他还说,文章里有些内容,居然连老灌县人都不十分清楚,“可算及时雨了!”12月何洁来访时又带来口信:流沙河认为“你觉得自己有用,就慢慢地用,不要一下子把它用完”;又说流沙河业已离开《星星》诗刊岗位,在家里翻译《庄子》(早在他拉大锯时已在极力钻研)。后来,流沙河出版了《庄子现代版》一书,赠送了我一本。
令我特别惊讶的是,没过多久,就听说流沙河与何洁“协议离婚”了!这事对我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回头一想,文人的行为与寻常百姓大相径庭,往往有出人意料之举,按谭楷的话来讲:应该属于“一个屋檐下容不得两个天才”。后来何洁与宜宾地區专员周继尧结婚,流沙河也与文化人吴茂华结婚,各自寻求幸福。
话说回来,我对流沙河的仰慕之情,常常表现为比较欢喜亦步亦趋地模仿他的行动——比如2000年时,流沙河寄来一张与南瓜相伴的照片,题为“我·瓜”(四川话里“瓜”与“傻”同义);我立刻抱着一个大冬瓜拍了张照片来模仿,冬瓜上刻“我是瓜”三字,寄给流沙河,他回信说,这算是“瓜瓜相慰”了;还考证“冬瓜”该写成“董瓜”,因为董是“大”的意思。
我曾模仿流沙河文风写了首《宽窄巷子吃面》的打油诗——
饥来驱我去,欲觅苍蝇馆,怀揣五元钱,原无豹子胆。行行至斯巷,每生怀旧感,眼前咖啡厅,蟹文横作榜,叩门欲参观,小姐花枝挡,先生不消费,进门可不敢!缩肩再前行,觉巷真不短,街尾有露台,台边喇叭响:全市最低价,七元面饱管。赧颜进杯葛,愿作七折讲,主人慨然诺,端是好老板!坐陪闲聊天,记者昨曾访,经商不言利,文士交游广,知君亦老九,相见颇恨晚。须臾小面来,味拟八珍爽,感子升斗惠,助我稻粱养,掩此阮囊虚,恭奉五元款,老板一笑收,取走桌上碗。
我将诗拿给流沙河看,他扭头笑道:你是个教授,何至于一寒如此!其实我不过是调侃自家,借己讽人而已!本来我想听听他评价这诗的质量,他倒没说一句,难道是“自郐无讥”?随后我看到成都市美轩饭馆1995年流沙河的题壁:
民以食为天,食以民为铨,百姓所称赞,物美且价廉。白肉拌齑蒜,腰花炒猪肝,落座便可啖,爽口即为鲜。鸡丁说宫保,豆腐说淮南,锅巴烩肉片,炸响满堂欢,嗟彼千金宴,凤牝配龙鞭,宴毕犹未饱,花些冤枉钱。惟食可忘忧,惟肉可延年,能吃你不吃,齿落吃铲铲!我来市美轩,青春想从前,幸哉胃口好,饕餮喜有缘。——市美轩题壁,乙亥腊月流沙河
对比一下,觉得他的打油作品活泼多了。
2005年前后,我专门研究巴蜀文字(或称图语),写了不少文章,每每都寄给流沙河看。2005年3月11日,他写给我一封信:“广宏兄:久疏音问,恭颂笔健”,你“释S形符号为‘寿字,深获我心,此即耕畴之畴,象形,以音借作寿也”。有个类似钟形的字,他说是个“皂”字,“义为栎实,俗呼青子,象形,其外有壳带刺如栗房。皂即造也,以音借也。你专攻巴蜀古字,所见藏品多,判断比外人准确。我见识少,妄说供一笑耳。”随后,他又来信详谈他的见解,对我把“双蝌蚪文”解释为“仁”很不赞成:“巴蜀文明远逊齐鲁,动辄打打杀杀,怎能孳育出‘仁的观念来呀。谨陈管见如上,亦愚者一得耳。兄之训练有素,头脑精密,立论又踏实,于古蜀文字之研究定有大成。”这些见解和鼓励对我帮助极大。
流沙河的知识面相当广博,懂得的东西很多。有一回,他在电话里说:“你把蜀王杜宇的图腾定为鹰鹃不妥”,因为鹰鹃不叫,叫三声者称为“李桂阳”,即子规,可能更接近事实;盖“子”字古音为“倪”,与“李”音近,“规”字则为“鹃”字音转也;叫“快快快谷”四声者,称为布谷鸟,而小杜鹃只叫二声,即鹁鸪。
有段时间,流沙河的书法忽然受到大众欢迎,请他写字的人越来越多,“润笔标准”也日益上抬。有人对我说:你和流沙河耍得那么好,赶快去找他写一幅字吧,恐怕过两年他不得给你写了!我觉得有理,赶快打电话去请他写字,声称“足下书法我想收藏”!他飞快地给我写了一副对联托人送来,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想送点礼,但又害怕“太俗”,正好2007年出版家吴鸿欲出《成都诗览》一书,让我找几个朋友进行编纂,要求收集齐全,不留漏网之鱼。我便约流沙河给《成都诗览》作序,趁机送去1000块钱稿费,借花献佛。
隔了不少时光,就到了2016年,流沙河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的上牙都是假牙,腰亦不太好,但如果人家邀请他讲课,他倒毫不犹豫,特别是讲诗。我回答“八旬开外的人,还是以休养生息为要,高兴就讲,不高兴就不讲,千万别勉强!”他好像哼了两声,也不知道同意不同意。
此后,我们的交往便越来越少——现在想想,更加深了无穷无尽的怀念。
记得流沙河评价我写的文章,总是夸我“出自性灵”,“举重若轻”;可是我写这篇怀念他的小文时,却感到有千钧之重,根本就轻不下来,写了三四个月,一直无法搁笔。
沙河兄——劳碌一生,总该安息了吧!?
(题图:流沙河在成都图书馆讲《诗经》 邓风/摄)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