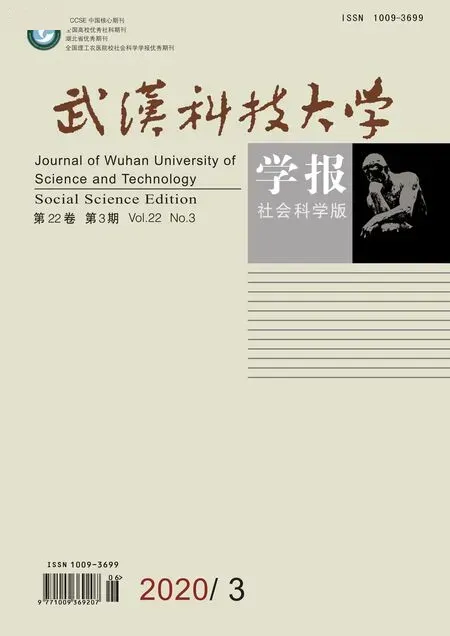人口与人文经济环境对家庭养老的制约性影响及其体系重塑
邹铁钉
(浙江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引言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道出了“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亲情伦理。多子多福的观念得以盛行并成为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其和子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家庭养老资源的充裕度和多样性。
子女作为家庭最核心的资源,其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创收能力是支撑赡养能力的三大要素,而个人品性、孝道伦理则是构成赡养意愿的内生驱动力。赡老育幼的代际星火传递是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文化命脉,让每一位老者在垂暮之年安享天伦之乐,是当前构建 “大健康”社会和全面部署实施老龄化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做好这项工作极为紧迫而又重大,关乎你我他,关乎千万家。
然而,受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市场化影响,子欲养而力不足以及“子欲养而亲不待”(《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的问题变得日益突出。2018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2.4亿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了1.6亿人,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7.9%和11.9%,社会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①。我国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早在2015年就已低至2.87∶1②,平均不到3个人就要养活1个老年人,一些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对夫妻至少要养活4个老人的情形比比皆是。
与此同时,中国失能老年人口超过4000万人③,而全国现有社区中拥有齐全服务设施的不到35%,拥有完善公共服务的不到40%,此外还有高达67%的家庭意外伤害发生概率④。所以,现有福利体系服务能力同与日俱增的老年护理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急需在家政服务、精神慰藉和医疗陪护方面增强供应。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2018年外出农民工超过1.7亿人⑤,随之而来的是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愈发突出。当前中国空巢老人占到现有全部老年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⑥,如何安置和照顾好这部分人口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特别是留守人员中部分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亟需社会从制度和资源上给予保障和帮扶。
可实际情形是专门为留守老人提供支持的福利资源极度匮乏,截至2017年底,全国注册登记的提供住宿的各类社会服务机构3.2万个,每千名老人能分享到的养老床位不到31张⑦,这方面的不足集中表现为养老资源供不应求、资金缺口大和政策落实不到位三个方面的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在经济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当下,生育率波动与文化冲击主要通过家庭规模、家庭结构以及居住方式和道德习俗改变人们的养老选择。国内外学者已经从功能、模式以及面临的危机等方面对家庭养老问题作了很多有益研究。笔者以此为基础,从生育行为的养老功能及其政策限制、生育数量与质量的理性权衡、生育率下降的家庭结构效应以及劳动力流动等人口冲击角度以及长者权威、孝道伦理和利他行为等文化传承角度,系统梳理家庭养老的影响因素及其体系重塑的方向。
二、家庭生育行为的动机与政策限制
从养儿防老角度看,生育子女与货币储蓄具有同等甚至更重要的作用[1]。曾经一段很长的历史里,子女在物质和情感上的回馈,是人们进行生育行为的主要动力。作为能带来预期收益的投资品,子女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父母获得赡养的可能性及其充裕性。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家庭只需在数量和质量之间作出取舍,便可实现生育收益的最大化。
多子多福是家庭追求生育收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更多的子女不仅意味着更小的风险和更充裕的养老资源,还意味着更为满意的情感关怀。通常,子女越多,父代对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的满意程度就越高。陈卫等通过抽样调查发现,中国适龄婚育青年中,出现偷生、超生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比例高达19%[2]。这种冒险生育更多子女的冲动,从侧面证实了有无子女在幸福感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有子女的要明显高于没有子女的。
但尹银却不这么认为,研究发现更多的子女除了增加亲代的婚姻满意度之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和生活质量[3]。所以,生育数量并不是决定老年幸福的唯一因素,也许增加教育投入和提高生育质量才是关键。
可见,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子女的数量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收入水平、性别差异以及户籍类型这些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王钦池认为,缩小个体收入差距、促进性别公平、加快城镇化建设以及提高生育行为对老年幸福有增进作用[4]。
然而,从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无论是“生育一个好”的号召,还是“生二胎”的松绑,生育政策都没有跳出抑制人口生育的惯性,追求多子多福的生育冲动是不允许的,而晚生少生则是常态。
当然,生育政策并不是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唯一原因,人们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估算也是影响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当前,急剧变化的经济与社会环境明显提高了家庭的生育成本,把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培养少数子女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因为子女能力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会对父母的老年幸福产生积极影响[4]。一般而言,能力越强的子女,给父母提供的赡养资源越充足。
可见,选择优生优育、注重教育投入、改善子女个人素养和经济条件能让家庭中的老人更容易获得物质和情感上的富足。伍海霞认为,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子女,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显然追求质量的生育行为强化了子女的赡养意愿及其力度[5]。
不过,在经济高度市场化和人口流动常态化的当下,无论是生育更多的子女,还是生育更优秀的子女,都不能完全消除家庭养老的不确定性,而发展以养老保险制度为主体的社会资助体系,则能从长远和根本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充足的问题。所以,协调政府、社区和家庭力量,构建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能更好地筑牢物质赡养和精神赡养的“篱笆”。
三、生育数量与生育质量在家庭养老中的替代关系
有学者认为,受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人口生育状况会从高出生率、高增长率逐步向低出生率、低增长率转变,进入人们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慢慢消失[6]。
Gary S. Becker对社会逐步走向低生育的现象给出了经济学解释,认为对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的考虑是家庭自发抑制生育冲动的根本原因⑧。Henry Aaron认为,当影响生育成本与收益的人口增长率、资本利率和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动后,将深刻影响到家庭老年抚养比和子女赡养能力[7]。一般而言,子女数量变少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享受到更多的成长资源,日后成为高质量劳动力获得优厚报酬的几率就会更大。
Oded Galor等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子女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生育的子女数量竟然越少[8]。这表明,单从家庭养老功能看,生育质量确实对生育数量具有替代作用,所以,将生育重心转移到生育质量上,不断提高子女的赡养能力,可有效应对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生育质量包括优生和优育两个方面。历史上,关于优生的说法数不胜数,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说法,汉代有“女不嫁消渴病”的观点,就连柏拉图也说过“不对婚姻加以约束,人类就会走向衰败”[9]。其实,优生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结婚对象、生育时间和终止妊娠的选择,生育出体质健壮、没有缺陷的后代。
而优育作为高质量生育的另一面,主要是借助后天教育,提高子女的综合素养和社会生存能力。优育论者认为,人的天生资质相差不大,后天环境对人的塑造才是关键。只要在成长的各个环节,辅以正确的家庭引导和良好的学校教育,成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为了追求生育收益的最大化,在对生育偏好和生育选择作出调整时是有风险的[10]。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出路。由于政府职位稀缺,知识分子容易成为失业者,家庭面临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比较大,而生育更多子女的家庭却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新生劳动力可以借助家庭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11],从而,生育质量对生育数量的替代是有限的。
如果政府能从制度层面参与进来,人们的生育动机和生育风险将会小得多。当然,过度依赖养老保险也不是什么好事,容易引发养老金支付危机,养老保险体系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必须控制好,所以,有必要建立与家庭养老互为支撑的综合养老保障体系,从根源上解决家庭养老资源不足和子女逃避养老责任的问题。
四、生育率下降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生育率下降会产生两个截然相反的影响。消极的一面是,子女数量变少将直接改变家庭结构、瓦解居家轮养方式和加重子女人均养老负担。积极的一面是,子女数量变少,家庭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培养单个子女,从而促进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技能成长,为日后步入社会拥有更高的就业竞争能力和经济收益打好基础,最终起到改善家庭养老状况、充实家庭养老资源的作用。
其一,生育率的变动改变了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互动关系,这便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家庭结构效应。过去数十年,中国的家庭结构在只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下,从金字塔型变成了倒金字塔型,一对夫妇要同时养活1个小孩和4个老人的“四二一”家庭结构越来越普遍。此类家庭结构由于子女的唯一性、直系亲属连接的脆弱性和成员之间的强依赖性,很容易受到诸如婚姻、生育和寿命等突发变故的冲击[12]。
生育率主要通过改变人们的居住方式、生活照料以及赡养负担对家庭养老产生影响[13]。然而,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年龄差距的存在,个体成员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扮演着自养和照顾他人的角色,并不需要太多的照顾,所以家庭养老危机也不像媒体所渲染的那般严重。
其二,生育率下降促进了对单个子女的精细化培养,个体可以积累起更多有助于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本。人的惯性思维通常会认为生育数量越小,老人获得照顾的可能性就越低,但当考虑到生育数量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后,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生育较少子女,意味着单个子女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投入,从而培养起更强的社会生存能力、取得更优越的经济条件,进而可以为家庭养老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源和经济支持,这也是之前生育政策向“少生、优生”转变的重要原因。
古有“凡子事父母,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⑨之说。赡养并不只是给钱给食物,还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敬意、情感关怀和生活照料。通常,生育数量越多的家庭,越容易在生活和情感上得到满足,比如张俊良等研究就发现,生育1个孩子获得赡养的可能性是43%,而生育3个孩子获得赡养的可能性则是69%[14]。这表明,子女越多生活越幸福的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
显然,在增进老年福利方面,生育更多数量和生育更高质量各有优势又各有缺陷。为了将家庭结构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除了优化生育政策和培育环境外,还得寻求外部力量的帮助,特别是要积极发挥政府和社区在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建设中的作用,为老年人创造阳光、温馨和舒适的生活环境。
五、人口流动对家庭养老的冲击
《明律·户役》记载 “同居共财,孰非己有”,这说明聚族而居、几世同堂的群居文化源远流长。历史上,以“亲缘、血缘”为纽带,以“同居、合灶、共财”为特征的居住模式非常普遍。郑军等认为,老年人对居住模式的选择与个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一般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时候选择分居,而在体弱多病的时候选择共居[15]。
共居离不开土地对人的束缚,更离不开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历史上的户籍制度和重农抑商政策就发挥了这种维持村庄社会形态和家庭结构稳定的作用,并由此演化出尊老爱幼、“父为子纲”等孝道伦理及礼节文化,为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中华文明奠定了强大的内在社会稳定机制。
然而,当中国自1978年开启市场化改革之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建设的推进,商业文明和人口流动对社会形态、运转方式以及经济结构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背井离乡前往远方谋生,以土地、户籍和孝道伦理为约束条件的传统家庭养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日起而作、日落而息的温馨场景和共居生活方式淹没在滚滚向前的市场经济洪流中。
首先,人口跨区流动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影响子女之间的养老分工,比如居家者负责日常生活照料和病痛护理,而外出者则负责生活开支[16]。二是外出子女在流入地获得好的就业机会,赡养能力得到了提高。三是居住分散化,家庭成员的亲情联络变得稀疏平淡,空巢家庭及其留守老人的照料难题比较突出。
其次,由于人口迁移弱化了家庭对子女的控制,父母获得赡养的不确定性风险必然会增加,先前那种子女萦绕膝前的天伦之乐也会受到较大冲击。同时,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受旅途时间、交通费用以及相关心理成本制约,不能在父母急需之时回到身边施以援手[17]。所以,一些人口流出地人员不愿多生的倾向非常明显,这当然和出于生育耽误抓经济的考虑有关[18],但更重要的是没有感受到生育更多子女所带来的好处。
可见,空巢家庭和留守老人得不到很好的照料便是人口流动最直接的负面影响。中国人口主要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空巢家庭及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在这些地区比较突出[19],而精神空虚、情感寂寞以及体弱多病又是空巢家庭的共性问题。
另外,人口流动还将一些诸如照看小孩、农业生产以及整理家务等本该由子女完成的事务压在了留守老人身上[20]。同时,外出子女还因为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改变,自动降低了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和对父母供养的积极性。虽然空巢老人可以通过参与生产劳动解决一部分生活来源,但若得不到子女的援助,不断瓦解的乡村社会也会将他们推向老无所依的生活困境。
考虑到市场化改革对就业机会的分散以及对“父母在,不远游”(《论语·里仁》)等孝道传统的冲击,让外出务工者心无旁骛地工作和让留守老人得到妥善照顾,理当成为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关心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家政服务组织,满足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又要调动社区和工作单位积极性,帮助留守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难题,同时还可以通过筹办老年互助协会来重塑老年人的精神家园,为他们提供老有所乐、老有所归的文化娱乐场所。
六、长者权威对传统家庭养老的支撑作用及局限
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父系社会,“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基于农耕文明、支配约束子女的长者权威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
子女主动提供经济援助和情感关怀,部分是出于父母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当然道德习俗和国家政治的支持也不容忽视[1]。社会变迁过程中,父代权威作为约束力量,在维系赡养伦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子代作为父母的利益延续,其数量多寡直接关系到父代的幸福感。
始于上古时期的父代权威虽然是确保子女具有反哺行为的激励机制,却具有时效性,只在子女成年之前具有约束性,一旦子女长大成人或者结婚分户就失效了,此后道德习俗、法律制度和子女的自觉性变得更为重要。
中国有过一段经济集体化的历史,代际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对传统父代权威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子女成婚分家和谋求经济独立的行为日益普遍,亲子之间更多的是平等互利关系而不是臣服和驾驭,这一转变有助于解决子女赡养动力不足的问题。当然,老人照料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制度设计、政策安排和社会支持上。
当前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已经动摇了父代权威的人口学基础[21]。家庭结构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成员规模的缩小,正从金字塔型向倒金字塔型转变,几世同堂以及几个子女轮养的格局被打破。
与之同时,伴随人口流动而来的居住分散化进一步削弱了父代权威的控制能力,昔日子孙萦绕膝前的天伦之乐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奢求。此外,中国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伟大转变,面对高度货币化的市场经济,自给自足的家庭赡养危机重重,需要借助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对其进行全面改造[22]。
基于以上分析,为了修补父代权威的弱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在继续弘扬尊老爱幼等美德的同时,尽快完善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从制度层面保障居家老人的基本生活及其精神文化需求。
七、孝道伦理对家庭养老的支撑作用及局限
孝道作为传统美德,在处理代际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孝经》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 谓之悖礼”,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呕心沥血,子女赡养既是本分,更是义务。
孝道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还有着深刻的现实基础,同西方社会重视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不同,中国社会比较关注亲子之间的纵向关系[23]。西方理论界比较倡导个体自由选择论,认为父母的生育行为是自愿主动的,而子女的出生则是被动接受的[24]。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既不是道德约束,也不是法律义务,而是一种基于血缘的亲情和友谊。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更注重于家庭经营。中国的国家特性建立在道德与伦理的结合之上,直接表现为家庭孝敬。子女对父母的敬畏和孝顺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父母对家庭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二是数千年来,几世同堂的共居文化所凝聚的同情共感基础[25];三是当政者基于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借孔孟之嘴在全社会树立的所谓“三纲五常”⑩的道德伦理。
孝道伦理的核心体现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情感关怀等三个方面。作为传统美德的孝文化,既响应了亲情的精神呼唤,又在融洽家庭关系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26],是确保父母在物质和精神层面获得保障的道德制衡机制。
然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冲击下,“孝, 善事父母者”(《说文解字·老部》)以及“善事父母为孝”(《尔雅·释训》)所提倡的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依从和赡养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低生育率所引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足以及分散居住所引起的子欲养而力不达等问题,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对养老意愿、养老情感和养老方式的认知。
一种源于西方、注重本我和追求个性发展的自由观念对家庭成员的互动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成为大多数新生人口的常识性选择[27]。亲子之前那种驾驭和臣服关系逐步被权利和义务上的对等互利取代。追求生活独立的分户而居和基于人口流动的分散而居,从根源上动摇了“父为子纲”的家长权威,同时也从社会网络结构层面瓦解了亲子互动的情感基础。
随着父代控制能力的下降以及社会道德约束的宽松化,子女赡养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大力发展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作为替代性力量,意义极为重大。正如龙大轩所说,孝道伦理存于大义,为宗法赡养规制所依赖。为遏制弃父不养以及为子不仁的悖逆行径,完善相关赡养法规十分必要[28]。
值得注意的是,孝文化只是能从心理、精神和道德层面对赡养行为起到引领和规范作用,易受外部环境影响,具体效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变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年轻人的生活环境日趋复杂,生活压力与日俱增,如何动员社会力量协助他们做好赡养工作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八、亲缘利他行为对家庭养老的支撑作用及局限
生育行为一方面浸透着养儿防老的自利动机,另一方面又彰显了自我牺牲的利他美德[29]。父母将部分资源用于子女培育和成长以最大化自身效用的行为便是利他动机的外在显现。
与父代相比,子代的赡养行为也极具利他偏好[30]。由于子代的效用函数囊括了父代消费,父母的幸福感会直接影响到子代的效用,亲子之间的互利行为还能带动彼此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家庭财富积累和生活状况也会因此得到改善[31]。子代之所以体现出极强的亲缘和互惠利他特性,是基于父母在幼年时所给予的情感关怀和生活照料。
然而,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却在家庭层面动摇了利他行为的人口学基础。若能够制定一个与赡养负担相同的养老保险缴费比例,则能达到与赡养同样的效果[32]。当然,面对生育数量的下降,亲代对子代的利他性投入也可从提高子女社会适应性及其经济创收能力上得到补偿。若能确保“子代福利增量”与“亲代投入回报”之和超过培育过程中的利他性成本,那么对子代的利他性培养便是应对家庭养老危机的有效策略。
但要注意的是,养老不仅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需求,还应包括精神和情感上的关怀,因此,发展公共养老保险体系并不能完全抹杀掉子女赡养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社会中逐利动机不断冲击人们道德底线的当下,受城市化、工业化和人口迁徙影响,家庭成员同情共感和互惠利他的生活基础逐步趋于瓦解,一些诸如空巢家庭及其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已成为一大社会难题。所以,需要协调政府、社区、家庭和社会等多方力量,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让他们心有所属、老有所乐。
九、结论与政策启示
家庭养老不仅包括衣食住行,还包括儿孙萦绕膝前的天伦之乐以及和睦互助的亲情愉悦和心有所属的精神需求。要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积极作用,就不能忽视生育理性、家庭结构、人口流动、长者权威、孝道伦理以及利他行为的制约性影响。笔者以现有文献的演进脉络为基础,系统梳理了人口、文化与经济环境变动对传统家庭养老的制约性影响。
研究发现,养儿防老是对繁衍生息这一动物本能的理性升华,人们不仅重视生育数量,还重视生育质量。在一个从鼓励生育向节制生育转变的国度里,多子多福被优生优育取代是一个自然过程。为弥补生育数量上的不足,进行精细化培养,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和经济创收能力是一种理性生育行为。
人的生活习性以及行为选择是外部环境长期塑造的结果。拥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在过去漫长简单非货币经济发展历史中,对生产资料和财富分配拥有绝对控制权的长者权威,在家庭代际更迭和协调成员互惠利他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闭塞农耕家庭生活受到的冲击越来越大,个体在高度分工的货币经济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亲子之间也不再是臣服和支配关系,而是基于平等和互惠的亲情关系。至此,道德囚笼的禁锢作用极大地弱化,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再是被迫被动的义务,而是自发自动的感恩和关爱。
自1988年邓小平提出“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以来,城市化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外出谋生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相闻于鸡犬的共室而居以及“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家庭生活场面被打破,随之而来的空巢家庭和对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越来越严峻。
此外,受计划生育政策和年轻人生育观念改变的影响,少生甚至不生的家庭越来越多,“老年人多、年轻人少”的倒金字塔型家庭结构日趋普遍,传统养儿防老以及依靠子女轮养的家庭养老观念难以为继。面对人文环境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剧烈冲击,如何重塑家庭养老体系,让老有所养不再成为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包括决策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应齐心合力共谋良策,从制度和政策设计上加以系统解决。
为应对人文环境变动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养老问题,我们在捍卫传统美德、调整计生政策和挖掘家庭自身潜力的同时,还得重视对公共养老保险体系的建设和投入,特别是对老年活动中心和敬老院等基础福利设施的建设。此外,还应当积极发挥社会资源和市场力量的作用,努力构建政府保基本、市场保多样化以及社区和家庭积极参与的综合家庭养老保障体系,力争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为老年人创造舒适、安心的生活环境。
注释:
①参见《老龄化加深!2018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24 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https://www.sohu.com/a/290724025_100146983)。
②参见《不到3个职工要“养”1个老人》(http://hebei.sina.com.cn/news/m/2016-08-15/detail-ifxuxnak0254117-p2.shtml)。
③参见《我国失能老年人超4000万 护理需求巨大》(http://baijiahao.baidu.com/s?id=1643067329607690617&wfr=spider&for=pc)。
④参见党俊武,周燕珉:《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版)。
⑤参见彭瑶:《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 836万人 近六成外出》(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06/11/content_74874576.htm)。
⑥参见《中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总数一半》(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3/c_1115276638.htm)。
⑦参见《民政部发布〈2017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每千名老人养老床位30.9》(http://www.sohu.com/a/246098937_100122244)。
⑧参见Gary S. Becker: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 inDemographicandEconomicChangeinDevel-opedCountri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⑨参见司马光:《居家杂仪》。
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三纲五常”这一道德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