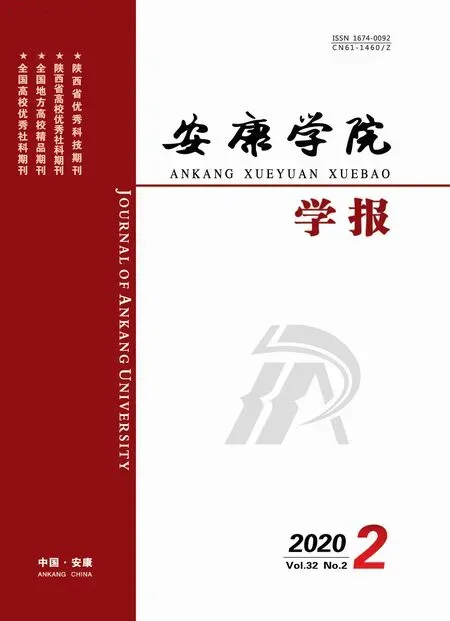在南方旧传统中挣扎的女勇士
——《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形象重读
陈韵祎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威廉·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曾被看作是一部关于男人的小说,因为小说中四位叙述者中男士占了三位,而当我们细致梳理小说情节后会发现,凯蒂·康普生才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在1946年的一次采访中,福克纳曾谈起《喧哗与骚动》的创作过程,他说:“为了讲好凯蒂的故事,我反复修改了五次才写好这部小说。当我最后完成时,我真正从创作的噩梦中解脱”[1]135。可见,福克纳为了写好这部有关凯蒂的小说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尽管修改了五次,小说的核心人物从未发生改变。福克纳借康普生家三兄弟之口,讲述了凯蒂的故事。三兄弟的叙述各有侧重,展现了凯蒂生活的方方面面。三人的叙述同时发生,就像一首乐曲的不同声部,演奏时,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实则和谐共生,为同一个主旋律服务。《喧哗与骚动》中,凯蒂就是全书的主旋律。
凯蒂是小说作者威廉·福克纳心目中的最爱。出于对凯蒂的特殊感情,福克纳把一则原名为《暮色》的短篇故事拓展成长篇小说,这才有了《喧哗与骚动》。他曾坦言:“我太爱她(指凯蒂)了,不能让她只活一个短篇故事的时间,她应得的不止那些。”[1]12但在许多评论家眼里,凯蒂只是简单地被视作一个“轻佻放荡的堕落女性”,如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曾说:“凯蒂只是一个性混乱的淫妇”[2]31;以格拉迪斯·米利娜(Gladys Milliner)为代表的评论家则说:“凯蒂是个非传统的南方女性,她不是通过爱或受诱惑而成为一个母亲,而是刻意地追求性自由,逃避规矩,最终逃离了康普生家的隔离……”[2]32。多数评论家只看到了凯蒂“堕落”的一面,而忽略了她反抗父权制文化、追求男女平等、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一面。
西蒙娜·波伏娃(Simone Beauvoir)在《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3]。也就是说,在男权社会中,有能力对凯蒂身份作出定义的,就是康普生先生和康家三兄弟。可是,通过这些男性的叙述,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凯蒂吗?借助这些男人的话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控诉凯蒂的“放荡和堕落”,很少有人从她的悲剧故事中发现这样一个“离经叛道”的女人其实是挣扎于南方父权制文化的阴影下,没有人看到她敢于反抗的勇气,没有人关注她在寻找自我征途中的努力。本文拟挖掘凯蒂·康普生反抗南方旧传统、构建女性主体意识所做出的努力,力图证明凯蒂并不是人们眼中的“荡妇”,而是挣扎中的“女勇士”,她挣扎在南方旧传统与自我意识的觉醒之间。
一、在南方父权制文化压迫下挣扎
凯蒂是《喧哗与骚动》的女主人公,也是串联整个故事的主线。她是一位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女性。她善良勇敢,从小就表现出对美国南方社会男尊女卑观念的不满,内心充满对男女平等的渴望。她七岁时就表现出了不服从哥哥的性格。“……昆丁打了她一下耳光,她一滑,跌到水里去了。她站直身子后,就往昆丁身上泼水。”[4]29她倔强勇敢,不惧哥哥的欺凌。当昆丁打了凯蒂耳光,她马上就反抗,对深受男尊女卑影响的哥哥,凯蒂丝毫没有表现出顺从、妥协。当昆丁警告她会受到惩罚时,凯蒂说:“我不怕,我要逃走,而且永远不回来”[4]30。凯蒂十六岁时义无反顾爱上了一个青年男子,两情相悦之下发生关系。在当时的南方社会,这是一个家族巨大的耻辱。康普生太太知道后,甚至在家里穿上了黑纱,宣称女儿死了。这是凯蒂追求男女平等的初步尝试,可是她出生于父权主义文化笼罩下的美国南方家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文化让她陷入挣扎。而这个让凯蒂在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和顺从父权制文化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男性就是班吉。
班吉是康普生家的三儿子,天生智力低下,家里所有人都嫌弃他,康普生太太甚至阻止凯蒂关心他。自私的母亲,让凯蒂代替了母亲的角色,成了班吉唯一的依靠。姐弟之间的感情日渐深厚,凯蒂成了班吉的精神支柱,同时班吉也成了凯蒂追求自由新生活的阻碍。凯蒂要想追求平等、自由的新生活就必须脱离这个腐朽的家庭,可离开家就意味着放弃班吉。正是对弟弟深厚的爱让凯蒂踌躇不前,反复挣扎。
班吉对凯蒂有强烈的占有欲,他不允许凯蒂同别的男孩约会。当凯蒂和男孩约会时,班吉觉得有人抢走了他的姐姐,便开始不停地哭闹。
“班吉。”凯蒂说。“你走开,查利。他不喜欢你。”查利走开去了,我(班吉)收住了哭声,拉着凯蒂的衣裙。
……
“我再也不会那样了。班吉。班吉。”接着她哭了起来,我也哭了,我们两人抱在一起。“别哭了。”她说。“别哭了。我不会再那样了。”于是我收住了哭声,凯蒂站起身来,我们走进了厨房,开亮了灯,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她的嘴。凯蒂像树一样地香。[4]69
……
“我(班吉)哭起来了。哭声越来越大,我站了起来。凯蒂走进房间,背靠着墙站着,眼睛看着我。我边哭边向她走去,她往墙上退缩,我看见她的眼睛,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还拽住了她的衣裙...我们走上楼去。她又停止了脚步,靠在墙上,盯看着我,我哭了,她继续上楼,我跟着上去,边走边哭,她退缩到墙边,可是我拽着她的衣裙,于是我们走到了洗澡间,她靠着门站着,盯看着我。”[4]97-98
当凯蒂洗干净之后,身上又重新有了“树的香味”,班吉才停止了哭泣。朝夕相处让班吉对姐姐身上的味道十分敏感。“树的香味”就代表了凯蒂的贞洁。班吉的哭闹其实是对姐姐失去贞洁的反应,他以为洗澡可以洗掉凯蒂的“不贞”。虽然班吉智力低下,但整个南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四处弥漫,班吉不自觉地接受着父权制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他在凯蒂追求自我的过程中不停地拉回她,让凯蒂在追求女性主体意识和恪守传统之间不断挣扎。
由此可见,凯蒂的初步反抗遭到了父权制文化的压制,而班吉对凯蒂的占有欲又进一步证明了父权制文化的渗透力的强大。父权制文化的根深蒂固加上凯蒂自身的不坚定,最终使她在反抗父权制文化时不断挣扎。
二、对南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
以种植园经济为生的美国旧南方社会保守、故步自封。为了抵御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冲击,捍卫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父权制文化不断深化。为了牢牢掌握对女性的支配权,强大的男权体制不仅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还制定了男女之间不公平的道德伦理。男尊女卑的思想不断加强,男人们强迫女性恪守妇道,循规蹈矩,使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主体地位。面对根深蒂固的南方父权制文化,凯蒂进行了勇敢的反抗。
凯蒂首先反抗以康普生先生为代表的父权制文化。康普生家族是典型的南方家庭,男性是整个家的权威,女性则要时时刻刻维护自己的淑女形象。康普生先生对“贞节”做了这样的阐述:“在南方,人们认为童男子是桩丢脸的事,小青年也好,大男人也好,因为女人认为童贞不童贞关系倒不大……童贞这个观念是男人而不是女人设想出来的……事情之所以可悲也正在于此;所有的事情,连改变它们一下都是不值得的。”[4]110对于男性来说,“贞节”根本就不重要,甚至保有童贞是一件丢脸的事情。也就是说,男性拥有对“性”的支配权,而女性甚至没有权利质疑男性的“贞节”。对男权世界的人来说,“童贞”这个观念是男人设想出来控制女性的,女性的价值只是做满足男人欲望的工具。康普生先生自然赞同这种不公平的两性地位,认为是“不值得改变的”。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让男人相信,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控制着物质世界和两性世界。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才是主体,而女性不过是被男性所欣赏的“第二性”。这种建立在父权制文化基础上的两性关系是自然而恒定不变的真理,女人就应该顺从男权社会制定的道德规范,认同男性的价值标准。一个女人如果不守“妇道”,就是十恶不赦的魔鬼。
凯蒂以放纵肉欲来作为对父亲、对南方父权制文化最致命的反抗。在视贞洁如生命的南方社会,凯蒂却认为,“贞洁连手指甲旁的一小块皮肤都不如”[4]325。男性对女性的“占有和奴役首先体现在他们对女性贞节的病态崇拜上”[5]63。对于父权制文化来说,女人的价值仅仅在于她的贞操,甚至超过了生命。为了确保女性的“纯洁性”,男人不惜泯灭女性的生理欲望,抑制她的自我意识,目的是把女人“赶进‘性空白的生活’中去……把性欲当作可耻的东西从后门推出去”[1]194。作为初具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女性,凯蒂不能忍受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她势必要反抗父权制文化,争取女性的权利和平等地位。她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束缚,未婚便与自己的爱人发生关系。这在当时父权制中心文化根深蒂固的美国南方社会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凯蒂勇于向社会偏见挑战,勇于向父权文化挑战,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争取性自由,追求女性的自由和主体意识,表现出无惧男权的勇气,体现出新女性的胆略,显示出独立的思想意识。她敢于逆传统而行,大胆表达对男权社会的反抗。“由于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声音,所以她唯一可资利用的就是自己的身体”[5]64,凯蒂以“性”的方式撕破男权社会虚伪的面纱。埃莱娜·西苏(H é lè neCixous)曾指出:“她的肉体在讲真话,她在表白自己的内心。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6]在当时的南方社会,凯蒂的所作所为被认为是彻底“疯了”,她在心理、审美和道德上完全迷失了自我,但她大胆地运用自己的身体,宣泄对男尊女卑、对性别压制的愤怒,以男人最惧怕的方式——放纵情欲来扰乱社会性别秩序,进而颠覆以男性为主体的南方社会,构建属于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这是何等的勇敢!
其次,凯蒂也反抗以母亲为代表的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凯蒂的母亲,康普生太太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女性,更是父权制文化最直接的受害者。对于康普生太太来说,没有什么比她的淑女形象更重要。班吉智力低下,经常需要抱着哄。康普生太太害怕自己的脊背像洗衣婆子一样弯曲,为了维护自己的优雅形象,她对班吉的哭闹置若罔闻。四处蔓延的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要求让本该拥有无私母爱的康普生太太变得自私冷漠。“女为悦己者容”,淑女形象归根结底是为了取悦男人。康普生太太已经将男性看待女性的标准自觉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时时刻刻从男性的角度思考问题,以男性的眼光规范自己的行为。她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缺失了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康普生太太的人生格言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没有什么中间道路,要么就是当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要么就是不当”[4]146。她经常教育凯蒂要做一位淑女,时时刻刻保持淑女形象。母亲对凯蒂的“淑女教育”更加深了父权制文化对她的戕害。康普生太太将自己所恪守的传统道德规范全部加在了凯蒂身上,所以凯蒂承受着来自男性和维护男性的“旧女性”的双重压迫。凯蒂不受母亲的影响,她不顺从男权社会对女性设立的条条框框,具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她觉得所谓的淑女形象只是一个空壳。凯蒂义无反顾地照顾班吉,“你不用为他操心,我喜欢照顾他”[4]70,她还对母亲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您回楼上去躺着,养您的病去”[4]91。这是对深受父权文化伤害的母亲权威的反抗,对所谓“淑女”形象的反抗,更是对南方父权制文化的反抗。
由此可见,凯蒂在追求两性平等、争取自己的话语权的过程中,对父权制社会女性遭受的不公平和压制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从不沉默寡言,听话顺从。相反,她总是大胆发表意见,投入反抗男权的行动,体现出女性的主体价值,与父权制文化赋予的传统女性角色不可相提并论。
三、结语
福克纳的作品几乎都以美国南方为背景。南方的社会发展影响着其文学传统,整个南方社会包含着“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现实主义趋势,保守的历史意识和厚重的悲剧感”[1]115。因此,有评论家认为,《喧哗与骚动》描绘的是“破落的康普生家族”[7]。这也是凯蒂想要逃离自己的家庭或者说逃离严峻的南方的原因所在。
福克纳所生活的南方社会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封闭的社会等级制度和严格的清教主义环境中成长的南方女性,面对新的工商业文明和自由的社会风气,内心爆发出强烈的反抗和叛逆精神,这种社会现实刺激了福克纳,因此使凯蒂具备了那种敢于打破枷锁、向往自由、不受约束的反抗精神和逃离意识。然而,由于福克纳对南方旧传统的依恋,他始终不肯彻底接受那个已发生了巨变的南方。因此,“康普生家的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只愿意承认那个漂亮、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小女孩子,而拒绝接受后来那个有个性、主张个人自由的凯蒂”[8],所以凯蒂的命运注定是悲剧。但是通过上文对凯蒂性格的解读分析,我们发现,那些单纯将凯蒂定为“荡妇”的评价有失公允。在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和清教主义环境严格的南方社会,凯蒂反抗男权的压迫,最终采取放纵情欲这样的方式来做出自己最后的挣扎。尽管她的反抗以失败告终,但她为构建女性主体意识所做出的奋斗和挣扎是值得称赞的,凯蒂是挣扎在南方旧传统与自我意识觉醒中的“勇士”。
通过康普生家族的没落,福克纳反映的是整个南方社会的变化。萨特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喧哗与骚动》:眼光总是往后看,就像一个坐在敞篷车里的人往后所看到的那样,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边出现,而左边是点点闪烁、颤动的光[9]。凯蒂和康普生家的男人不同,她的眼光始终是向前看的,她要为自己在这个男权社会争取话语权。她不愿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固守旧传统,做所谓的“南方淑女”。“康普生家的男人们都是深受男权思想荼毒的窝囊废,相比之下,凯蒂的生命是多么地鲜活有生气。她的反抗虽然以悲剧收场,但是她所执着的女性主体意识却并没有消亡。”[5]64正如小说结尾所说的那样:“反正凯蒂并不需要别人的拯救。她已经再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拯救得了。因为现在她能丢失的都已经是不值得丢失的东西了。”[4]431康普生家唯一的后代就是凯蒂的女儿小昆丁,她选择了比母亲更加极端的方式来颠覆男权,构建女性主体意识。这样看来,凯蒂的希望正在一步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