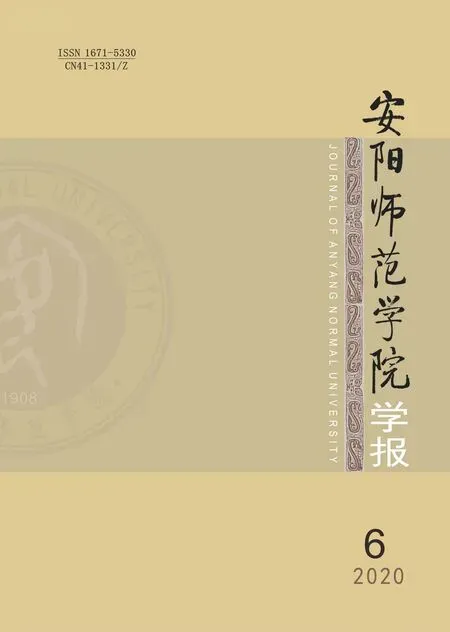《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得与失
季淑凤
(1.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2.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一、引言
《剑桥中国秦汉史》(下面简称《秦汉史》)是由费正清、崔瑞德任总主编,于198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卷。对于把《秦汉史》作为第一卷的原因,总编辑在一开头就做了交代,“最初打算从中国历史的最早时期写起,因后来大量的考古发现及一大批新材料的出土一再改变了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且至今也没有对这些新出土的证据和文字记载做出任何普遍公认的综合……因此,出于无奈,就从秦汉这两个最早的帝国政体的建立开始。”[1](译序2)从中可见总编辑的美好愿望与面对现实冲突时的遗憾和无奈。令人欣喜的是,1999年由鲁惟一和夏含夷教授编辑的《剑桥古代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仅弥补了《剑桥中国史》丛书中未能包含中国先秦史研究的遗憾,也是西方汉学界在条件成熟之后对秦帝国之前中国历史研究探索中积聚的自信心的体现。《秦汉史》的出版,无疑是从西方吹来的一股清新之风,中国读者得以“他者”的视角来回眸中国历史。在通读《秦汉史》后,西方学者的思维方式、观察与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以及他们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等论述的方式都给人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总体来讲,作者基本达到了“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的目的”。[1]
二、《剑桥中国秦汉史》的特点
《秦汉史》作者阵容庞大,由来自欧美的12位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秦汉历史的海外学者组成。李学勤曾称赞道:“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2](译序2)在总主编的指导下,这种各章均由该领域专家学者撰写,然后合编于一部大著作的模式,被称为“剑桥体例”或“剑桥体”,这种体例已被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熟悉和接受,影响较大。《秦汉史》共分16章,从脉络分布来看,主要可分为三大块:第一部分为政治及政治制度史(1-9);第二部分为经济和社会史(10-11);第三部分为思想文化史(12-16)。从篇幅来看,第二部分的经济和社会史稍显不足,相对而言,全书用5章来论述秦汉的思想文化,可见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视,这与国内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从时间的跨度还是从内容的覆盖方面来看,该书都较为完整,其中不乏编者精妙的描述和独辟蹊径的见解。具体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以批判的眼光审视历史,审慎的态度运用史料
由于撰写者们局外人的身份,撰写过程中少一点民族感情和价值参与,他们不盲目信从文献记载,不囿于前人成说,往往能跳出传统观念的窠臼,对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先入为主的偏见进行辩驳。如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卜德解释了秦帝国灭亡的五个原因,其中在论述道德因素时,他引用了贾谊在《过秦论》中阐释秦帝国灭亡的原因,“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1](P85)贾谊显然认为秦帝国是因为仁义的缺失而亡。卜德并没有受该传统观点的束缚,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一味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对秦帝国进行判断,而是基于对《史记》等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局限性的认识上,做出自己的判断,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只是部分地正确。作者认为《史记》中无论对秦帝国还是秦始皇的记述都过于阴暗了,“如果把出土的秦代法律条文与法家理论进行比较,就会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形象,这并非指秦王朝的政策不残暴和不存在剥削……事实上,如果其他国家也拥有秦王朝那样的实力,他们的政策也许与秦的政策不会有多大差别。”[1](P85)
对秦朝和秦始皇不太友善的记载还有很多。卜德在附录二中列出了《史记》中记载的六件事的描述都对秦始皇持有强烈的憎恨情绪。如怀疑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问题、公元前212年的坑儒、公元前221年水德的采用、公元前215年呈现的预言文字、公元前211年的坠星、公元前219惩罚山神之事。作者认为除却这些事件本身的虚构性、不可能性外,只要冷静地考虑一下与这些情节相联系的事情,就足以看出“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1](P94)
秦汉史的撰写者不但注意破除传统历史学家的偏见,对近现代中西学者的先入为主的观点也颇有揭示。例如,在解释秦朝灭亡的另一个原因时,作者提到西方普遍认同秦始皇由于采用法家的学说,建立了一套官僚统治机构,抑制了商业的发展,因而阻止了中国出现像西方那样的文艺复,以及随之出现的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式。”[1](P87)卜德认为“这种批评过于简单化了。”
美国学者柯文曾说过,“西方历史学家最大的挑战不是要达到消除民族中心主义的扭曲,而是尽量将这种歪曲减少和降低到最低点,以一种新的不那么西方中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3](P1)对历史已有观点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尽可能地去接近历史、还原历史, 这是中西学者都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二)注重文献资料的同时又善于利用考古材料
《秦汉史》编者在重视传世文献的同时又极为关注出土的考古材料。因为文献资料并不是很全面,传世过程也是错综复杂,难免带有史家的偏见,但是发掘的遗址和出土的文物也只能代表地下文物的一部分,而且往往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两种证据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偶然性,最好的研究方法就是要互相参照。《剑桥中国史》从秦汉史开始编写的原因正是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次考古新材料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早期史的看法,而一时又难以对早期中国史实进行综合,因此暂时放弃了撰写早期史。在秦汉史研究中,编者结合丰富的考古材料和现有文献记载进行论述。何四维(Anthony Fracois Paulus Hulsewé, 1910-1993)认为,“史书叙述中引语的可靠性以及这些著作作为整体的传统的忠实性为考古发现的物证所证明。”[1](P521)其中第九章在描述“行政法规” 时,作者认为首先根据史书和碑铭中的大量零散记载能整理出一些法规的轮廓,如征税制度或文官的职能。再加上充分利用在中国敦煌和居延附近的遗址中大量的完整文书,以及湖北睡虎地的秦代文书等考古材料,作者认为从这些片段的法令法规材料中也可反映当时官僚机器的工作情况。[1](P538)
同样重视考古材料的卜德,他在第一章“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部分,将有关商鞅政策的传统记载与1975年出土的法律文书进行对比,发现这些考古资料中的法律文书表现出一种较为实用、较少片面性的行政方法。虽然包括出土文书在内的法律是严厉的,但是不能由此断定它们就比同时代的普遍情况更加严厉。“而且法家理论也不像人们根据史籍记载的个别事件或后世儒家作者的责难所设想的那样教条,而是比较通情达理的。”[1](P74)通过将文献与最新考古材料的对照分析,卜德的评价更为客观、中肯。
(三)以长远的眼光和宏大的历史背景来重估历史事件
西方学者与传统历史学家保持了客观的距离,立意在“同情的理解”基础上,视野广阔,不局限于对一朝一代的史实分析,而是将秦汉时期作为持续不断的华夏文化的重要一环,把它与前代和后代紧密连接,切实从秦汉历史丰富多彩的实际出发,印证或辩驳中外史学家们已有的成说,最大可能地靠近、还原历史真相。
在导言中,编者认为中国的三部正史(《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没有把短命的王莽政权视为合法的王朝予以尊重,其缘由在于“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造者值得上天的赐福……他重视正统性......它对公正地评价像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虽然王莽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1](P223)为此,《秦汉史》单辟一章对该段历史进行完整地叙述。传统历史编纂学家在给王莽的传记中带有无情的偏见和捍卫汉朝的情绪,在论述中,毕汉斯对王莽的统治中一些偏见进行了辩驳。他认为对王莽政策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学者的目光短浅,中国学者往往在狭隘和孤立的情况下对王莽的政策进行研究,而且易受传统历史编纂学和班固对篡位者的敌对态度的影响。[1](P233)要看清王莽的政策,毕汉斯认为必须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在广泛的背景下才能进行更好地分析。通过把王莽时期采取的各种政策与前后汉时期采取的政策进行对比,“发现王莽并不是一个标新立异者,他的一些重大政策是在前汉政策的基础上的延续,班固对王莽的指摘缺乏根据。”[1](P234-235)关于王莽对待境内外非汉族民族的政策也同样有偏见,编者立足于史料的基础上,通过把王莽时期的对外关系与前后时代进行比较后发现,该时期的对外关系中,王莽的政策都是机敏、灵活和较为成功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和能干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有点迂腐气的儒生。”[1](P239)
再如,在考虑秦汉思想史时,编者认为“把本卷绝对限定在秦汉两朝的时期内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的。”[1](P1)因此戴密微教授在编写第十六章时,并未将佛、道两教的哲学和宗教的论述限定在秦汉时期,而是从秦汉一直延续到隋朝,将魏晋时期的哲学和宗教的发展始末完整地展示出来。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可避免过分地受朝代划分的限制,以便用宏观的眼光写出历史发展的前后连续性和因果性。
(四)系统方法的使用与文献计量分析法的运用
系统方法通常把历史看成“综合历史”“整体历史”,坚持多角度、多侧面地看待和分析问题。《秦汉史》即采用了这种方法,将每个历史时期切分为几个专题,专题之间既有关联性,又存在时间或空间上的跨越性。这种结构组织形式虽然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实则有着自身的规律,即按照系统方法的原则,围绕秦汉历史的各个方面和一切可变因素组织章节。比如“秦国和秦帝国”“前汉”“王莽,汉之中兴,后汉”“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汉代的灭亡”“汉朝的对外关系”“政府的机构与活动”“后汉的制度”“秦汉法律”,这几个专题是对政治方面的叙述。而“前汉的社会经济史”“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显然属于社会和经济方面。思想文化方面主要包括“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主权的概念”“儒家各派的发展”“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同时系统方法的使用还体现在谋篇布局上,采用了总分的结构。导言中,鲁惟一教授首先对秦汉卷撰稿人所依据的史料的价值和缺陷,该时期的考古的物证、已有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以及秦汉帝国独特的发展进行了总体评价。接下来,《秦汉史》以秦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为中心,探讨秦汉政治架构的形成、演变及精神内核,这属于顾钧教授总结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四种模式之一的“帝国模式”。这种采用总分结构,分专题进行历史叙述的方法,兼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结构上的关联性于一体,让读者对秦汉的历史有一个全方位、立体性的感知,便于对历史的整体理解与把握。
文献计量分析法就是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来研究历史,它是国外史学者在史学研究方面的社会科学取向,此方法在《秦汉史》中被较多地使用,有时还辅以表格进行叙述。如第十章《前汉的社会经济史》部分,东京大学荣誉教授西嶋定生在介绍少府的收入来源之一——口赋时,论述到“公元2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59,594,978人,假定1/5的人口是7-14岁的儿童,每人缴纳口赋20钱,那么总额就是3.8亿钱。”[1](P592)另外还包括它分管的国有土地的收入,“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5000顷(57000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4000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岁入一定相当可观。”[1](P592)像这样通过计算分析引导出结论的方法,在秦汉史中的“经济”“社会”模块中尤为常见,有时还采用表格的形式,将人口、耕地面积等数据更为直观地展示出来。这种计量方法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结论,更具有信服力。
(五)中西视野夹叙夹议,语言表达通俗流畅
《秦汉史》读者群定位于一般读者的普及读物而非为中国学家打造的史学专著,因此出于对读者阅读习惯的考虑,将文献中常用的枯燥的专业术语、史学名词以及乏味的文献引文等都加以改造,变成通俗流畅的文字。行文尽量将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时时迸发出与传统史书不同的精彩叙述和独到的见解,体现了求新求异的倾向。另外,文中还配备了大量的地图、表格、注释、附录、序言、导言等,帮助读者了解该书成书的背景、运用的史料情况等,便于读者深入了解本书内容及中国历史文化。
卜德在第一章介绍秦帝国修建的道路、城墙和宫殿时,为了让西方读者对这些道路、城墙等的长度及修建难度有一个更为清晰、客观的了解,多处采用与西方读者更为熟悉的事物进行比较分析。如“秦帝国公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的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3740英里(5984公里)两者可以互相对照”。[1](P61)接着,作者在审慎地运用《史记》所记载的材料基础上,描述了秦帝国一项伟大的防御工事——长城后,不禁感叹“建造这样一种防御工事,其后勤供应比建造一座金字塔、堤坝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要大得多……而且,似乎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具有更浓厚的筑垒自固的心理。”[1](P63)作者站在中西文化的高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而不是一味地平铺直叙。在中西文化的视域下,读者透过表面现象,更能看清中西民族的特点及深层的文化差异所在。
三、《剑桥中国秦汉史》的不足
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尤其对秦汉时期历史事件的评述,有其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其中也不乏精彩之处,但是也不应忽视其中的不足。
(一)《秦汉史》对国外成果借鉴较多,而对国内研究成果的借鉴太少
诚然,国外史学家在研究他国的历史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只有身在这种文化背景中的人才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内核有更深的体悟,更有发言权。然而,秦汉史撰稿人除了对原始资料批判性地选用外,很少采纳中国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引用了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如毕汉斯、德效骞、鲁惟一、沙畹、顾立雅、何四维、马伯乐、戴密微等。尽管崔瑞德等西方学者已意识到传统汉学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强调要注意吸收中国学者研究的经验和成果,认为西方社会科学如果没有中国学者的研究经验及成果也将是不完整的。[4](P1)然而,在《秦汉史》的撰写中,借鉴较多的依然是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无论是语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兼具优势的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却有轻视之嫌。
(二)《秦汉史》的合编模式导致的缺陷
《秦汉史》除导言、二、四、七、十二、十三章是由剑桥大学的秦汉史研究专家和简牍研究学家鲁惟一撰写外,每章的撰写基本是在主编崔瑞德、鲁惟一总体指导下,由不同的编者独立完成。这种每章由该领域资深专家撰著的方式,充分展示了各家所长,学术个性突出,保证了该部分的准确性。但是,也正因每位作者优势不同,文风互异,而且由于各自只负责自己那部分,会造成章节之间的失联、衔接不够紧密或者内容重复、前后观点冲突等问题。如第二章《前汉》已有“王莽谋害了平帝”的叙述,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中“王莽的崛起”部分又重新论述了该事件,而且前后两章都赞成“没有证据能证实或否定这个指控”,[1](P229)但通过对旁证的分析都说明王莽不可能犯这类罪行。与此相类,第一章《秦国和秦帝国》单列一节详细叙述了秦朝的“暴政”——焚书坑儒的缘由、过程及实际影响,而第十四章《儒家各派的发展》论述“秦国的法家思想”时,又有对“焚书坑儒”的描述,前后必然存在重复之处,似乎编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后面叙述简略。
此外,同一个事件的描述也有冲突的地方。如十四章中,罗伯特·P·克雷默描述到“当局对在京城的学者进行了审查,皇帝本人从中挑出大约460人,然后加以活埋(buried alive)。”[1](P752)而在第一章卜德描述到“秦始皇于是亲自挑选出460名触犯禁令的人,把他们全部处死。”[1](P72)编者还进一步解释传统意义上“坑”传统上是“活埋”的意思,而在这里,其真正意义应该是处死,而不是埋葬(不论是死埋还是活埋)。[1](P72)而且,小标题“焚书坑儒”对应的英文为“Burning of the books and execution of the literati”,作者用了“execution”(处决)一词而非“buried alive”。可见,前后两章编者对“坑”的理解是存在争议的。
四、结论
《秦汉史》作为《剑桥中国史》的第一卷,在汉学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其中章节之间难免存在重复、冲突等不协调之处,以及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借鉴较少等问题,然而总体来说,《秦汉史》是欧美专家学者研究的典型范之作。首先,由于欧美学者跨越中西的独特视角和批判精神,将秦汉史放在世界文化大背景下进行鸟瞰,使其研究呈现出异于国内学者研究的面貌,大大丰富了秦汉研究的内容。其次,欧美学者综合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朴记”,二者相互补充,互相印证,拓宽了研究视野。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欧美学者采用系统方法及文献计量分析法,更新了国内治史的方法,该方法将秦汉史直观、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行文通俗流畅,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秦汉时期“伏日”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