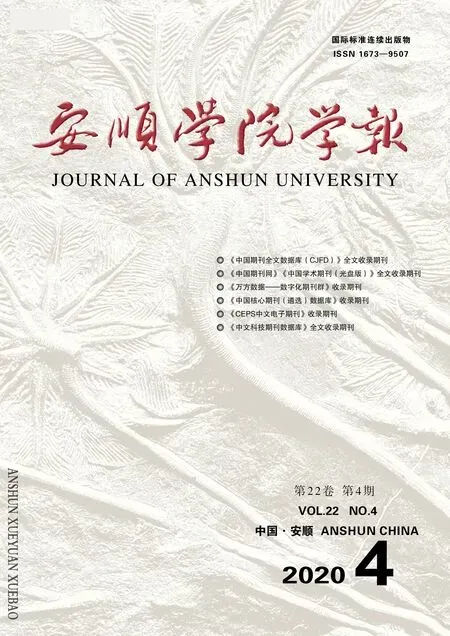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流”阐释
汪 燕
(贵州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人的自我实现是人类最迷人的话题之一,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尤以若干圣贤和智者的探索、践履影响为大,中国古代由于注重君子圣贤道德理想的修养和实现,在这方面给后人提供的案例足堪垂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学科的兴起,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理论建构,比如积极心理学的“心流”理论对此就有着系统的阐释和深刻的洞见,契克森特·米哈伊(Csikszentimihalyi)在20世纪60年代对“心流”(flow,也称最优经验)曾下过定认,认为是指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中,无视其他事物存在,意识和谐有序的一种状态[1]。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静养就颇为相似,藉此可以解释儒学史上最为重要的“龙场悟道”事件,为之提供另一种观照视角。“龙场悟道”是指武宗正德元年王阳明因仗义上疏而得罪权阉,被贬谪至贵州龙场驿,在近三年的时间内领悟了儒家“格物致知之旨”,并得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2]的结论,从而奠定了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的这一事件。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王阳明的龙场顿悟主要是在其精神修炼工夫中进行突破的,在儒家的思想视野中,“工夫”是指精神实践的具体方法[3],精神修炼工夫则归趣于内心世界的完满圆融和圣人君子的理想达成。这种精神修养工夫显然与心流理论存在“心同理同”[4]的共通之处,因为心流理论作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其主要目的与传统的宗教、哲学、文化一样,都试图为人类提供一套意义体系,帮助人们重建意识秩序,获得内心的和谐和自我的实现。但两者也有不同,王阳明精神修炼工夫注重自身体悟,较少逻辑严密的论证,因而可操作性和普及性受到限制,只能成为部分人向往和实践的成圣之学,而心流理论则运用现代科学思维和方法,对意识及其运作方式及心流体验的条件、结果等进行了细致严密的分析,并针对如何获得心流体验提出了明确的、具操作性的方法,从而使普通人也能够重建内心的秩序、达至内心的和谐。因此,我们以心流理论来阐释王阳明龙场悟道时期的精神修养工夫,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儒家修养的内在突破历程,并力图获得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创造性阐释,使其重焕当代的生机。
一、 “心流”理论与悟道过程
(一)意识及其运作方式
米哈伊的心流理论强调幸福来源于对自身心灵的掌控,只有学会掌控心灵、掌控意识的人,才能控制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和经验的品质。为帮助人们学会掌控意识,米哈伊对意识及其运作方式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指出,意识可视为“经过刻意排列组合的资讯”,它带有主观选择性,反映的是“我们心目中的人生”。[5]在意识运作过程中,注意力这一精神能量决定了在数以百万计的资讯中哪些能够进入其间。因而控制意识最明显的指标就是能随心所欲地集中注意力,不因任何事情而分心。而掌控注意力这一精神能量的主体是自我,这个“自我”代表我们建立起来的目标的先后次序。由此,当注意力唤起对一件新资讯的觉醒时,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精神能趋疲(psychic entropy)和心流体验;后者是积极发挥作用的一面,最为关键,即知觉收到的资讯与目标亲和,精神能量源源不断,一个人可以投入全部的注意力,以求实现目标,没有脱序现象需要整顿,自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无需分心防卫威胁的体验。在心流体验中,我们是精神能量的主宰,无论做什么事都能使意识更有秩序[6]。
(二)获取心流体验的条件
由于心流状态是人意识中一种自带目的的内在动机活动方式,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体验行为本身而不是想获得行为所带来的任何外在奖励或其他好处[7]。因而心流体验的获取除了受所从事的活动的结构特征及个体所感知的挑战和技能水平的平衡影响外,还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特点。米哈伊将那种更易产生心流体验的人称为“自带目的性人格”(autotelic personality),拥有这种人格特质的人喜欢享受生活,他们只是为了自身的内在目的做事,而不是受外在目标的驱使[8]。“自带目的性人格”是获取心流体验的基础条件,拥有这类人格的个体在各种情况下都能找到乐趣,并有能力对外来刺激进行筛选,只注意与这一刻有关的事物,由于其动机在于行动本身,不易受到外来威胁的干扰,因而有足够的精神能量,可对周遭环境进行客观分析与观察,也比较可能从中发现新的行动契机[9]。
(三)心流体验的过程
心流体验会通过“独特化”和“整合”这两种心理过程而使自我变得比过去更复杂和深刻,从而使自我得到成长。“独特化”是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朝独一无二的方向发展,这里实际上是指对“目的性人格”的坚守,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内在的向度;“整合”则恰好相反,借着超越自我的观念和实体,与他人和外界所获取的资讯联结,实际上是指对他者、外界资讯的处理方式,所以尽管仍然指向心理活动,实际上却是依赖于外缘的刺激而获得的心理整合机会,从信息源上讲我们可以称之为外在的向度。“独特化”和“整合”看似矛盾,实际上复杂的自我能够在紧张和平衡的心理进程中成功地融合二者,最后,自我会化整个生命为统一的心流经验,由此建立心灵的秩序[10]。
米哈伊指出:“心流与宗教有密切的联系,宗教实际上就是创造意识秩序最古老、最野心勃勃的尝试。”[11]同时文化确立起来的信念、目标和规则也可以促成心流体验的获得。因此米哈伊的心流理论也被应用于阐释宗教经验[12],这恰恰给王阳明的龙场悟道提供了一种解释的机缘,龙场悟道的关键在于静坐修养工夫,理论上虽源于儒家,在行动上却有对禅宗的借鉴。但龙场悟道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儒家事件,而有着前因、机缘、历程、后果、思想理路等要素,所以仍需通盘阐释。按王阳明十一岁时,便曾认定“第一等事”是“读书学圣贤耳”[13],这正是传统儒家君子圣贤理想的承续;置之于思想史,孔子最早发掘出“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以“君子”为教育旨归,以“圣人”为最高鹄的[14],下至韩愈和宋代士人紧承儒家“道统”理想,逐步系统化和光大了圣贤之学,但经元明两代战争和科举的冲击,宋代的圣贤之学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一般经生读书便径直以做官为目的,所以连当时阳明的塾师也认为“第一等事”是“读书登第”,两相映照,便可见出阳明少时所立的“做圣贤”之志,具有超越当时一般人的“自带目的性人格”。这是王阳明后来能在龙场洞悟的精神力量和先决条件,是他能进行心理“独特化”和“整合”的“超我”和“复杂自我”;按照“心流”理论,这种“目的性人格”越高,便越具有自我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样才有足够的意志力去应对大坎坷、大变故。在具体的龙场事件中,被贬的王阳明则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困境:就内在刺激而言,他需要在逆境之中保持内心的安定宁静;就外在挑战而言,他需要应对物资匮乏、官卑职小、仕途不明等种种现实的困境。这样的环境一方面激发了他从小立志做圣贤的记忆,另一方面激发他通过不懈的精神修炼成功地应对了困境。首先,在内在向度上他通过静坐澄默的精神修养工夫成功地掌控了意识,凸显了自我的精神能量,达到了内在的心定理明,在追慕圣贤之境中实现了自我的“独特化”。其次,在外在向度上,他通过事上磨炼的精神践履工夫积极应对外在的挑战,将压力转化为心流,超越自我并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实现了自我的整合。他自道良知之说的甘苦,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15],直到今天我们仍不难通过纸面阅读获得关于他受难的惊心动魄的想象,去想象当时外界的苦难刺激,揣摩他心理的复杂斗争和自我调适。当立志成圣贤的“目的性人格”遭遇了种种坎坷之后,其内心世界“独特化”和“整合”势必有着丰富的展开,只有如此,才能促成他自我的成长而最终实现龙场顿悟。
二、静坐澄默与掌控意识
根据“心流”理论,掌控意识是通过内心和谐而达到自我实现的关键。米哈伊特别注意到“在控制意识方面,我们可以向东方宗教寻求指引”,并且“东方有很多控制意识的技巧,能使人达到高层次的满足感。印度瑜伽,中国道教及佛教禅宗,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以从生物或社会的命定论下解脱意识为宗旨。……不同的方式却可以得到相同的效果,瑜伽徒的严格心理自律,禅宗信徒培养源源不断的自发性,目的都在于从混沌的威胁和生理冲动的严重制约下,释放内在生命,不再受制于以两者为工具的社会”[16]。按他所说,中国道教和佛教禅宗的精神修炼方法都有利于提升个体掌控意识的能力,达至心灵的和谐。儒家的静坐与佛家的禅定、道家中的心斋坐忘的修养相关,尽管它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佛”或“道”的属性,任何精神传统中也都可以容纳静坐作为一种修养方法。宋代儒家特别注意到静坐的工夫,周敦颐、二程、朱子也都有所论及,陈来就特别指出,宋代儒家的修养方法中,静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17]。在朱子看来,静坐的目的不是坐禅入定,而只是为了使主体获得一种清明的状态,以便识理接物,“静”的真正意义不是静坐,而是心定理明[18]。可见,儒家所强调的通过静坐而获得主体心定理明的状态与心流理论中强调通过佛道二教的修炼方法而实现对意识的掌控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王阳明青年时期就曾筑室洞中修习静坐,也曾出入佛老多年,深受佛道二教精神修炼方法的影响,在静坐修养方面有相当丰富的体验。他被贬龙场后,能够超脱外在的夷狄患难、得失荣辱,达到内在心定理明的状态,其关键即在于静坐澄默的精神修养工夫带来了对意识的掌控。具体而言,被贬龙场后王阳明内心面临着多重的刺激,一是才华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他十五岁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二十六岁学兵法,二十八岁考中进士,上边务八事,颇有韬略统驭之才,之后历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等职。三十四岁时,已在仕途历练了六年的他希望能够施展抱负,安邦定国、平定叛乱。同年,他与湛甘泉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19]。然次年被贬龙场骤然使他陷入仕途无望、成圣无果的苦闷之中。二是忠诚进谏却被贬的冤屈。正德元年(1506年),忠直之臣戴铣、薄彦徽等上疏进谏,武宗听信权阉刘瑾的诬告,将二人罚下诏狱。王阳明“首抗疏救之”[20],在奏疏中他并未直言戴、薄二人所言是否正确,只是反复强调言官因言获罪的危害,在奏章的最后他指出自己是一介小官,因为皇帝曾下有“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21]之旨,才敢冒死为皇帝进谏。这样委婉的上疏,如果皇帝本人看到,未必会勃然大怒。但不幸的是奏章先要经过刘瑾之手,即使王阳明措辞委婉,并未直言斥责刘瑾,但依然触怒了权阉,他被罚下诏狱、廷杖四十,之后终被贬谪至龙场。三是生命时刻面临危险的担忧。正德二年(1507年)夏,王阳明赴谪至钱塘,“瑾遣人随侦”,王阳明自度不免被害,危急关头他用计“托言投江”才得以逃脱[22]。经历了一路艰辛跋涉,他终于在第二年春抵达贵州龙场,但由于“瑾憾未已”[23]而一路追杀,即使在远离京城的深山之中,他仍然面临着生命的威胁,对生死的担忧依然笼罩着他。四是对异域环境生存不适的焦虑。生长于中原的他被贬谪至龙场后,面临的是一片几乎未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熏陶的蛮荒之地。此地自然环境极端恶劣,“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之中,魑魅魍魉,蛊毒瘴疠”[24],又当地少数民族不通汉语,难以交流,足见他遭遇异域环境时内心所受到的冲击。五是对亲人父母的顾念。他在抵达龙场后,有大量的诗体现了对亲人父母的深切顾念,如《龙岗漫兴五首》:“梦魂兼喜无余事,只在耶溪舜水湾”[25],《赠黄太守澎》:“惟营垂白念,旦夕怀归途”,《秋夜》:“山泉岂无适?离人怀故境。安得驾云鸿,高飞越南境。”[26]在多重的刺激之下,王阳明如何能够超越外在的夷狄患难、得失荣辱,重获内心的安宁呢?有着多年佛道精神修炼经验的王阳明在龙场深山之中为自己寻到了一处山洞,他在山洞中制作了一个石椁,“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不知经历了多少时日,在不懈静坐澄默的修炼之中,在不断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的过程中,终于达到了“胸中洒洒”的状态。[27]这一状态是他心理世界的凤凰涅槃,他突破了往昔的自我,重塑了自己的圣贤理想,完善了自己的心理世界,在此基础之上才彻悟了格物致知之旨。从心流理论的视角来看,他通过静坐工夫的修炼,久之而胸中洒然,于荣辱得失皆已超脱,实际上也就是达到了对意识的控制,实现了意识的独立性,从而获得了心灵的和谐。意识的独立性从本质上讲,蕴涵了自身的“独特化”过程,这种“独特化”的内涵是“自带目的性”的“做圣贤”人格的达成,所以才能转化成一种不为外在所动的意志力。他静坐修养返照内心,以“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来作对比追问,实际上关系对“自带目的性”的“圣贤”理想的审视、比较、质难、修补、调整,等等;意识掌控也必然是在“圣贤”理想的映照中获得的,所以从心理分析来看,这里的静坐修养实际上和“自带目的性”的“超我”人格是交融发生的,这样才会提升修养工夫的品格。
没有这种修养工夫的普通人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可从与王阳明具有相似处境的仆人和吏目的对比中彰显出来。据钱德洪所著《年谱》记载,在龙场艰辛的生活中,王阳明的仆人们全都病倒了,身为主人的阳明亲自找木柴生火煮粥喂食给仆人,细心的照料他们;怕仆人们心情抑郁,阳明还以歌诗愉悦他们的身心;仆人们还是郁郁寡欢,阳明又为他们调曲诙笑取乐,慢慢地仆人们才忘记了自己身处疾病夷狄患难之中,逐渐康复起来[28]。此外,王阳明在龙场时还写过一篇《瘗旅文》,正德四年(1509年)秋,一小吏携一子一仆赴任,途中经过龙场,寄宿在苗家。阳明听说他们是从京城来的,本来想找他们打听消息,但因天色已晚,阴雨连绵,遂作罢。第二天一早,阳明打发仆人去时,发现一行人已经离开了。到了中午时分,有人说,在不远处的山坡下,有一个老人死了,另外有两个人在旁哀哭。阳明心知,一定是那小吏死了;傍晚时分,又有人来报,说城下有两个死人,另有一人在旁叹息;阳明询问情状,知道必是那小吏的儿子也死了;第二天又有人来报,说坡下已经有三具死尸了,阳明知道连那仆人也死了。阳明怜悯其曝尸荒野,带领两个童子去埋葬他们。阳明和仆人埋葬了三人,还亲为之撰文为祭,其祭文中除了对三人的悲痛怜悯之外,还有阳明的敏锐的洞察,阳明不明白这个小吏为何要为了微薄的俸禄,携子千里迢迢赴任,这样的俸禄即使是携妻子躬耕于山野也完全可以得到,既已为了这份俸禄赴任了,就该欣然而往,又为何愁眉不展,不胜其忧呢?阳明于是分析:这个小吏经历了层层险阻,跋山涉水、攀崖行峰,饥渴劳顿、筋骨疲惫而来,到了龙场,瘴厉攻其外,忧郁又攻其内,怎会不死呢?于是想到自己背井离乡到龙场已经两年了,两年的时间中经历了种种艰险,历尽瘴毒而仍能保全自身,为何那小吏到了龙场后就死在这里了呢?阳明自己洞察到了关键的所在:“吾未尝一日之戚戚也。”[29]正是精神修养工夫给他带来了内心世界的心定理明,并实现了自我对意识的掌控。
以心流理论来解释阳明与仆人、小吏对夷狄患难和得失荣辱的不同看待、处理方式,可见其根源在于他们对意识的掌控能力不同:阳明由于不懈的静坐澄默,培养了独立的意识,带来了心体的澄明无滞和心境的安定宁静,实现了个体成圣的“独特化”,从而能够将龙场之苦化为乐,并保持“未尝一日戚戚”的心境。正如米哈伊所指出的那样,在“自带目的性人格”的基础条件下,“一个人可以不管外界发生什么事,只靠改变意识的内涵,使自己快乐或悲伤,意识的力量也可以把无助的境况,转变为反败为胜的挑战。”[30]
三、事上磨炼与压力应对
从“心流”理论的达成来看,内在向度掌控意识后所取得的“独特化”有着“陷入自我中心的危险”,即便王阳明有做圣贤的“目的性人格”,也仍容易走向教条主义和执着自偏。所以“心流”还要追求向外的“整合”,以期形成“复杂的自我”,在“超我”独特化和“整合”融通化之间达成平衡,建构起既不失去个性,又能融和世界的成熟自我。所以米哈伊又特别强调将外在压力转化为心流体验而获得自我的整合,这有似于儒家的内外兼修或文质彬彬的交互调济。与“心流”理论对内在意识掌控和外在压力应对的同等重视相一致,阳明的精神修养工夫也同时重视静坐自省内心的良知德性及事上磨炼自身的喜怒哀乐。虽然阳明“事上磨炼”的口号晚年才提出,但此种精神修炼工夫在龙场悟道时期已经体现出来。他所谓事上磨炼,是指于人情事变中磨炼自己一心的喜怒哀乐,磨炼自己良知的感应,磨炼知行合一的本体[31],要在具体、复杂的行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心理应付能力,应对外界的种种困境,承担起社会责任,做一个刚毅强健的实践家[32]。仔细钩沉他当时所经历磨炼之“事”,最少面临着异域冲击、物资匮乏、官卑职小、仕途不明这四大苦难和困境,我们不妨分别观察他对此压力的应对和自我“整合”。
(一)异地冲击之苦转化为与民同乐之乐
阳明初至龙场,面对的是“瘴疠蛊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33]的自然环境,且面临与当地土著言语不通的困难:“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34],就连当地人都认为王阳明无法久居于此。阳明认为此地虽无高楼殿宇之宏伟,无文仪揖让之礼节,却自有淳庞质素之遗风;龙场当地的老百姓虽好骂人、好说粗话,但性情率真、淳朴,如“未琢之璞、未绳之木”,却“无损其质”[35]。在龙场近三年的时间中,王阳明以其圣人人格感染和教化了龙场的百姓,将异域冲击之苦转化为了与民同乐之乐。他在《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中写道:“群獠环聚讯,语庞意颇质。鹿豕且同游,兹类尤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36],可见他已和龙场的村民互相放下戒备,能够一起尽醉畅饮取乐。而随着了解的加深,龙场的村民们受到王阳明圣人人格的感染,越发敬重和同情王阳明。他们自发为王阳明修建了房屋,阳明对于村民为他新建的住所甚是满意,他在房屋的四周种上蔬菜和花草,房屋掩映在浓荫之下,打开窗户可以看见远山,这样的景致当然不能自己一人独享,因此他还常在这里与百姓们对坐饮酒,乐而忘忧。这一过程可以见出他在“独特化”之外重新认识到他者的价值,转苦为乐实际上就是“整合”的实现历程。
(二)物资匮乏之苦转化为自食其力之乐
生于官宦之家的王阳明,从未亲自从事过劳作。到了龙场后,面临居无定所,生活无着的困难,他开始向村民们学习筑屋、种田、种菜、采薪等生存本领,将物资匮乏之苦转化为自食其力之乐。阳明所留诗作《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中写道:“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及兹春未深,数亩犹足佃。岂徒实口腹?且以理荒宴。遗穗及鸟雀,贫寡发余羡”[37],在阳明看来,学习开荒种田不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劳作之中也有乐趣,劳作的成果除了供自己及仆人所需外,还可以惠及鸟雀,贫寡。在《观稼》一诗中,他写道“下田既宜稌,高田亦宜稷。种蔬须土疏,种蓣须土湿。寒多不实秀,暑多有螟螣。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38],可见在阳明的眼中,四时农务,稼穑之事中也有物理,也有至道,值得细细参究。在《龙岗新构》一诗中,王阳明写道:“素缺农圃学,因兹得深论。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39]。
(三)官卑职小之苦转化为护国佑民之乐
龙场驿丞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但身处低位的王阳明却始终未忘记自己作为儒者的社会责任,并将官卑职小之苦转化为护国佑民之乐。在《龙岗漫兴五首》诗作中,王阳明写道:“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40],虽然自己身处夷狄患难之中,但是从未丧失过忧国忧民之心。事实上,王阳明也是做到了这一点。王阳明抵达龙场后不久,水西安宣慰因不满朝廷设置驿站于其城中,想要拆除驿站,并就此事寻求王阳明的建议。王阳明在《与安宣慰》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不能拆除驿站的缘由:“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如果擅自拆除,那就是违反天子礼法,将为安氏招来祸患。安宣慰最终采纳了王阳明的意见,没有拆除驿站,维护了朝廷的威严。后宋氏辖下的阿贾、阿札部叛乱,为祸一方。当时有传言说二部叛乱乃为安氏指使,政府于是下令让安氏平叛祸乱。但安氏却迟迟按兵不动,安氏之民还扬言宋氏之乱应当宋氏自己平定,安氏怎么能受宋氏役使呢?王阳明听闻此事后,即修书一封与安宣慰,直言指出“使君与宋氏同守土,而使君为之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独委之宋氏乎?”并且将安氏目前面临的局面进行了分析,如果不出兵相助宋氏平定叛乱,安氏也终将不保。收到书信后,安宣慰方悚然有怵,于是率领部下平定了叛乱,当地的老百姓也得以重获安宁[41]。
(四)仕途不明之苦转化为讲习教化之乐
王阳明始终具备儒者忧国忧民的用世情怀,但拥有雄才伟略的他却在正当壮年的时候被贬龙场,面对权阉当道,仕途不明的困境,王阳明转而将人生的价值体现于教化众生的实践之中,将仕途不明之苦转化为讲习教化之乐。在王阳明居夷期间系列诗作中,有不少描述了王阳明与诸生的讲习游学生活。如在《诸生来》一诗中,他写道:“门生颇群集,樽斝亦时展。讲习性所乐, 记问复怀腼。”[42]在《诸生夜坐》一诗中,他也写道:“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43]而在诗作《诸生》中,王阳明同样描写了师生之乐:“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44]。可见王阳明在龙场时常与诸生一起,或讲诵、讨论、静坐,或歌咏、鸣琴、聚饮,虽然所居之处条件简陋,但谈笑无俗流,王阳明不禁感叹这样的师生之乐乃是同孔子与学生“浴乎沂,风乎舞雩”之乐不谋而合的,他有意如孔子一般诲人不倦、教化众生。
需要注重这几种苦乐转化的共性,艰难困苦的外界磨炼作为一种资讯在进入心理场域时,最初与王阳明做圣贤的“独特化”理想是相冲突的,可以说如没有这种苦乐转化,他的圣贤人格就容易变成纸上谈兵,不可能走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但他成功地应对了各种挑战,体现了儒者的责任和担当,超越了个人荣辱得失的小我,而复归于天地万物一体的大我,则其间较然呈现出了一个高蹈的圣人理想和艰难实际的现实语境两相冲突和调适的“整合”历程。这正与心流体验下围绕“自带目的性人格”浑然忘我、与大我密合、超越自我的状态完全相一致。恰如米哈伊所指出的那样,在压力之下变得更坚强的人“懂得如何把无助的状况转变为新的心流活动,并加以控制,为自己找到乐趣,在考验中锻炼得更坚强”[45]。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是将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到周遭环境中去,持有开放的态度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这不仅是享受心流经验乐趣的重要因素,也是克服困境的中心机制”[46]。这正是“心流”理论视域下事上磨炼的积极意义,庶几可以解释王阳明悟道之后能与民同乐,最终自道其学问“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其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动态的心理世界,唯此才能明白他最终达到“久之胸中洒洒”圣人境界的艰难不易。
概而言之,一方面王阳明通过静坐修养,成功解决了内在种种心理冲突,实现了对意识的控制,达到心境的安定平和,从而能够超越外在的得失荣辱,实现自身的“独特化”;另一方面,王阳明通过事上磨炼,成功应对了龙场时期的种种外在的苦难,达到了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超越境界,实现了自身的“整合”;向内的“独特化”必经向外摄取所返照的内心“整合”,才能走向圆融的新自我。自身的“独特化”和“整合”都是紧紧围绕“成圣人”这一“目的性人格”的基础条件而展开的,所以他最终才能实现自我的成长,顿悟出圣人之道,成就至圣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