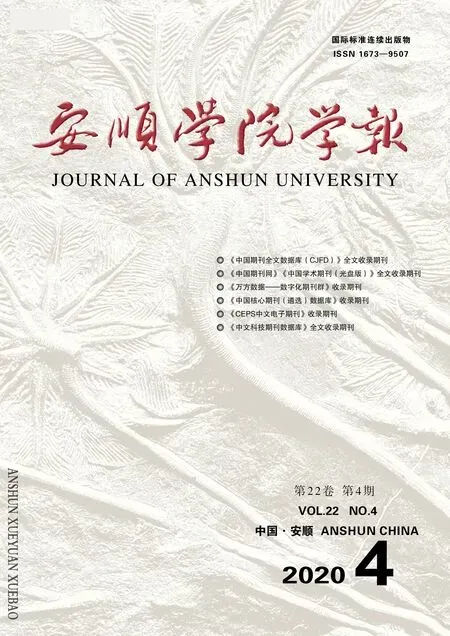城市超大居住社区的特点与治理分析
——以贵州省贵阳市H社区为例
谢景慧
(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贵阳学院法学院,贵州 贵阳550000)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大中城市陆续出现了一批超大型居住社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城中之城”。大型社区在缓解城市住房问题,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城市隐患与治理挑战。
一些学者对大型居住社区治理已经做了相关研究,吴晓琳从空间风险的角度对大型居住社区的问题与治理进行了分析,并对治理过程中社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机制进行阐述[1]。范志海等人以上海大型保障房社区为例,提出大型社区居民自治、社区共治、社会公治的复合治理模式[2]。金桥、徐佳丽则认为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具有一系列的标签与特征,如“保障社区”“居住社区”“速成社区”“弱势社区”“问题社区”“无根社区”“镇管社区”等,并从改善配套、产城融合、去标签化、加强社区治理和多元服务等方面促进社区健康发展[3]。彭善民认为城市大型新建社区具有城市孤岛、文化洼地、管理经验缺乏等问题,并从社区规划、社区服务、地区发展三个方面的转变来实现社区管理创新[4]。陈荣武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大型居住社区为研究对象,阐述大型社区基层治理的现状与成效基础上,提出大型居住社区治理存在功能布局不合理、建设质量与居住环境堪忧、基础设施与公共配套滞后等问题,并相应地提出了优化策略[5]。
由于上海率先在国内建设大规模的超大保障房社区,所以上海的大型居住社区研究比较集中,保障性社区的特点也比较突出,社区治理也形成了一些模式。本文以贵阳市花果园社区(以下简称“H社区”)为个案,运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的研究方法,提炼大型居住社区的特点与问题,并社会组织参与城市超大居住社区治理。
一、核心概念
(一)城市超大居住社区
城市超大居住社区到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有学者认为,超大型居住社区是一个量化概念,主要通过居住人口与用地规模两个指标来衡量,居住人口超过3万,面积大于2平方公里的社区为超大型社区[6];还有学者认为用地规模约为5平方公里,人口规模约10万人,居住、生活、就业等功能基本完善的城市社区是超大社区[7]。北京市从社区治理精细化的角度出发,在2020年初宣布年内要对80多个5000户以上的超大社区进行拆分,以实现更加科学、有效的社区治理与服务整合。本文同样重点关注超大社区的治理议题,追求人性化的社区治理图景,所以采用北京市的标准,将5000户以上的居住社区称为城市超大社区。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定义,贵阳H社区50万的居住人口规模、10平方公里的用地规模,在全国来看,是仅次于天通苑社区的全国第二大社区,而且建筑占地仅是天通苑社区的一半,这种密度形成了H社区的突出特征,同时也是该社区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H社区
H社区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属贵阳市主城区二环以内的中心位置,是2010年启动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辖区共22个居住区,规划入驻30余万人。H社区的拆迁规模庞大是其突出特点之一,涉及拆迁户2万多户,拆迁人口10多万人,拆迁面积400余万平方米。H社区的定位是集住宅、商业、艺术文化、商务办公、旅游、智能生活服务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总规划面积10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18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230万平方米、商业200万平方米,商务办公200万平方米、公寓及公建200万平方米。目前已入住人口14万余户,50万余人;入驻企业6800余家;入驻商家13400多家;日均人流量达到80万人次。H社区为贵阳市经济发展、城市改造等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突出问题。
二、H社区的特点
H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是典型的人口导入型社区,体现为人口规模庞大,需求异质多元,人群成分多样,老幼弱势群体集中,但服务功能迟钝滞后,管理力量与模式明显无力。如何有效强化对花果园这个大型居住社区的治理,是新形势下社区与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人口特征
人口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规模庞大与构成复杂。人口规模方面,“亚洲第一大盘”“中国第一大盘”“全国最大棚户改造区”等等这些称号都是来形容H社区的人口庞大。H社区规划入驻居民40万,就业人口15万,日均人流量100万,这些数字无论哪一个都不像是一个社区可以承载的。人口构成方面,H社区的人口来源多元化,有来贵阳发展的外来者,有贵州省下面州县上来的居民,有贵阳本土居民,有棚户区改造时的安置居民,有在当地就业的上班族,有奋力拼搏的年轻租户,还有在居民楼里租赁的商户……有自由时尚的两口之家,有上有老下有小三世同堂的主干家庭,有一家三口的核心家庭等等。
(二)社区楼栋“高度”与“密度”双高
H社区最典型的一个特点莫过于“高而密”,这点最直观,最具有视觉冲击力。H社区的“双子塔”坐成后将成为贵阳一个坐标性建筑,这个导向与社区的基调也非常一致。居住楼除了一期外,几乎都是43层,这个层数刷新了贵阳乃至全国居住楼的高度。同时,H社区户型采取极度密集的扇形设计,一个楼栋里三个单元,每个单元最少六户,小户型楼栋每栋多则十几户,甚至有的户型中总有房间是永远照不到阳光的。
(三)社区老幼群体集中
只要自己的儿女有孩子,当下老年人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年轻人上班老人要照顾孙代。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安全放心的角度还是从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角度,自己家的老人永远是照顾家中小孩子的最佳人选。这种现象在H社区同样存在,在调研中发现,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时间,走在社区平台上会看到满目的老人与孩子;还有一个现象,原本稍微平静的平台,待孩子们四点半放学后立即变成了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的场景。
(四)商居混合
无论在H社区的哪一个区哪一个楼栋,几乎都能看到各种类别的商户,特别是在海豚广场附近、购物中心附近、金融街、商务街附近的居住楼里,商户更多。另外,H社区中的居住区与商务区混合在一起,没有任何分割。
(五)社区庞大
H社区由22个区组成,包括一期区、A区、B区、C区、E区、F区、G区、H区、J区、K区、L区、M区、O区、Q区、R区、S区、T区、U区、V区、W区、X区,主要以高密度、低绿化为特征。
(六)社区“新而慢”
H社区属于新建社区,大多数在2013-2015年才实现逐渐交房,社区的很多硬件仍然处于追赶阶段,“软服务”基本以房开的物业服务为主,入驻居住社区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市场性组织,服务类社会组织、社区内生性组织都屈指可数。
三、H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 )治理理念滞后
从社区治理的内涵来讲,社区治理就是让居民、社区组织等与社区事务有关的各个主体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相互协作中承担治理责任,有效解决问题的同时形成社区治理模式。但是从现实来看,新建大型社区一旦有了生活图景,各种问题就随之出现,如流动人口问题,对于管理者来讲解决问题或者预防问题升级已是分身乏术。另外,对社会组织的了解不够全面而产生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现实中的行为选择。比如现在的H社区仅有的公共服务是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的基本行政服务,虽然也有少量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服务,但从每年的政府购买服务立项清单中就可以看出来,政府对社区基层的“六小联通”组织和小微组织的支持还是比较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组织是社区内生型组织,具有行政上的同源性、亲和性,但是这些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和专业性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同时也无法避免官民二重性的弊端。另外一个普遍的挑战是嵌入性社会组织切入社区的难度大。这些现象背后都反映了同一个问题:社区治理的理念问题。基层政府主导的大型居住社区的建设的明显的特征表现为“政府社会职能社区化,其行动特征是政府多而社会少”[8]。比如,基层政府对于社区建设中的各项制度措施和政策安排,往往借助于政府官员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对社区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公共政策,并通过政策安排来解决社区存在的实际问题。于是社区就出现一个悖论:“法律意义上的自治单元,在现实中却高度依赖政府。因此,这种政府行为往往忽略了社区发展中社区组织参与以及公民参与的深度,忽视社区组织和居民个体的主观能动性。”[9]要想实现“善治”“共治”等目标,无论在哪个层面,思想格局的打开永远是第一步,理念转变才能引入更多的治理力量。
(二)社区融合与社区认同淡薄
由于现代性为人类生活提供的便利性,人们在新环境的生活方式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相互尊重的“个人生活圈”,但是在价值层面的融合由于多元、自由等客观因素就困难很多,这些直接导致了居民之间相安无事的交际收缩。H社区是一个完全的陌生社区,在遵守公共基本道德的基础上,居民之间是一个冷漠、隔绝的理性状态。同时,随着社区人口的持续导入使得社区治理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就使得居民的社区交往融合的难度加大。另外,新建大型社区的居民离开原来的“熟人环境”,从四方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会产生本能的心理防御机制,在缺乏外力的情况下个体之间很难冲破各自的围墙,从而产生“虽一墙之隔但迎面不识”的常态,社区只是物理意义上各自分割的生活空间,完全没有了“共同体”的温度。
(三)社区公共服务供给薄弱
H社区是一个新建社区,居民来源复杂,老弱群体所占比例较大,社区基本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配套薄弱,在社区产生严重“服务挤压。第一,社区基本公共服务配比失衡,且缺乏动态应变机制。如服务50万居住人口的H社区服务中心只有37个编制,平均一个编制人员要服务一万多位居民,而且整个社区只规划了4个居委会,从配比数据就能感觉到公共服务中的拥挤排队。再比如医疗方面,50万居住人口的H社区规划了四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而且现在还未全部投入使用,虽然不久的将来会实现全部运营,但是仍然是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在调研中,一个业主表示,孩子打疫苗问题,第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早上九点以后几乎就拿不到当天的号了,他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孩子三岁每次打疫苗都到旁边的蔡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疫苗。比如教育方面,幼儿园入园都需要摇号排队,录取比例达到4:1、5:1。二是社区基层治理框架还未成形,社区公共利益无法得到维护。H社区规划的居委会还未成立,很多区无法成立基本的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很多公共利益无法表达无法得到有效维护,比如人车矛盾、社区改造问题、卫生问题等,居民经常是投诉无门不了了之,久而久之这些都会积累成日后的社区矛盾;有的区即便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也存在组织涣散、作用受限等问题。三是社区公益服务、志愿组织十分欠缺。目前H社区有的“小瓜子”志愿者组织、“花儿”志愿者组织、乐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南明区青年之家等社会组织,志愿服务具有偶然性,社会组织服务具有领域性,这些社会组织远远无法满足庞大的H社区的居民需求。特别是H社区有庞大的老幼群体,怀揣各种新型理念的社会组织的介入,能够某种程度上回应居民的需求、预防老幼群体常见问题的发生。
(四)业主与物业关系紧张
房地产产业爆发式发展的今天,舒心有效的物业服务是衡量一个楼盘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是,在H社区存在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业主与物业关系非常紧张。在媒体中经常看到H社区居民与物业的激烈矛盾与对抗,在调研中,某区一位业主骨干表示,在楼栋微信群中,物业会把极具批判性挑战性的业主踢出去,她就是其中之一,后来这位业主到物业服务中心亲自询问剔除原因,物业工作人员的回应也很消极应付,后来各种矛盾积累形成现在单元业主对物业的集体抵制与不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物业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是一方面,另外,社区人口众多,素质参差不齐,要求异质多元,物业疲于应付,就在这种关系中恶性循环下去,必然导致双方关系恶化。一般情况下,社区层面的很多问题是物业和业主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造成的,比如一个最基本的物业职责范围问题,很多业主不清楚物业服务范围,出现任何问题都向物业反应,不在其职责范围的自然无法解决,但是业主会误以为是物业的不作为与逃避责任,类似的情况在H社区非常多。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可以担任物业与业主之间的桥梁,也可以是物业的合作伙伴,在处理社区事务、缓解社区矛盾、营造良好社区关系中发挥润滑剂作用。
(五)社区公共空间严重挤压
H社区被调侃为“亚洲第一神盘”,“神”的方面有很多,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高度与密度,这两个“度”都会导致社区空间的高度挤压。一方面是高楼中的户型高度挤压,户与户之间的隐私性欠缺,调研中一位业主反映在自己家里可以听到隔壁家的说话声音。另外H社区还建了很多小户型高密度的楼栋,这无形中也会形成一种人口挤压;另一方面是高楼外的公共空间挤压,居民的公共活动空间小,公共空间的卫生问题等。物理建筑的高度挤压已成事实无法改变,但是社区公共空间是可以营造与拓展的。H社区规划建设了14个党群活动中心,这是社区营造的唯一一个居民可以文体活动、文化滋养的场所,包含了儿童绘画室、DIY室、沙盘室、舞蹈室、社区电影院、社区图书馆、棋牌室、乒乓球运动区等各个功能区。但是最近一部分党群活动中心被挪为他用或者闲置,之前的居民可以打乒乓球的运动区也被改造,这就更加削减了原本严重不足的社区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是营造社区组织的基础阵地,是社区文化培育展示的载体,是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成长基地,是居民共融共睦的归属阵营。H社区的公共空间不足问题在本就拥挤的社区环境中显得更加迫切与凸出。
(六)社区治安管理混乱
在调研中关于社区安全的方面,一位业主调侃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便进出任何一栋楼”。H社区是典型的开放式社区,楼栋多而密,社区面积庞大,不可避免会产生偷盗失窃问题,严重影响居民的安全感。一位业主在调研时说:“我曾经在业主微信群里看到同一天两个区同时抓到两个小偷的视频”。虽然偷盗问题在任何时期任何社区都可能会存在,但是H社区的安全管理形同虚设,无形中会增大社区的安全风险。另外,在调研时,很多业主反映,经常会有陌生人以各种理由按门铃,比如洗油烟机、清洗洗衣机等,但实则另有猫腻。还有业主反映,社区的平台上经常会有小摊小贩,严重影响小区环境和形象。这些问题都反映了H社区的治安管理状态,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楼栋的门禁系统没有运用起来,虽然门禁系统也有不可避免的问题,但是完善的门禁系统可以一定程度上阻挡闲杂人等的混入。
(七)社区公共卫生问题
公共卫生问题主要指社区平台、停车场、电梯间等公共区域的卫生问题,调研中许多业主反映社区公共区域存在脏乱差的问题,这些琐碎的细节直接影响居民的居住质量与社区认同。虽然物业提供了最基础的卫生清扫服务,社区的公共区域比如每个楼栋楼道、楼梯间及电梯间每天都会有专门工作人员清洁,社区平台卫生每天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但是由于社区公共区域人流量大,居民生活方式、素质理念异质多元,公共空间是动态的,但是工作人员的清扫是定时定点的,这样不可避免会造成社区公共区域的卫生问题,这些小的细节虽然细微,但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甚至是恶性循环。在这个问题上,整体居民的公共意识是解决的关键。
(八)社区弱势群体问题
调研中发现,H社区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存在着需要关注的弱势群体,如比较突出的老年人、儿童青少年、全职妈妈群体。如前所述,H社区住有大量的老幼聚集,老人隔代抚养会带来一定的教育问题,比如过分宠溺、强者为胜、不会分享、不会礼让等等,这些在教育领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议题,在调研过程中也有业主反映,部分全权由老人带大的孩子会有骄纵无礼的个性。另外就是老人这个群体,人进入老年本身就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正因如此也更容易弱势,照顾孩子又是一个琐碎辛苦的事情,这些老年人是不是也值得关注?我国自古以来,养老育小的责任都在家庭这个层面,但是当出现一些新情况或者具有一定普遍性的时候,就会成为社会问题。比如幼儿这个群体,现在是幼儿阶段对社会产生不了影响,但是待孩子长大入学入社会就会影响他们的与人相处与行为方式。同时,调研中发现,社区中全职妈妈的数量也很大,曾有调侃“全职妈妈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这其中的寓意主要是指全职妈妈的个人发展问题、与家人相处的技巧以及照顾孩子的技巧,这也是全职妈妈这个群体面临的三个最大的挑战。
四、社会组织介入大型居住社区治理的思考
伴随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以及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扶持,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并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鉴于大型居住社区的特点与问题,社会组织参与大型社区治理需要注意两个基本方面,一是精细化治理原则,二是“助人自助”原则。精细化治理是因为大型居住社区的“大”,人口规模大、社区范围大等等,需要分而治之的基础上进行深度、精细的治理。“助人自助”是由于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社会组织经过一定的阶段与基本服务过程,催化社区自治主体与自治机制。社会组织参与大型社区治理在前面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可以从治疗性服务、预防性服务、发展性服务、社区公共空间营造与社区微组织培育五大块内容开展服务。
治疗性服务主要基于问题取向,对社区内已经存在的问题性需求进行回应。根据需求主体的分析逻辑,可以分为关系性需求、公共性需求、群体性需求、特殊性需求等等。关系性需求主要指社区范围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如较为常见的物业公司与业主、商户与业主之间的矛盾与缓和。公共性需求则涉及社区范围内大多数业主的利益,如社区卫生问题、停车难问题等等。群体性需求主要针对社区内有共性特点的人群问题,如困境老人、偏差青少年、失业人员等等。特殊性需求则是针对社区内一些特殊个人或家庭而提供的服务,如高危个案辅导、特殊家庭帮扶等。
发展性服务则是针对功能状况良好的社区居民,基于发展视角而开展的延展服务。无论是基于何种视角的服务划分,其目的都是在解决问题或提升能力的过程中去实现居民与社区的更好发展。无论是社区工作强调的社区组织培育,还是居民参与社区的能力与意识提升,以及社区整体功能的激发与增进,都体现了社区服务中社会组织从解决问题到发展能力的取向递进,且在增进社区福祉的道路上没有尽头。或者从阶段取向来分析,解决现有问题与矛盾是治理的首要任务,但是并不意味着结束,在治理与发展的新趋势下,社会组织又要不断承担新的使命。
预防性服务在现实视域中是最容易被忽略掉的内容,它主要针对社区群体容易出现的一些可以预期的破坏性问题而提前开展一些预防性服务,以减少问题的产生。典型的如针对青少年的毒品教育、性教育以及针对老人的一些慢性病锻炼等等。很多领域的研究都已证明,预防一个问题远远要低于治疗一个问题的投入成本,且预防的现实样态远远要比问题爆发以后的破坏画面积极正向。所以,这种服务广泛被社会组织所重视,这种意识也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社区公共空间培育主要基于城市化背景下的空间正义思考。现代化与城市化把越来越多的人局囿在狭窄的私人空间,公共空间不断被经济理性所挤压,严重侵犯了市民的基本公共权力,同时也造成了无尽的城市风险。从这个角度讲,空间培育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与防范城市空间风险的弥补策略。社区范围内,公共空间不单单是一间屋子,一个场地,它还承载着居民的社区归属与情感,是社区空间布局的一种公共生产,也是居民物质空间与心理空间进行转换的第三域。
社区微组织培育主要是针对社区内的不同利益群体,基于共同态度与规则而将个体通过群体动力汇聚成一个团体的过程,它既是一个组织化过程,也是一个意识与共识达成过程,更是一个共同行动与相互支持的过程。从最现实的角度看,社区微组织是社区治理的内生载体,也是社区动力的基本细胞。社会组织通过社区微组织培育而实现社区自治与共治,从而持续实现社区治理的动力供给。
结 语
城市大型居住社区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何有效治理以及实现社区良性发展是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与访谈的方法,以贵阳市H社区为个案,对超大居住社区的特点与问题进行分析,并从社会组织的角度对大型社区的未来治理进行探索。第一,大型居住社区的治理工作需要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主体的有效协作,限于篇幅,本文只是从社会组织的主体角度对大型社区的治理策略进行了分析。第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社会与社区领域中可以承担相应的功能,大型居住社区的治理工作千头万绪,社会组织可以在其中发挥其独特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是改善基层社会秩序的一种新视角。第三,贵阳市近些年陆续出现了大量的超级大盘,如花果园、世纪城、未来方舟等社区,这些资本驱动下的超大居住社区不同于已有研究中北京的大型社区郊区化、上海的保障性大型居住社区,市场化的大型居住社区的现有研究不多,不同类型的大型居住社区的图景各异,更值得分别深入关注。但大型居住社区具有其共性,应该警惕德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大型保障社区治理的经验教训,避免“类贫民窟”式的非良性发展以及“超级大盘”带来的“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