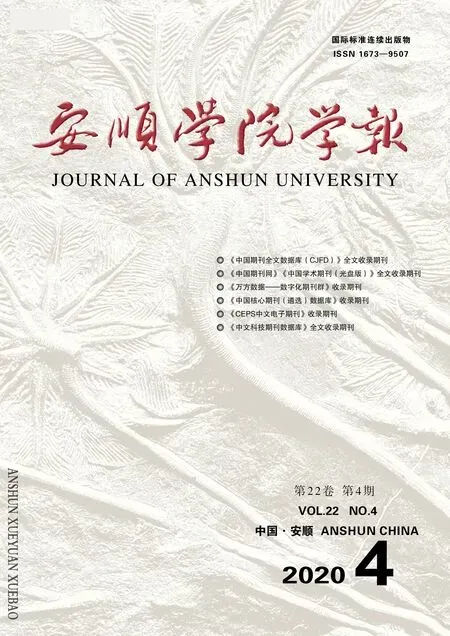焦竑研究综述
黄 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焦竑(1540—1620年),字弱候,号澹园,江宁人(今江苏南京),万历乙丑(1589年)状元。焦竑师承泰州学派耿定向、罗汝芳诸人,又问学于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容肇祖称其“泰州学派后劲”,对晚明学术产生重大影响。焦竑在晚明多以思想家、考据学家为人所熟知,然其于经学、文学及史学等方面俱有建树,《明史》称其:“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训雅,卓然名家。”[1]7392这样一位学者确实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近三十年来学界对焦竑生平著述、思想、文学、史学及文献考据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然其经学著述却少有人问津,尚有较大可以开拓的空间。
一、早期焦竑研究的回顾
余英时认为:“在心性之学方面,弱侯实可说是一结束人物。此与其在博学考订方面之为开创人物,适成为有趣之对照。”[2]315由于焦竑在晚明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早在明末清初及清中叶已有学者对焦竑其人其学作出评价。
焦竑作为在晚明时期影响巨大的思想家、学者,其身前身后的评价却分为两撅。明末清初学者多肯定焦竑作为思想家、学者的重要地位,如黄宗羲《明儒学案》云:“先生积书数万卷,览之略遍。金陵人士辐辏之地,先生主持坛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学倡率,王弇州所不如也。”[3]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亦言:“渊博演迤,为东南儒者之宗。”[4]而清中叶后,焦竑学术多遭贬低,其中以四库馆臣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虽对其著述有评述,但多持否定态度,如《国史经籍志》提要言:“负博物之名,莫之敢诘,往往贻误后生。其谲词炫世,又甚于杨慎之《丹铅录》矣。”[5]744《焦弱侯问答》提要则言:“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5]1077同时四库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时对焦竑著作多有禁毁,其集《澹园集》四十九卷、《澹园续集》二十七卷作为研究焦竑学术的重要文献,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被列入禁毁书目,导致清代罕有学者对焦竑作出进一步关注。由于四库馆臣对焦竑学术的贬低,加之其著作屡遭禁毁,清中叶后焦竑逐渐湮没无闻。
民国时期,容肇祖、嵇文甫等学者以思想史、文学史视角切入的研究,使焦竑重回学者研究视野。容肇祖最早整理出《焦竑年谱》,对焦竑生平、交游、师承情况作了简要梳理[6];容氏《明代思想史》则对焦竑思想进行考察,称焦竑为泰州王学后劲,认为其为学主张下学上达、由博返约,呈现出“得于内又尚实用”的特点[7]。嵇文甫《左派王学》从焦竑与袁宏道的师授情况考察其与性灵文学兴起的密切联系[8];嵇氏另一书《晚明思想史论》将焦竑作为晚明古学复兴的代表,对其文献考据学作出初步考察,对焦竑提出的“古诗无叶音”说高度赞扬[9]。两位学者对焦竑学术特点作了初步的总结,认为其学术具有会通儒佛、博学返约的特点,显示出浓厚的时代特征。
由上可知,学界对焦竑生平及学术的考察在明清与民国时期就已发其端绪,然而因立场和时代风潮的差异,此段时期的焦竑研究虽显得多元却流于表面,对焦竑其人其学都未能进入深层次的探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两个时期的研究为接下来对焦竑的再认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近三十年来焦竑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焦竑的研究开始深入,在生平著述、学术特质、思想、文学及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一)生平与著述研究
目前学界对焦竑生平行迹、著述情况及学术特质的考究较为详实。王琅《焦竑年谱》以容肇祖《焦竑年谱》为底本,对焦竑生平、交游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其中将焦竑学术渊源上溯到其父兄实乃新见[10];李剑雄《焦竑评传》从心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对其学术特质作出总结,后附“焦竑著述小考”首次对焦竑自作、编纂的著作进行了考证与辨伪[11];姚家全《焦竑的编纂活动考略》进一步对焦竑著述年代、版本作出详细考证,但仍略有遗漏[12]。目前学界对焦竑交游情况的考察集中在李贽与公安三袁上,邬国平《〈复焦弱侯〉异文与李贽、焦竑、耿定向关系》通过考察焦竑与李贽书信往来异文,探析“耿李之争”中焦竑与李贽的微妙关系[13];韩伟《杨慎对焦竑之影响考释》从由博返约的为学态度及实学取向两方面考察了杨慎对焦竑的间接影响[14],是对大多学者仅从师承与交游范围考察焦竑学术渊源的突破;卜键《焦竑的隐居、交游与其别号龙洞山农》从隐居、《焚书》相关记载及交游情况考证焦竑别号“龙洞山农”[15]。对于焦竑学术宗向与特征,陈鼓应等人所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中指出焦竑的“实学倾向”和李贽异端色彩[16];赵树廷《心学的绝唱,实学的序曲——焦竑学术递嬗的个案探析》认为焦竑学术“上承心学余绪,下启实学开端”,在明清学术风气转换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17];代玉民《论焦竑的身体与哲学——兼谈晚明哲学中的“认知”与“体验”》认为焦竑以知性为核心的求知取向与身体健康状况紧密相关[18],是研究焦竑学术的新视角;刘海滨《焦竑与晚明会通思潮》提出“王学会通派”概念,从交游和师承两方面梳理了焦竑会通之学的由来,进而将焦竑置于晚明思潮中去考察[19];余英时在《从宋明儒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一宋明儒学中智识主义的传统》一文中提出焦竑心性之学与博证考据学实各成系统,并无内在关联;[2]290-310黄熹《试论晚明儒学转向说的理论缺陷——以焦竑思想为中心》对余英时观点做出反驳,认为焦竑学术实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20]。
学界目前对焦竑生平著述及学术特质的研究较为深入,为接下来对焦竑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便利,但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如生平研究方面对焦竑交游情况尚未详细展开,仅集中在公安三袁和李贽上失于片面,焦竑交游情况亦尚有值得挖掘的空间。同时著述方面对焦竑作品的整理力度显然不够充分,目前尚未有焦竑全集点校本出现,更遑论书信编年等进一步研究。
(二)思想研究
焦竑作为晚明时期重要思想家,后世对其思想的研究主要以心学、佛道、三教会通思想为中心展开。钱新祖《焦竑与晚明新儒思想重构》以理气一元论考察焦竑考据学的由来,并由此将清代考据学溯源至陆王之学[21],此观点受到余英时剧烈反驳,在为此书撰写的书评《重访焦竑的思想世界》中批评钱氏脱离了明代历史语境来考察明代三教合一思潮,并未能真正的认识焦竑三教思想[22],其后梅广在《钱新祖教授与焦竑的再发现》一文中对钱新祖作出回护[23];龚鹏程《晚明思潮》辟专章“焦竑的儒释道三学”指出焦竑儒学思想对佛道之学心性层面的吸收[24];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对焦竑儒释道思想三者关系做了剖析,认为焦竑心学继承孟子以来心学传统,吸收王阳明、耿定向和罗汝芳心学思想而独成一家[25];白静《焦竑思想研究》对焦竑三教思想与文学思想进行分析,其中对焦竑四种《精解评林》的研究实为首创[26];黄熹《焦竑三教会通思想的理论依据》指出焦竑三教会通理论以“学以复性”为目的,以三教同归于性命之学为基础[27]。佛道家思想研究方面,王诚《从〈焦氏笔乘〉看焦竑佛学思想》认为焦竑援佛解儒,以佛教我空和法空阐述心性修养,从而主张顿悟之法[28];黄熹《〈庄子翼〉及其思想特色》指出《庄子翼》阐释体例及思想对《老子翼》的继承,并以《庄子翼》为切入点考察焦竑“儒道不二”观念[29];黄熹《从“明道”到“明性”——焦竑〈老子翼〉思想阐释》认为焦竑《老子翼》在深入思考道、有与无的辩证关系中,吸收道家之无而维护儒家之有[30]。
此类研究注重从时代背景出发,将焦竑心学、佛道及三教会通思想置于晚明学术转变中去考察,还原焦竑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但学者多集中在焦竑的佛道及三教会通思想研究上,焦竑作为泰州学派后劲,其理学思想理应得到重视。同时在既有三教会通思想研究成果上,考察焦竑理学与佛道的互相交涉亦是不错的研究视角。总而言之,焦竑的思想研究仍有待学者的进一步挖掘。
(三)文学研究
焦竑在晚明虽以理学家闻名,但在文论、小说、戏曲等方面亦取得不错成就,得于20世纪嵇文甫、郭绍虞等学者的开拓,学界对焦竑的文学研究已取得不错进展。周群《融通儒佛的焦竑文论》从融摄佛儒角度对焦竑文论进行考量,认为焦竑即重悟又尚实用,反对摹拟因袭[31];杨敏《焦竑文学思想简论》指出焦竑文论重实用,主张文道合一而反对理学家文以载道,对明性灵派有开创之功[32]。对焦竑的小说研究则集中在《焦氏类林》和《玉堂丛语》两部著作上,胡翠娈《焦竑〈焦氏类林〉研究》对《焦氏类林》选材、体例和小说特性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33];樊蓝燕《焦竑〈玉堂丛语〉的文学研究》对《玉堂丛语》产生背景、体例、内容、艺术手法,最后将其与《世说新语》对比,指出虽在艺术上不及后者,但亦是明后期“世说体”小说佳作[34];赵超《焦竑“世说体”小说研究》从作品体例、选材来源和叙事艺术三方面对焦竑小说作出评析[35]。对焦竑的戏曲研究则集中在焦竑选编、校订的《四太史杂剧》和《重校北西厢记》上,刘根勤《明代文学中的“太史”群体角色──以焦竑〈四太史杂剧〉为例》以焦竑推动编选和刊刻的《四太史杂剧》透视明代政坛的基本要素与运作规则,进而体察“晚明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与文学间的游离心态”[36];白静《崇北抑南:焦竑的戏曲思想研究》认为焦竑崇北曲而黜南曲,对晚明南曲崇尚辞藻的风气有所修正[37]。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可以看到焦竑心学、佛道、三教会通思想与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的交涉,焦竑文论主张文道并重,以尚实用、重性灵为指归,既是对前后七子复古摹拟文风的不满,又是公安性灵文学的滥觞,显示出浓厚的时代特色。但此类研究仅集中在小说、戏曲研究上,对焦竑诗文创作和选编作品有所忽略。
(四)史学研究
焦竑除在思想、文学等方面有重要地位外,在明代亦以史学家闻名。杨绪敏《论焦竑及其史学研究的成就与缺失》从史学观、史学编撰及考证等方面总结焦竑史学成就,认为焦竑治史详实,不依傍古人,在晚明空疏学风中独树一帜[38];展龙《论焦竑〈献征录〉的史料价值》认为焦竑《献征录》补明史之缺、纠《明史》文献之误、辑明史文献之散佚,是明史文献重要来源[39];李权弟、张金铣《〈国史经籍志〉论略》指出一方面四库馆臣受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影响而对此书多有贬低,一方面清朝官修史书又对此书多有借鉴,为重新考量焦竑史学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40];薛万新《〈玉堂丛语〉文献史料探源》分析《玉堂丛语》史料主要源自明代笔记、明人别集及明人著作中碑传、年谱和地方志,具有较高史料价值[41]。
由上可知,学界对焦竑的史学研究突破了四库馆臣的不公正评价,重新认识到焦竑史学的重要价值。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注意到焦竑“世说体”小说《玉堂丛语》的史料价值,并由此探寻焦竑史学与文学及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向互动,可谓对焦竑史学研究视角的延伸。
(五)考据学研究
焦竑作为明清实学转向的关键人物,其文献考据学在晚明独树一帜,涉及书籍辨伪、字词考据、古音考证等多个方面。李剑雄《焦竑评传》辟专章对焦竑考据学的思想基础、考据内容、特点及成就作出介绍[11]187-225;代玉民《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指出焦竑考据学与其智识化良知学紧密相关[42];亢学军《从〈焦氏笔乘〉看焦竑的文献考据学成就》认为焦竑博学考据是对晚明空疏学风的回应,并从小学、古籍辨伪、校勘与辑佚三个方面肯定其考据学价值[43];赵良宇《明代考据学的学术成就与缺失》提及焦竑考据学,认为其考据广博而精审[44];李晓英《〈俗书刊误〉研究》对焦竑小学著作《俗书刊误》的成书目的、正字俗字成就进行考察[45];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从经学考据、文字音义、史事、诗句考据四个方面对焦竑考据学作了全面的考察,最后指出焦竑考据学亦有引文失误、论证轻率等缺失[46]。
以上研究均肯定焦竑在考据学上的重要成就,亦认识到由于处在明清考据学的起步阶段,焦竑考据学具有粗疏之弊。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焦竑考据学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遗憾的是对焦竑心学与考据学内在联系的考察学界仍未有定论,焦竑考据学与清代考据学关系探源等议题仍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六)经学研究
焦竑作为晚明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除在文学、史学等方面的成就外,其经学亦有造诣,然从现有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焦竑的经学研究尤为不足,较学界对焦竑的思想、文学研究而言,焦竑的经学研究极为冷清。吴正岚《焦竑〈易筌〉对吴澄易学的沿革及其学术史意义》认为焦竑解《易》多引元吴澄说,重视象例和训诂的同时又显示出浓厚的汉《易》学倾向[47];郭素红《明代经学的发展》对焦竑的小学、古籍辨伪和考据学进行了分析,认为焦竑经学虽不成系统但在明清经学的汉宋转向中占据重要地位[48];丁国春《焦竑易学研究》认为焦竑《易》学打破汉“象数易”与魏晋“义理易”的对立,综而有之自成一家,同时训诂方法的引入为解《易》提供了新方法[49];谢成豪《焦竑考论《尚书》之几项议题探析》认为焦竑厘清了汉魏以来《尚书》之演变历程,并考辨了古文《尚书》之伪[50]。
此类研究注重恢复焦竑的经学家身份,同时又注意到其学术的独特性,将焦竑经学与考据学结合起来考察。然就目前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焦竑的经学研究多流于文本层面的梳理,而缺乏对焦竑经学与晚明心学、理学内部发展关系的探析,下文以焦竑《四书》学为例,对其经学研究作出开拓。
三、研究展望:以焦竑《四书》学为例
综上所述,学界多注意到焦竑作为思想家、文学家在晚明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而对其经学成就少有关注。焦竑自述“余髫年读书,伯兄授以程课,即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51]538徐光启亦称:“吾师澹园先生,以道德经术表标海内,巨儒宿学,北面人宗。”[51]532由此可知焦竑于经学实用力颇深,其经学著述有《易筌》《焦氏笔乘》《焦氏四书讲录》,其中焦竑《四书》学相关论著尤值得注意。
《焦氏四书讲录》十四卷,焦竑撰,是书讲解《四书》不录经文,多主于论说阐明大义,《续修四库总目提要》称其:“大旨近于王阳明之学,以心学为宗,故其讲说以求诸己心为标准,又主知行合一之说,时亦杂入释道。”[52]是焦竑以心学讲解《四书》的代表之作。焦竑其他《四书》学相关论述还有散见于《焦氏笔乘》中早年读书笔记九十八条,及《澹园集》中晚年讲学记录《明德堂答问》《古城答问》《崇正堂答问》三卷。焦竑作为明代著名学者,远绍阳明,近承泰州,又身兼文学家、经学家与考据学家多重身份,通过焦竑《四书》学的研究,可以窥见焦竑经学与晚明学术发展及时代思潮的多重互动,兹举两例:其一,经学与心学的互动。明正德三年(1508年)王阳明龙场悟道后,阳明心学以其简易工夫逐渐兴盛,受此影响晚明时期出现以心学诠释《四书》的“新《四书》学”[53],焦竑即其代表之一。在对《四书》的阐释中,焦竑直言对阳明良知学的赞赏:“孔孟之学至宋儒而晦,盖自伊川、元晦误解格物致知,致使学者尽其精力旁搜物理,而于一片身心反置之不讲。阳明先生始倡良知二字,示学者反求诸身,可谓大有功矣。”[54]焦竑对宋儒后学穷究学识而缺少向内的心性工夫表示不满,认为阳明以良知之学统筹知行才是真正的孔孟之承。在对阳明心学表示赞赏的同时,焦竑亦对阳明后学流弊进行了客观的审视,如《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章云:“阳明子自谓万死一生中得此二字,亦苦心矣。奈何近日学者专以知鲜为良知,而无万死一生之功,辄高谈性命玄之又玄,而试以经纶之事,则皆不识作何状者,竞笑宋儒以闻见为致知,而不知其所谓良知者亦闻见也,以穷物为支离,而不知其所谓忘物者支离尤甚也。求其实致徳性之知,而为知之上者,几何人哉。”[54]107阳明从向内的心性体验出发,克服了程朱理学的繁琐与僵化开辟了新儒学,然晚明时期王学末流空谈心性,时人标举阳明简易修养工夫而忽视践行之功。焦竑针对此批驳时人既无阳明深切的个人体验,又束书不观,只知体验而忽于实践,最终实未得阳明德性之知。通过其《四书》学,可以窥见焦竑于晚明变局中反思心学流弊以纠正学风的努力尝试,亦可探析晚明士人精神风貌的时代展示。其二,经学与文学的共振。受晚明评点风气和八股时文影响,焦竑在阐释《四书》时亦旁及对语言文法、篇章结构的总结与评点,以《中庸》“唯天下至诚”章为例:“尽人性者,抑其过而引其不及,矫其偏而归之于全;尽物性者,因其材质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节以遂其生。赞天地之化育接着‘尽物’句是文法,如此其实通承人物之尽来。”[54]45从“至诚”到“化育天地”实以人物之性串联,展示出文章背后紧密的句法铺排。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1]1694自此《四书》成为明代取士的主要内容,而“八股取士”的形式标准让《四书》与八股文不断靠拢。八股文讲究起承转合,承题、破题之间需要对《四书》字词句意的精确理解,受此影响明代《四书》阐释著作多注重章句文法的爬梳。焦竑对《四书》的文学性观照正是晚明时期传统经学与科举时文之间碰撞与吸收的结果。
目前,学界对焦竑的研究多囿于学术思想、文学、史学等方面,对其经学研究较为忽视,《四书》学作为焦竑经学成就的重要代表,理应得到重视。韩焕忠《佛教四书学》注意到焦竑《四书》学阐释中的佛学倾向,将焦竑列入晚明居士群体中考察其佛教《四书》学阐释的意义[55];康宇《论晚明“四书”诠释中的佛学路向——以焦竑、袁宗道、智旭为中心》认为焦竑虽以佛学解《四书》,但始终坚持儒学本位[56];吴伯曜《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以焦竑为证说明阳明心学影响下,晚明出现的心学立场《四书》阐释之作及三教合一《四书》阐释倾向[57];谢成豪《焦竑经学史学之研究》对焦竑《四书》观点学相关论述作了逻辑梳理,但涉及宋明理学思想部分均略过不谈[58];李春强《明代〈论语〉阐释研究》认为焦竑自觉使用心学构建《论语》阐释,对阳明心学有发扬之功[59];刘娟《明代论语阐释研究》对焦竑《论语》阐释的仁、礼、孝、君子小人等重要思想进行分析[60]。以上学术成果虽都涉及焦竑《四书》学,但仅停留在对既有描述作总结和提炼的层面上,对其《四书》学思想史意义亦未有深入考察。
总而言之,经学作为焦竑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四书》学为切入点,通过其经学阐释观念与方法的申发,可以窥探焦竑经学、心学与文学的多重互动,进而构建更为全面的焦竑学术图像。同时就晚明学风与思潮而言,《四书》作为明代儒学的中心,透过焦竑《四书》学亦可以具体而微地了解明代思想的阐释方法及价值取向,可以多维解析明代文化背景和精神构建,进而对明代学术的深层形态探究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