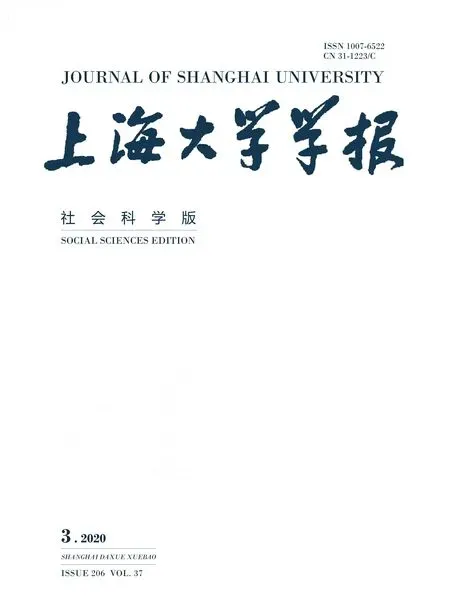我国剥削性滥用行为违法性判定基准审视
——以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为视角
陈 兵,赵 青
(南开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50)
一、由“二选一”引发的对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行为的思考
2019年是我国全功能介入国际互联网的第25个年头。特别是近十年来,互联网技术、互联网模式及基础设施的迅猛发展,带动了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算法等信息通讯技术和数字计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适用,深刻改变了我国经济社会生产组织形态和日常生活消费方式。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平台经济(体)的出现和快速增长在为各类用户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其中超级平台的“二选一”即为一例。近期,有关“京东与淘宝二选一”管辖之诉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社会各界从竞争法治维度讨论“京东与淘宝二选一”争诉之际,却较少有人从这两大互联网平台均涉及的一般用户利益和商家用户利益的实际或可能遭受损害的维度,直面平台对其用户可能或已经实施的剥削性滥用行为,而这类行为在现行竞争法治框架下并不以改变、扭曲甚至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结构为前提和效果。譬如,平台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可能侵害用户自由选择权益和公平交易权益。①有关反垄断法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对消费者或交易相对人自由选择权益和(或)公平交易权益的讨论,可参见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载《法学》2011年第1期;陈兵:《反垄断法实施与消费者保护协同发展》,载《法学》2013年第9期。又譬如,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即有可能被认定为滥用市场力侵害用户的合理知情、公平平等交易等权益。2018年,携程“酒店同房不同价”的定价行为被曝光,利用老顾客的信赖对不同客户群进行区别定价,这种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损害了交易的公平合理性,[1]同时也引发了对客户的不平等对待问题。进一步而言,在互联网时代滥用市场力的行为,不仅可表现在传统的价格歧视行为上,还存在其他交易条件基于大数据算法设计上的不公平的问题。[2]由此,引发了对平台可能滥用市场力对其用户施行除价格外的其他剥削滥用行为的关注和回应之必要。
时下,普遍关注以是否损害竞争利益与竞争秩序为前提和效果来判定经济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类型,其中排他性滥用行为成为竞争主管机构与司法机关着重受理和防治的主要违法类型之一。然而,对剥削性滥用行为及其规范却一直未有足够重视,以至于剥削性滥用行为条款一度处于休眠状态。②有关剥削性滥用条款的适用,在2016年湖北省物价局处罚本省五家天然气公司价格垄断案之前很少被提及,之后几乎没有得到适用。在该案中,湖北物价局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销售商品为由做出处罚,虽然在处罚决定中执法机构提及了“这些公司滥用该市场支配地位,即在非居民管道燃气设施建设安装经营成本、市场价格并没有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不允许交易对象自行选择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以及自行购买建设安装材料,并以不公平的高价且大幅高于公司经营成本的价格,收取非居民管道燃气设施建设安装费用”(《企业价格垄断 湖北省物价局处罚5家天然气公司》,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7-12/doc-ifxtwchx856470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年11月24日)。然而对于何为“显著变化”和“大幅度高于公司经营成本”,却没有提供具体论述。这就引起了部分学者的隐忧,即便是在该案中没有问题,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判断指标,执法机构对“不公平高价”的判断很可能出现任意性的危险,甚至成为执法机构过度或滥用执法的借口。故此,主张谨慎援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不公平高价或低价行为条款,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对剥削性滥用条款的闭锁。然而,伴随互联网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体)的奇点勃兴与高速增长,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动态性和多边性愈发明显,致使对其市场结构的影响,在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下并不足以引起竞争主管机构及司法机关的充分关注和有效判定,或者说即便是相关有权主体和利益主体欲就互联网竞争市场结构问题展开行动,然而由于缺乏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下市场竞争秩序是否受到扭曲或破坏的直接证据和实际效果而不得不放弃。但是基于可能存在的限制、排除竞争行为给用户利益带来的损害确实是存在的。这种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就为激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项下的剥削性滥用条款提供了可能和必要。
竞争法学界在区分和界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时,通常将其区分为排他性滥用(Exclusionary Abuse)和剥削性滥用(Exploitative Abuse)。①有关反垄断法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分类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讨论和实证案例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陈兵:《我国〈反垄断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适用问题辨识》,《法学》2011年第1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法类型在欧盟法上的分类,除了上述两类外,意大利卡梅里诺大学欧盟法教授佩斯(Lorenzo Federico Pace)还提出了第三种分类,即“歧视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类型。详见Lorenzo Federico Pace,European Antitrust Law:Prohibitions,Merger Control and Procedures,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7,pp.152-153。但是,欧盟委员会认为这种分类并不很重要,各类违法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有时甚至可以联合使用。详见 D.G.Goyder,EC Competition Law 4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283。所谓排他性滥用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从市场中封锁、排除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者来维持、强化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剥削性滥用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通过设定在有效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维持的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来侵害交易相对方利益的行为。[3][4]区分排他性滥用与剥削性滥用的意义主要在于两类行为具有不同的违法性判断基准。认定排他性滥用的时候,考虑的重点在于行为人和与之有竞争关系的竞争者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一种横向的平行竞争关系;而认定剥削性滥用的时候,考虑的重点在于行为人和与之有依赖关系的交易相对方之间的关系,通常可限定为一种纵向的供给或需求关系,即行为人的得利以及交易相对方利益的损失。[5]
在各国反垄断法实施中,垄断性价格的设定可以说是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在《欧盟运行条约》第一○二条(a)②《欧盟运行条约(TFEU)》第一○二条:禁止在内部市场或在其主要部分具有支配地位的一个或多个企业的任何滥用行为,只要它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就与内部市场不相容。这种滥用尤其可能包括:a)直接或间接施加不公平的购买/出售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条件。和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十九条③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如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作为某一类型商品或商业服务的供应商或采购商,要求的交易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不同于存在有效竞争时很可能出现的交易条件,则可能构成滥用,此时,应特别考虑存在有效竞争的可比市场中经营者的行为。当中都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设定不公平的或者说在有效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维持的交易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的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然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则在2004年“弗莱森诉多林克(Verizon v.Trinko)”案中指出:“仅仅因为拥有垄断势力并由此索取了垄断价格不能被视为违法,因为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机制。可以索取垄断价格,或至少可以在一个短时期内索取垄断价格,这对企业来说首先是一个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它还可以降低企业在创新和研发中的风险。为了保护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拥有市场势力不能被视为违法,除非它同时实施了反竞争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垄断性高价不是反竞争的行为,而是有利于竞争的行为,因为,垄断性价格和垄断性利润可以吸引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6]但同时,需要注意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中也指出了“在一个短时期内索取垄断价格”的限制性条件。换言之,如果经营者保持一种长时间的垄断定价,势必会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利益,这一点与联邦最高法院在1985年“阿斯彭滑雪公司诉阿斯彭高地滑雪公司(Aspen Skiing Company v.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oration)”①Aspen Skiing Company v.Aspen Highlands Skiing Corporation,472 U.S.585,603.案中认为“竞争是一个以消费者利益为基石且被其引导的过程,强调在自由竞争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似乎不相符合。
相较美国的做法,无论是早期的欧共体(EC),还是后来发展的欧盟(EU),对待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剥削性滥用行为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且严厉。譬如,在1973年大陆罐案(Continental Can)②Europemballage Corporation and Continental Can Company Inc.v.Commission Case 6/72[1973]E.C.R.215.中,欧洲法院就认为,第八十二条可以适用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直接或间接地向其消费者施以不公平收费的行为。法院进一步述明,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者向其消费者所提供的产品价值与其定价之间没有合理关联时,该定价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过高定价;如果消费者因为该经营者之定价蒙受损失,即使是该定价行为或政策并不对相关市场竞争产生影响,该经营者亦会被认定违反第82条规定,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7]后来2000年公告的足球世界杯案③1998 Football World Cup O.J.L.5/55,2000.(Football World Cup)在肯定“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因不公平定价致使消费者利益受损的,该定价行为应认定为‘滥用’市场优势行为,即使该行为没有对相关市场上的竞争结构产生危害”的判例法做法时,还进一步主张“没有必要开示涉嫌违法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经营者从其滥用行为中获得商业利益”的证据。[8]我国现行《反垄断法》虽然在立法过程中参考借鉴了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吸收了各自先进的理论与经验,但是从基础理论和立法例上主要参照了欧盟模式,故,在法律文本中也规定了剥削性滥用行为条款,这就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了正当性和必要性基础。
事实上,在存在严重的市场进入壁垒,垄断性市场结构已经长期固化的市场上,在不能期待市场的自我矫正机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竞争监管机构介入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定价行为就具备了正当性。在没有事前价格规制或者事前的价格规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的情形下,则有必要将竞争监管机构对剥削性价格的规制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规制手段来加以适用。[9]而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可以通过取得垄断利润而强化其市场支配力,那么对剥削性价格的规制虽然是直接保护交易相对方的利益,但是最终可以达到抑制市场支配力的效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对剥削性价格的规制也并非与竞争毫不相关。[10]进一步而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排除竞争者的行为也是以谋求垄断利润为终极目的,故此,将剥削性滥用完全排斥于滥用的概念之外也是不妥的。[11]然而,要认定价格是否过高,价格是否具有不当性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应当仅限于过高的价格设定具有显著的不当性的时候才对其进行规制。①有关显著不当性的讨论,在我国《反垄断法》上并没有详细展开。考虑到我国《反垄断法》与韩国《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在立法例的设定上具有相似性,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德国模式,以及韩国作为典型的财团经济体国家,在处理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或者说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剥削性行为方面具有较多的经验,建议考虑借鉴韩国公平交易法上关于显著不当性的理论阐述、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参见[韩]李奉仪:《韩国禁止垄断法上对剥削性滥用的规制》,陈兵、赵青译,载《经济法论丛》2017年第1期。
我国现行《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明确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同时,我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1号,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中也强调了在认定“不公平的高价”或者“不公平的低价”时应当将“明显性”作为考虑要件,即在认定“不公平的高价”或者“不公平的低价”时,可以考虑:“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其他经营者在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下销售或者购买同种商品或者可比较商品的价格”;“销售价格或者购买价格是否明显高于或者明显低于同一经营者在其他相同或者相似市场条件区域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是否超过正常幅度提高销售价格或者降低购买价格”;“销售商品的提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或者购买商品的降价幅度是否明显高于交易相对人成本降低幅度”;等等。
此外,剥削性滥用行为不仅可以表现为垄断价格,包括不公平的高价和不公平的低价的设定,也可以表现为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条件的设定。譬如,搭售行为、差别待遇行为既可能构成排他性滥用也可能构成剥削性滥用,抑或同时具备两种行为的性质。[12][13]对于以价格以外的其他交易条件的设定来剥削交易相对方的行为,应当以何种标准来确认其违法性?如果以价格以外的其他方法侵害交易相对方的利益也可以构成剥削性滥用的话,是否意味着交易相对方的自由选择权和平等交易权等非经济性的利益也可以得到《反垄断法》的直接保护?对此我国法律上虽然没有进行明示,但是,经由《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即对“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禁止性规定是可以为规制以非价格方式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提供法律依据的,这一点已有相关论述。[14]同时,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也已经出现了对以非价格手段剥削交易相对人,主要是终端消费者或者终端用户(end-user)利益的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判断的案件。基于此,本文以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判断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判决要旨,总结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对比借鉴具有相似立法例和具有较为丰富的处理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剥削交易对象行为的韩国经验,为改进我国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行为的违法性判断基准提供参考,以期能够为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场景下,不断出现的可能涉及经营者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挤压甚至剥削与之有依赖关系的交易相对人接受其非价格型不当交易条件的违法行为的防治提供可行方案。
二、我国司法实践中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行为案件判决要旨梳理
在我国有关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例当中,明确论及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判例当数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上诉案(以下简称“腾讯360案”)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三终字第4号民事判决。和吴小秦诉陕西广电网络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再审案(以下简称“陕西广电案”)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再98号民事判决。最具代表性。“腾讯360案”和“陕西广电案”分列“2008—2018年中国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十大案件”③参见“2008—2018年中国法院反垄断民事诉讼10大案件案情简介”,中国法院网: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11/id/357764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9 年11 月11 日。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也足以说明其典型性与指导性意义。
在“腾讯360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即使被诉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判断其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需要综合评估该行为对消费者和竞争造成的消极效果和可能具有的积极效果,进而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与否作出判断。”进而,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对腾讯的“产品不兼容”行为和“打包安装”行为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作出了分析。对于“产品不兼容”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即时通信市场和安全软件市场均有充分的替代选择,腾讯QQ软件并非必需品,因此,腾讯限定自己的腾讯QQ软件的使用环境的行为可能给消费者使用腾讯QQ或者360安全软件造成不便。然而,这种不便对消费者利益并无重大影响。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进一步阐释“重大影响”的判断基准。对于“打包安装”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考虑到,腾讯虽然在QQ即时通信软件与QQ软件管理打包安装时并未向用户提示将同时安装QQ软件管理,但其提供了卸载QQ软件管理的功能,消费者可以方便地自主选择卸载。另外,在将QQ软件管理和QQ医生升级为QQ电脑管家时,被上诉人通过公告的方式向用户告知了选择权,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被诉搭售行为的强制性并不明显。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在被诉搭售行为的强制性明显的情况下,是否可认定被诉行为的违法性。
在“陕西广电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陕西广电网络将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数字电视付费节目费一起收取的行为并非仅针对个别消费者,而是其普遍做法。此行为客观上影响消费者选择其他服务提供者提供相关数字付费节目,同时也不利于其他服务提供者进入此电视服务市场,对市场竞争具有不利的影响,从而构成违反《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行为。从表面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虽然谈及了限制竞争效果,但是,陕西广电网络是陕西境内唯一合法经营有线电视传输业务的经营者和陕西省内唯一电视节目集中播控者。结合本案相关市场的特征、数字电视收视服务的特殊性、行为的内容等实际情况来看,被诉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排除竞争者来巩固垄断地位,而在于垄断利润的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认定行为违法性的时候也并没有具体分析在相关市场中是否存在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行为前后竞争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等,而是将违法性判断的重心放在了消费者选择权的存在与否以及选择权受限的消费者范围方面。
综上,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判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违法性时,是将侵害消费者利益作为独立的违法性判断基准的;而且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行为并不仅局限于垄断价格的设定,价格以外的交易条件的设定亦可构成剥削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都会被认定具有违法性,因为问题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消费者利益损失需要达到有“重大影响”的程度。至于如何判断行为对消费者利益有“重大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案例中分别考虑了替代产品的存在与否、行为的强制性程度以及受影响消费者的范围,但仅凭这些零散的考虑要素尚不足以归纳出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并且上述两个案例,一个是发生在互联网领域,是有关免费服务的供给条件发生的纠纷,而另一个则发生在公用事业领域,是就有线电视的收费行为所发生的纠纷,在市场构造、交易的商品或服务的属性方面,两个案件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就更不可能仅从这两个案例的分析对比来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而韩国的《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简称《公平交易法》),则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明文规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当中的一种。在司法实务中,韩国大法院也对判断消费者利益受侵害的“显著性”和行为的“不当性”阐释了一般性的判定基准。因此,韩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经验可以为我国剥削性滥用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完善起到借鉴作用。
三、韩国法上对非价格型剥削性滥用行为的规范与适用
韩国竞争法学界通常将《公平交易法》第三条之二第一款①韩国《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第三条之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第一款: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从事下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1)不当地设定、维持或者变更商品或服务价格的行为;(2)不当地调整商品销售量或者服务供应量的行为;(3)不当地妨碍其他经营者的经营活动的行为;(4)不当地妨碍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行为;(5)为了不当地排除竞争者而进行交易的行为,或者有可能不当地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中的第一项“不当设定价格的行为”、第二项“不当调整供应量的行为”以及第五项后段“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归类为剥削性滥用行为。[15][16][17][18][19][20]公平交易法在不当设定价格的行为和不当调整供应量的行为之外另行规定了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那么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利益”则应当理解为除价格和供应量以外的其他利益。[21]264这也就意味着,除了剥削性定价以外,对消费者选择权等非经济性利益的侵害也可以适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条款。[22][23]但是,过于扩大剥削性滥用的规制范围可能会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带来消费者保护法的性质;而且排他性滥用行为具有严格的成立要件,过于扩大剥削性滥用的适用范围的话,也可能打破排他性滥用行为和剥削性滥用行为成立要件的平衡性。[24]因此,仅在问题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效果特别明显的情况下,才可以对其适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款。[21]265
在司法实务中,韩国大法院明确阐释,要构成公平交易法第三条之二第一款第五项后段的“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第二,消费者利益侵害程度具有显著性;第三,行为具有不当性。判断“显著性”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来具体分析。①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2.11宣告2008Du16407判决书。而在判断“不当性”方面,因为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直接保护作为行为对象的个别消费者的利益,而是在垄断性市场上促进竞争的同时,通过规制市场支配经营者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的行为,来保护在竞争市场的状态下消费者所能享有的利益。所以,要判断“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中“不当性”存在与否,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商品的性质、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的构造和特征等。但是,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因该行为导致消费者利益显著受到损害的话,通常可以认定行为的不当性。②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5.27宣告2009Du1983判决书。这也就意味着,通过证明剥削性滥用行为效果的“显著性”,可以事实上推定“不当性”的存在。[25][26]
简言之,韩国大法院在认定以垄断价格之外的方法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时,还是以抑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过度获取垄断利润为导向的,即: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了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只是构成了剥削性滥用的行为要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分析,行为是否出于过度谋求垄断利润的目的,客观上也可能造成消费者利益被侵害的显著效果,从而判断行为的违法性。这种分析方式可以说是与规制剥削性滥用的立法目的相符的,因为反垄断法的本质还是保护竞争法,而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是所有交易条件的不公平性问题都可以拿到反垄断法的层面上来解决。然而,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以过度谋求垄断利润为目的,从事了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从而可能获得过度的垄断利润,最终巩固其市场支配地位的时候,则有必要适用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条款对其进行规制。从目前的韩国大法院判例来看,在有线电视公司变更电视频道服务包案、广播电视公司终止团购收视服务案和SK移动通信设置非兼容性的数字权利管理保护装置(DRM)案中,涉及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判断。
在变更电视频道服务包的案件当中,涉案的有线电视公司将原来属于普及型服务包的几个收视率较高的电视频道调换到高级型服务包,又将几个收视率较低或者新晋的频道加入到了普及型服务包。公平交易委员会认为该行为构成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是行政诉讼中的一审首尔高等法院和终审韩国大法院都认为该行为不具备“显著性”的要件,因此撤销了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罚决定。具体来说,首尔高等法院认为,从消费者的立场来看,有线电视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就在于能够以高清的画质收看几个传统的主流电视频道,而本案服务包变更行为并未触及主流电视频道。包括主流电视频道和电视购物频道的话,因本案行为导致的普及型服务包收视率的减少幅度仅为4.9%~9.97%。而且,本案行为之后,普及型服务包内仍然包含很多收视率较高的频道。另外,得益于电视频道服务包的变更,新晋的频道可以进入普及型服务包当中,这有利于促进对电视节目的投资,促进电视频道经营者之间的竞争。新加入普及型服务包的频道有些是全新的频道,有些是还未有机会充分接触电视观众的频道,待电视观众熟悉新的频道以后,收视率是可能上升的。虽然本案行为发生之后,由普及型服务包转换为高级型服务包的消费者的数字有些许的上升,但与全体收视者数作比较的话,上升率仅为0.07%~0.69%。此外,行为人的有线电视服务合同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间隔6个月以上,可以对电视频道服务包进行编辑,消费者对6个月以后服务包的变动也是有合理预期的。综上,本案行为对消费者利益的侵害并不具有显著性。①参见首尔高等法院2008.8.20宣告2007Nu23547判决书。韩国大法院则认为,首尔高等法院没有将本案电视频道服务包变更后的交易条件与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进行比较就作出了否定侵害程度的“显著性”的判断有不当之处,但是,鉴于没有相关的证据资料,故一审判决的结论是正确的。②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2.11宣告2008Du16407判决书。
在广播电视公司终止团购收视服务的案件当中,涉案广播电视公司对于自己提供的收视服务中,收费处于最低档的团购收视服务采取了逐步废止的措施,即:该档服务不再接受新的收视申请,对已经到期的合同不再续约。因该档价位服务的终止导致原本享受团购价收视服务的消费者中一半停止了收费电视节目的收视,另一半原本享受团购价的消费者则只能转换为个体单价继续收视,在享受相同服务内容的情况下,个体单价要比团购价高出2到9倍之多。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该行为属于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在行政诉讼中一审首尔高等法院也支持了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处罚决定。③参见首尔高等法院2008.12.18宣告2007Nu29842判决书。但是,大法院则指出,因涉案行为导致部分消费者收视费上升或者放弃观看收费电视节目,这仅仅反映行为前后消费者利益的变化程度,并不是与相似市场上的交易条件作出的比较,因此,不能成为证明消费者利益侵害显著性的判断指标。结果,大法院作出了撤销一审判决,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判决。④参见韩国大法院2010.5.27宣告2009Du1983判决书。
在SK移动通信公司设置非兼容性DRM的案件中,SK移动通信公司对自己的MP3手机和自己运营的音乐网站上提供的音频文件设置了自己开发的DRM。该行为造成使用SK移动通信公司的MP3手机的消费者只能收听从SK移动通信音乐网站上下载的音频文件,消费者若想在SK的MP3手机上播放从其他网站购买的音频文件,则需要加入SK音乐网站的会员再对音频文件进行格式转换。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SK移动通信公司的行为构成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但是,在行政诉讼当中,首尔高等法院认为,消费者已经从其他音乐网站购买了音频文件的话,该音频文件不能在SK的MP3手机上运行,或者运行程序非常复杂,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部分消费者重复购买相同的音频文件,发生重复费用。但是,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这种侵害并达不到“显著”的程度;另外,音频文件格式的转换仅仅给消费者造成了不便而已,尚不足以构成显著的侵害。①参见首尔高等法院2007.12.27宣告2007Nu8623判决书。大法院也肯定了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结论。②参见韩国大法院2011.10.13宣告2008Du1832判决书。
综上所述,韩国的公平交易法在垄断价格的设定行为和不当的产量调整行为之外,另行明确规定了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这也就意味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选择权等非经济利益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但是,规制剥削性滥用行为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直接保护作为行为对象的个别消费者的利益,而是要通过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的行为,来保护在竞争市场的状态下消费者所能享有的利益。因此,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的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并不当然违法,要判断行为的违法性,还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判断消费者利益的侵害程度是否具有“显著性”,以及行为是否具有“不当性”。而且,在“显著性”存在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认定行为具有不当性。对“显著性”与“不当性”进行判断,需要综合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时间,市场的构造和特征,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化程度以及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的差异等要素。就具体判例来看,韩国大法院在认定以非价格手段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时,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并且在判断“显著性”时,非常注重与相似市场上的交易条件的比较,这也是符合剥削性滥用的基本概念的。因为剥削性滥用行为本来就是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通过设定在有效竞争的条件下不可能维持的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来侵害交易相对方的正当利益的行为。
四、完善我国剥削性滥用行为违法性判断基准的思考
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可以通过设定不公平的交易价格来剥削消费者的利益,也可以通过设定价格以外的其他交易条件来剥削消费者的利益。不管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所采取的具体行为方式如何,如果其行为的目的在于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客观上其行为也可能给消费者利益造成重大影响,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反垄断法来扼制这种谋取过度的垄断利润的行为。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也可以为规制以非价格的其他交易条件设定来剥削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也已经出现了对以非价格的其他交易条件设定来剥削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违法性分析的案例。这说明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侵害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等非经济性利益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是,遗憾之处在于,在我国的司法实务当中尚未形成对此类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一般性基准。
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既决案件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时是考虑消费者利益的受损程度的。也就是说,在行为要件之外还存在另外的违法性要件。问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就消费者利益受损程度的判断基准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而在韩国,对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的违法性判断基准,也是韩国大法院在裁判过程中逐步完善与确立的,而且韩国大法院对该类行为违法性考虑的重心也在于消费者损失的“显著性”,这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思路是相吻合的。鉴于此,在我国的司法实务过程中,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过程中,可以考虑超越个案,阐释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的个案分析,以提高司法的可预见性。
作为对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违法性的一般性的判断基准,可以参考韩国大法院所阐释的法理。即,“不当的显著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要具备三个要件:第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第二,消费者利益侵害程度具有显著性;第三,行为具有不当性。判断“显著性”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来具体分析。而在判断“不当性”存在与否的时候,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谋求过度的垄断利润、商品的性质、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的构造和特征等来进行判断。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了可能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因该行为导致消费者利益显著受到损害的话,通常可以认定行为的不当性。
五、结语
当前,在我国竞争法适用过程中普遍关注以是否排除、限制竞争来判定市场竞争行为是否构成反垄断法上的违法类型,其中排他性滥用行为成为了竞争主管机构与司法机关着重受理和防治的主要违法类型之一,对剥削性滥用行为及其规制却一直未有足够重视。在现实中,一方面,伴随互联网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动态性和多边性愈发明显,致使对其市场结构的影响,在传统反垄断法分析框架下并不足以引起主管机构及司法机关的充分关注和有效判定,但是(超级)平台企业的不公平交易行为给用户(消费者)利益带来的损害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在存在严重的市场进入壁垒,垄断性市场结构已经长期固化的市场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直接侵害交易相对方正当利益的行为也时有发生。这种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就为激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项下的剥削性滥用条款提供了可能和现实需要。
现行《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即对“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的禁止性规定可以为规制以非价格方式侵害消费者利益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也已经出现了对以非价格手段剥削消费者的行为的违法性进行判断的案例。然而,遗憾的是,在我国的司法实务当中尚未形成对此类行为违法性判断的一般性基准。鉴于此,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阐释一般性的违法性判断基准的同时,细化“显著性”和“不当性”的内容,即前述我国《暂行规定》第十四条中的“明显”和“不公平”的内容和指标。譬如,对“显著性”的判断要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性质,行为发生的时间、次数与持续期间,被侵害消费者的范围,相似市场上其他经营者的交易条件,交易条件变更前后市场支配经营者的成本变动程度,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差异等。对“不当性”存在与否的判断,应当具体考虑行为的目的是否在于追求过度的垄断利润、行为的性质、行为的持续期间、市场结构和特征等。在此基础上,再结合进一步的个案分析,为规范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的剥削性滥用行为提供指引,提高法律适用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