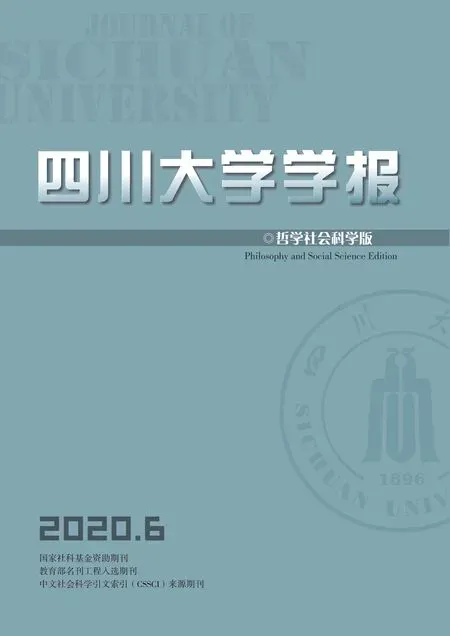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生培养述论(1928—1949)
——以史语所档案记载为主的探讨
马亮宽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斯年被任命为专任研究员兼所长,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拟定的史语所《组织大纲》和章程中都将研究生招收和培养作为史语所的基础性工作。考察史语所研究生招生和培养,可分两个阶段:前期(1928—1938)是试验阶段,后期(1939—1949)进入规范化时期。现根据史语所档案资料和相关论著对史语所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进行论述,敬请方家指正。
一、招收研究生的尝试
1928年,傅斯年主持制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第十八条特别规定:“本所得设置研究生,无定额;以训练成历史学及语言学范围内共为工作之人,而谋集众工作之方便以成此等学科之进步。”(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大纲》,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年,第137页。为落实研究生培养工作,傅斯年多次与史语所同人协调导师人选问题。1928年9月傅斯年致信在北平的陈寅恪:“本研究所之研究生须分附研究员名下,以便指导其工作,或须请先生担任此项研究生一人或三人,至感高谊。”(2)《傅斯年致陈寅恪》(1928年9月2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49页。傅斯年在聘请李济时,除了要求其主持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之外,另一项任务便是“负训练史语所考古学研究生之任”。(3)《傅斯年致杨铨》(1928年11月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65页。笔者查阅1928—1938年史语所年度报告,发现史语所招收的研究生并不多,并且没有连续性。1932年第一次招生,第一组(历史组)招收邵君璞、劳幹,第三组(考古组)招收石璋如、刘耀(后改名为尹达);1934年第二组(语言组)招收方国瑜,第三组招收胡福林(即胡厚宣);1937年第二组(语言组)招收邢公畹等人。但是史语所前十年对于研究生招收和培养没有计划和规程。傅斯年曾在致友人信中解释说:“弟数年中,颇思在研究所中招研究生,终以各种不便,未能实现。”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是科研机构,研究人员没有时间和精力给研究生讲课,“本所既无讲堂上之课程,而每人之工作又紧张,故一入所便等于做事,所习之题专之又专”,“故在研究所中训练研究生,不如在一个好大学中,教师较多,有课可上,不必做机械事,空气比较自由”。(4)《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0页。正是鉴于上述原因,史语所无法专门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因此,史语所在组织规程中虽列有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计划,实际上却没有条件正常实施。
二、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1938年,史语所迁至昆明,租赁云南大学附近的青云街靛花巷三号的一座楼房,暂时安居下来。同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也迁至昆明,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经过整合,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开始进入正轨。1939年4月,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与傅斯年等人商议,决定恢复因战乱停止活动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以便于史语所与北京大学合作进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并商定由傅斯年负责筹办。蒋梦麟等人如此安排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傅斯年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兼任导师,并参与了1934年北京大学内部的体制改革,对文科研究所的组织、培养人才的方式非常清楚。傅斯年在致杭立武的信中叙述说:“北大原有此一研究所,在中国历史最久,即所谓‘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也。此一所,与北大他事皆同,即每每为政治之牺牲品,旋作旋辍。五、六年前适之先生发愤整顿,弟亦大有兴趣,弟曾为北大借聘半年,即为此事。当时适之先生为主任,弟为其秘书,弟只任半年即南迁,受颐继之。卢沟桥事起而一切休矣。”(5)《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1页。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与史语所恢复了合作研究的关系,恢复文科研究所,傅斯年成为双方认可的领导人。
其二,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培养有成熟的思考和计划。如其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弟数年以来,深感觉大学毕业生之优秀者,如于其毕业后不置之于良善环境中,每每负其所学,故以为大学毕业研究生一层实属重要,此等兄亦具有同感者。尽此一关之力,未必皆成,然无此一关,中道而废者多矣,良可惜也。并以中国大学之多不长进,高材生毕业者不过初得其门,若一旦置之四顾茫茫之境,实不知所措。”(6)《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0页。另一方面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云集,招收的研究生有课可上,不必机械做事,学术氛围自由,完全符合傅斯年“狼狈为善”(7)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致信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要求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进行合作时创造了一个名词。信中说:“合作乃是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从此成为傅斯年与其他学术单位合作的专有名词和基本原则。参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第152-153页。的理念。
傅斯年在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商定恢复文科研究所以后,开始就研究所的组织管理机构、学术研究领域、研究生招考及聘请导师等事项拟定规程、创立制度。其筹备工作及运作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四项:
第一,建立研究所的管理机构。傅斯年设计的管理机构人员包括主任、副主任、委员等,领导机构对招收研究生及相关工作进行科学而严格的管理。他在致友人的信中说:
拟定之组织如下:
已与蒋梦麟先生商定:主任由弟代理。(照章由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北大文学院长系适之先生,不在国内,故由弟任之,名曰代理者,以为代适之先生也。)
副主任:郑天挺先生。(或名秘书,未定。郑先生虽刊布之著作不多,然任事精干,弟知之深,故推其任此事,亦因弟事不专此一件也。)
委员:已定者有汤用彤、罗莘田、姚从吾、叶公超、钱端升(法学院无研究所,故暂入此,此一研究范围,兼括经济及制度史,端升列入,亦当时枚荪之例也。)诸位,其他尚有二人待与梦麟先生商定。
此当为一个“民主组织”,庶几各个人均能发挥其责任。弟亦可谓好事,此一事等于自寻兴趣之大可知,办时必负责尽心,故兄如即以为弟之事业视之,亦无不可也。(8)《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2页。
傅斯年拟定的文科研究所管理机构成员在以后的运行过程中,因各种原因虽时有变化,但基本设施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
第二,加强研究生导师的选配。傅斯年经与蒋梦麟、郑天挺等人协商,决定为文科研究所招收的研究生增聘导师,聘向达为专职导师。在蒋、郑等人同意后,傅斯年于1939年4月致信向达,商议聘其为研究生专职导师。信中说:“适北大有恢复其‘文史研究所’之议,其中设专任导师,不教书,事务极少,不过指导二、三研究生,故其事与敝所之研究员无别,而比之更为自由,当时佥以为应聘先生来滇专任此事。”(9)《傅斯年致向达》(1939年4月20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65页。同时除文科研究所委员兼任导师外,又聘西南联大和史语所的知名学者如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等人为导师。另外,为加强对研究生的管理、协调导师与研究生关系,傅斯年又特别聘请留在北平的邓广铭到所担任专职管理人员。傅斯年在恢复研究所过程中采取的各项措施对于研究生的管理和培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三,寻求研究所的经费保证。傅斯年认识到,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与史语所合作招收研究生,必须解决经费来源问题,没有固定的经费支持,诸事无法进行。1939年5月18日,傅斯年写信给杭立武,要求从中英庚款委员会补助学术研究款项中,安排专款补助此项事业。他在信中阐述说:
此举与贵会补助学术研究,实同其性质。试看请款之目,共有三项:
(一)研究生。此即贵会补助各大学之助理,组织考察团以容纳新毕业生之意。然彼似较此为散漫,此则为一有组织之训练,且选拔上亦严也。此虽不限于新毕业生,然年龄有限,决非老毕业生矣。(考选方法,以论文为主要,笔试乃为每一人出一份题,此取外国高级学位考选之办法。既如此则论文审查,不得不严矣。)
(二)专任导师。有学问极有可观而不肯教书者。此中固可待贵会补助科学工作人员之救济,然目下既不再登报,而人才若发现,不可交臂失之。前与兄商及向达君,兄允待补助事项结束后为之设法(此君绝不愿教书),弟心中即以彼为一人,其他要看此待办研究所之需要。目下弟心中尚无其人也。此一类实即补助科学研究人员之事,特亦须顾到北大之需要耳。
(三)助理。此等助理事务甚少,实即导师研究生中间之一种研究员,论其性质亦与贵会补助科学人员为同类事。
故请款之三项,论其性质可谓全在贵会现在各项救济工作范畴之中,特彼以救济之用心达到补助学术之目的,此则虽不免或有救济之用,要以给学术工作者以适宜之机会为其目的耳。(10)《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2-973页。
傅斯年在信的附件中开列了“请款概算”:“第一项,研究生十名(每名每月生活费五十元),每月五百元。第二项,专任导师二名(每名每月薪俸平均一百五十元),每月三百元。第三项,助理员二名(每名每月薪俸平均一百元),每月二百元。以上每月全数一千元,全年一万二千元。”(11)《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7页。
傅斯年请求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款项一事迅速得到批准,杭立武5月25日给傅斯年回信通知招考研究生的费用得以解决。信中说:“北大文科研究所事,弟已在香港会议时代为提出,……增加经费五千元,当经通过照办。”(12)“傅斯年档案”,I-126,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经费解决为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事宜奠定了基础。
第四,研究生招考设想与办法。傅斯年等人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重要目的是招收研究生,培养社会科学研究人才。他在同意恢复研究所时就曾强调,“研究生。此一事业,弟之兴趣所在,皆在研究生,注意之、分配之,为之引近相合之导师,督责其课业,均弟所好之事也”。(13)《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2页。
傅斯年在决定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并兼任主任时做出了两项承诺:一是要负责任,办好此事,为将来胡适回国接任奠定基础。他在致友人信中曾表示:“弟之热心此事,非一新花样,乃是多年之志愿,且曾一度行之。在弟虽多些事,却觉得值得。弟虽未必永负此任,亦盼适之先生能早早建一功,回到北大,由其主持耳。”傅斯年此时设想为胡适回国复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所长打好基础,其结果由于时事变化,傅斯年1945年代胡适做了北京大学校长,待胡适1946年回国交付其一个复原后的北京大学,这恐怕是傅斯年本人此时所没有想到的。二是招收研究生要严格选拔,对各高校的毕业生一视同仁,不只限于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他曾表示:“此一组织虽在系统上为北大之一部分,但决不予北大毕业生以特殊之方,研究生之考试乃向全国公开,其考试委员会组织,亦系内外参合,以明一视同仁之义。”(14)以上引文参见《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4页。傅斯年的承诺在以后的工作中分别得以兑现。
为了使招收研究生有章可循,按制度办事,在招考以前,傅斯年等人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招考研究生办法》,对研究生招生数量、专业、考生资格、考试办法、待遇、考试时间等都做了明确规定。具体规定是:
(一)名额
本所暂设研究生名额十人,每人之科目,应不出下列范围:
1.史学部分。通史中各段,及哲学宗教史,文学史属之。
2.语学部分。汉语学各科,边地语言,英吉利语言学属之。
3.考古部分。考古学及金石学属之。
4.人类学部分。物质及文化人类学属之。
以上1、2两项名额约当全数十分之六七,3、4两项约当全数十分之三四。
(二)资格
应考人之资格需具备下列各条件:
1.公私立大学文学院毕业者,但其他学院毕业有适当之论文者,亦得应考。
2.著有论文者。
3.年龄在三十岁以下,身体强健者。
(三)考试
考试之程序如下:
1.应考人需于报名时缴付:(1)毕业证明文件,(2)论文,(3)其他关于学业之证件(此项如无,可缺)。
2.本所收到后即付审查,初审合格者,通知其在昆明或重庆应试。
3.考试科目如下:(1)口试,(2)外国语试(英、法、德之一),(3)笔试(就其论文性质作成试题以副其学力)。
4.注意点:初审及录取,均以论文为主要,此项论文以确有工夫并颇具心得者为限。
(四)修业及待遇
1.研究生修业期限为三年,但得延长之。
2.在第一年修业期中,每人每月给予生活费五十元,并由本校供给住宿。
3.在修业期中应遵守本校各项规则,并服从导师之指导。
4.在第一年修业满期后,考核成绩。其有成绩者分别给以奖金,以为第二年之生活费,无成绩者,停止修业。
5.全部修业满期后,考试及格,由本校依照部章给予证书,并择成绩尤佳者三分之一留校任助理,或介绍服务。
(五)考期
为适合投考者之方便,将入学考试分作两期举行:
1.第一次考试。接收论文于本年七月十五日截止,八月五日考试。
2.第二次考试。接收论文于本年八月三十日截止,九月十五日考试。
3.论文随到随付审查,故以早缴为有利。
4.第一次考试中,如录取名额已满,即将第二次考试取消。
(六)考试委员会
考试委员会由本校聘请校外学人参加。(15)《傅斯年致杭立武》(1939年5月17日),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第975-977页。
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后,于当年开始招收研究生。6月3日,上海《申报》对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工作进行了详细报道,其内容为:“北大文科研究所于1939年7月和8月两次举行研究生考试和论文评审,招收科目为史学、语言、中国文学、考古、人类学、哲学。初审合格者被通知前往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报到。每月发给生活费50元。”(16)夏本戎主编:《五华教育史话》,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9页。从各地报名与应考情况来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和招收研究生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事件。
1939年7月,研究生招考正式开始,招考完全按预先规定程序进行:每一位报考的学生在报名时先提交一篇论文,由专家委员会审查。审查论文主要是考察考生的学术功底和科研能力。论文审查通过后再由本专业的专家出题进行笔试。笔试内容主要根据考生的专业,检查其专业知识和知识结构,基本上每一位考生一份考题,由考生到指定的考试地点参加笔试。例如杨志玖的学习领域是元史,所以论文审查通过后由姚从吾命题。姚从吾出了三个题目呈送傅斯年,其附信特别说明:“弟意每人两题,不挑选,因此系就个人素有研究之部门出题也。若用两题,可抹去一题,不适用,尚祈另拟。”其题目是:
蒙古文字晚起,记载复少,现存蒙古朝初期之史料,可约分为:(一)自南宋人传下者,(二)由西域人记述者,(三)蒙古著作译成汉文者,三大系统。试就所知择要列举之,并比较其价值。
蒙古入主中原,儒者独尊之传统习惯为之打破,各派宗教,一时蜂起。试述除儒回二教外,当时比较著名之教派,及其所拥有之势力。
试述忽必烈对于统治汉地的见解和他对于采用汉化的态度。(17)“傅斯年档案”,I-910,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从姚从吾为杨志玖所拟试题可以看出,导师的笔试试题主要根据考生提交论文的专业领域,虽然试题难易有差别,但没有超出考生的学习领域。考生笔试通过后,再由专家委员会面试。傅斯年特别重视面试,正如一位学者回忆说:“傅先生对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非常严格。每逢口试,他多参加主持。众导师亦就某一问题向考生反复询问,直至考生语塞为止。然尽管所问严格,其目的并非要求全答,而是在测验考生之知识面,亦非单纯之下马威,故意刁难。”(18)郑克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7页。许多考生对傅斯年主持和参与面试留有深刻印象。杨志玖曾回忆说:“1939年秋,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生,由先生任所长,郑天挺先生任副所长。先生劝我们投考。先生对这次考试非常重视,亲自主持了一些口试,并检阅每个人的英文试卷。”(19)杨志玖:《我在史语所的三年》,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下),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第784页。
文科研究所经过严格的招考程序,共录取十名研究生,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生六人:杨志玖、马学良、王明、逯钦立、任继愈、阴法鲁。另外四人:阎文儒毕业于东北大学史地系,汪篯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周法高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刘念和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傅斯年兑现了对各高校一视同仁的诺言。第一批研究生录取后集中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楼,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昆明北郊龙泉镇外宝台山,靛花巷三号楼便成为文科研究所专用的办公地点。史语所和北京大学的部分学者陈寅恪、董作宾等人也住此楼。食堂、图书室皆在其中,研究生与导师切磋问题极为方便。
傅斯年对文科研究所的生源和师资力量极为满意,在1940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20)《致胡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7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1940年8月,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又进行了第二次研究生招生工作,招生方法与第一次大体相同,傅斯年等人亲自主持面试。在昆明考试过程中,北京大学应届毕业生王玉哲、李埏、刘熊祥、董庶,清华大学毕业生王永兴等同学报考,其中李埏和王永兴顺利通过,王玉哲被录为备取,最后获得补录。
傅斯年在昆明主持完考试后又到重庆主持了招生考试。在重庆参加考试的有殷焕先、王叔岷、李孝定等人。其中,殷焕先、李孝定毕业于中央大学,王叔岷毕业于四川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二届研究生共招收7名,分别是李埏、王永兴、董庶、王玉哲、殷焕先、王叔岷和李孝定。其中在昆明考取者入校初仍住在昆明靛花巷,后为躲避日机轰炸,随研究所迁至昆明郊外龙泉镇龙头村。郑天挺在晚年《自传》中记述了研究生生活情况: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21)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99页。
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因为图书馆随迁,为保证研究生有书可读,郑天挺专门致信傅斯年商议此事:
北大研究所址,非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22)郑克晟:《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兼忆傅斯年、郑天挺先生》,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第29页。
傅斯年与郑天挺等人经反复协商,决定文科研究所所址仍留原处,研究生去留自愿,仍愿留昆明者由郑天挺等人负责管理。随史语所迁到李庄者与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一起居住、生活与学习。邓广铭随史语所迁至李庄,管理随迁研究生日常生活。为了保障留昆明的研究生有书可读,史语所迁移时留下部分图书资料供其使用。
1941年,史语所与文科研究所进行第三届研究生招生,王利器、魏明经、王达津、程溯洛、高华年等在不同地点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1942年,史语所与文科研究所进行了第四届研究生招考,胡庆钧、方龄贵、李荣、汪子嵩等人被录取。
三、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状况
史语所和文科研究所四届共招收二十多名研究生。郑天挺曾对研究生的师承关系及学习情况记述说:“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我亦在其中);李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其后,史语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李孝定)相随,就学于李方桂、丁声树、董作宾诸教授。”(23)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99-700页。现根据郑天挺的记述对这四届研究生的专业及学术研究成就进行简要记述。
王明、魏明经、任继愈师从汤用彤。王明从事道教研究,1941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1957年调哲学所工作。王明一生主要从事道教经典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魏明经从事庄子研究,1941年毕业后,先后在华中大学、齐鲁大学、山东师范学院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思想政治室工作,一生从事庄子研究。任继愈1941年毕业留在西南联大工作,1946年随北大迁回北平,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6年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1964年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87年调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论》《中国哲学发展史》《佛教史》等。
阎文儒师从向达,从事西北史地考察和研究,曾撰写有《汉唐西域文明史》《西京胜迹考》等。1948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隋唐考古和石窟艺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王永兴、汪篯师从陈寅恪、郑天挺,主要从事中国隋唐史学习和研究。王永兴1943年毕业后担任陈寅恪的助手,1978年调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隋唐史、敦煌学研究。汪篯毕业后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以此名义继续担任陈寅恪助手。
杨志玖、李埏和程溯洛师从姚从吾、向达学习中国史。杨志玖毕业后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隋唐史、元史研究。李埏学习宋元史,毕业后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是研究中国土地国有制和西周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程溯洛从事宋辽金元史学习和研究,1952年调任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致力于少数民族历史的教学和研究。1959年编辑出版了《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曾撰著《维吾尔族简史》,被认为是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开创者。
殷焕先、王玉哲、王达津师从罗常培、唐兰教授。殷焕先学习中国语言学,毕业后任山东大学教授,长期担任《文史哲》主编,为新中国的语言学术建设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王玉哲1948年受聘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从事先秦秦汉史教学和研究,其代表作《中国上古史纲》《中华远古史》《古史集林》等,是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的权威学者。王达津1952年调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著有《唐诗丛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等,是唐代文学研究专家。
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师从傅斯年,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王利器1944年毕业后受聘于四川大学,1946年,被傅斯年调回北京大学,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知名于世。王叔岷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迁居台湾,任史语所研究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其代表作有《庄子校释》《列子补正》《史记斟证》等。李孝定毕业后留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1949年随史语所迁居台湾,任史语所研究员,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其代表作有《甲骨文集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等,在海峡两岸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阴法鲁、逯钦立、董庶师从罗庸、傅斯年和杨振声等人。阴法鲁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曾对中国音乐史、舞蹈史进行专题研究,被认为是中国著名的古代音乐文化研究专家。逯钦立学习中国文学史,毕业后留在史语所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调任广西大学工作,终生从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董庶学习和研究中国音乐史,毕业后留在昆明,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
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师从罗常培、李方桂等学习中国语言文字。马学良在求学期间经常随李方桂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实地录制少数民族语言、语音,解放后长期担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成为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专家。刘念和学习中国汉语历史音韵学,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解放后长期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法高学习和研究中国声韵学,毕业后进入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随史语所迁居台湾,继续从事中国声韵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客座教授,后长期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1977年后返回台湾史语所任研究员。其研究成果《中国古代语法》《汉字古今音汇》等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高华年毕业后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1951年调往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语言学教授,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广东语言学会会长等职务。
对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抗战期间培养的研究生,郑天挺数十年后曾进行评论,王永兴对此记述说:“在(郑天挺)先生逝世前二年,我去天津南开大学拜谒先生,……先生命我详述四届学生之人数姓名以及目前的工作情况,我一一禀告之,数十人均在高等学校任教和高级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我的禀述有脱漏或错误,先生补正之。最后,先生笑语曰‘我们(指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没出一个废品’。”(24)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7页。郑天挺的评价表面看来是低标准,但结合研究生毕业后工作科研状况,此评价准确而且标准很高,从中也透露出郑天挺为此项事业艰苦努力的成就感。
四、认识和评价
历史语言研究所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是为训练和储备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由于考选严格,培养精准,管理科学,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合作招考和培养研究生,虽环境艰苦,但广大教师和研究生克勤克俭、一心向学的风范和为抗日救国而学习研究的精神为后人树立了典范,一代学人的行为给后人许多启示。
其一,广大师生树立了为抗日救国而努力向学的思想意识,是学习和科研取得优异成绩的主要动力。研究所的导师和研究生基本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辗转到达西南的大后方,他们经历了因日本侵略而国破家亡的痛苦,同时奠定了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而努力学习的思想观念。师生们都具有为抗日救国而积极求学的意识,郑天挺曾总结说:“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宝台山的研究生(或称宝台山士)就是这样的。”(25)郑天挺:《自传》,《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700页。傅斯年等学人为抗日救国而致力学术研究,培养人才,他们以身作则,经常对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进行科学救国的教育,许多研究生都树立了读书救国的思想理念。正如当时一位研究生所评论:研究所内“学风正,工作勤,大家专心科研,很少受到外界影响”。(26)马学良:《历史的足音》,杜正胜、王汎森主编:《新学术之路》(下),第863页。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受到严格而科学的训练,学术研究方法和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
其二,其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使研究生接受了严格而科学的教育,成为研究生成材的重要原因。傅斯年等人对研究生培养和教育的准则是“高标准要求,自由式发展”。所谓高标准要求在研究生的录取和培养方面体现得相当充分,研究生考前先提交一篇论文,论文审查通过,才有资格参加英语和专业笔试,也就是考生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是第一位的。在研究生录取后,实行导师负责制,对研究生进行的专业指导侧重于学习方法和研究路径。这里仅举一例,王叔岷是傅斯年指导的研究生,他曾回忆第一次见到傅斯年的情境,为显示才气和学习成就,特地呈送给傅斯年自己平时写的诗文,不曾想遭到傅斯年严肃的训诫,要其沉下心好好读书,“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27)王叔岷:《慕庐忆往》,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93年,第43页。王叔岷第一次拜见傅斯年受到的训诫,影响了他一生。所谓“自由式发展”就是研究生的学习方法和论文选题等有较大的自主权,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互相启发。傅斯年等人为了营造研究所内学术研究的氛围,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让师生相互讨论,相互启发,并规定史语所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师生轮流担任报告人,在读研究生也不例外。据何兹全回忆:“史语所有个好传统,就是不定期的学术报告。在李庄期间,我记得傅先生、董彦堂先生、劳幹、董同龢、逯钦立都做过报告。这是学术交流,对每个人的研究也是个督促。”(28)何兹全:《李庄板栗坳·史语所》,《新学术之路》(下),第824页。王利器也有相似的记述,其中逯钦立、王利器都是在读研究生。王利器就曾做过一次题为《“家”、“人”对文》的报告,颇得傅斯年的赞赏和大家的好评。除傅斯年以外,研究所导师陈寅恪、郑天挺、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认真负责,他们曾长期与研究生一起生活,督促他们读书研究,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问题,为研究生学习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其三,研究所学人纯正的学风,对研究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恢复后,为了加强文史等学科的学术研究、培养人才,特从西南联合大学和史语所中聘请了许多大师级学者,西南联大的汤用彤、罗常培、唐兰、罗庸等人,史语所中的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丁声树等人,以及傅斯年、郑天挺等也亲自兼任导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学者把在北京大学和史语所培育的纯正学风融合在一起,在所内发扬光大,在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方面表现得相当充分。概括起来就是,以道德学问为规约,以教学传道为天职,潜心治学,授业传教,对研究生的教育、指导认真负责。这方面事例很多,略举一例。1941年7月初,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曾专门到李庄主持研究所研究生的答辩,罗常培记述李庄几位研究生学术研究及与导师关系情况说:“马、刘两君(马学良、刘念和)受李方桂、丁梧梓(声树)两先生指导,李君(李孝定)受董彦堂(作宾)先生指导,李、董、丁三位先生对他们都很恳切热心。据马君告诉我说,李先生常常因为和他讨论撒尼倮语里面的问题,竟至忘了吃饭,这真当得起‘诲人不倦’四个字。任君(继愈)研究的题目是‘理学探源’。他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熏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29)罗常培:《苍洱之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0页。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生潜心向学,取得优异成绩,与研究所优良纯正学风的培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