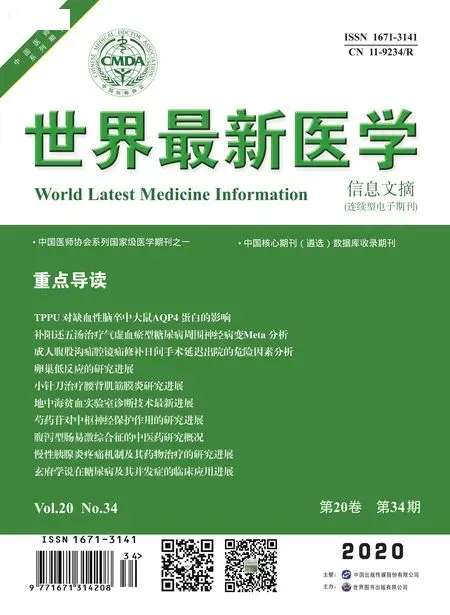苯二氮卓类药物依赖性失眠的临床研究进展
高宇星,白玉昊
(1.内蒙古医科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2.乌海市蒙中医院,内蒙古 乌海)
0 引言
苯二氮卓类药物(Benzodiazepine,BZD)从20 世纪60 年代被临床使用至今已有60 余年历史,因其具有镇静催眠、抗焦虑惊厥等药理作用被广泛应用于临床。BZD 可缩短入睡时间、减少觉醒时间和次数、增加总睡眠时间,具有安全性高、耐受性较好的优点,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治疗失眠症药物[1]。也因其广泛的使用,其不良反应也逐渐被人们认知,主要包括白昼疲倦、头晕乏力、跌倒、认知功能减退等[2-5]。但是持续使用BZD 超过2 个月产生依赖的风险会加大,骤然停药可发生戒断反应,出现情绪紧张、恐惧焦虑、激惹易怒等[6]副反应。临床中存在相当一部分患者因失眠而依赖于BZD 入睡,且长期使用BZD 使其机体产生耐受性和依赖性,一旦停药后其戒断反应随即出现。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显示[7]:在日本开始服用BZD 的患者中,20.1% 的患者日后服用BZD 会超过1 年以上,而在自然人群中,BZD 依赖(>6 个月)的患者所占比为3%。
1 BZD 在临床的使用现状
BZD 因起效快、作用强、效果好且副作用小被临床各科室使用广泛[8],尤其神经内科及老年病科。杨庆林[9]在本单位精神疾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得出,服用BZD 者占41.3%。李会玲[10]研究本院2011-2015 年睡眠障碍用药现状得出,BZD 的使用比例逐年下降,但其使用比仍占首位。刘志伟等[11]对其医院2015-2017 年的8 种镇静催眠药进行临床用药分析发现,BZD 居首位,使用比均超过75%,销售总额的年增长率超过50%。巢云等[12]调查上海某社区274 例老年失眠患者安眠药物使用情况得出,社区门诊失眠患者中BZD 助眠治疗的使用率为85.8%。姜春和[13]对本院2012-2014 年第二类精神药品的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出3年来BZD 的用药频度(DDDs)均超过86%。由此可见,BZD 是治疗精神类疾病的常用药物,也是目前治疗失眠症的主要药物,因其使用的广泛,产生药物耐药性与依赖性的几率大大增加。
2 BZD 在失眠症中的应用
失眠是指尽管有合适的睡眠机会和睡眠环境,依然对睡眠时间和( 或) 质量感到不满足,并且影响日间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14]。研究表明有45.4%的中国人在过去一个月中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而在人群中慢性失眠的患者占6%-10%[15-16]。失眠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入睡困难,易醒早醒、醒后难以入睡,多梦噩梦,睡眠质量轻、稍有噪音即醒等直接影响睡眠质量的症状及次日晨起后疲劳乏力,精神不振,情绪低落等日间功能障碍。临床具有催眠作用的药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非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具有催眠效应的抗抑郁药物、镇静安神的中成药和中药处方等。而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又分为苯二氮卓类药物和非苯二氮卓类药物。
生活质量可影响睡眠质量,睡眠质量亦可影响生活质量,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呈恶性循环。为了摆脱此类恶性循环,失眠症患者会选择镇静催眠药以改善睡眠。而BZD 因其起效快、价格廉成为首选药物之一。马欣荣[17]研究老年失眠症患者生活质量及BZD使用情况发现,生活质量、心理功能、社会功能与睡眠质量呈明显负相关,88 例失眠症中平均使用BZD 的时间为12 个月,依赖发生率高达71.59%。丁兆生[18]研究老年失眠患者用药情况得出,因失眠而就诊的老年失眠患者的BZD 使用频率在91%左右。两项研究中艾司唑仑在所有BZD 中使用频率最高。王守芝[19]对100例使用BZD 的患者进行分析发现,用于治疗失眠的占95%,其中单纯失眠症占21%,精神障碍(包括抑郁焦虑、精神分裂症和脑器质精神障碍)伴失眠占58%,使用精神活性物质致失眠占3%,继发于其他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的失眠占13%。
3 BZD 的作用机制及不良反应
BZD 主要作用于大脑皮层苯二氮卓受体(GABAA 受体),GABA 受体激动,Cl-通道数目开放增多,流入细胞内的Cl-增多,超极化而引起抑制性突触后电位,减少中枢内神经元的放电,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BZD 大多属于亲脂性药物,与细胞膜有很高的结合力,口服后吸收快,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能快速发挥药效。其主要通过肝药酶代谢,BZD 及其代谢产物最终与葡萄糖醛酸结合而失活,经肾排出。根据其半衰期可分为短效、中效和长效。其中三唑仑作为唯一的短半衰期催眠药物,因其遗忘、欣快、胃部不适,头痛头晕,皮肤刺痛等不良反应和成瘾性发生率高,被我国列为一类精神药品管理。
BZD 的主要不良反应有头昏、嗜睡、乏力等“宿醉”现象,部分药物可引起口干、便秘;长期服用会产生耐受性、依赖性及成瘾性,突然停药可出现失眠、头晕、焦虑、震颤等戒断反应。研究表明,中短效的BZD 更容易产生BZD 依赖的风险[20]。长时间或大剂量服药会引起BZD 中毒,出现昏睡嗜睡,意识障碍,呼吸抑制,严重者可引起死亡。有报道一例患者因轻度抑郁症,长期睡前服用阿普唑仑2 片,突发神志不清,出现浅昏迷状态,被误诊为脑梗死,后给予氟马西尼注射液对症治疗后好转出院[21]。白志冬[22]在诊治一例慢性心衰患者时,植入永久起搏器术后因其烦躁不安,分两次间隔一小时给予艾司唑仑2mg,出现嗜睡,继而出现深昏迷,考虑肺性脑病,对症治疗后好转。另有报道,男性患者因家庭琐事,口服8 片地西泮后出现脑干梗死[23]。
4 BZD 依赖性失眠的临床治疗
药物依赖性指是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所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也包括身体状态,它表现出一种强迫性地要连续或定期追求重复用药的行为和其它反应,为的是感受它的精神效应,或是为了避免由于断药引起的不舒适,可以发生或不发生耐受性,同一人可以对一种以上药物产生依赖性[24]。药物依赖性可分为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两类。临床中以精神依赖性为多。对于长期服用BZD 助眠的患者而言,仍自觉睡眠质量不可理想,且白天精神不振,头晕乏力,烦躁焦虑等症状,停药后失眠加重,头晕焦虑等戒断症状出现。临床中针对BZD 依赖性失眠的治疗主要包括,西医疗法和中医疗法。
西医疗法主要包括药物递减、隔日给药、药物替代及药物辅助治疗。药物递减和隔日给药属于计划停药治疗方法,目的是有计划的逐渐减少BZD 用量而摆脱对BZD 的依赖。其中药物递减法适用于短、中效BZD,隔日给药法适用于中、长效BZD 依赖。药物替代治疗是使用不易产生依赖性的长效或其他非BZD 的苯二氮卓受体激动剂代替目前已经产生依赖的BZD。临床中在停药计划的基础上可配合使用某些药物提高疗效。赵君[25]对80 例BZD依赖性失眠患者用盐酸曲唑酮联合BZD 递减方法治疗后,总有效率为80%。甘伟明[26]使用黛力新与佐匹克隆治疗苯二氮卓类药物依赖性失眠症的对照观察中得出其总有效率均在97%以上。
中医疗法主要包括中医辨证处方和针刺治疗等。李海宏[26]认为此类患者长期服用BZD 导致阳郁于内,耗伤阴液,久郁化毒,在治疗中以养阴清热、泻火解毒为主。杨新国[27]用院内制剂安神交泰胶囊联合BZD 递减治疗,总有效率为90%,其主要认为BZD依赖性失眠责之于心肾不交。陈颖[28]探讨针刺治疗对苯二氮卓类药物依赖性失眠的临床疗效和药物戒断作用得出,依据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积分(PSQI) 总有效率为85.71%,减药率为92.86%。
5 不足与展望
BZD 因其镇静催眠、抗焦虑惊厥的作用被广泛使用于临床,在治疗失眠障碍中所占比例更是居于首。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不良反应,尤其是耐受性及依赖性的问题。面对BZD 依赖性问题,医务人员应该合理用药,避免其转化成BZD 依赖性失眠。如果说BZD是一把双刃剑的话,那么医者就是手持利剑的武者。如何将其作用发挥最大化,规避其不良反应,是一个优秀医务者首先考虑的问题。当然临床中大部分失眠患者的病因主要来自于心理问题,心理治疗是解决失眠问题的一种新途径。如果心理疏导效果欠佳,不得不采取药物治疗时,给予BZD 持续用药时长不应该超过2 个月。采取多种给药途径,如隔日给药,交替使用不同种类BZD 治疗等。准确告知患者BZD 的副作用,避免其追求效果而贸然加大药量。同时对于睡眠障碍的患者可以给与非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镇静催眠药,如佐匹克隆、右佐匹克隆、唑吡坦、扎来普隆等。其中扎来普隆起效快,无宿醉和残留,是现在唯一可以达到“按需服用”要求的安眠药,使用较广[29]。
中医药作为祖国的传统医学,对失眠的认识有2000 多年的历史。从《黄帝内经》开始就有“卧不安”的记载,更是记载了第一个治疗失眠的中药方半夏汤(由半夏、秫米组成)。其对失眠的治疗手段也多种多样,如中药、针灸、耳针、穴位贴敷、推拿等。而中药的治疗又依托于辩证论治。在治疗失眠的汤剂方面,各医家在中医理论的基础上辨证施治,以阴阳气血为纲,从脏腑、三焦、六经、经络等角度辨证分型。失眠症中医称之为“不寐”、“不得卧”、“不得眠”、“目不瞑”。“不寐”最早见于《难经·四十六难》,其原文曰:“老人卧而不寐,少壮寐而不寤者,何也?然:经言少壮者,血气盛,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于常,故昼日精,夜不寤也。老人血气衰,肌肉不滑,营卫之道涩,故昼日不能精,夜不得寐也。故知老人不得寐也。”至金元后逐渐统一,并一直延用至今。中医认为失眠的主要机理是:阴阳失和、营卫失调、气血亏虚、脏腑失养及胃不和则卧不安等理论。中医药经过千年的临床实践的,对失眠的治疗有确切的疗效。临床中遇到失眠障碍的患者,可以更多的选择中医药治疗。对于BZD 依赖性失眠的患者,在停药计划的基础上依托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病求本,同样也会有确切的疗效。当今中医工作者对BZD 依赖性失眠的研究较少,仅有数篇相关报道。对于治疗BZD 依赖性失眠,还需更多的中医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