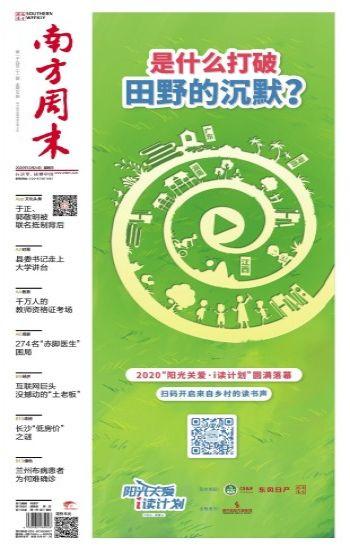值得信任的书评
王晓渔

凌越:《见证者之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
凌越先生是文艺领域值得信任的书评家之一,在2020年出版了两部书评集《见证者之书》和《汗淋淋走过这些词》。他有着数十年的文学阅读与新诗写作经验,熟谙写作的技艺,著有诗集《尘世之歌》(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法学的专业训练(虽然他自称在政法院校读书时经常逃课)以及对社科类书籍的关注,又使他对公共问题有着条分缕析的能力。
美国诗歌评论家文德勒有篇文章《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讨论了见证/社会责任与愉悦/诗学自由的关系。对此常有固执一端者,凌越选择了“徘徊”而非“固守”的姿态。《见证者之书》侧重“见证”却并未忘记“愉悦”,《汗淋淋走过这些词》侧重“愉悦”而并未忘记“见证”,书中第一辑即为“从道德看文学”。这里所说的“道德”不是道德审判,道德审判常把道德简单化,道德的复杂超过任何一团乱麻。
《见证者之书》主要关注对非常状况的书写,苦难需要被讲述,讲述又不能仅限于“诉苦”模式。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化学家兼作家莱维,近年有十余部书被引入中国,凌越撰写了四篇书评讨论他的作品,可谓简明的莱维导读。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有两部回忆录被译为中文,凌越有两篇书评进行评介。他不仅关注写作者在艰难时代的境遇,还注意到一些微妙的细节:在撰写第一部回忆录时,娜杰日达对诗人阿赫玛托娃有温情的书写;等到阿赫玛托娃去世,她在第二部回忆录里却有相反的描述。
凌越对评论对象的引述通常准确而精到,比如他引用莱维的说法“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指出在集中营里“那些自私者、麻木者、施暴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最终幸存了下来”。见证者常是幸存者,但他们又很难见证那些未能幸存者所经历的现实及精神世界。他们的幸存,通常又会和妥协甚至共谋相关联,具有着原罪。这样说有些苛刻,如果没有这么苛刻,反思很难深刻。
凌越对评论对象不只是推崇,而是多有商量。德国学者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里试图反思第三帝国的兴起,认为这是一种偶然。在凌越看来,作者淡化了第三帝国和德国古典文化尤其是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
凌越的志趣在文艺领域,却没有完美化文艺思维,对纯净美学多有批评。他注意到两位集中营幸存者威塞尔和凯尔泰斯,都讲到集中营里的医疗如何“美好”,这不是为集中营辩护,而是呈现集中营如何贯彻纯净的美学。在第三帝国里,清除“肮脏”的犹太人与治疗疾病是同样的逻辑,纯净和美好是恶最常用的托辞。凌越提醒注意莱维的话,“肥沃的土壤中,要有许多杂质。异议、多样性、盐粒和芥末都是必要的”;也提醒注意社会学家鲍曼所说的现代“园艺”国家观,为了美观而忽略或伤害不美观者的权利。
另一本书评集《汗淋淋走过这些词》更注重诗学的维度,比如对阿赫玛托娃晚年的名篇《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有着敏锐的批评,虽然这些作品试图承担见证的责任,但凌越认为,阿赫玛托娃更擅长微观的书写,于此反而有扬短避长之嫌。略有遗憾的是,凌越对此仅点到为止,如能展开,将是一篇重要的诗学文章。
每篇书评不过数千字,但为了撰写这些书评,凌越不仅仔细阅读评论对象,也阅读了诸多与之有关的书籍。在评论另一位白银时代诗人茨维塔耶娃时,他曾透露,“曼德尔施塔姆、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这五位诗人译成中文的诗歌、随笔以及专辑评论资料等”,会尽可能找到细加阅读。凌越还翻译了被忽略的白银时代诗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集《迟来的旅行者》(与梁嘉莹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可见他对这一领域用力之深。有着完整的视野,才能把某位诗人或某部作品放在合适的位置。
凌越持续撰写着这些耗时费力又缺乏回报的书评,不把书评当作图书营销或人际交往的工具。这种沉潜,是撰写书评者尤为需要又常匮乏的品质。或许对他来说,阅读和写作带来的愉悦,本身就是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