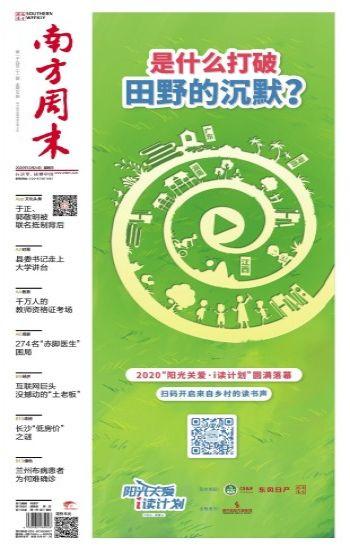“女性是如何在艰难的时代自我实现的”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发自上海

1995年6月,时年70岁的黄宗英在上海。视觉中国❘图

黄宗英在电影《家》(1956)中饰演梅表姐。 资料图

1982年,中日第一部合拍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摄制期间,黄宗英(左二)、孙道临、杜澎(右一)拍摄之余在无锡蠡园合影。 IC photo ❘图
★“当时的演员不论在戏剧舞台还是在片场,所受到的历练强度是今天的演员不可想象的。演员一天就排数场话剧,戏服穿上后就不能卸妆,吃饭都是在后台随便解决。他们也许没有接受过太多科班教育,却在社会大学里迅速成长。”
“我父母始终都没有对我们讲起她们对过去的人和事有什么怨言。而那些争议,在历史里,看上去一点也不重要。”
2020年12月14日,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去世,享年95岁。临终前她留下遗言:我走了,我深深爱你们。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两天前,黄宗英的儿子赵左参加了母亲的告别仪式。他本来不想发言,但作为唯一在黄宗英身边的子女,他需要上台向来宾致意。悼念现场,表演艺术家秦怡、田华、谢芳、陈道明等人敬献花圈。告别会上,很多“影二代”“影三代”都到场了。他们面对媒体镜头,一一自报家门,“我是某某,是某某的儿子(女儿)”。黄宗英的逝世把他们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有人看到视频对赵左说:“你们上海电影人的后代都很低调。”
黄宗英静静躺在偌大的纪念堂中间,在她一头白发、目光炯炯的照片两侧,是挽联“惊涛时代一女性,宽广银河一颗星”。黄宗英主演的电影不多,却几乎全是经典(《乌鸦与麻雀》《家》《武训传》《聂耳》),她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也曾轰动一时。
尽管黄宗英遗嘱说可随意处置骨灰,赵左还是想有机会让母亲与父亲赵丹合葬。这些年,随着老一辈人的去世,后人们的走动反而多了一点,他们的微信群里已经有八十多个人。他们共同的希望,是可以在上海最大的墓园——福寿园建立一个电影和戏剧人的墓园。
“不要按照名气来排,就按照年代,1920年代(出生的)一排,1930年代一排,1940年代一排……不要叫名人园,可以叫‘中国戏剧电影公园之类的名字。每个人占据一个小小的地方,能照到阳光就好。”赵左说。
母亲“头七”那天,赵左没有接任何电话,他的理由是“尊重必要的传统”。面对记者,他多少有些顾虑。作为赵丹和黄宗英的儿子,赵左继承了父母一贯低调的作风。
“她可以被看作中国新女性的典范”
黄宗英曾说:“从小我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她的前半生,似乎充满了偶然性。若不是9岁那年父亲去世,黄宗英应该和几个兄弟一样读大学,或许会成就别的事业。黄家的几个孩子后来都投身文艺界,一方面因为家族的传承,一方面也是生活所迫。
黄宗英15岁那年被迫中断了学业,去上海投靠兄长黄宗江。她寄居在哥哥租住的亭子间,以见习生的身份进入上海职业剧团,用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她曾说自己“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后来,由于成为话剧《蜕变》的替补演员,她登上了舞台。
没多久,黄宗英在话剧《甜姐儿》里扮演一位娇艳可人的大小姐,在上海滩走红,“甜姐儿”的外号也不胫而走。1946年,黄宗英演了生平第一部电影《追》,由舞台走上了大银幕。导演陈鲤庭很欣赏她,邀请她出演影片《幸福狂想曲》的女主角,而男主演则是赵丹。据说在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赵丹对她说“你应该是我的妻子”,这句话改变了黄宗英的一生。
时任黄宗英第二任丈夫的程述尧是黄宗江的同学,因为赵丹的介入,两个人离婚了。这些聚散离合的背后,是一个价值观碰撞的动荡时代。难得的是,程述尧后来与上官云珠结合,生下了儿子韦然,两家人依然走动频繁。韦然一岁多的时候,父母离婚,有时候程述尧没空从幼儿园接他,赵家保姆就会带他回到赵丹的家里。直到2015年左右,黄宗英急病做手术,黄家的孩子无法立刻赶回国,赵左就给韦然打电话,韦然第一时间赶到华东医院处理手术事宜。上代人纠葛的情感,在下代人这里成了剪不断的情谊。
黄宗英后来主演的电影很少,除了《幸福狂想曲》,其它几部代表作品《丽人行》《乌鸦与麻雀》《武训传》《聂耳》等,都是与赵丹合作的。她的演技高峰普遍被认为是饰演电影《乌鸦与麻雀》里国民党官员的情妇,这或许是因为这个有点泼辣风情的人物和黄宗英本人差异很大。
从黄宗英的角度来说,她正好赶上了中国话剧和电影的蓬勃时代。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认为,时代风潮把黄宗英推到了最前沿,她在抗战结束后进入戏剧电影界,起点很高,而当时整个行业水平比战前有一个大的迈进。
“就像一个风筝,风来了你就要飞。”石川告诉南方周末。“当时的演员不论在戏剧舞台还是在片场,所受到的历练强度是今天的演员不可想象的。演员一天就排数场话剧,戏服穿上后就不能卸妆,吃饭都是在后台随便解决。他们也许没有接受过太多科班教育,却在社会大学里迅速成长。”
石川始终不忘少年时代在电影《家》里看到的梅表姐,虽然戏份不多,但梅表姐的郁郁不得志和善解人意都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梅表姐早早失去了丈夫,黄宗英的第一段婚姻也因为丈夫心脏病突发去世只维持了18天。在一定意义上,她和梅表姐的心灵有着相通的地方。多年后,已经九十多岁的黄宗英在《可凡倾听》节目里说,自己最好的角色就是梅表姐,这么苦情的角色,她赋予了其微笑。当然,黄宗英自己也带着玩笑的意味讲过,要说最难扮演的角色,则是赵丹的妻子。
演艺事业停滞后,黄宗英开始了漫长的写作生涯,她后来一直在上海市作协工作,以报告文学成名。她的写作方式更接近于记者,经常需要下乡考察,黄宗英在许多地方留下足迹。
因为经常不在家,赵丹和叶露茜的女儿赵青在回忆录里有过一些抱怨,她认为黄宗英没能给赵丹一个温暖的家庭。对此,赵左则认为“我父亲是欣赏母亲的,他们都是很独立的人。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家里很安静。他们各自在房间的一角写作看书。我母亲那么好强的人,是不甘于仅仅作为赵丹的妻子存在的,她是独立女性,她有自己的世界”。有种说法很生动地反映了他们的关系,赵丹一遭到“运动”,黄宗英就会回家变成“贤妻良母”,在大风大浪中,他们夫妇始终同在。
赵丹去世后,黄宗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在她的诸多报告文学里,《小木屋》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篇,讲述的是女科学家徐凤翔致力于建设高原生态研究站的故事。后来,央视以这部作品为蓝本拍出了同名纪录片。在这之间,她还尝试在深圳“下海”经商,在作家中属于敢为人先的。虽最终以“经营不善”作罢,也足见其性格。
为了《小木屋》的拍摄和写作,黄宗英三次进藏,1994年,69岁的黄宗英第三次跟随徐凤翔入藏考察,遭遇了严重的高原反应。据说,去西藏后,黄宗英就给自己的子女和家人留下了遗书,她是带着决绝的态度来写作的。
1993年深秋,黄宗英透露出自己要结婚的意思,对象是翻译家、书评家和散文家冯亦代,当时供职于《读书》杂志编辑部。这之前,他们已经鱼雁传书一阵子了。他们在信里,一个自称“小妹”,一个自称“二哥”,十分亲热。这场黄昏恋在当时得到了很多祝福,也收到一些闲话。儿子赵左很支持,他说:“我想冯亦代是理解母亲的。”
这场婚姻维持了十二年,直到冯亦代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多天后,他们的情书要出版了,黄宗英给“二哥”又写了一封信,她写道:“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里,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拥抱在一起了。你高兴吗? 吻你。”那时候,黄宗英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杨远婴谈起黄宗英的时候,至今难忘她在1980年代末期著名的纪录片《望长城》里的造型——黄宗英以一头白发的形象出现,光彩照人,一边主持一边骑马。杨远婴对南方周末说:“今天来看,黄宗英的写作是非常浪漫主义的,凭借着一种激情在写作。她可以被看作中国新女性的典范,她的人生体现了那一代女性是如何在艰难的时代里自我实现的。黄宗英就是到了晚年也始终保持着那种激情,即使是吃苦也还在坚持着爱情。”
“我母亲几乎不会讲起仇恨和痛苦”
“我自己不好讲我父母的事迹的,讲什么都似乎是吹嘘,我请大家来谈谈我们父母彼此之间的交往吧。”赵左回忆,小时候父母几乎不会教训自己,只有一点,不能仗着自己的家庭出去乱讲。
2020年12月22日下午,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在上海淮海中路黄宗英和赵丹生前的家里见到了其子赵左,为了这次采访,赵左特别约了上官云珠之子韦然,魏鹤龄之子魏迦以及高淬之子武小朋。“若不是因为工作,现在还有年轻人喜欢看他们的电影吗?”他们问。
1949年后,黄宗英就渐渐淡出影坛,学者一般认为这与其形象有关。她的形象比较柔美,适合演资产阶级小姐,不符合当时流行的工农兵形象。石川认为,这在上海演员中是一个普遍问题。对此赵左却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母亲不再演戏是一种主动的退让——那么多人没有戏演,赵丹的妻子还在演戏,大家会如何想呢?
赵左生于1957年,当时正逢“反右”,因此单名一个左字。到了美国,因为别人说这名字容易让人联想,他一度加上单人旁,改成“赵佐”。
作家陆正伟则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纪念文章里,披露了这样一件事:1959年初,黄宗英正在电影《聂耳》摄制组中饰演舞女冯凤。一天,电影局领导在会上突然向她宣布,将她从电影演员剧团调至电影文学创作所,专业写剧本。黄宗英听后大吃一惊,头即刻疼得如炸裂一般。由于过度焦虑,就此落下缠绕终身的病根。
“文革”期间,赵丹再度入狱,一关就是五年。如果加上1938年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监狱里的6年,他一生中有11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赵左还记得,“文革”后期赵丹刚出狱就到结义兄弟魏鹤龄的家里,历经浩劫的二人抱头痛哭,但对彼此遭遇的细节并不多讲。一度,赵丹是苦闷的,他有时候会在湖南路的老房子向下张望。有一次看见巴金行色匆匆去上班,赵丹跑下去打招呼,回来很释然地告诉子女:“巴老说,这是中国人的浩劫,我们个人的遭遇不算什么。”
黄宗英也进了上影厂的“牛棚”,她同上官云珠、王丹凤、白穆等人在一起彼此照料。当时的上官因为做过脑部手术,身体很虚弱,长期的审问和折磨把她的身体彻底击垮了。1968年11月21日,黄宗英几个人一起离开电影厂回家,她感觉到上官的状态不好,应该陪她走回去,但这个念头一转而过。在那个年代,这样几个有“问题”的演员是不敢在大街上交谈的。当夜,48岁的上官云珠回家,凌晨即跳楼自杀。
▶下转第20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余雅琴发自上海

2020年12月22日,赵丹黄宗英上海故居的饭厅摆放着赵丹肖像油画和黄宗英的遗像。 余雅琴 ❘ 摄

1984年2月11日南方周末创刊号头版刊登了黄宗英在深圳“下海”经商的报道。
◀上接第17版
后来黄宗英想,如果陪着上官回家,结局会不会不同。守望相助是需要勇气的,上影厂女演员高淬本来和黄宗英并不熟悉,因为住得不远,又都受到冲击,两家人走得很近。“那时候,大家都不敢来往的,大街上见到点点头,但我妈觉得不能这么势利。”武小朋回忆道。
1977年,“文革”结束一年了,上官云珠还没有得到平反,黄宗英在当时尚不明朗的局势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纪念上官的文章《星》,产生了很大影响。她曾说:“我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勇敢的人,我只不过想用笔向社会说话。”
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赵丹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两天后,赵丹因为胰腺癌去世,享年65岁。他和黄宗英一生患难,却没能一起安享晚年。他生前最遗憾的,就是没能在有生之年饰演两个角色,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恩来。
2006年11月13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同文学艺术家谈心》的讲话,提到了赵丹的遗言。温家宝说:“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人们心中。”
“面对历史,我们都很释然。”多年后,这些影星的后人提起少年时代所受的恐惧和屈辱,都一笑置之。“我母亲几乎不会讲起仇恨和痛苦,有时候我问她谁谁谁演得如何,同代人她就点评几句,上一代人她都不说话的,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谈到上官云珠,妈妈说她‘台下马马虎虎,台上光彩照人。”赵左回忆。
“面向光明”
赵左说:“我的父母很平凡。”笔者表示不解,坐在一旁的魏迦解释,在孩子眼中父母就是父母,很少会去想他们是明星。日常生活中基本都是琐事,哪里会想到他们的作品。
“我父母这一代人,说白了也简单,就是那个奖杯上(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说的‘为人民讴歌,为时代立传。”母亲去世后,赵左下了这样一个判断。在告别仪式上,赵左以“始终面向光明”对母亲进行了盖棺定论。他说:“我妈妈是幸运的。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德高望重的师长的指导,兄长的提携,有亲如兄弟姐妹的同事的帮助,一生经历了几代人才有可能经历的人与事,过程中,有失败,有成就,始终面向光明。”
赵左记得父亲临终前只让自己陪着,怕自己形容枯槁吓到其他孩子。弥留之际,赵丹讲了一句话“阿左不要走”,这是让他学会有担当和责任;在送走患癌的弟弟和年迈的母亲时,他们几乎都对自己说了一模一样的话“阿左,你可以走了”,那是他们心疼自己,怕自己累着。走和不走之间,都是家人深沉的爱。“说起来,父亲当时不知道我打算出国的事,但这个‘不要走,我也觉得冥冥中在讲这个。”
如今,赵左一家生活在美国洛杉矶,兄弟姊妹们四散在世界各地,已很难聚齐。疫情期间,赵左是唯一陪在母亲身边的人。本来只是想陪母亲过年,一直就耽搁了下来。“也亏得我在上海,不然疫情之年,母亲去世不在身边,对我来说,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我们这代人几乎没有因为是名人之后得到父母的关照,因此我们很独立。”赵左少年时,父母都很忙,几个子女都是保姆带,“野生”成长的。父母既没有打骂过自己,也很少过问成绩之类的事。他还记得考小学的时候,老师问自己父母的职业,他张口说“开会的”,引得老师一阵笑声——开会是一个什么职业,这孩子莫不是有点傻? 但对于赵左来说,一年也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和父母相处,他们都各自在忙事业。后来,父亲在很多高校都有讲座,唯独不去北京电影学院,理由也很简单,小儿子赵劲在导演系读书。
赵丹和黄宗英的孩子们后来陆续出国,大部分定居海外,“我们当时出国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吃了很多苦,但因为父母的教导,我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迅速掌握,也都拿得下来……”赵左说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不太会讲中文了,“在美国,他们这样的ABC(美国生的华人)也基本上是在一起玩,白人圈子不太接纳的。”
面对父母生前所遭受的争议和是非,赵左沉默片刻之后说:“我父母始终都没有对我们讲起他们对过去的人和事有什么怨言。而那些争议,在历史里,看上去一点也不重要。”
上海人的“不响”(指沉默)在这一家人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赵左没听母亲讲过谁的坏话,母亲也不会干涉子女的任何选择。“后来我每年回来带她出去吃饭,老太太也一定要自己付钱的,你说说……”临终前,黄宗英望向门口,赵左觉得她在等小儿子出现。2013年,赵左的弟弟赵劲去世,他是黄宗英最疼爱的小儿子,家里人不敢告诉老太太,用各种方式隐瞒着。“我觉得她心里多少清楚,开始几年还问赵劲怎么不来看自己,后来也不问了。”赵左说。
赵左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他不喜欢上幼儿园,母亲就陪着他去。“那时候我们都是睡地铺的,午睡的时候她就坐在我旁边看书。我总是不想睡,就睁着眼睛看天,她就用手去捂我的眼睛。可我还是淘气,就硬睁着眼,非要去看外面。我是透过母亲的手指缝看到外面的整个世界的。”
“我在病房陪我妈妈的时候,她也常常睁着眼睛不睡,我说你睡呀,闭上眼睛打呼噜。她笑了,说闭上眼睛可以啊,打呼噜不是说打就打的,我于是就用手轻轻捂上她的眼睛。”说这些话的时候,赵左坐在上海常熟路一家本帮菜馆里,他就着一杯加冰的XO,眼圈红了。
几个小时的对话结束后,和赵左告别,他在微信里回复:“面向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