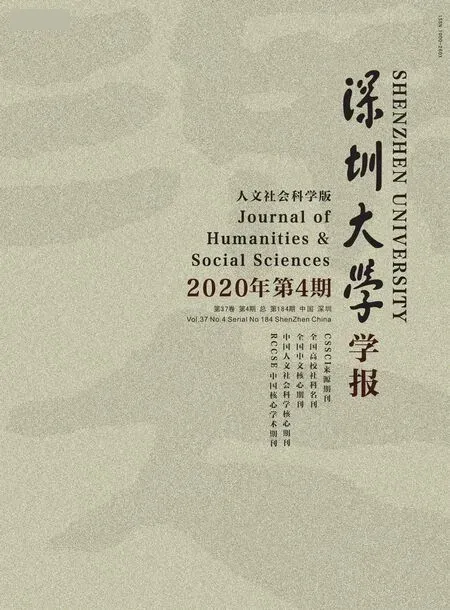幻体之幻与真:关于身心关系的思想实验
朱光亚
(1.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241;2.阳光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350015)
胡塞尔晚年在“C手稿”中探讨过身体构造学说,这一学说代表着“胡塞尔不再满足于对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身体的单纯描述,而是从先验现象学和单子论出发对身体的出现和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现象学说明”[1](P65)。这表明胡塞尔晚年非常关注身心关系问题,这是与其现象学哲学的前瞻性分不开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今天,“我们既可以看到以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概念为基础或受启发而出现的具身心理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政治学、身体符号学、女性主义身体学、身体美学等学科,也可以看到现象学对身体的研究成果为精神病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以及人工智能所借鉴或利用。”[1](P65)尤其是在为科学突破进行奠基的哲学学术前沿,诸如“缸中之脑”、“续命游戏”等思想实验早已逐步突破人文社科领域而进入自然科学领域,并不再局限于“心”对“身”的反思。基于此,我们将返回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思想实验,并借助当下哲学界最新的思维突破,以重新反思身心关系。
一、思想实验一:“庄周梦蝶”,基于梦境与现实之同一性的身心同一
在中国历史上,“庄周梦蝶”的思想实验最早讲到了身心关系。“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尔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2](P52)“庄周梦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确定你不在梦中?
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当我们处于梦中的时候,“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2](P46),当时的场景是如此的鲜活,甚至“梦之中又占其梦焉”[2](P46),以致于我们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然而,按照弗洛伊德的解析,“梦是一种受抑制的愿望经过伪装后的达成。”[3]也就是说,梦境是一种经过了伪装的现实而已,它只是对现实的折射。弗洛伊德用“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go)去分析梦境与现实的关系,在他看来,“本我”、“自我”和“超我”就是人的三重心理结构,“本我”是人天性的流露,处于“无意识”的阶段,这是人的心理层次中最深层的一个领域,其实质是“里比多”(libido,原意是性欲)。“里比多”遵循快乐的原则,强烈的寻求发泄与满足,不可遏止。“超我”是后天的养成,是在宗教、道德等社会意识的熏陶之下构成的“下意识”,也可以说是“潜意识”,它是一种盲目的是非感,通常将其称之为“良心”。“自我”则是人的“意识”,是一切感觉、知觉和理性思维的主体,是自觉活动的激发者,与现实世界直接联系。“超我”处于“本我”和“自我”之间,压抑并阻挠“本我”的欲望闯入“自我”的领域,这是因为“潜意识”处于“无意识”和“意识”之间,防止“无意识”的本能干扰“意识”的正常活动。这样,“无意识”的“本我”就常常受到压抑,当这种压抑得不到正常的释放之即,它就会以伪装的形式潜入意识系统,梦就产生了。弗洛伊德将梦境与现实分为从心理活动到现实世界的4个层次,从“心”到“身”逐步过渡,体现了“身”与“心”的同一。从梦的解析的意义上来说,“庄周梦蝶”既是梦境与现实的同一,也是“身”与“心”的同一,这从庄子对“梦蝶”的判断语——“此之谓物化”[2](P52)——中即可断言,所谓物化,即万物与我浑然同化,物我、人我无有差别。
《庄子·齐物论》的核心思想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P39),这是对“物化”的极致描写。在《齐物论》中,庄子论证了万事万物齐同为一,生死、寿夭、荣辱、贵贱、成毁无有差别。当然,“身”与“心”也无有差别,这在《齐物论》开篇就讲到了。“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2](P22)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南郭子綦靠着几案在静坐,仰着头慢慢的在呼吸,就像遗忘了自己的形体一样。他的弟子颜成子游在旁边侍立,问南郭子綦说:“为什么这样呢?人的形体固然可以静止如同枯木,难道人的心也可以如同死灰一样吗?”庄子的回答是:“吾丧我”[2](P22),意思是说,我自己把我自己丢掉了,本真的我忘记了社会关系中的我,心灵意义上的我忘记了身体意义上的我。在庄子看来,本真的我与社会关系中的我、心灵意义上的我与身体意义上的我是不可分的,因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2](P27)也就是说,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我,没有我,对立面也就丧失了意义。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亦近矣”,离“道”就近了。
“庄周梦蝶”是中国人审视身心关系的开端,确立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道家对待身心关系的基本路向。道家在先秦时代就主张“物化”与“吾丧我”,到了魏晋玄学,更是充分发挥了《齐物论》中的“神全形具而体与物冥”之思想而“独化于玄冥之境”。至于道家向道教转变之后,“老子骑青牛而出函谷关、羽化成仙”的传说,更是将宇宙发生论意义上的身心同一提升到了宗教信仰意义上“身”与“心”的合二为一。
二、思想实验二:“我思故我在”,基于“心智之于身体优先性”的身心对立
与“庄周梦蝶”相反,在西方哲学的发端,“身”与“心”是对立的。奥尔弗斯教派的灵魂观就持有一种身心对立的观点,到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更是以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方式正式确立了“身”与“心”的对立。在这里,关键是“认识你自己”的“自己”究竟为何物?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从智者学派而来的,其鲜明特征是反对自然哲学那种对“本原”的外向而求。苏格拉底本来对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则”寄予厚望,但后来他却说:“我往下看,发现这位哲学家完全不用心灵,也不把它当成安排事物的原则,而是求助于气、以太、水和其它稀奇古怪的东西。”[4]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拉底的“自己”首先决非“身体”意义上的自己,而是“心灵”意义上的自己,他要求“通过审视人自身的心灵的途径研究自然”,“认为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主张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再依照这些原则规定外部世界。”[5](P39-40)这样,他的“认识你自己”,首先是心灵的一种自我观照,在自我观照的基础上才达到外向而求。
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启了思维观照自身的哲学路径,这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形式说中都能找到其踪迹,但集中反映这个思想的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虽然与中国哲学有本质的区别,笛卡尔的思想却具有一种“庄周梦蝶”的意义,因为在他那里也是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的。在笛卡尔看来,外界世界是否存在非常可疑,我们对于身体活动的感觉也非常可疑。笛卡尔甚至声称,人们可以怀疑自己手脚和身体的存在,他的理由是:做出这样的怀疑在思想上并不产生矛盾。但是,笛卡尔所思与“庄周梦蝶”不同。“庄周梦蝶”代表了一种宇宙发生论意义上的身心同一,但笛卡尔在提出“怀疑一切”之际,他已经将自身的存在置之于被观测的位置,这是一种基于“心智之于身体优先性”的经典认识范式。后来,在胡塞尔的先验还原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笛卡尔身心对立的影子。胡塞尔并不否定和怀疑世界的存在,但他却使用悬搁“去中止任何经验信仰(Erfahrungsglauben),以致经验世界的存在对我来说始终是无效的”[6],这样,世界的存在,包括自身的存在,都变成了单纯的“存在现象(seinsphnomen)”。这种“存在现象”被“在世界中获得了自己的显现,有了自己的‘定位和时间’(Lokalisation und Temporalitt)”的作为单子的我所观照,“这样一来,我们便看到,‘我’的在此存在着的身体持续的是一个物体,不可放弃地、直接地为‘我’而在此,以合乎感知的方式直接当下,‘我’直接推动这个物体,直接将‘我’的因果性作用于它并通过它作用于外部世界以及与世界中的他人发生‘现实的’关系”[1](P66-67)。
无论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还是胡塞尔的先验还原,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存在的基石。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论证了“自我”的存在。他将“我思故我在”当作绝对可靠、牢不可破的真理,当作他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我”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它并不需要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便存在,也不依赖于任何物质性的东西。不言而喻,“自我”只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而“我思”包括一切意识活动,不管是理性、感性,还是情感、欲望,都是“我思”。更重要的是,“我思”是没有内容的纯粹活动,否则它就是可怀疑的。在笛卡尔看来,一切思想活动的核心就是对这些活动的反思,而思想的主体和反思的主体是同一个主体,主体就是实体,“我思”和“我在”的“我”是同一个实体;“故”表示两个实体之间的必然联系而非因果关系。
“对笛卡尔而言,身体与心智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因为物质的身体无法进入心智,而理性的心智也无法真正下降到身体。”[7](P73)他最终确立了“身心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而“身”与“心”的对立则造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内在的、‘主观的’视角,从我们对内在体验的知晓出发”,另一种是“外在的、‘客观的’视角,从对大脑的科学研究出发。”[8](P115)奥尔弗斯教派以来对身心关系的看法属于第一种视角,而当各门自然学科在哲学中完善成熟并逐渐从中脱离出来而导致哲学的虚无化之后,科学的发展却越来越反过来回答哲学的问题,逐渐出现了研究身心关系问题的第二种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心智之于身体的优先性”逐渐被“身体之于心智的优先性”所取代。
在第一种视角下,“我思故我在”用严密的逻辑证明了,“所有存在于外部世界里的东西,都只不过存在于心中。”[8](P57)然而,在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理论和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论围绕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达成“天赋观念”的共识之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洛克的观念完全可以以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存在,而知识根源于观念之间的同异、关联、并存和存在关系。休谟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怀疑论的解读,在他看来,所谓关系,无非是两种现象恒常结合在一起在人们头脑中引起的习惯性联想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笛卡尔的“我思”就成为一种梦呓,因为,“我思”的对象无非是观念,而观念本身仅仅是联想的结果,它根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根基。这一点也被胡塞尔敏锐地发现了,在他看来,如果心灵最终以物理之物为基础,而由于物理之物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因果关系,那么心灵也必然将受制于这种关系,但实际上,心灵之物的个体性和因果性完全不同于物理之物,因为,心灵之物没有广延,而物理之物不可能存在着动机引发,二者不存在一种奠基关系[9]。“我思”的崩溃也预示着世界的崩溃,“由于世界的存在需要‘预设’我的存在,所以,这一预设的失败实际上就宣告了世界的不存在”[10](P57)。
三、思想实验三:“缸中之脑”,基于“身体之于心智优先性”的身心隔离
究竟世界是否存在?我们似乎感知到眼耳口鼻舌五种感觉器官时时在进行世界存在信息的收集并输入给大脑,大脑也不断输出改变世界的指令。我们发现,世界的改变确实大体上符合我们对于指令的预期。然而,如果我们其实并不是世界中存在的一个个个体,而仅仅是“缸中之脑”呢?
1981年,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在他的《理性·真理与历史》(Reason、Truth and History)一书中,阐述了“缸中之脑”的假想:“一个人(你可以想象是你本人)被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施行了一种手术,他的脑被从身体上切了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缸里。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一台超级科学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能使脑的原有者产生一切情况完全正常的幻觉。对于他来说,似乎人们、物体、天空等等还存在。但实际上,这人(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由计算机向神经末稍输送电脉冲的结果。这台计算机的智力水平很高,如果这人想要抬起手来,计算机的反馈就会使他‘看到’并‘感到’自己的手举起来了。邪恶的科学家还能够通过改变计算机的程序,按照他的意志使实验品‘经历’任何境遇或环境。他还能让实验品丧失被施行过切下大脑手术的记忆,使它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就是处于这种境况。实验品甚至可以感到自己正坐在那里阅读描述这个有趣但十分荒唐的假设的文字:有一个邪恶的科学家,他把人们的脑从身体上切下来,放进一个盛有维持脑存活的营养液的大缸里……”[11]“缸中之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如何确保自己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
“缸中之脑”的设想源自于所谓“哲学家不能确证自身存在”的哲学丑闻,这个丑闻是专门指向怀疑论者的,在他们看来,感官会欺骗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和摸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真理可以区分为真正的表象和失真的表象”[12],建基于感知能力之上的知识大厦很可能是一场幻影。对他们来说,即便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能确保我们不处于这种困境之中,因为“我思”当然可以由计算机进行设定,而“我在”就很有可能是一种虚假的存在。这是所有用“心”来观照“物”(“身”)都不可避免的陷阱。在这里,“心智之于身体的优先性”被彻底抛弃,认知不再是“一种源于客观世界模型并基于抽象运算法则的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而逐渐转向“主体在身体—环境的动力耦合中涌现出来的具身行动能力”[7](P72)。
由于我们不能确定世界的存在,因此我们更不可能确定事物的性质,这是“心”对“身”的无力。“缸中之脑”告诉我们,人们的“身”与“心”是不可能同一的,它们之间存在不可翻越的藩篱,“身”与“心”的隔离会引发我们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对于一个人而言,“缸中之脑”的困境也许仅仅是一种个体的认知假设,但如果我们设想有一个巨大的计算场,使整个人类都处于“楚门的世界”①,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科学的发展已经侵蚀了哲学上人类生存合法性的根基。我们无法破除“缸中之脑”的迷障,因为人工智能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缸中之脑”。我们可以设想,当我们操纵人工智能之时,何尝没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超人类”在操纵着我们?当哲学家在担忧未来的人工智能失控之际,今天的人类会不会是“超人类”视域中一种已经失控了的智能?当人类无法认识世界之谜,从而寄希望于“上帝”这个第一推动力之际,人类自身会不会是人工智能的上帝?从人工智能到人类和上帝,是否存在着一种由高熵体向低熵体排列的顺序?
“缸中之脑”显然是我们观察身心关系问题的一种“外在的”、“客观的”视角,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普特南说:“倘若我是一个观察者,那么,在时间t我就会有两个‘将来的’自我。我每个将来的自我都会认为自己是惟一的,而其‘分支’则是‘整个世界’……这样就会有两个‘我’,一个体验着‘原子尚未蜕变的世界’,一个体验着‘原子已经蜕变的世界’。”[13]普特南的“两个我”显然分别代表了关于“心”的主观主义(心智优先于身体)和关于“身”的客观主义(身体优先于心智),无论是主观主义还是客观主义,哲学的丑闻都未能得到消解,我们也没有找到确立我们自身存在的根基。
四、思想实验四:《幻体:续命游戏》,基于具身性认知的身心突破
在前科学时代,主客观的分离是人们的认识活动得以展开的前提。那么在科学时代,一种基于科技无限发展基础之上的思想实验将带来一种对身心关系进行审视的新的视角。塔西姆·辛导演的电影《self/less》(中文名字《幻体:续命游戏》)显然映射了对身心关系进行思索的一种新的突破。在这部电影中,亿万富翁马丁·戴米恩饱受癌症折磨,不得不面对即将在半年后去世的事实。菲尼克斯生物科技公司声称使用最先进的蜕变技术可以帮助马丁重获新生,重生的方式是将他的意识或者灵魂注入一具更加年轻健康的躯体内再生。在接受蜕变技术以后,马丁尽情享受了重返青春的乐趣。然而,只要马丁停止用药,这副陌生躯体背后所隐藏的秘密就会让他感到不安,因为这副躯体是通过杀死(或者收购)一位名叫马克的陌生人的健康躯体而获得的,停止用药会让马丁重返马克的记忆。那么,这部电影的主角到底是马丁还是马克?进而引发了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或者更直接的说,究竟灵魂是自我呢,还是躯体是自我?电影的主人公因为是灵魂(“心”)与躯体(“身”)的组合体,引发了自我的一次次冲突与抉择。
灵魂具有独立性在中西方哲学中均得到过设想。在西方哲学中,早在奥尔弗斯教派那里,灵魂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生物都有共同的灵魂,灵魂是不朽的,可由一个身体转移到另一个身体。”[5](P16)到了毕达哥拉斯,他甚至认为灵魂能够在不同物种之间异体传递,他说:“灵魂是个不朽的东西,它可以转变为别种生物。”②在他那里,“身体就是灵魂的坟墓”③,躯体仅仅是灵魂的栖息地。在中国,灵魂在不同躯体间的异体传递早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就有记载:“子产适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孙,子耳之子,敝邑之卿,从政三世矣。……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后来,这种异体传递被道家称之为“夺舍”,又在藏传佛教中成为活佛转世的理论依据。
如果说,奥尔弗斯教派的灵魂观以及中国哲学中的“夺舍”只是一种先知式的猜测,那么今天,意识的异体传递似乎已得到现代科技的有限论证:如果我们还没有办法将灵魂(意识)注入某一躯体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将躯体拼接给灵魂(意识)。现代医学已经能够完成器官移植,近几年来,通过手术将大脑与身体拼接在一起的构想也被现代科学工作者屡屡提起。尤其是克隆技术产生以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破除伦理的束缚,人们进行躯体器官的再造与更换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未来如果医学科技真的发展到了《幻体:续命游戏》中的水平,那么,究竟什么才是马丁自己呢?是他的躯体?还是他的灵魂?抑或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我们似乎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一种具身现象学的意义上,身心关系似乎正在突破边界而趋向同一。梅洛-庞蒂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消除意识与存在的对立。在他看来,身体既是存在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又是被作用的客体和被认识的对象,他将这样的身体称之为“身体-主体”。在这样一个概念中,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又是被显现的对象,既是存在着、经验着的现象,又是现象的场所。梅洛-庞蒂说,当我们用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的时候,每一次触摸都是身体向自身的一次显示,虽然一只手触摸,另一只手被触摸,但是身体的感觉却是触摸和被触摸混沌不可分、内在和外在彼此交融,这正是“身体-主体”的意义所在。
梅洛-庞蒂将“身体-主体”赋予广泛的本体论意义,把世界的基质说成是有生命的肉体(flesh),这其实源自于胡塞尔的“单子共同体”对高阶“身体”的构造,“在单子共同体中存在着不同于个体单子且高于个体单子的新的身体意向,对这种意向的‘放松’或‘充盈’必然由一种新型的身体来实现。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身体呢?其实,每一个共同体就是一个身体。”[1](P73)当然,世界是最大的一个共同体,也是最大的身体。显然,这样的世界就成为身体意义上的知觉世界,它源自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梅洛-庞蒂将生活世界等同于人的意识的背景,将其看成“身体-主体”向身体以外空间的拓展。他说,身体不像其它事物那样在空间之中,它既非在空间之内,又非在空间之外包围空间,身体之于空间如同手伸向工具一样。“身体-主体”的这种延伸就是知觉,知觉是“身体-主体”与世界的对话而非认知行为。在知觉中,世界不是意识的对应物,而是“身体-主体”的对应物。那么,“身体-主体”的外在化就成为世界的肉身化,即知觉既是对外物的直接接触,又是世界的内在化,即外物向知觉的显现。在这一互为表里的过程中,世界既不被给予,也不被创造;既不是完全主动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一个画家面对他作画的对象森林之时,知觉使其身临其境,他看着树木,树木也好像看着他。这说明,在知觉中,“身体-主体”与世界彼此开放,没有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心灵与形体之间的对立。这样,那种经过了先验还原的处于“原模态的当下”(urmodale Gegenwart)或“原活当下”的“世界联同身体一起成为现象,成为‘效应形象’……成为先验意识的各种行为可以直接在其上发挥效应的存在。 ”[1](P68)
五、思想实验五:“忒修斯之船”,基于科技无限发展基础上的身心同一是否可能
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描述了身体的显现,这一描述似乎为身心关系的突破开辟了新的可能。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幻体意义上的“身”与“心”的“联接”(verbunden)似乎不再是难题,然而,这个突破本身却成为一个问题:“身”与“心”在何种意义上算得上同一?在同一的意义上,我们所讲的“身”还是原来的“身”吗?在前技术时代,“身”的意义是确定的,“身体的出现过程是这样的:先有物理化学个体,通过相互作用逐渐变成越来越复杂的个体直至最低等的生物,而后展开从低等生物向高等生物和人的发展,最终出现了心灵以及由心灵和物理之物组成的身体。”[1](P68)然而,这一切在技术时代好像都发生变化了,在人们失却“心灵之广延”与“躯体之动机引发”之间的联接之后,人们拥有了对身体的另一种视角,组成我们身体的单子化了的器官好像是一个一个的零件,哪个零件坏掉了,我们就换掉哪个零件?现在的问题是:换掉了零件的身体,还是原来的身体吗?
逻辑学中有一个“忒修斯之船”问题,“设想有一艘船,因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忒修斯曾经驾驶它建功立业,我们就叫它忒修斯之船,它停泊在港口。为了简化问题,我们令这艘船没有复杂的结构,完全由一块块木板拼装而成,拼装过程类似于搭积木。当发现其中的任何一块可能不再适用时,我们就用同规格的木板替换它。时间一长,所有的木板将会替换完毕。”[14]试问,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与此等同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经过拼装后的身体,还是原来的身体吗?
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所有的木板替换完毕以后,假如将时间的流逝加速推进,我们分明就会看到,这相当于模仿原来的船A又重建了一艘船B,A明显不等于B。再则,如果假设被替换掉的木板仍然可用,我们就能够利用它们再造一艘船,这相当于将原来的船拆卸掉又变换了一个地点进行复原,那么,此时,究竟谁是原船忒修斯号呢?
我们再看对这个问题否定的回答,部分学本质主义者就持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物体的任一部分对于该物而言都是本质性的,失去则不复为该物。”[15]那么,部分学本质主义者的主张就会衍生下列问题:修补后的这艘船B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等于船A的。一艘船在航行的过程中不免会修修补补,难道只要经历了修补,这艘船就不再是原来的那艘船了吗?这显然违背常识。一种可能的界定是中间数据50%,即当船A修补超过了50%,船A不等于船B;当船A修补没有超过50%,船A等于船B。那么,假设现在是第二种情况,船A等于船B,现在看船B,我们在它维修49%的这个时间节点开始计算,经历一段时间后,船B又开始维修,维修到船B的49%这个时间节点,得到了船B′,按照刚才设定的逻辑,船B等于船B′。由于船A等于船B,船B等于船B′,我们就得出结论:船A等于船B′。但事实上,船B′相对于船A,维修比例显然已超过了50%。所以,关于50%的中间设定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身体拼装后“我”之定位的思考,也是迷茫的。
“我”是谁?在哲学史上,“我们不能单独地谈到我而不谈到别的东西。当我们像寻找经验世界中的其它东西一样,去寻找我时,我无处可寻。”[10](P56)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可以消除的。”[10](P56)然而,“我”的无处可寻跟直觉强烈冲突,因而我们不得不“将我说成世界的边界”,这“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我无所不在……一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我无处可寻。”[10](P56)然而这样的解释好像在强烈暗示,“无所不在”的“我”只是指我的躯体,设若如此,“‘我的躯体’中的‘我’,也就无法消除了。”[10](P58)“如果‘我’不能消除”[10](P56),那么,“我是什么?”“一个极为自然的回答是,我就是使用‘我’的人。”[10](P59)这样,对“我”的讨论又再次回到了笛卡尔的立场。
事实上,具身认知对身心关系的思考根本就没有解决笛卡尔以来人类关于“缸中之脑”的焦虑,这一点维特根斯坦早就告诉过我们:妄图对传统身心关系问题进行解决,根本就毫无意义,它不能经过经验和理性的确证,只能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我”在哪里?现代科技已经告诉我们,它和忒修斯之船一样,因为处于无限的变动之中,根本就无法定义,而身心关系不可避免所涉及的指称定义也并无意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指称无法确证,所以并不能直接明白地传递含义。不仅如此,对于同一个人而言,我们不仅无法传达一段特殊的心理感受“S”,甚至无法对比类似的再一次特殊心理感受“S′”。因为,如果要对比两段不同的心理感受“S”和“S′”,我们将不得不借助主观感觉的工具。然而每个人都可以有心理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感觉,但却无法判断自己的心理活动或者感觉与他人的心理活动或者感觉是否有某些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进入他人的心灵。说存在某种心理活动或者感觉是无意义的,这仿佛又回到了哲学的丑闻,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只是根据他人的外在行为判断他人的话语,而对这些话语所涉及的心理内容则无须加以深究。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对这个问题的回避。正因为如此,“试图通过自然实在与虚拟实在在经验层次的不可分辨性来支持实在论的崩溃这个结论”[16](P43)并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任何借助于人的技术或者其它原因带来的强幻觉来否定物质实体实在论的做法”[16](P39)都毫无意义。这样的话,也许我们苦苦追问何谓“身”?“我”是谁?也将毫无意义。
注:
①《楚门的世界》是派拉蒙影业公司于1998年出品的一部电影,主角楚门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平凡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忽然发觉自己似乎一直在被人跟踪,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楚门决定逃离他生活了30多年的地方,但他发现自己怎样也逃不出去。真相其实很残忍,从楚门呱呱坠地开始的30年来,他就是一部肥皂剧的主角,他居住的海景镇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摄影棚,而他的亲朋好友和他每天碰到的人全都是职业演员,他生命中的一举一动、每分每秒都暴露在隐藏于各处的摄影镜头面前,全球上亿观众都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而他就像是活在玻璃罐里的蝴蝶。
②(英)康福德:《从宗教到哲学》,第201页。转引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9.
③伯奈特:《早期希腊哲学》,第108页。转引自(英)罗素.西方哲学史[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