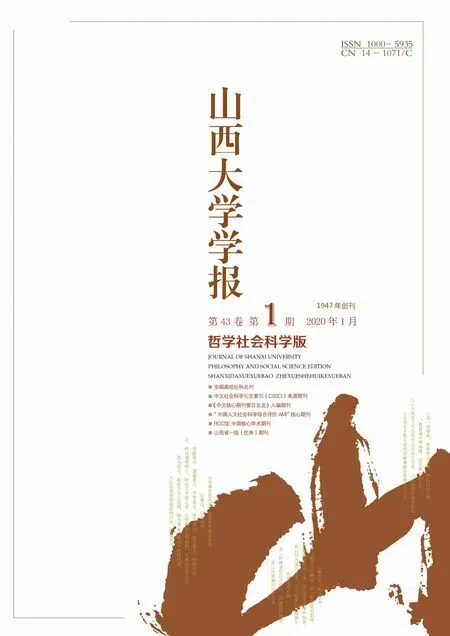陈运彰词学综论
刘宏辉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陈运彰(1905—1955),字君谟,又字蒙庵(也署蒙厂、蒙父等),号华西、证常等,室名有纫芳簃、华西阁等,原籍广东潮阳,生长于上海。南社成员,曾任之江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等校教授,与易孺、詹安泰、陈乃乾、夏承焘、汪东等词学名家交游,工诗词书画,篆刻亦精。陈运彰师出词学名门,不仅是填词名家,也是词论家,词籍校勘更是卓有成就。目前学界已整理他的《双白龛词话》《纫芳簃说词》(1)张璋主编《历代词话》(大象出版社,2002年)已收录有陈运彰《双白龛词话》;杨传庆、和希林辑校《辑校民国词话三十种》(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收录陈运彰《双白龛词话》《纫芳簃说词》。,其批校的《炊闻词》也得到关注[1]。然而作为词坛名流,陈运彰流传于世的论词资料还有不少,如《纫芳宧读词记》[2],批校本《宋元名家词》(2)陈运彰批校《宋元名家词》共有两种:张埜《古山乐府》、倪瓒《云林词》,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等,尤其是陈运彰去世前一年详细批校的《古山乐府》保留有大量论词文字,且多有总结之语,最能体现他的词籍校勘理念,价值极高,惜未见论者。本文以陈运彰词学文献为基础,尤其注重新见之词学资料,从弘扬师法、词学批评、词律思想、校勘原则等方面综合探讨其词学理论主张。
一 弘扬师法:词学研究的立足点
陈运彰为晚清词学大家况周颐的入室弟子。况氏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毕生致力于词学,成就极高。陈运彰追随其师脚步,既留意况氏词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又注重词学理论的引用阐释,在多个层面承继况氏之说。
况周颐词学论著极为丰富,除了著名的《蕙风词话》外,还有不少发表于报纸期刊的论词之语,如《玉梅词话》《餐樱庑词话》等,此外还有许多况氏生前未曾刊行的论著。况氏去世后,龙榆生、唐圭璋等词学大家都留意其遗著的整理发表(3)如龙榆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创刊号载有况周颐《词学讲义》(龙沐勋.词学季刊:创刊号[J].上海:民智书局,1933:107-112)、唐圭璋编成《蕙风词话续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4529-4584)等。,而陈运彰更是注重其师词学文献的搜集整理。如他在论及朱祖谋编《宋词三百首》曾与况周颐斟酌讨论后,继而云:“先师亦有十四家词之选,其目为:温飞卿、李后主、晏同叔、晏叔原、欧阳永叔、苏子瞻、柳耆卿、周美成、李易安、辛幼安、姜尧章、吴君特、刘会孟、元裕之。又备选三家:冯正中、秦少游、贺方回。惜其稿已佚。异日当重为写定,以为《词莂》之先。”[3]310在书稿已佚的情况下,仍能记清选目、拟“重为写定”,由此可见陈氏对其师论著颇为熟悉。又如况氏生前未刊稿《玉栖述雅》即由陈氏传录、整理发表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第六期,陈氏跋语云:
《玉栖述雅》一卷,临桂况先生未刊遗著之一。……先生于国变后,遁迹沪上,以文字给薪米,境啬弥甘,不废纂述。夙昔文字及身刊行者,毋烦赘说;遗稿藏家,幸未失坠。或俟编订,或从删汰,整比理董,时犹有待。惧违素志,未敢率尔。……传录是本,藏之有年。比者《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征及先生遗著,因以授之。扬潜阐幽,有炜彤管,固先生本旨也。[4]120
况周颐晚年隐居沪上,以文字谋生,笔耕不辍,况氏去世后还有很多遗稿尚未整理。陈运彰庆幸其师遗稿尚未坠失,有编订董理的想法,只是尚未实行。从他抄录、珍藏《玉栖述雅》可以看出他对其师论著的珍视,而“扬潜阐幽”则是他弘扬师法的立足点。
在陈运彰所撰词话中,有多处称引况氏论词之语并加以阐发的。如在指示填词门径方面,陈氏云:“囊(曩)侍临桂先生坐。一日,先生忽诏予曰:‘欲作词,须读古人词五千首,然后下笔。’当时未尝不惊怖其言,若河汉也。由今思之,始忱然而叹曰:‘嗟乎!此先生不惜心法传授者,政复在此。差幸不误落尘网中,端赖受此当头一棒。’试问:从古至今,何曾有五千首可供我读之佳词?即读得五千首佳词,又有何用?默察世趋,则此五千首之说,尚嫌其少。何则?不如是,不足以别白是非也。‘读千赋然后能赋’与‘说法四十年,未曾道着一字’同一义理。要悟到此境,方合分际。”[3]308-309陈运彰回忆先师指导作词的寥寥数语,经过多年的揣摩,方悟得其师心法,于是加以扬潜阐幽,点出真谛。
另外,陈运彰还常借鉴况氏词论作为自己立论的参照。况氏对历代词人均有精辟的论述,而陈运彰以论清词居多,借鉴论词成为陈氏阐释词学观的重要方法。如引《蕙风词话》“北宋人手高眼低”之论,进而云:“清代词人乃反是,其流传论词之语,议论之精辟,乃有夐绝古人者,怠其自为之,乃多不践其言,不仅为眼高手低已也。是以读宋人论词语,当别白是非,读清人说词,尤当知其蔽。”[3]305这是在肯定其师词学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成为自己论清人词论与填词的参照。
需要指出的是,陈运彰提倡填词之“厚彀秀重拙大”,实际上也是弘扬况周颐最核心的词学理念“重拙大”。陈氏云:“半塘论词,以‘重拙大’三字为揭櫫,乃人人所习闻者,此‘厚彀秀’三字,则知者鲜矣。尝谓能‘厚彀秀’,始能达‘重拙大’之境,此固互相表里,亦填词之六字真言也。”[3]307这里虽然将“重拙大”视为王鹏运(半塘)的词论,实际上是因为陈氏知悉其师况周颐的“重拙大”理念源于王鹏运。况氏曾回忆学词经历云:“戊子入都后,获睹古今名作,复就正子畴、鹤巢、幼遐三前辈,寝馈其间者五年。”[5]532又云:“己丑薄游京师,与半塘共晨夕。半塘于词夙尚体格,于余词多所规诫。又以所刻宋元人词属为斟酬,余自是得窥词学门径。所谓‘重拙大’,所谓自然从追琢中出,积心领神会之,而体格为之一变。”[5]534-535其实“重拙大”理念于端木埰(子畴)、许玉瑑(鹤巢)已初显端倪,王鹏运集为一说,况周颐始畅其旨。[6]况氏能成为集大成者,正是源于与以上诸人的切磋。陈运彰提倡“六字真言”,经“厚彀秀”达“重拙大”,况氏倡导的“重拙大”才是终极之境。
二 自然流露:词学批评的核心理念
陈运彰所处的民国词坛上承晚清,仍然笼罩在常州词派的影响之下。由晚清入民国的词学家,如晚清四大家中的况周颐、朱祖谋、郑文焯,都受常州词派思想的影响。陈运彰词学承况周颐而来,但他不只是弘扬师说,而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形成自己的词学批评理念。
继承常州词派的词学主旨,这是晚清民国词坛的总体风气,陈运彰也同样受常州词派的影响,陈水云指出:“作为况周颐的入室弟子,陈运彰、赵尊岳论词亦贵于寄托。”[7]285常州词派自张惠言《词选序》标举“意内言外”,强调“比兴寄托”,此后,寄托说成为常州词派的标志性论词范畴。由于“词体宜于表现寄托,词之写作当以情物交感为主,词之解说可以有别具会心的领悟”[8]350,即词本身的体性、词的解说都在很大程度上契合比兴寄托之说,加上晚清民国内忧外患、词人忧国忧民,使得寄托之说大行其道。晚清四大家之外,谭献、陈廷焯、吴梅、詹安泰、夏承焘、龙榆生等词学家都承袭比兴寄托之意。而陈运彰“尝问津于晴皋沤尹”[9]668,与詹安泰、夏承焘等人又有密切交往[10],因此也自然受到寄托说的影响。如他评论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诸名家词集后》云:“以屈、王二家冠首,题屈集云:‘湘真老,断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峤,江南哀怨总难平。愁绝庾兰成。’王集云:‘苍梧恨,竹泪已平沉。万古湘灵闻乐地,云山韶濩入凄音。字字楚骚心。’此则身世之感,后先同揆,故知有所托而言者。”[11]317陈运彰认为朱祖谋以屈大均、王夫之作为《望江南》组词之首,既因为屈、王二家词寄托遥深,有“哀怨”“楚骚”之心,也因为朱祖谋在题词中寄托了异代同悲的遗民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陈运彰虽然也讲寄托,但他却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分强调寄托,尤其是解读词不宜牵强比附,他说:“自有寄托之说兴,诗词遂成隐谜。”[3]307又说:“侈言寄托,皮傅骚雅,适成其猜谜射覆也。难测其意所寓,此近代词之一劫。”[11]318民国词坛有不少词学家注意到专尚寄托的弊病,与陈运彰交往颇深的詹安泰就指出:“论词之不能蔑视寄托,斯固然矣。然一意以寄托说词,而不考明本事,则易失之穿凿附会。”[12]72在寄托说应把握的限度方面,陈运彰与詹安泰是同声同气的。
注意到寄托说在词坛的巨大影响,在了解其弊病之后,陈运彰在论词文字中有意地淡化寄托说,而将“自然流露”置于核心位置。陈氏论词强调自然流露也可说是承袭其师况周颐,但他又有突破,形成了自己的论词理念。况周颐在论寄托时,已经强调自然流露,他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于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13]4526况氏强调寄托要自然流露,不能刻意,否则“横亘一寄托于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则是门面语耳,略无变化之陈言耳”[13]4526。况氏更重视寄托的表现方式是否自然出之,而陈运彰已经将论词重点转到情感的自然流露层面上,寄托并非他关注的重心。
考察陈运彰自然流露说对况氏词论的突破,我们可以从民国词坛一股现代词学风气入手。以王国维、胡适为代表的新派词学影响渐大,两人身份虽有极大不同,但在词学理念上,两人“竟有出人意(料之)外之如许相同处”(4)关于王国维与胡适二人词学之比较,可参见任访秋《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中法大学月刊》,1935年第7卷第3期,第107-120页)、曹辛华《王国维与胡适词学观异同辨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第117-121页)、彭玉平《王国维与胡适:回归古典与文学革命》(《复旦学报》2013年第5期,第47-54页)等文。。两人在强调语言的自然、感情的真切方面,具有很大的共通性。王国维、胡适的词学在民国中后期词坛掀起了一股现代词学之风,无论新派旧派词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二人的影响。陈运彰自然受到影响,他推崇的自然流露,强调的是真情实景以自然之语出之,他说:“语益浅近,而愈觉其深厚,景至平庸,而不碍其韶秀。要本出之自然,不假雕琢,斯为得之。”[3]307只要诗词出自自然,不假雕琢,则其语言之浅俗、景物之平庸都无伤大雅。他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流传千古,就因为“情弥真切”[3]307。语言方面则勿追求新奇,要归醇厚,“虽庸言常景,自然惊心动魄,本不暇以文藻之为妆点也。第一须避俗,俗不在字面,而在乎气骨”[3]308。陈运彰心目中最好的词是自然流露的,“有一种词,纯以天分性灵出之,好在无意求工,自然流露天真”[3]313。由此可以看出,陈运彰吸收新派论词理念,突破了其师论词的界限。
与自然流露相对的则是雕琢求新、堆砌典故,而这两种词风都是陈运彰严厉批判的。如他评尤侗《西江月·咏新嫁娘》句“昨宵犹是女孩儿,今日居然娘子”云:“此等句,看似新颖,实则浅俗,一中其病,将终身不克自拔。”[3]308刻意求新,反成浅俗。尤侗曾批判清初词风浅俗之弊云:“近日词家,爱写闺襜,易流狎昵。归扬湖海,动涉叫嚣,二者交病。”[3]308陈运彰感慨尤侗能言中时弊,作词却不免浅俗,可谓“眼高手低”。陈运彰批校过王士禄《炊闻词》,对《点绛唇·闺情》一阕用“嬲”字,他评道:“《四库全书提要》尝讥其‘失之雕琢,过于求奇之病,非词家本色。’此虽非笃论,然过于求奇之病,当知所戒。”[3]313陈氏虽言四库馆臣的批评“非笃论”,但反对雕琢求奇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词用僻典,致使语言生涩难懂,这也与自然流露大异其趣。陈运彰批判赵执信《减字木兰花》、李良年《解连环》说:“清初词家为词,喜掉书袋,援引僻典,上及经子,非自注不能明,其实与词之工拙无关也。即如赵词之用《诗疏》,李词之引《孝经纬》,细按之,究亦未当,抑且色泽不侔。自注之,则味同嚼蜡。不注,则人莫知所谓。好奇之过,知所勉夫!”[3]312由此可知,好奇而致雕琢,好奇而用僻字、僻典,这都是与陈运彰自然流露的论词理念格格不入的。
三 严守韵律:词律理论的主要倾向
张尔田在《彊村遗书序》中将守律、审音、尊体、校勘并称为清代词学四盛,守律之学以清初万树为代表,因此在四盛之中历时最久。民国时期,传统词律学仍得以延续,守律是许多词学家的共同主张。陈运彰承袭传统词学之路,严守韵律是他的词学主张,更是他词律理论的主要特点(5)有学者认为陈运彰词律观偏于“对破弃音律的强调”(胡建次.民国以降对传统协律之论的修正[M]∥胡晓明.古典诗文的经纬——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四十七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405-406)从陈氏词话及批校的词集评语来看,他还是以强调守律之论为主。。
词本是合乐歌唱的文学,但到了元代以后,词与音乐逐渐分离,词由原来的“倚声而歌”变成“按谱填词”。词体与音乐的关系决定了词的语言在格律、用韵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万树在《词律序》中指出:“诗余乃剧本之先声,昔日入伶工之歌板,如耆卿标明于分调,诚斋垂法于择腔,尧章自注鬲指之声,君特致辨煞尾之字。当时或随宫造格、创制于前,或遵调填音、因仍于后。其腔之疾徐长短,字之平仄阴阳,守一定而不移。”[14]8可见虽然词之音乐唱法已失传,但音调、字格都有一定的规则。清代的各个词学流派大抵都强调词体的韵律,词学家甚至依律校词,如朱彝尊《词综》就有依律改词的现象。清季的吴中词派,更是以声律论而驰名,晚清四大家也强调词律的重要性。到了民国,强调守律的词学观受到不小的冲击,尤其是新派词学家强调词的思想内容,主张解放词体,除去词律的束缚,给予词更自由的表达空间。陈运彰虽然受到新派词学的影响,对旧谱之说持怀疑态度,但却主张要严守韵律。他论道:
草窗西湖十景词,自序云:“西湖十景,尚矣。张成子尝赋《应天长》十阕,夸余曰:‘是古今词家,未能道者。’余时年少气锐,谓:‘此人间景,余与子皆人间人,子能道,余顾不能道耶?’冥搜六日而词成。成子惊赏敏妙,许放出一头地。异时,霞翁见之,曰:‘语丽矣,如律未协何?’遂相与订正,阅数月而定。是知词不难作,而难于改;语不难工,而难于协。翁往矣,赏音寂然。姑述其概,以寄余怀云。”按:填词协律之说,百年来,学者精研探讨,各有创获。旧谱既亡,亦徒具其说而已。观草窗十词,试比勘其音节句法,能得其与霞翁数阅月相与订正之苦心否?即此可知南宋时,乐律已不能具守。易安所谓“句读不葺之诗”,霞翁删削当时“官谱”诸曲以为“繁声”者,则谨守古词遗谱,亦当慎所抉择。畏守律,则古调放失,辄便自恣;与泥古法,而穿凿附会,有乖雅音,其弊适相等。宁失之拘,毋失之放,亦或折衷之一道。[3]309,[11]318
《双白龛词话》《纫芳簃说词》中都收录了这段论述,可见这是陈运彰的得意之论。这段话一方面怀疑守律之说的依据,认为南宋时旧谱已经失传,后世的守律之论有些流于穿凿附会;但他又强调要遵守古调,不能恣意破弃音律,要“宁失之拘,毋失之放”。可见在守律与除去音律束缚之间,他仍是强调守律之论的。
陈运彰精通韵律,这是他守律之论的前提。对于宋词中的一些不协音之处,他也敢于提出异议:
仇山村称张玉田词“律吕协洽,当与白石老仙相鼓吹”。然《山中白云》,用韵至为泛滥,真、文、庚、青,阑入侵、寻;元、寒、删、先,杂用覃、临。句中于双声叠字,亦有安之未洽者,读之顿觉戾喉棘舌,如《新雁过妆楼·赋菊》云:“瘦碧飘萧摇梗,腻黄秀野发霜枝。”飘、萧、摇三字连用,政恐未易上口。惟用入声韵,则又极为谨严:屋、沃,不混入觉、药;质、陌,不混入月、屑,极为可法。[3]308
玉田即张炎,南宋著名词人,填词成就极高,且精通音律,著有《词源》。清代浙西词派颇推重玉田词,有“家白石而户玉田”的说法。陈运彰能对玉田词的用韵以及字词的音律提出质疑,可见他在音律方面的造诣。对入声韵的关注,也体现出他对传统词学韵律的重视。词中入声韵的独特用法宋人已有关注,李清照在《词论》云:“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15]195可知即使同为仄声韵,上声与入声又有区别。此后,宋代沈义父《乐府指迷》,直到清代万树《词律》,对入声韵都较为关注。而清季吴中词派,对入声韵要求尤其严格,如杜文澜、勒方锜、潘锺瑞批校《鸥梦词》,凡词调宜用入声韵处皆一一指出。[16]陈运彰注意到历代词论中对入声韵的重视,也自然能察觉到张炎词中入声韵的谨严。
入声韵之外,陈运彰同样注意到入声字在词中的特殊作用,他论道:“入声字在词中,用之得当,声情激越,最是振起其调。此惟美成、尧章两家,独擅其胜。盖出天成自然之音节,有定法,即非有定法。当验诸唇吻齿牙之间。不能泥守一字一声,锲舟守株以求之也。昧者为之,步趋不失,而未有不捩喉棘舌者。”[3]310陈运彰对入声要求极高,仅精通音律者如周邦彦、姜夔才最擅长。
以上所引陈运彰数则论词文字,或“比勘其音节句法”,或“顿觉戾喉棘舌”“恐未易上口”,或“验诸唇吻齿牙之间”,由此可见他的严守韵律之论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精通音律的坚实基础的,他所叹赏的也是严守音律的优美之作。
四 多闻存异:词籍校勘的基本原则
晚清民国的词籍校勘之学蔚然成风,很多词学大家都孜孜从事词籍校勘。如王鹏运与许玉瑑、况周颐等校刻《四印斋所刻词》,成为词籍校勘精审之代表;又与朱祖谋校勘《梦窗词》,议定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等词籍校勘义例,词籍校勘之学得以确立。陈运彰承袭词籍校勘之风,批校多种词籍,取得了较高的校勘业绩,然而学界关注不足。(6)如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岳麓书社,2012年)未论述陈运彰词籍校勘业绩。今依时间先后,先将陈氏校勘之词籍略作梳理:
壬申(1932)、庚辰(1940),《莲社词(道情鼓子词附)》,各一卷。
庚辰(1940),《天游词》。
庚辰(1940),《东海渔歌》。
庚辰(1940),《词林书目》。(以上据陈运彰《纫芳读词记》)
壬辰(1952)、癸巳(1953),《炊闻词》。(据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藏陈运彰批校本)
壬辰(1952)、甲午(1954),《古山乐府》。
甲午(1954),《云林词》。(以上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陈运彰批校本)
陈运彰批校之词籍当不止于此,但据以上词籍的批校可知他在校勘词籍上用力颇勤。从他校词实践中也可以发现其校词理念也颇有创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广求异本,同时也注重各总集、别集、选本、词话中的异文,最大限度地参校各本。陈运彰文艺双馨,与词学名家、藏书家有着广泛的交游,往往能得珍稀之本。如倪瓒《云林词》末尾注云:“甲午二月初三夕,以吴文恪《百家词》本《云林乐府》校。吴本章次与此异,并注调下。彰。”又注:“甲午四月十二日,从载如叚万历本《倪云林先生诗集》本校一过,诗凡六卷,乐府廿六首。”[17]倪瓒《云林词》版本并不多见,明清七大词籍丛刊仅见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江标《宋元名家词》,而江本从况周颐而来[18]。两本之外,陈氏能参校万历本《倪云林先生诗集》,可以说是弥足珍贵的。
版本搜求非一时一地能够完成,因此常有数年反复批校一部词籍的情况。如陈运彰从抄录到校勘《莲社词(道情鼓子词附)》历时八年。其跋语云:“辛未岁,彊翁谢世,藏书间有散出者。越岁正月于友人斋头见之,假归一夕,遽还之。仅及此种,惜未尽其余。”[2]2可见陈氏在壬申(1932)曾校勘此词籍,至“庚辰三月”,又参校劳巽卿校本、吴兔床钞本。有时陈运彰因后见异本而叹前校之失,如批注《古山乐府》云:
予校此本毕,特与吴眉文共商订之。顷从眉文叚得林勉之重刊明吴文恪编写《百家词》本。因并携此册归,对勘一过,旧所校文,颇多脱漏,略为补之,且为更订一二事,以见曩时之草率,亦知扫落叶之喻为不诬也。甲午二月初五夕,碧双楼与梦秋翁及贞白谈词归后补录,校通卷竟。彰。[17]
由此可见陈运彰与吴眉文、汪东(梦秋翁)、吕贞白等亦有交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仍醉心词艺。而得新版本又再校一过,可见他校勘词籍的细致。
另一方面,陈运彰在校勘词籍时,非常注重保留原文,他曾总结说“未经意改处为可贵”[17]。因此他往往以眉批出校记的形式加以比勘,而不更改原文。如《云林词》中《踏莎行》一阕,眉批云“‘东风’吴本作‘西风’,‘陶朱’作‘颜朱’;万历本‘东风’作‘西风’,‘萋’作‘凄’”,等等。
对于一些错误的字词,陈运彰往往尽力考查致误之由,并指出正确的字词,努力完成校勘学“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19]148的任务。如批《古山乐府》云:
《清平乐·和李御史春寒》“小桃犹指霜痕”。《水龙吟·戊午春咏杏花》“上林桃李寒犹”,缺一字,《历代诗余》作“紧”。朱刻知圣道斋明钞二卷本“指”字、字并作“掯”。“掯”,俗字,不见字书韵书,其音读若“墾”。先临桂师引“小桃”句入《蕙风词话》,既释其义,又谓“掯”字入词仅见,亟赏之也。今按此本《清平乐》“犹指霜痕”,“指”字不辞,明是形近致误。《水龙吟》“寒犹紧”则趁韵补字,以此字不经见之故。此二字朱本之最佳者也。[17]
陈运彰指出了《宋元名家词》本因“形近”、《历代诗余》因“趁韵补字”而致误,并引况周颐之语,指出朱祖谋《彊村丛书》本为最佳。但即使如此,他在校勘时,并未更改原文,只在《清平乐》眉批云:“况先生曰:‘掯’犹言不放也。与‘余寒犹勒一分花’之‘勒’略同。‘掯’字入词仅见。运彰按:本集《水龙(吟)·戊午春咏杏花》次句‘上林桃李寒犹掯’,是古山喜用词字。”在《水龙吟》眉批云:“朱本‘□’作‘掯’……《历代诗余》‘犹□’作‘犹紧’。”[17]
值得注意的是,陈运彰注意到校刻词籍的种种弊病,尤其对更改原文而不加按语的校勘方法提出了批评。如他在《古山乐府》初校跋语中云:
《古山乐府》著于录者旧皆二卷本,其移并为一盖始于汲古毛氏,以其所刻所钞它家词。按之厥例至多。侯本不言所从出,实亦汲古阁本也。朱刻知圣道斋明钞本足资补缺,然不免有后人就词义以意增改处。细勘各本异同可见也。古微丈刻《彊村丛书》,所校多善本,而得本即校,不惮再三剜改,用力至勤,唯往往不加按语,致尽失原来面目,是亦一弊。丁氏《八千卷楼书目》卷二十集部词曲类《古山藏本乐府》一卷,元张埜撰,《名家词》本,即侯刻也。“藏本”二字疑衍。壬辰闰五月廿六日。蒙父。[17]
这则跋语指出了《古山乐府》的版本源流,批评了《彊村丛书》校改文字不出按语的弊病。由此可见陈运彰的词籍校勘是与版本之学紧密结合的,同时他也注意保留原文,以求其真。他复校《古山乐府》跋云:“金氏《栗香室丛书》重刻侯本,虽不精,尚能存其真面,于其讹夺,但加校语,此例最善者也。”由此可见,保留原本面貌是陈氏校词的高标。
“依韵改字”是明清及近代词籍传抄、刊刻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常有臆改之处,且往往不加按语,这与陈运彰校词高标相距甚远,因此陈氏在校勘词籍时,对韵字格外细致。由于他广求异本、注重版本源流,又精通音律,故能梳理出韵字异文之源流,常有精到的校词意见,得出令人信服的校勘结论。如“《蓦山溪》‘玉纤分露’,‘露’与‘里’叶,此两韵通叶之例。朱本以‘玉纤分露’与‘小园秋晚’两句乙转,改‘晚’为‘霁’;《历代诗余》仍其原句,而易‘露’为‘翠’;皆误认为落韵而改之者,其题显然可见。”[17]这首《蓦山溪》是张埜的和韵之作,题为“和卢彦威应奉食柑韵”,采用两韵通叶之法。《历代诗余》误改韵字,而《彊村丛书》不仅臆改韵字,且将词句倒乙,颇失原貌。陈运彰指出二者错误之后,又举宋元旧例以证自己的见解,“昔人常疑白石《长亭怨慢》‘青青如此’之误,厥后遍寻宋词,始明其理。比后雪楼诸家词,此两韵通叶者不一而足,知元人尚沿其例也。”[17]陈氏先引姜夔词例证明两韵通叶之法古已有之,又指出元代程文海等人之词也沿用宋人做法,最终目的是指出“玉纤分露”之句不误。此后,陈运彰进一步引申发挥,指出“依韵改字”现象由来已久,“景宋钞本赵用父《虚斋乐府》,《水龙吟·次李起翁中秋》歇拍‘古今同梦,不知何世’,此刻及侯刻均作‘何处’,知宋末人亦有疑此字者,而故书之,未经意改处为可贵也。”[17]总之,不随意更改词句原文是陈运彰反复强调的校词原则。
从以上两方面的论述可知,陈运彰的词籍校勘理念是注重不同版本的对勘,反对无据的就词义、依音律的校改;在批校时,又注重留存异文,以存词籍旧貌。可以说,多闻存异是其词籍校勘的基本原则。
20世纪上半叶是词学极为兴盛的时期,在新旧词学风气的影响下产生了一大批词学名家,词学各领域也取得了众多成果。陈运彰是近代词学兴盛的一个例证,他师出词学名门,又转益多师,与新旧两派词学家均有很深的交往,因此其词学能取得较高的成就,在近代词坛应有一席之地。惜其身体欠佳,加之时代风云变幻,以致病虑交加,未知天命而逝世。他在批校完《古山乐府》时说:“业十年以来,既阨于人,复困于病,神思渐减,送藏且尽。又复抱守残余,重理故业,藉四当之说,聊以自慰,可叹也。”[13]若加之以天年,则其词学定能有更大的成就,实可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