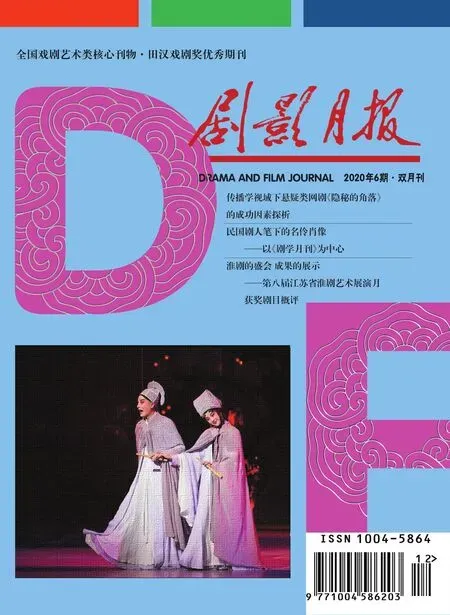观看与认同
——好莱坞华裔女性导演的自我身份建构
■刘亚玉
关键字:华裔女性导演;认同;自我建构
在好莱坞电影中,呈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持久的兴趣,他们试图通过西方立场的演绎、判断和表述,让西方理解中国。在这种被支配性话语框架控制的表述中,对华人形象塑造一直存在刻板印象,从早期电影中狡诈、精明的傅满洲、陈查理等男性角色,到黄柳霜饰演的善恶二元的柔弱东方女子与蛇蝎“龙女”形象,再到黑色电影片的华人黑帮头目,以及好莱坞大片中的华人女战士等,勾勒了东方性格、氛围、故事,甚至是专制主义和生产方式,其中也包括东方的浪漫主义与阴谋论,这些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政治权力有着对应关系,在殖民时代他们塑造的东方形象是为欧洲寻找亚洲市场、资源、殖民地制造文化优越感,在今天东方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影可以成为我们了解西方文化话语力量的一个途径。
在萨义德的理论研究中,深入分析了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的东方学研究中殖民主义的政治色彩,东方学研究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在东方题材的艺术创作处理中,也存在着一种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的机制。西方电影银幕上华人形象的定型化降低了人文精神,人物塑造的脸谱化也变得令人厌烦。然而,随着中国导演群体在国际舞台上崛起,他们的表达输出打破了基尔南(V.G.Kiernan)所说的“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2000年之后,好莱坞青年华裔导演的电影也越来越多出现在观众视野中。他们的作品因为获取了更准确的现实指涉力,使中国文化被放置在更大的全球化语境中聚集、凝结,其中不乏女性导演的作品,她们准确地把握、接近中国题材,发掘东方文化的内蕴,回答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疑问,寻找自我的情感建构。
一、观看:从建构他者到审视自我
个人身份作为独特的集体经验的汇集,最终都成为一种建构,它相对于和自身不同的“他者”身份建构,是对“自我”(alter ego)与“他者”差异性特质不断阐释与再阐释。每个时代的“自我”和“他者”都有不同定义,“自我身份”与“他者身份”也非静止,很大程度上与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的变化发展息息相关。对东西方观众来说,都早已厌倦了艺术创作中,充斥着西方优越感的叙事方式,而华裔导演视角所展示的道德伦理关系,摄入了西方对“古代中国”浪漫幻想,也展示现代中国的面貌,打破了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无论作者写任何凭想象编造的事情,事实上都面对一个主题:身份。每一部作品都只是对那个特殊主题的另一种演绎,也就是作者自己的身份。电影作为创作者自身的写照,与生命经历有着相似之处。在好莱坞的华人题材电影景观中,西方导演的镜头好比是一个窗口,窥探东方人的生活,华裔导演的电影是一面镜子,他们从中照见自身。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华裔女性导演开始进入跨文化电影创作领域,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批文化交流的使者,美籍女性导演孙小玲从1980年代末就回到中国,拍摄了《中国城市》系列,《新中国的宝藏》《四川》等纪录片,使隔绝交往几十年的美国人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她也是电影《末代皇帝》的顾问。她担任制片和编剧之一的故事片《北京的故事》讲述了美国一个华裔家庭到大陆探亲的故事,故事用幽默的手法表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将两种文化放置于同等地位,以平等相待的心态和记实的手法展现了中国面貌。故事片《铁与丝》(1992)在杭州拍摄,根据美国青年马克·沙兹漫同名回忆文章改编,讲述马克到中国教英语、学习武术的故事,邀请了当时刚演出完《末代皇帝》的邬君梅和当时在好莱坞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女演员林苹出演,并且邀请铁砂掌的传人潘清福扮演片中马克的老师,整部影片无论是画面还是音乐都沉浸在浓浓的中国文化氛围之中,展现了一幅八十年代前期中国的较为真实的图画。电影为社会、历史和文本自身特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例证,她的创作为当时的中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影像文本。

作为纪录片导演,杨紫烨与孙小玲有类似经历,曾在好莱坞从事多年电影幕后工作,参与《喜福会》《天浴》《纽约深秋》等多位美国华人导演作品的剪辑工作。她的创作经验是从西方视点追述自身历史,再进入中国社会内部重新深入了解、研究、纪录的过程。2003年她曾担任长四个半小时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的剪辑师,该片讲述华人从十九世纪初期至二十世纪末美国的历史;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风雨故园》是她首部执导的长篇作品,在全美二百四十七个公共电视台播放。2004 年她开始回到中国大陆拍摄纪录片,用一年时间驻扎中国安徽颍州进行拍摄,完成了纪录片《颍州的孩子》,影片用一种带有主观情感的镜头语言,走进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真实记录了当地艾滋孤儿的生活状况。影片以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呼吁社会给予对艾滋病病人更多的关注与心灵上的的救助,片中所蕴含的人道主义理性光辉超越了创作者的国族身份而具有普世价值。她运用西方经验所给予的历史、人文、文化研究工具,使自己保持一种严肃理性的批判精神,在创作的过程中融入真实情感,从未忘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文化现实。
华裔女性导演作为华人的后代或在传统华人家庭成长的女性,他们与华人社会存在有机、内在和联系,这些文化被某种氛围、精神、天性或民族观念凝结在一起。她们带着这种潜在的认同和西方式局外人的视点,进入内部视点,透过历史内在认同的方式进入深层的中国文化。在2000年之后开始创作的好莱坞华裔女性中,伍思薇导演的影片是风格独特的存在,2004年的电影《面子》将故事背景设置在唐人街,包裹在西方文化氛围里的中国文化的特质被放大凸显,故事讲述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却不会讲英文的母亲,丧偶多年后48岁却意外怀孕被父亲赶出门,她与外科医生女儿同住,却发现女儿喜欢同性,母女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陈冲扮演的母亲一直试图逃脱父权社会密置的藩篱,在她的人生观排序中,她首先是家族的成员,父亲的女儿,其次才是自己,在她的身上体现了传统父权专制下的情感创伤和人格缺陷。压抑之下的纵欲和根深蒂固的宿命感,使这个人物具有普遍性、代表性也有特殊性。这种特质在以往西方导演的视点中往往是“被冒犯的观看”,他们营造的感受力是居高临下的巡视,表现其为行动的怪异性,但他们并不介入其中,与其保持距离。但在伍思薇导演的电影中,这种观看是参与式的,尽管在观看中依然存在文化冲突和心理距离,但也融入了情感认同和文化寻根的移情。
在早期赛珍珠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等作品中,西方导演构建的中国故事,不论是场景,还是扮演中国人的西方演员,呈现给观众的是高度虚构性的表演,一个非东方人被转化为代表整个东方的符号。而在华裔导演的作品中,这种虚构被打破。当华裔女性导演刚刚进入电影创作中,她们多年所受的西方教育和生活经验会不自觉地将西方视点带入,在表述自己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建构他者的疏离感。随着她们走进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对中国家庭的传统伦理进行逻辑性分析,不知不觉中摒弃了她们对西方价值观所谓的某种文化话语中“真理”的偏执。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论》中提出每种文化对别的文化都充满敌意,要想进入这一文化,观察者必须放弃自己的偏见,而采取一种移情(Einf ü hlung)的方式。
在华裔女性导演的视点中,展示了中国城市不断变化的面貌之下,依然留存着内在一致性,以家族为纽带的生活方式、历史和习俗,如同信仰一般植根于中国社会。追寻个人价值,还是遵从集体价值,成为女性导演考察中西方文化异同对应关系的起点。从1980年代至今,她们的电影创作,起初开始对地域政治文化意识的考察,转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分配。通过情感体验、语言重构、心理分析、自然描述和社会描述将完整的中国社会体系再现出来,并且使其维持下去。2000 年之后的华裔女导演也将视野投入历史时空,胡安导演的作品《西洋镜》戏说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诞生的故事,展现西方文明与中国古老艺人们在意识、民俗方面的冲撞、纠缠、融合,《美人依旧》将故事背景放置在1949年前后,在时代的动荡与变迁下,表现人的精神状态和复杂的情感关系,影片中周迅主演的妹妹小菲一直想要回归家庭,在某种层面上与导演的渴望回归故里的情感交织着内在呼应。
二、认同:从关系疏离到回归移情
从创作目的来说,历史中欧洲东方学的持续讨论和中国题材的持续被书写、中国元素被运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出于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耐力与力量。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拔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在女性导演的电影中,东西方文化的霸权和怀疑精神被转变成为社会结构内部对父权和家庭关系的反思,但对于中国文化到最后依然持肯定与尊重态度。

知识是外来移民超越局限向遥远陌生的文化推进的方式,对华裔女性导演来说,西方的教育背景使她们自身的文化也在经历发展、演变与转化。在华裔女导演的电影中,主角大多是社会精英,有才华、较高的职业素养以及独立人格,在影片叙事中,她们不可避免地透过西方视点看中国文化,带着某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在情感叙事中被解构弱化。
陈苗导演2019年纪录片《上海的女儿》讲述生于上海成名于西方世界的著名演员,京剧大师周信芳的女儿周采芹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她从东方进入西方社会,多年后又回归中国。在她进入西方艺术创作的时代,东方人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是没有能力表述自己的,只能被别人表述。影片彰显了周采芹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尽管受到西方文化挤压,但当她成熟之后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好莱坞银幕上所扮演的是略带西方偏见的、脸谱化、同质化的角色,从1980年代她开始回归中国题材的创作,对父亲的追思,在文化中寻根,成为她找寻、回归自我的路径。在这个人物的身上,保持着东方学内在的一致性,又与周围的西方主流文化存在着可提供认同且复杂的关系。
2019年《别告诉她》是近年来继《摘金奇缘》之后最受关注的好莱坞华裔导演的电影,编剧兼导演王子逸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搬上银幕,讲述女主角碧莉远在长春的奶奶患了癌症,但大家都不打算告诉奶奶实情,全家人以表弟结婚为借口,从日本和美国和奶奶见最后一面。电影让观众从美籍华人碧莉的归乡之旅中看到海外移民三代人之间的观念差异。故事最核心的冲突是关于生命知情权的讨论,碧莉认为剥夺奶奶对自己病情的知情权是不人道也是违法的,但最终她在深入走进中国文化之后,逐渐理解了中国人的生死观。
当碧莉从美国纽约街头走进中国,家乡从儿时记忆里的遥远面目不清的想象变成了可见可感知的存在。电影开篇碧莉走在纽约街头和奶奶通电话,是她对中国文化和家族关系的间接在场,镜头跟随主角进入中国后,她变成了直接在场。影片对中国社会面貌的展现依赖公共空间、传统、习俗,其中包括了带着猎奇视点的洗浴中心、葬礼上的哭丧队伍,酒店里喧闹的喜宴等等。这些故事场景过于概念化,在影片中甚至超出了叙事的功能,试图呈现西方人眼中真实的中国社会。然而在格格不入的文化语境中,主人公试图慢慢排除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干预,使东方化的情感认同凝固在特定的时空中,达到跨文化的理解。
对于是否该告诉奶奶患病的实情,主人公碧莉经历了质疑、追问,到放弃,再到协同大家一起维系谎言的过程。事实上“一种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而只是对它的一种表述”,对“是否告知真相”的这个情感问题,她和不同身份背景的对象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探讨,引发观众对中国人的生死观进行批判性反思。提炼和表达重要的疑问成为电影的价值。美国编剧理查德·沃尔特说:艺术不寻求答案,只是提出问题。“无解的情感问题”在影片中成为一个中介,展现过程变成更为重要。碧莉从“认识中国”作为出发点,最终以“认识自己”为落脚点,将自我认同呈现为历史过程的产物,她在这一趟旅程中,深刻地感受着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而这种外部视点正是当下中国在全球语境中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
从历史脉络来看,华人女性形象在西方导演和华裔导演的表述中是不同的存在,前者是对东方富于想象的审查,或多或少站立于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后者则是从西方意识到东方文化立场的转变。华裔导演的情感立场超越了审视的范畴,她们用真实的东西双重身份体验,重新建构国族身份文化认同,展现了对中国历史的延展与想象,在文化的表征中塑造与现实接近、具有深远影响的东方女性形象——她们为家族的责任和利益而存在,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经历。
在华裔女性导演的表述中也有犀利批判的一面,电影的戏剧冲突不是肢体暴力,而是心理、精神和情绪上的对峙。在伍思薇《面子》等多部早期华裔女导演的影片中,都揭露了中国传统人情社会中亲密关系里的虚伪和控制欲,中国的人情社会和血亲关系中的道德绑架,尤其是父权的压迫。家族中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联有时让人压抑,但却在喧嚣表象的联结中建立起相对安全稳定的社会机制。《别对她说》相对于十五年前的《面子》,降低了这种亲密关系的约束力,两部影片都用了“婚礼”的文化意象来营造中西文化的差异。从李安的《喜宴》开始,华裔导演电影里,中国人的婚礼就成为极具文化意味的场域。《喜宴》中李安将婚礼称作“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面子》中婚礼成为女性反抗父权的战场,《别对她说》中婚礼则成为海外游子和二代移民子女回归中国人情社会的情感宣泄场。在《面子》和《别对她说》两部影片中,也存在着两种仪式的比较——西方人的生日聚会和中国人的婚礼。生日聚会成为西方人凸显个人价值的表征,中国人的婚礼则是彰显家族情结和表现集体主义最典型的环境,在这场盛装出席的集体狂欢中家长意志是主导,结婚的男女双方成为婚礼的配角。
总而言之,在年轻一代华裔女性导演的电影中,东方和西方之间这种传统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被打破了,她们的西方价值观在传统中国家庭或现代中国社会屡屡碰壁,试图说服他们最终却被群体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反噬、同化,在家族情感的关系中找到了慈爱宽厚的人性。最终她们开始尊重并且试图把握交织在家族权力话语中的各种力量关系,回到西方社会的机制中,继续保持她们与西方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关系,而身上又增加了一重来自古老文化中家族伦理观念挥之不去的持久影响力。
尽管华裔女性导演影片中依然有西方立场的表达,但因为作者个人经验中的历史复杂性、情感细节和价值观念,中国的文化现象被处理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类产品”,抛弃了传统西方式至高无上的道德判断。中国文化叙事不再是冷冰冰的逻辑推理,而是注重人文表达,关涉政治和文化的责任。她们的作品中有类似的一脉相承的流动意象,母题种类,综合成为了复杂精细的表述方式。她们试图解释中国人社会体系中的组织结构,具有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质和内在一致的原则。好莱坞的华裔女性导演运用她们的国族与文化身份,在西方电影中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客观表达,展示了西方看待中国的视角,也从女性的视点揭示了宏大叙事之下性别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