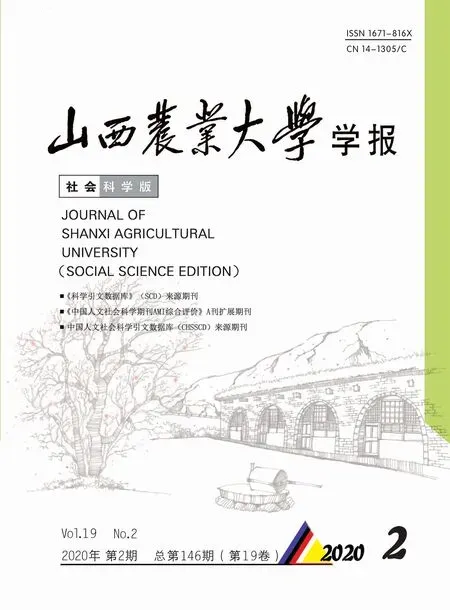生活本位:新时期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
——基于川西平原Z村的实地考察
张欢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不断增长的离婚率已成为普遍现象;而正在工业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婚姻的稳定性也受到挑战[1]。根据我国民政部每年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363.7万对,离婚率2.7‰;2015年有381.4万对,比上年增长5.6%,离婚率2.8‰;2016年有415.8万对,比上年增长8.3%,离婚率3‰。由此可见,我国离婚率呈逐年攀升趋势。其中,农村离婚现象成为一种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针对日益普遍的农村离婚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展开。首先,在国家法律制度层面,比如新中国新婚姻法的颁布,使得乡村社会确立了自由自主的婚姻伦理,以至于当时的农村出现了一个解除包办婚姻的风潮,无疑国家权力在新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2]。长期以来,离婚不但在法律上受到极大限制,而且在道德上也被视为极不光彩的事情[1]。但是,在倡导婚姻自由的现代社会,社会舆论与法律制度对离婚更加宽容,使得离婚者的心理社会成本降低,离婚行为变得简单容易[3]。闫云翔在其著名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结尾,明确提出国家政权介入是推动下岬村村民私人生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4]。
其次,在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层面,随着电视媒体传播与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社会的冲击,乡村社会中原本发达的防止婚姻破裂的社会约束机制逐渐瓦解[5]。因此,以“熟人社会”为本质特点的传统乡村社会正在向陌生人社会过渡,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强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逐渐突破熟人社会,社会规范的约束力也就陡然减弱,从而使得已婚人士能够更加从容地选择和面对离婚[6]。也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认为传统道德、舆论、地方性规范的式微与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是外出打工家庭离婚的重要原因[7]。
再次,在婚姻文化价值变迁层面,传统社会的婚姻价值是在传统“家本位”文化之下服务于农民家庭传宗接代的本体性价值,是超越于夫妻关系和个体本身的[8]。然而,随着打工潮的兴起带来的人口流动,传统婚姻圈被全国婚姻圈所取代,妇女在全国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离婚现象大量出现,农民家庭伦理观念得以变迁,即传统“家本位”逐渐向现代“个人本位”迈进[9]。传统时期女性面对家庭暴力、婚外性行为走投无路会选择自杀;而社会流动背景下妇女在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得以在以平等和情感为基础的家庭生活中寻找归属,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传统婚姻价值解体[10]。随着传统婚姻逐步瓦解和自由浪漫型婚姻形成,婚姻价值由“双系抚育”向“个体性生活”转变,因此婚姻是个体追求幸福生活的渠道,婚姻价值发生了变革[11]。
最后,在现代性视角下,打工潮对农民的婚恋方式和婚恋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农民的婚姻生活更具现代性和浪漫性[12]。然而,打工潮背景下妇女的经济独立、婚姻优势以及观念解放等因素使得离婚成为妇女婚姻主导权的表现[13]。随着打工经济的深入,农村妇女逐渐将婚姻作为向上流动的手段,带来的结果是各阶层之间的高度竞争与地位焦虑,婚姻演变为阶层分化和社会排斥的工具,由此妇女主导的离婚新秩序成为底层社会问题的集中呈现[14]。基于此,新时期“经济贫乏型离婚”呈现快速增长趋势,这种婚姻物化倾向形塑了农村地区贫困阶层的弱势积累与地位焦虑,具有一定的道德风险与社会风险[15]。
综上,既有研究已经从多维度对农村离婚现象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阐释,为理解当前不断攀升的离婚现象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既有研究往往从某一个方面去分析婚姻变迁,而较少从婚姻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迁角度来分析农民家庭的婚姻稳定性问题;第二,近年来的离婚研究侧重于从打工潮背景下的女性优势视角去分析离婚的新特点,而忽视了对一些年轻女性主导不明显地区的离婚现象以及中年群体离婚现象的关注;第三,既有研究还强调女性主导的离婚新秩序下带来的阶层分化与社会竞争问题等等,忽视了对低度社会竞争、低度阶层分化地区离婚现象的研究。本研究立足于川西平原Z村的离婚实践,提出“生活本位”这一视角,试图从婚姻、家庭、社会三重关系为农村离婚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本研究意义上的“生活本位”,是指在现代性力量的冲击之下,不仅传统家本位观念对个体的结构束缚弱化,而且伦理本位的社会规范对行动主体的约束也在弱化,农民家庭在满足生养送终的基础功能上,越来越遵循一种“生活本位”的逻辑,成为个体的生活与情感寄托,离婚成为个体追求美好生活过程中的一种调适手段。
二、川西平原Z村离婚的特点
(一)川西平原Z村概况
Z村位于川西平原西北部,距地级市15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全村现有9个村民小组,529户,1704人,耕地面积128.67公顷。作为城郊村,Z村成为满足城市农产品需求的菜篮子,因此村民农业收入来源以种植蔬菜、水果、苗木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为主。城郊村还具有在地化务工的区位优势,全村劳动力约900人,在本村附近工作的村民约700人,主要从事一些工厂上班、园林护养以及其它服务行业,因此农民家庭劳动力配置方式与生活观念易受到城市影响,这不同于一般空心化村庄。总体而言,该村的经济分化与社会竞争不明显,但村庄内部公共生活与休闲文化发达,体现为随处可见的、人满为患的各类茶馆、麻将馆等等。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成家立业之后的日子就是属于自己的“幸福安逸”生活。基于这种“生活本位”的观念,当地农民原有的婚姻秩序与家庭观念正面临一系列的影响。
(二)Z村离婚概况与特征
Z村年轻人的初婚年龄一般是22~23岁,以自由恋爱为主,父辈不会主动干涉子女的婚姻,一般选择尊重子女的婚姻自主权。当地婚姻成本与结婚压力不大,一般彩礼1~2万元。在全国性的打工经济背景下,Z村二三十岁的年轻群体一般选择省内镇外务工,但中老年群体以本地化就业为主。因为2006年左右,该村周围招商引进了两家大工厂,可吸纳近千人的劳动力就业,村民由此从土地上解放出来,逐渐实现了农民非农化转型。因此,2006年以前,Z村离婚现象并不多;2006年以后,Z村离婚现象明显增多,尤其是年轻人离婚易冲动赌气,本来很简单的事,最后闹到离婚。据统计,2006年以来Z村共有19例离婚案例。具体来说,Z村离婚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离婚主体。以年轻男女为主,逐渐向其他群体扩散。离婚群体中年龄主要以三四十岁的年轻群体为主,共计12例;近年来五十多岁的中年群体离婚也逐渐出现,一般子女成家立业之后,中年父母就开始追求个人向往的婚姻生活,共有5例;还有老年群体离婚现象,只有2个特殊案例。还有一些特殊案例并未完全统计,比如老书记两女一儿全都离过婚,又比如一家七兄弟姐妹都离婚的现象也有。由此可见,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且逐渐向不同群体进行扩散,而且在家庭内部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2.离婚原因。2000年前后,男方有家庭暴力倾向、有不良嗜好是主要原因;2010年以来,婚姻不忠诚、男方经济条件差是离婚重要诱因。据统计,Z村因女方出轨离婚的有7例,因男方出轨的有2例,因男方经济条件差的有4例,因男方有赌博、喝酒、抽烟等不良嗜好而离婚的有4例,因男方有家庭暴力的有2例。由此可见,Z村离婚的原因主要是因婚姻不忠诚,且以女性不忠诚者为多。此外,女性在离婚中并非起绝对主导作用,男性本身的不良嗜好与经济条件也逐渐成为离婚的重要影响因素。
3.离婚方式。不仅形式多样,且具有反复性,复婚者多。如果说结婚证意味着一种约束,那么离婚证意味着一种释放。从婚姻形态来讲,主要有四种离婚类型。一是离婚后一拍两散,双方互不往来;二是离婚不离家,扯了离婚证,但夫妻俩还住在同一屋檐下约4~5年,其中房子与土地等财产已经分开,村民解释说因为女方还没找到一个好去处,所以暂时过渡一下,也就是说在法律上离婚,但在村庄意义上并未离婚;三是反复离婚复婚,比如刚结婚一个月就离婚,很快又情感愈合再复婚;四是离婚后,又娶一个,然后与原配、新配三人住同一个屋檐下,各住各的房子,像朋友一样继续往来。
4.离婚成本。再婚市场发达,一般离婚男女均有机会再婚,有些再婚者也过得很幸福。离婚意味着双方都重新获得自由与私人空间,可以重新进入婚姻市场,寻找新的生活伴侣,追求自己认为幸福安逸的生活。由于初婚市场具有长远预期、感情基础好、社区认同强等特点,因而往往比较有序;而再婚市场一般追求合得来的生活伴侣或者老来伴,这种无规则的剩余性婚姻市场对初婚市场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一般而言,离婚妇女不愿意带走小孩,因为会影响到再嫁状况。村民对于离婚者再婚的评价是:若男性离婚后很快找到一个女性再婚就是很厉害,若一个女性离婚后找到一个二婚男性,人们评价往往不好。
三、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
既有研究针对农村离婚现象,一般是家庭与社会的两层分析,对婚姻与家庭并未作出明确区分。本研究基于川西平原的离婚实践,将从婚姻、家庭与社会的三个维度出发,试图阐释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婚姻是构成家庭与社会的基本前提,婚姻涉及的是夫妻关系,而家庭关涉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类型,也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共同体。在传统家本位观念下,夫妻关系是服从于家庭的,家庭对于婚姻主体而言是具有价值生产能力的,婚姻主体的人生意义与价值归属是深嵌于家庭内部的。而在川西平原的离婚实践中,小孩不足以成为婚姻稳定的维系纽带,因为婚姻个体不愿为了小孩而忍受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代际关系相对独立,夫妻关系逐渐脱嵌于家庭本身的功能体系,从而使得婚姻的工具性与个体性凸显。本研究将从婚姻对象的可替代机制、家庭的弱劝解机制、社会的弱约束机制以及再婚市场的可选择机制四个维度来分析新时期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从而呈现出离婚现象之所以攀升的经济空间、家庭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市场空间。
(一)婚姻对象的可替代机制
在传统家本位观念下,婚姻与家庭是一致的,婚姻的价值性较强,村庄社会规范比较完整,对婚姻主体具有一种外在约束机制,女性处于依附性地位,妇女离婚不仅没有收入来源,而且会面临社会的污名化压力,离婚代价大,因此婚姻相对稳定。而现在打工经济背景下,婚姻的价值感弱化,婚姻是一种生活方式,婚姻双方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比如Z村夫妻俩外出上班,各开一辆车,这样你不会束缚我,我也不会束缚你。婚姻与家庭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即使离婚,家庭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好,离婚家庭与正常家庭之间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大。
翻阅陈雷部长的工作报告,以人为本的理念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民生”成为此次会议的最强音,指引着水利事业的发展方向。
在Z村,婚姻对于农民而言意味着什么?具体说来,婚姻的工具性替代了婚姻的价值感,体现在:一是养老功能,即通过结婚生子、生儿育女来实现未来养老,这是婚姻的基础性功能,体现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与代际责任;二是陪伴功能,即通过结婚形成一种夫妻陪伴,生病时有人端茶倒水,年老时有人常伴左右,这是婚姻的生活性功能,体现的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夫妻关系与夫妻陪伴。这种功能性婚姻的性质在于,婚姻对象的替代性强,他们需要保持的是婚姻关系,而不是与某个特定个体的婚姻关系,如果这种婚姻关系基本能够实现基础性功能与生活性功能,那么具体的婚姻对象也是可替换的。因此,婚姻的工具性一定程度上使得婚姻对象具有可替代性,影响了夫妻关系的稳定性。
在打工经济背景下,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参与市场,个体得以实现经济独立性,现代社会男女之间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双方之间没有明显的地位失衡,经济能力差不多,女性脱离丈夫也可以独立生活。基于这种独立的经济空间,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成立家庭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为了过一种幸福安逸的生活,生孩子不是一种必然性需求,有孩子也不会成为维系婚姻稳定的一种纽带,那么结婚或离婚就容易成为常态。在川西平原,父母一般不会为了孩子而忍受不幸福的生活方式,Z村19例离婚案例中有13例都是在有小孩的情况下仍选择离婚的。这与川西平原相对独立的代际关系与相对有限的代际责任有关,在这种低度压力社会中,夫妻之间有各自独立的生活方式,既可保持距离,也可以很亲密。可见,打工经济为农村离婚双方提供了经济空间与物质条件,因此婚姻双方的这种低度依赖关系进一步强化了婚姻对象的可替代机制。
(二)农民家庭的弱劝解机制
在传统乡村社会中,阻止婚姻破裂的两套关系网络即亲友网络与行政网络(村干部、乡司法所、法庭)在婚姻发生危机或者当事人有离婚倾向时发挥了重要作用[5]。但是打工经济背景下,当前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即使离婚后也不愁嫁,且在不断攀升的高额彩礼诱惑下,女方娘家亲属网络不但不会劝阻女儿离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女儿离婚,由此出现“娘家人心术不正”的现象[13]。由此可见,农民家庭本身的劝解机制逐渐弱化。这在Z村离婚实践中也得到一定的印证。以前离婚双方会经历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既有父母兄弟姐妹的劝解,也有家族权威的干预,夫妻关系是深嵌于家庭之中的,夫妻之间的大声吵架是希望借助外部力量来评理,并在家庭内部通过“家庭政治”[16]形成家庭正义,从而给离婚一个合法性解释。而现在,一般针对子女闹离婚现象,父母几乎不会去过多介入干涉,而是尊重子女的自主选择权,家族内部的亲属关系网络更不会去干涉别人家庭内部的私事。甚至有时子女离婚之后,父母才知道离婚结果,村庄社会才会传播开来,其离婚过程是平静而简单的,是一种更加个体性或者是夫妻之间的行为,而不需要在离婚过程中弄得人尽皆知。
农民家庭不仅越来越无法发挥劝阻离婚和维持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反而其他家庭成员的离婚会对已婚兄弟姐妹产生一种示范性效应,比如Z村老书记两儿一女全都离过婚、一户人家7兄弟姐妹全都离婚以及一个村民小组有10户离婚等现象,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婚姻的示范性。不过从离婚实践来看,这种婚姻示范性也并不完全是消极作用的。因为一些再婚家庭反而比离婚之前过得更加幸福和睦,当人们看到离婚并不必然意味着家庭的失败,也不是所谓的悲惨下场,因而在家庭内部、亲属之间或者是村庄社会中进一步再产生离婚的正面示范效应,这不同于以往对离婚的负面性认识。由此,离婚不是特殊事件,反而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人们尝试通过离婚再次选择更高质量的婚姻生活。随着离婚越来越普遍,大家对离婚现象也越来越习以为常。因此,农民家庭本身不断弱化的离婚劝解机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离婚在家庭社会内部的示范与强化效应,为农村离婚现象提供了家庭空间与社会基础。
(三)社会规范的弱约束机制
一般而言,在婚姻发生危机时,除家庭内部的劝解机制之外,还有地方性社会规范为婚姻稳定性提供了一层保护网。这种地方性社会规范是指乡村熟人社会内部具有一套约束与规范农民的行为规则,这对农民婚姻家庭具有一定的社会约束力与社会整合功能。随着现代性因素的进入与打工潮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乡村公共性的消解[17]与社会规范的弱化,使得农村离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
在川西平原Z村,农民婚姻的个体性较强,村民对离婚的负面评价不强,因此村组干部一般不介入离婚的私人领域中,除非夫妻双方出现暴力打架或其中一方向村委会求助。正因为婚姻属于私人领域的事务,离婚越来越不受社会规范的约束,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容易产生冲动性离婚,比如年轻夫妻吵架时会赌气说出“离就离,不离是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婚姻裂痕,离婚爆发点往往就是直接崩溃,没有任何调解与缓冲,离婚双方也不会因为孩子而忍受不和谐婚姻生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离婚。这种赌气性质的离婚,若有一方能冷静地给对方道歉,或者有家族亲属、村干部等外部力量介入,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很快就能达成和解。
随着社会规范的弱化,婚姻逐渐脱嵌于家庭与村庄社会而成为私人领域的事务,离婚双方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通过村干部或乡镇法庭这些外在力量介入,虽然整个离婚程序是饱满而复杂的,但婚姻发生危机时还有挽救的可能。现在,婚姻关系是个体的、私人的事情,没有外溢出家庭,也没有公共化。这种婚姻无序,与缺乏外在风险干预机制有关,与缺乏社会舆论、缺乏闲话机制的弱社会结构有关。Z村老书记甚至认为,婚姻法应该修改,对私人领域的离婚进行干预。在当前村庄社会评价中,若维持一种冲突的婚姻状态而不离婚,村民反而不认可这种婚姻形态。若因男性好吃懒做或有不良嗜好而离婚,在村庄社会内部不会有道德谴责,别人反而对男性持负面评价,离婚在村庄社会具有正当理由与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婚是一种追求幸福安逸生活过程中的调适机制。因此,村庄社会规范的弱化使得农民婚姻越来越具有个体化特征,这种弱结构约束为农村离婚提供了一种社会空间。
(四)再婚市场的可选择机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从区域范围来看,当前“婚姻市场”[18]可区分为地方性婚姻市场与全国性婚姻市场;从结婚次数来看,婚姻市场可区分为初婚市场与再婚市场[19]。初婚市场与再婚市场这二者之间在性质上是有差异的,初婚市场往往更有序,初婚年龄一般在22~23岁,人们有相对稳定预期,而且有感情基础,社区认同强;而再婚市场有两种群体,一是丧偶群体的再婚,为了寻找新的婚姻伴侣,二是离婚群体的再婚,追求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由于再婚市场是无规则的,适婚对象也是参差不齐的,无疑会影响初婚市场的稳定性与有序性。但是再婚市场并非完全是低劣性质或质量不高的婚姻对象,因为离婚过程的个体性、随意性本身就容易形成冲动性离婚,这样因双方误会或者性格不合而离婚的也不少,因此再婚市场也可能是一次新的排列组合。再婚实践最终指向的是家庭,无论你以什么方式组建家庭,只要家庭和谐、子女孝顺就是被接纳的。由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高离婚率反映的是一种追求和睦、幸福、安逸的家庭生活的调适机制,离婚成为追求幸福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
在川西平原Z村,离婚现象比较普遍。一般来说,离婚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与代价的,比如再婚本身的困难与劣势。但是普遍性的离婚现象,也使得农村离婚者的再婚空间与机会比较多。随着家庭调节机制和社会规范约束机制的双重弱化,农村离婚成本与代价都变小了,因为在村庄社会中,村民并不会以一个人是否离婚来判断你的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村民重视的是家庭生活是否幸福安逸的状态或结果,而不是婚姻本身的过程,只要结果有效即可,过程之中的结婚再婚等婚姻实践是为村民所接纳的。除了离婚者的心理社会成本或违约成本不高,离婚也不会像传统时期一样对家庭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有损祖先形象、辱没门风等道德性评价,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离婚会对小孩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总体来说,整个大众舆论、法律制度以及熟人社会评价体系都对离婚表现出更加宽容的一面,因而呈现出离婚的普遍性与个体性特征。基于此,当前农村就出现了数量不少的再婚群体,这种剩余性婚姻市场就为农村离婚者提供了再婚的市场空间。
四、延伸讨论:生活本位下的婚姻调适逻辑及其后果
随着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农村的婚姻家庭领域正面临转型,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既有研究较多地关注婚姻家庭的价值变迁层面,而较少关注婚姻家庭的生活转型层面。传统伦理本位的婚姻家庭,强调的是家庭内部主体行动与规范性结构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在打工经济与村庄规范瓦解背景下得以缓解,生活本位的婚姻生活逻辑由此兴起。在这种生活本位之下,人们在完成基本的人生任务与代际责任之后,就开始转向关注个体的生活体验。这种对既有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会成为行动主体进行自我决定与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比如“抛夫弃子”行为背后的目标指向是追求一种美好生活[20]。
在传统家本位观念下,婚姻与家庭是一体化的,其婚姻是深嵌于家庭之中的,也就是说夫妻关系是服从于家庭目标本身的,因而只有婚姻家庭与村庄社会两层分析;而在生活本位之下,婚姻与家庭之间是有距离的,二者并非是统一的,家庭是有价值生产能力的单位,而婚姻是脱嵌于家庭的,是注重个体的生活体验的,因而在生活本位框架下,村庄原有的婚姻家庭与村庄社会两层分析进一步分裂为婚姻、家庭与社会三层分析。也就是说,相对于传统婚姻中的伦理责任对个体的结构性约束,伦理弱化与村庄规范弱化背景下的现代婚姻在实践中越来越具有一定的调适空间,个体越来越注重个体生活体验,农民婚姻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安逸的生活。比如在川西平原离婚实践中,子女成年后,中年群体离婚现象逐渐增多。这主要是因为父母抚养小孩长大成人是父母基本的代际责任,一旦子女成家立业之后,父母就转向体验个体的美好生活。一旦既有的生活方式不如意,很可能就会在一个偶然的时间节点爆发,离婚成为中年群体对婚姻生活进行再调适的表现。由于生活过程本身具有很多偶然性,当人们试图通过生活的体验与实践去实现向往的美好生活时,当前农村必然会呈现复杂多样的离婚实践样态。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与社会的基本前提。随着现代性的冲击与生活本位观念的兴起,农民家庭领域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老人养老、生活模式等各要素之间形成了一套不同于家庭政治框架下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在川西平原,农民生活是通过家庭来实现的,家庭是通过“生养送终”两个方面来实现的。子女是父母生活的精神动力与寄托,因而子女也是父母奔波奋斗的动力。因此,有子女的家庭,父母仍然需要竭尽所能地储蓄,为子代结婚积累所需成本,这是父母对子代的家庭代际责任。但是这种责任并非刚性的,因为父母不会因储蓄不够而面临社会谴责。父母会根据经济实力与家庭关系进行相适应的调整,其实不稳定婚姻关系也是这种调整的一种表现。虽然川西平原的代际关系是相对独立的,但这种代际关系是一种“独而不散”的形式。比如子代具有底线养老的基本责任,父母也要为子女成家立业提供帮助。但是在这种代际责任之下,父母在家庭负担与生活体验之间需要达到一种均衡,这种均衡就是一种幸福安逸的生活。
然而,在不同生命周期,代际责任与父母经济能力是不同的,子代对父代家庭的依赖程度也就不同,那么子代的成熟期也存在差异。从当前实践来看,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他们基本上能够顺利地实现代际责任与生活体验之间的均衡。但是,还是有部分人没有成熟起来,其个体的生活价值即现代浪漫主义的婚姻生活观念是排第一位的,由此导致了个体的家庭伦理责任与美好生活体验之间的失衡。一旦婚姻家庭本身的责任伦理弱化,就容易产生一种异化的婚姻家庭形态,离婚由此生成。可见,当前离婚率的攀升,既是个体在实践中进行婚姻调适的表征,也是当前家庭责任伦理弱化的表现,更可能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农村婚姻家庭领域在转型过程中正面临一种“伦理性危机”[2]。
五、结语
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婚姻家庭领域正面临变革与转型,其中农村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就是一种体现。本研究结合既有研究成果与川西平原的离婚实践,提出“生活本位”这一概念,为解释当前越来越普遍的农村离婚现象提供一种新视角。研究发现,农村离婚现象不仅局限于青年群体,随着生活政治的兴起,也逐渐拓展到中年群体,农村离婚群体不断扩大,与当前农村为离婚提供的多维经济社会空间有关。本研究从婚姻、家庭、社会三层分析框架出发,揭示了农村离婚现象的深层机制,在打工经济背景下,个体具有经济独立性,婚姻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人们的家庭责任伦理弱化,因此在发生婚姻危机时,不仅婚姻对象具有可替代机制,尤其是在个体生活本位观念强势崛起之下,家庭内部缺乏劝解干预机制,村庄社会崛起也缺乏约束机制,而且离婚双方在发达的再婚市场具有再选择的空间,农村离婚不再是高成本与高风险的,由此农村离婚现象不断增多。当前农村离婚现象的攀升,不仅是个体进行婚姻调适的表现,也是婚姻家庭责任伦理弱化的表现,更可能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家庭转型过程中正面临着“伦理性危机”。因此,关于农村离婚问题,直接关涉的是中国农民最深层次的价值意义世界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