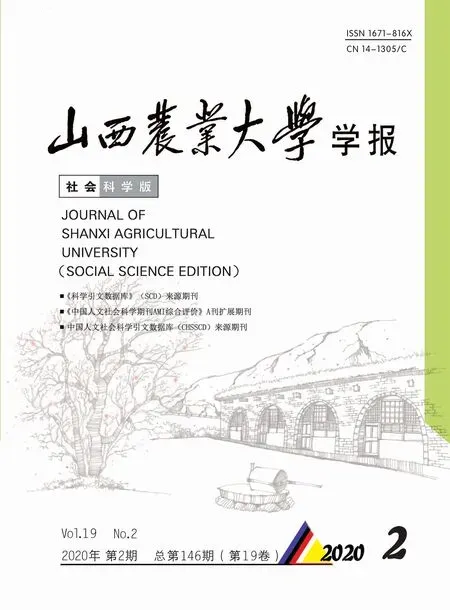疫情反思:中国为什么需要发展农村小城镇?
庄晋财,黄曼
(江苏大学 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1月23日武汉开始实施“封城”管理,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春节过完过元宵,接着是情人节,之后是“二月二龙抬头”。这些往年热热闹闹的节日,今年变得冷冷清清,大家只能各自宅在家里消磨着时光,焦心地等待疫情结束。随着一个个节日过去,转眼已到惊蛰,大地万物复苏,早该是谋划一年生计的时候,“一年之计在于春”,错过就要等来年。对于农民兄弟来说,今年特别难,往年春节刚过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踏上东去或者南下的列车,直奔城市的企业工厂,今年突然遇上疫情,四处封路设卡,人人出不了家门。因为疫情的停工歇业,城里那个工厂是否还能继续都成了问题,对很多农民工兄弟来说,或许回到原来那个工位上的可能性不大,维持生计日益艰难!可想而知,农民工兄弟们眼前的焦虑日甚。来自农村的我们,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都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为什么农民兄弟如今身在家乡,心系远方的焦虑却如此之重?答案当然在于城乡二元发展格局下的“打工经济”,如果不破除这个格局,实现农村从打工经济向创业经济的转型,农民兄弟的这种焦虑将会继续下去!
论及如何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的格局,大城市化是一种十分时髦的观点,通过发展大城市把农民转移进城,既有规模经济,又能实现真正的农民市民化、农村城市化,似乎一切都那么完美!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按照这个思路走过来,这样的美好却没有如期出现,反倒是越来越严重的农村人口钟摆式迁徙。今年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让农村流动人口“摆”回农村之后,无法及时“摆”回城市,形成两个奇特现象:一方面城市企业复工找不到工人;另一方面大量农民滞留乡村找不到工作。于是出现很多所谓“硬核”做法:城市的地方政府或者企业包飞机、包高铁到中西部地区接回农民工!很多人褒奖一些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这种开先河的做法,但是笔者却在这种褒奖后面存在着种种担忧。在笔者看来,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它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城市产业结构,至今没有完成转型升级,仍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农民工断档对产业发展形成毁灭性打击,所以不得不要包飞机、包高铁抢民工;二是许多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产业结构仍然是单一农业,无法提供就业岗位,农民的收入增长依然依赖跨区域外出打工,一旦这条道路被疫情阻断,基本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所以,包飞机、包高铁接民工返城复工,不是什么“硬核”,而恰恰是“软肋”!
大城市论者经常抛出三个理由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一是农村衰退是必然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是趋势;二是大城市才有规模效应,资源配置到大城市才有效率;三是政府控制大城市的政策总是失效,无论国家如何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还是不能阻挡人们奔向大城市的脚步。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笔者看来,这些论点存在两大错误:
一是没有历史观。中国的城乡差别是规律使然吗?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建国后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我们用差不多30年的计划经济手段,依靠行政力量将大部分的农村剩余用于城市建设和完善城市工业体系,奠定了城乡差别的基础;随后市场取向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再用40多年时间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这种城乡差距,才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农村衰退愈演愈烈的现实。现在农村劳动力往城市跑,不是什么追求美好生活的结果,而是农村要素被城市定价造成的无奈。城乡差距是历史形成的,如果不顾历史事实,把它当作历史规律,对中国的发展将十分有害。
二是颠倒因与果。农村人往城市跑说明政府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无效吗?那先得问问我们是如何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最常见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政策,就是设置农村人口落户大城市的门槛。大概就是因为无论怎么设置门槛,我们都看到很多农民会想办法进入大城市的缘故,才有一些专家学者关于大城市趋势是控制不住的观点,但这显然是因果倒置。我们将绝大多数资源用于建设大城市,再对农民进城设置门槛,这被理解成控制大城市发展,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控制不住的。因为人都是理性的,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别那么大,由此决定了人口的流向。如果要真正控制大城市规模,应该是在政府公共资源的配置上去控制,如果今天中国有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城乡有相对接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那样的人口流动走向才能够说明究竟什么是趋势!
如果不走大城市化的道路,中国有什么办法让农民走出“钟摆式迁徙”过上好日子吗?笔者认为,最理想的道路是以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思维,构建大中小城市协同的城市网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先从概念说起。我们知道,所谓城市,是一个空间聚落,在历史上是先有用于防御的“城”,后因为要满足“城”里的生活需要才有了“市”,随着“市”的繁荣进而发展出为“市”交易的产业,吸引人口聚集,成为今天所说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走大城市化的道路,就是指把一个城市做得很大,人口很多,就像有人主张的把上海建成5300万人口的城市那样。怎么建呢?一般的做法就是从城市中心开始,不断摊大饼式地往外拓展,一圈又一圈,城区的范围不断增大。中国的大城市基本上是这样建起来的,许多如今的大城市在20年前只有一环、二环,如今都有五环甚至更多,这就是大城市发展的思路。
如果我们讲城市群,那就不是大城市的概念了。因为“群”不是个体,要有很多个体聚在一起才能称为“群”。城市群就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聚集着多个城市,这些聚在一起的城市,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有相互的关联性,城市之间形成分工合作的关系。我们说长三角城市群,就不单单是指上海这个大城市,而是由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在内的一定空间范围内的27座城市形成的“群”。显然,发展城市群跟发展大城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发展大城市往往强调的是“规模效应”,而发展城市群更强调城市之间的“协同分工”,思路是不一样的。现在是分工的时代,城市之间形成的分工合作关系所带来的“协同效应”,比“一城独大”的“规模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
最近网络上不少比较江苏与浙江的文章,似乎对浙江的褒奖要远远超过江苏,不管是这次防疫还是疫情之下的企业复工举措,似乎浙江都是领先于江苏的硬核榜样。但在笔者看来,浙江和江苏是长三角两个各有千秋的发达省份,地理虽相近,城市化发展道路却不同,这种不同在早前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中就已经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城市化道路来说,浙江是“省城独大模式”,杭州在浙江的地位远超过南京在江苏的地位,这就是人们常常对浙江津津乐道的一个原因,其中还产生了一个专门的词叫做“省会城市首位度”!江苏走的是“城市群模式”,沪宁线上短短的300公里距离,摆着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5个城市,经济实力最小的镇江,人口只有不到320万,GDP总量却在4000亿以上,更不要说苏州、无锡了。因此,尽管江苏与浙江的地理面积相差无几,但要比GDP总量、人均量、公共预算收入、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公路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等,浙江与江苏相比还是差距不小的。进一步比较就会发现,浙江是靠以家庭私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起家的,因为家族式的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选择的产业基本上也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因为这样的产业选择,专业型市场变得非常重要,所以造就了“义乌小商品城”的辉煌。同样在今天, 还是因为浙江轻工业产品需要聚合销售的特点,像原来“义乌小商品城”这样的专业型市场,在互联网时代就演变成阿里巴巴这样的电商平台。有人说,在互联网时代浙江比江苏早走了一步,其实并不说明浙江的优势,而只是历史原因使然。江苏由于是靠以集体社队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起家的,集体企业规模比家庭私营企业大一些,所以江苏的产业结构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为主。江苏省的现代制造业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次疫情中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中展示得非常好。浙江和江苏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导致两个省有诸多不同:浙江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产业发展,需要包飞机和高铁去西部地区拉民工,江苏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对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就不是那么急切;浙江做的大多是轻工业产品,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分工,比如海宁做皮革,嵊州做领带,不太需要城市之间的产品内部分工,而江苏做的大多是现代重型制造业,需要有城市之间的产业内部分工,比如镇江做的很多零部件,就是为南京和苏州等城市的整体组装服务的,城市之间的协同在江苏显得非常重要;浙江家庭式的私营中小企业比较多,而江苏现代公司制的大型企业比较多,所以江苏GDP总量大,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要比浙江少很多,这就是人们常说浙江藏富于民,江苏政府有钱的重要原因。
从浙江与江苏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城市群的发展有不同的模式:浙江以杭州为核心,省城独大,可以称之为“轮轴型城市群”,由一些骨干城市围绕省会城市这个核心来布局经济发展,省会城市就像一个平台,聚合着各个骨干城市的经济力量;江苏省的地级城市如苏州、无锡、常州,不是围绕南京转,个个实力非凡,号称“十三太保,散装江苏”,可以称为“马歇尔式城市群”。由此看来,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并不止一种,没有必要在全国强行推动“大城市化”道路,各种不同的城市群发展模式,都有其清晰的历史路径依赖。
但是,无论何种城市群发展模式,除了需要骨干城市之外,都需要大量的小城镇作为支撑,这倒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大城市论者喜欢用东京来证明大城市化的正确性,但是如果看看这个城市的人口数量就会发现,东京都核心区的人口910万,外层的东京市(底下管着好多个城市)人口1370万,再外一层的区域叫做东京都市圈,人口则有3700万,象埼玉、千叶、横滨、神奈川都囊括在内。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城市圈”,这是一个圈层结构,由核心城市、骨干城市、中小城镇组成。我们今天可以把长三角看作是一个城市圈,核心城市是上海,骨干城市是长三角的其他20多个城市,而最外围的则是众多的小城镇。长三角经济之所以发达,关键是因为在核心城市和骨干城市底下,存在无数的小城镇,可以源源不断向它们输送物质资源,最终汇聚出巨大的动能,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繁荣!
从概念上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只建设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叫“大城市化道路”,就是把某一个核心城市建得大大的,一环又一环;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群”,就不一定要扩大某个核心城市的规模,而是要让众多骨干城市能够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形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就像现在所说的“长三角一体化”;如果我们选择的是建设“城市圈”,那除了要注意城市群建设,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强外围的小城镇建设,以提升各骨干城市的能力,这样才能提升城市群的竞争力。比如说,要是没有昆山、常熟这样的县级城市及其下面的农村小城镇做支撑,就不会有苏州的城市实力,那长三角城市群的能力就要弱得多。
由此可见,一些具有协同分工关系的城市连接在一起,可以形成城市群,由众多小城镇围绕着城市群里的骨干城市,可以形成城市圈,由小城镇、骨干城市、核心城市形成的城市群、城市圈这样的城市结构,可以称之为“城市网络”,这才是中国将来城市化发展的方向!有学者说,大城市才有规模效应,才有效率,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超过一定的规模边界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这次疫情的发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疫情的发生也许跟城市大小没有关系,但疫情控制的难度,一定跟城市大小有关。广东疫情最严重的是广州与深圳,浙江疫情最严重的除温州的特殊性之外是杭州,江苏疫情最严重的是南京与苏州,这不需要多少知识去证明,因为这接近于常识。反过来看规模效应,则不是城市越大效率越高,看看江苏苏州市下面的昆山,这是一个县级市,但人均GDP接近上海的2倍。广东的专业镇经济、浙江的块状经济、江苏的产业集群,大多都是在诸如昆山这样甚至更小的城镇上,一点也不影响其规模经济的实现,也就是说,规模经济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越好!
那么,如果中国要发展城市群,建设城市圈,构建城市网络,缺的是大城市还是农村小城镇呢?答案显然是农村小城镇。据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现在有近680座城市,其中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290多个地级市,380多个县级市。这些城市是目前中国公共资源的主要投入流向目的地,有着与农村完全不一样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保障。如果大家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座落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地级以上城市,繁华的程度并没有太大差别,但东部地区城乡差别很小,中西部地区则是人们所形容的“城市象欧洲,农村象非洲”。由此可以判断,如果现在要在各区域建设城市群,城市圈,形成城市网络,关注点一定不是核心大城市,也不是骨干地级市,而是农村小城镇。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就是注意发展农村小城镇,让众多的农村小城镇围绕地级骨干城市,使区域经济有强有力的基础支持。这不仅是中国的经验,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家喜欢拿来跟中国比较的美国,一个3.2亿人口的国家,拥有1万多个城市,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数量都在10多万人,有的甚至只有几万人,这其实就是小城镇。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只有857万人,排位第二位的洛杉矶不足400万人,整个美国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10个左右,那我们有什么理由以美国为榜样还说要发展大城市呢?
按中国的行政区划标准,县是城市之尾,农村之首,中国现有380多个县级市,1300多个县,近2万个建制镇,都属于农村小城镇的建设范围。如果把这些县级以下农村小城镇的产业发展起来,成为地级骨干城市的经济支撑,区域城市群的发展能力就有可能得到不断提升,这样才能形成城市圈,建构出经济活跃的城市网络。若如此,今天疫情之下的农村居民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因为他们不需要依赖遥远城市的工作岗位来谋生,他们可以通过自己在附近小城镇里的工作岗位求得生计,通过在小城镇里创造的财富流动来替代自己的钟摆式迁徙,以谋求生活的改善,因此,当下的中国,最需要发展的是农村小城镇。农村小城镇的发展,需要依赖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类人员入乡创业,这些创业者在多大程度能够入乡,则取决于城乡一体化的公共品供给政策体系何时能够真正形成并发挥实质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