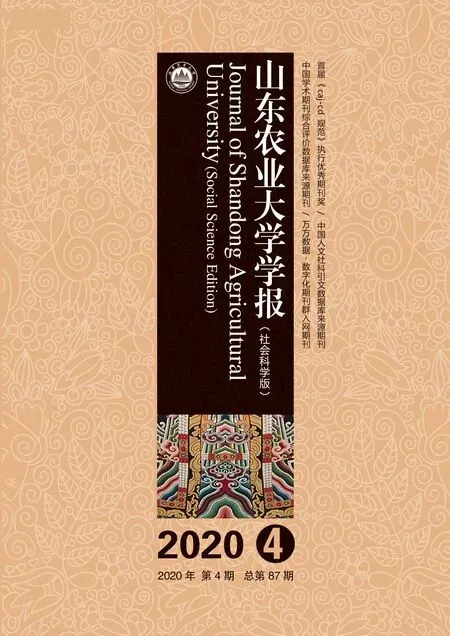城乡空间转换与女性形象建构
——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现代性”书写
□欧芳艳
[内容提要]新时期经济逐渐复苏繁荣,促使文学寻找合适的叙述路径以阐释现实境况,即文学如何表达“现代性”这一问题。这种创作动力,成为迟子建执著书写“现代性”的重要缘由。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具体表现在欲望的释放、精神的异化以及人性的堕落等方面,而这又体现在她小说的女性形象书写上。在“现代性”视野中,迟子建早期小说大都是书写乡村愚昧落后的女性,对现代文明则表现出认同态度;然而199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开始书写城市女性的精神异化与孤独状态,将女性意识的觉醒放置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借此以“反现代性”的态度批判现代文明;2000年以来,迟子建小说对城市的绘写更加深入,她在理性认识“现代性”的同时,也试图找寻超越“现代性”的方法。因此,分析小说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书写,成为考察迟子建小说“现代性”表达的重要路径。
处于时代重要转折点的迟子建,在中国当代小说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最具时代意义的便是迟子建对“现代性”的不断思考。“现代性”在她的小说中不只是一种文化空间,更是一种思考社会人生的方法,这具体呈现为城乡文化空间下的女性形象建构。就文本创作而言,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她们身上呈现的文学内涵,始终与文学思潮呈现出互动性。因此,迟子建书写女性形象的历程,表现了她对“现代性”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与体悟,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文学思潮的对话。
20世纪80年代中期,迟子建初入文坛便因《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等文章,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评论家们纷纷注意到迟子建小说中对愚昧落后文明的批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树声认为迟子建的小说“从这边远林区凝滞的生活氛围中,从一系列自我意识极端贫弱的善良老人身上,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劣根性。”[1]表明要“完成实现现代文明这一巨大社会工程的迫切性和艰难性。”[1]王干则认为,迟子建小说流露出一种“审文意识”[2],“即是对前人的文化准则和思维归向用现代文明的尺度进行理智的或情感的审视和反思。”[2]他们都看到迟子建早期小说所流露出的寻根意味,这是通过对愚昧落后文化的批判,来达到启蒙的目的。
然而199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表现的却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否定。毛克强认为“迟子建的《原始风景》,则是躲开现代都市文明,描绘了一幅牧歌式的亲情画面。”[3]郭力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小说“会促使我们反思现代化立场,以及并不很现代的思考问题的方式。”[4]张东丽认为“迟子建对于大自然主体地位的重视与思索,是在她离开故乡进入城市生活后开始的。”[5]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看到,199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对乡村生活的书写,已经成为她批判城市、反抗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式。
2000年以来,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认知更为理性。小说内容批判都市喧嚣与人性迷狂的同时,以同情与理解之心,试图寻找超越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方法。金钢认为迟子建融入都市之后,作品开始书写“都市底层的平凡人生”并对“都市的历史深入开掘”[6]。汪树东则认为,新世纪以来迟子建“从乡土经验角度来理解城市,接近城市,发现城市生活的富有乡土温情的一面。”[7]迟子建对城市认知的逐渐深入,也使其对“现代性”的认识与理解更加深刻。
那么,“现代性”在迟子建小说中是以怎样的形态呈现?乡村与城市两个迥异的空间领域,为“现代性”的呈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女性形象,她们自身又有着怎样的特点与内涵?二者又是如何勾连,完成对“现代性”的叙事?迟子建缘何执著书写女性形象,这种执著书写又有何价值意义呢?以上是本文试图探讨的一些问题。
一、女性镜像:城乡空间视域下的“现代性”表达
迟子建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性”叙述,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伴随着迟子建精神资源的变化,以及创作主体与1980年代、1990年代文学思潮的呼应。综观迟子建小说的创作历程,以时间脉络来明晰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识,恰好体现了迟子建对“现代性”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即从感性体悟、理性反思到寻求超越。这种认识上的不断深入,体现的正是后者对前者的不断超越。
沿着时间脉络考察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的早期小说大多是以乡村为背景展开叙述。小说或是书写乡村的闭塞、愚昧与落后,亦或是展演乡村人与人之间的质朴情感。同时,小说在批判与同情的矛盾叙事中,展开对乡村生活的状写。但是通过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察觉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始终贯穿她的小说创作。那么,迟子建究竟是如何书写乡村生活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呢?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实则是“现代性”呈现的桥梁。如《旧土地》(1986年)、《北国一片苍茫》(1987年)、《没有夏天了》(1988年)、《奇寒》(1989年)等,文章中女性形象的书写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明显关联。细细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对“现代性”的思考始终若隐若现的存在于迟子建小说。
在城乡文化的冲突、碰撞中,女性的情感状态、精神面貌与行为举止发生明显变化。因此,这自然成为考察迟子建小说“现代性”呈现的重要路径。从文本表层来看,这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实际上,这是通过女性形象来呈现“现代性”在城乡视域下的形态。《旧土地》中老女人与棺材、铁轨之间的博弈,《北国一片苍茫》中芦花与大山之间的抗争,《没有夏天了》中丑儿与家仇无法挣脱的束缚等等,表明这些女性形象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苦苦挣扎。小说对众多女性形象的刻画,其实是从正反两个层面表现作家对落后文明的批判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在这一创作阶段,作家更多是描写乡村生活中的女性形象,书写她们的愚昧、落后以及所遭受的压迫与苦难,以此反衬现代理性精神破旧立新的积极意义。迟子建早期小说内容,就乡村世界的建构而言,乡村多是以漠河北极乡为代表,这是一个充满灵气与温情,却又较为封闭、落后的北国世界,此时的城市则是作家感性认识中的想象空间。换言之,古老的乡村是作家启蒙视角下的乡村,它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焦虑状态与忧患意识。小说中楠楠的离开、芦花对大山外世界的渴望,隐含的正是作家对现代文明启蒙疗救作用的渴求。因此,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书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寄托着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与想象。在迟子建这一阶段的小说中,“现代性”被认为是现代理性精神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奇寒》的出现,却表明作家对现代理性精神开始产生质疑。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将真实事件与虚构情节自然融合,营构出神秘诡谲的氛围。“我”以作家身份回到乡下,试图探求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乡村发生的巨大变化。然而,“我”却惊异地发现乡村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多了铁轨、电视等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物。从本质上来说,它依旧是当年的“大固其固”。现代理性精神似乎并没有在人们生活中留下太多痕迹,而“我”更似外来的闯入者,难再融入曾经的故乡。这场知识分子的返乡之旅,无疑是令人感到失落的。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程来看,这样的结局并不令人陌生。人们似乎还在重复《故乡》的故事,知识分子也难以逃离“离去——归来——再离去”[8]的循环模式。这表明现代理性精神要对乡土中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条道路漫长而艰难。
然而1990年以后,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认识变得更为理性。她不再以启蒙的姿态,批判愚昧落后的乡村,而是以反思的态度,批判城市、反抗现代文明。以《原始风景》的发表为标志,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进入新的阶段。《原始风景》中开篇和结尾都直接表现了作家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及对现代都市的排斥。当然,作家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并不是偶然,就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来看,此时迟子建正在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异地求学的经历,城市与乡村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无形中让迟子建产生强烈的异己感。因此,《原始风景》的主体部分都是在描述东北乡村生活,月光、星星、大雪这些迟子建早期小说常常出现的意象,再一次出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相反,城市则是陌生的、令人抗拒的。
1990年以后迟子建回到哈尔滨工作,并定居哈尔滨。她的生活世界难免会受到城市的影响,况且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来看,城市与乡村其实都是截然相反的两个面。因此,城乡之间的矛盾,自然也就体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中,迟子建更为直观地展开了她对“现代性”的思考。《与水同行》中直接将叙事者言明是女性,讲述她从城市来到苇河镇后展开的所思所想。乡村的质朴与城市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抗争也在回忆过去中拉开序幕。《银盘》中吉爱进省城务工后的初心不变,与虎生的变心形成鲜明对比。吉爱与虎生的爱情,其实正是乡村与城市的某种对抗。那美丽的“银盘”,正是吉爱质朴之心的体现。小说中女性自身的优势与弱点被放大,女性与“现代性”紧密粘结的过程,正是迟子建对“现代性”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
当然,迟子建小说对城市女性生活的描写,更让我们直接察觉到她对“现代性”所持的态度。《格局》中讲述米小扬、许东方等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而他们精神上的焦虑、孤独与尹平秀、丁丁等人的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形成鲜明对比。保姆阿三与雪凤的儿子回到乡下,米小扬走出电报大楼时的孤独,更表明作家创作态度的某种倾向。《晨钟响彻黄昏》中刘天园在精神病院的“清醒自杀”[9],菠萝背井离乡远离熟悉的城市,巧巧始终不知儿子意外身亡的真相,这些女性的命运看似不同,却又戏剧性重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展演了现代人的精神失落,人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人性的弱点被暴露无遗。迟子建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对城市女性精神状态与心理结构进行了大篇幅的探讨。小说将对女性心理状态的描摹,肉欲的描写,身体感官的刻画,与意识流的小说技法、荒诞奇谲的氛围营造交汇合流。这表明“现代性”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对文学思潮的直接反映。因此,这使女性形象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的同时,作家对“现代性”的阐释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2000年以来,从小说内容来看,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认知更为深入。一方面书写乡村的文本,转为书写少数民族的民俗民情和怀想过去以原始生态的生活对抗现代文明;另一方面书写城市的文本,不再是书写迷狂的人性,而是以同情与理解之心书写城市底层人们,尤其是女性生活的困境;亦或是藉以宗教信仰的力量,寻找精神的超越等等。
《微风入林》中方雪贞表现出的灵气、朝气与陈奎的暮气已经难以相容,而当孟和哲的野性与方雪贞的灵气相碰撞,俨然孟和哲更能打动方雪贞。方雪贞因受孟和哲的“惊吓”而“绝经”,又因与孟和哲发生关系而来了月经。这种不合逻辑、不合传统伦理道德的小说情节,却让我们看到民间的包罗万象。民间内容的书写无形中与现代文明、现代理性精神形成对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我”对部落的深厚情感、对森林与驯鹿的始终坚守,妮浩萨满的大爱救人等等情节,俨然将原始生活的灵性与城市生活的枯燥进行鲜明对比。《黄鸡白酒》中春婆婆遭遇的苦难与她的善良、豁达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作家对人性之善的赞扬。而对城市底层生活的描写,对城市女性命运的关注,表明作家对“现代性”的思考愈发深入。
从站在启蒙立场对现代理性精神的颂扬,到体验城市生活后对现代文明的理性认知,再到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寻求精神的超越,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逐渐深入。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伴随着女性形象书写的不断变化,换言之,女性形象是迟子建对“现代性”思考的具象呈现。女性细腻而敏感、多疑而易焦虑的性格特点,使女性形象成为迟子建小说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女性形象无疑成为分析迟子建小说的重要切入点。那么,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究竟有何特点?她又是如何将女性形象放置在时代语境中来描摹呢?
二、女性寓言:“现代性”表达的时代语境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女性形象不仅是其建构城乡空间的重要方式,更重要的是女性自身的特点,更易表现时代发展的脉搏。女性形象在不同时空不同语境中呈现的特质,是迟子建小说“现代性”表达的方式。显然,女性主体意识的淹没与觉醒,肯定“现代性”与“反现代性”,历史语境与现实状态等范畴,在小说内容中表现出的勾连关系,让我们无法忽略这一文学现象。因此,将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放置在时代语境中加以考察,我们能更易发现创作主体与时代语境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综观迟子建1980年代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某种再现。她们身上善良、无私、隐忍、充满母性的特点,饱受压迫、尝尽悲苦的经历,无疑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化身。这些女性形象在迟子建早期小说中大量存在,她们或是小说情节的推动者,或是小说内容的丰富者,是小说不容忽视的精彩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她们大都是乡村中的女性形象,并且遍及各个年龄层,从多面体现了“现代性”对乡村的影响。《沉睡的大固其固》在内容上并无太多新意,迷信而愚昧的媪高娘,只是千万中国乡村妇女的缩影,且这一类型的女性形象,在莫言等人的小说中并不陌生。但这却从反面印证,女性形象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是不可缺少的存在。作家们自然选取女性形象,作为阐释其观点的重要载体。而老一辈女性形象与“现代性”之间的反差,更突出了作家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
1990年以后,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与前期作品相比,无论是表现方式还是精神内容,都有了新的呈现,这体现了迟子建对“现代性”思考进入新的阶段。1990年代这一时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女性意识的觉醒。首先,这一特点表现在小说中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大量运用,并且叙事者大都是女性。《奇寒》中“我”以作家身份返乡,《遥渡相思》中“我”来展开叙述;《怀想时节》中“我”既是故事的叙事者,又是写故事的人;《麦穗》中麦穗便是“我”,“我”就是故事的主角。《与水同行》中叙事者“我”是一个女孩,对祖父母、父母一辈的故事展开怀想;《向着白夜旅行》中“我”与马孔多的旅行,是一场与灵魂的漫游;《晨钟响彻黄昏》中不同角色直接跳出,而以自己的口吻言说;《原野上的羊群》“我”因为不能生养,所以有了接下来的故事;《旅人》中“我”作为精神的旅者,始终在不断寻找、探索,以求走出精神困境。因此,迟子建在1990年代小说创作中,对创作主体的强化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强调,成为分析其小说不容忽视的方面。
其次,女性精神空间的建构、爱情主题的描写是这一时期迟子建小说的又一特点。“非个体化和个体化、厌世和激情,自保式的算计和高傲的卓尔不群,这两种个体的造型在现代都市的生活舞台上上演。”[10]118《与水同行》中“我”逃离城市,回到故乡,展开一系列怀想。我对祖父辈、父母辈故事的怀想,对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环境与精神状态的细致描绘,从侧面反映了“我”对现实的反讽。在“我”的精神世界中,老一代人的生活观念与深厚情谊,正是身处城市的“我”所需的养分。无独有偶,《格局》中的女性形象,其实是身处城市的人精神状态的缩影。女作家米小扬反思城市,讽刺周围利欲熏心之人,内心充满绝望与忧伤。从这些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此时迟子建刚来到哈尔滨不久。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精神状态,市场化、商业化的环境氛围,无疑激起了她对“现代性”的反思。
相较于城市中的两性爱情,迟子建笔下的乡村爱情似乎更符合她的女性观。《亲亲土豆》中秦山与李爱杰平淡却温暖的爱情,引发无数读者的共鸣。《灰街瓦云》则直接以主人公瓦云之名作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代表着作家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肯定。瓦云品性坚韧、善良,对丈夫的事业给予最大的支持,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她既似瓦片般坚硬,又似云朵般柔软,刚柔并济的性格并存之。而这一坚强女性形象,反衬的是村民贪婪与丑陋的面孔。《踏着月光的行板》中夫妻二人的相濡以沫、互相关爱,恰是最令人畅想的婚姻。但是这爱情的背后,是农民进城务工的辛劳。他们二人遭遇的种种不平之事,恰是农民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映现。这既表明迟子建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理解,也表现了其对“现代性”的反思。
从2000年以后的小说内容来看,作家将女性形象放置在历史时空中绘写,使之具有历时性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小说中几乎所有处于历史语境中的女性形象都是“老女人”形象。这可以看作是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小说走向历史叙事的重要策略。将“老女人”形象放置在特定历史时空中,既使历史的厚重感与“老女人”形象的丰富内蕴结合,也使得“现代性”的思考与时间、空间、历史勾连。然而迟子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不是宏大历史场面的铺展,而是“用民间立场书写历史。”[11]作家站在民间立场的历史叙事,使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具有日常性与生动性等特点。“老女人”形象的产生是叙事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读者注意。由此,迟子建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强化了时代语境中的民间立场,这关键就在于对“老女人”形象的塑造。“老女人”形象具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情感内蕴”[12]等特点,是迟子建选择这一形象的重要缘由。穿越岁月的“老女人”,丰富的人生经历,无疑使她们对时代跳动的脉搏有着敏感觉察。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穿梭中,无论是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来看,她们都是迥异的存在。她们对过去的执著坚守与现在的格格难容,共同表现了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
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小说中的“老女人”形象,具有某些共性,即她们饱受苦难,却总是宽宥于人。以《黄鸡白酒》和《晚安玫瑰》为例,春婆婆和吉莲娜穿越了大半个世纪的岁月,哈尔滨发生的变化她们再熟悉不过了。春婆婆的出生,就像是哈尔滨的雪地精灵出现了。她讨厌葬礼、喜欢吃酒,经历了鼠疫与战争,失去了丈夫,年老时无所依靠,还遭遇供暖收费不合理等不平之事。她一生饱尝苦难,却从不怨天尤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春婆婆有意被作家处理为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即母性与神性同在的女性形象。她身上积淀着中华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代表着作家对“现代性”无序的某种对抗。这也成为迟子建小说创作所常用的方式。吉莲娜的存在也蕴涵着这样的深意。年轻时的不幸遭遇,使她对赵小娥充满同情。这位从农村来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她的人生经历,仿佛让吉莲娜看到曾经的自己。因此,吉莲娜一直努力帮助赵小娥,希冀能以宗教的力量救赎她。因此,从春婆婆和吉莲娜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一与历史贴缝得如此紧密的人生历程,呈现出“现代性”对哈尔滨逐渐渗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作家对“现代性”的理解。一方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被放置在历史时空中得以衍生,另一方面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中,“现代性”的流变在迟子建小说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过去,学界对迟子建小说“现代性”的研究,一般停留在文本表层,认为迟子建对“现代性”是持批判的态度,小说对城市的描写是其对现代文明反思的表现,这固然有其依据。但是我们更应该透过表层,发掘文本背后的潜在内涵。通过探讨迟子建小说“现代性”思考的过程,将其小说创作自然与时代语境相连,考察每一阶段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方式、表达内容及潜在含义。因此,从整体上观照其小说内容,更易分析迟子建小说的“现代性”表达。
从早期小说对中国传统女性形象的刻画,到后来书写“现代性”视域下女性的异化、彷徨与孤独,再到对历史语境中女性魅力的绘制,可以看出迟子建小说中的“现代性”与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从这些女性形象中可以看到,迟子建对“现代性”的思考是如何逐渐建构成一个有序系列的。那么,迟子建为何执著书写女性形象,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与文学思潮的起伏、作家的女性观等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三、溯源阐释:文学思潮的更迭与创作主体的选择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众多文学思潮交替与更迭,这些变化对迟子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书写影响颇深。我们可以看到,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声音,并且这些声音与文学思潮有着或隐或现的关系。然而,不论文学思潮如何涌动,女性形象的塑造始终是迟子建与之呼应的重要切入点。“文学思潮是现代性的产物”[13],“现代性是文学思潮发生的原因”[13],换言之,“现代性”是迟子建执著书写女性形象的重要动因。当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与迟子建早期形成的女性观,她对文学对象的关注,以及女性形象自身的特点也有着密切联系。
如果说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那么谈论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换言之,迟子建小说创作类型、风格趋于稳定的视域下,我们要如何分析它是否受到文学思潮的影响?她的小说创作具体受到哪些文学思潮的影响?她在文本中又是如何呈现的?这种成果呈现与前期创作成果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差异?我们该如何多角度、多层次对其进行分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其作品潜在深意。
1980年代、1990年代及新世纪以来等三个阶段的女性形象书写各有其特色。从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来看,我们发现文学思潮对其创作有着直接影响。可以看到,女性形象的塑造随着新作品的不断出现而被推进。且作品的重要转折期,一般都与时代语境有着密切联系。迟子建小说与文学思潮的互动过程,大致可以概括为从呼唤理性的启蒙到讲究技法的先锋,再到贴近民间的“新历史”。“文学思潮是大规模的文学运动,是一定时代产生的共同的审美理想在文学上的自觉体现。从根本上说,文学思潮是文学对现代性的反应。”[13]因此,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敏感察觉、理性认知到反思超越的过程。这一动态的转折过程,表明不论是自主靠近还是无意被影响的创作主体,在面对文学思潮时都会做出一定的选择。这一选择不论是接受还是排斥,在作品中都或多或少留有痕迹。
迟子建自登入文坛始,便因书写东北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广受关注。早期小说如《沉睡的大固其固》《旧土地》等,书写旧土地中愚昧落后的老一辈女性,藉此唤醒民众以达到启蒙的目的。这一主题内容与19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不谋而合,评论家们也纷纷认为其作品内容与寻根文学遥相呼应。1990年刊发的《原始风景》,则体现了迟子建对现代文明的反抗和对故乡的怀想。当然,市场化、商业化的文学语境,未必没有影响其对“现代性”的反思。如果说《原始风景》是迟子建对“现代性”的初步反抗,那么《炉火依然》等作品,则是技法的探寻与“反现代性”的融合。如《向着白夜旅行》中第一人称叙事角度的采用,与灵魂一起旅行的独特构思,诡异的死亡事件等等,诠释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由此,既将先锋小说荒诞等特点融入作品,又结合独特的地理环境,共同营造出奇谲的氛围。而《旧时代的磨坊》《黄鸡白酒》等作品的出现,表明女性形象被放置在历史语境之中刻画。当然,“讲述女性历史故事几乎成为八九十年代之交文坛的一股潮流。”[14]这足见迟子建的小说创作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
然而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受文学思潮影响的同时,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也与女性形象自然融合。迟子建在《我的梦开始的地方》中说到,她最初的文学启迪便是童年生活。乡民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脸上”[15],“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和超然”[15]。不论是初登文坛,愚昧迷信却又坚忍、善良的“老女人”形象,还是新世纪以来,饱经人生苦难却拥有人生大智慧的“老女人”形象,这类女性形象一直是迟子建小说创作的持守。女性形象本身的特点,促使迟子建不断以此为桥梁,构筑起对现实人生的认识。而小说中对女性形象内涵的不断深化,表明迟子建对“现代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迟子建的女性观,无疑成为她书写女性形象,理解人生的重要标杆。她认为“女性应该包含母性特有的宽容、善良、隐忍、无私的性格特征。”[16]因此,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也无论她们遭受多大的苦难,迟子建笔下的女性形象,始终持守着女性的性格特点——善良、隐忍、宽容。从初入文坛书写乡村女性,到后来书写处于时代浮沉中的进城务工女性,再到书写城市底层的女性,迟子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兼及到不同时代、年龄和区域空间。这些女性形象,凝聚了迟子建对社会、人生与命运的思考。女性形象也就自然处于迟子建观察和思考社会人生的前景位置。
综上所述,迟子建小说中女性形象书写的持守与变奏,始终与作家对“现代性”的思考相连,且内蕴着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因子,这无疑成为迟子建创作的推进器。因此,迟子建小说对“现代性”思考的过程,应该在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视域、女性形象的系列建构以及对文学思潮的复杂过程中进行比较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