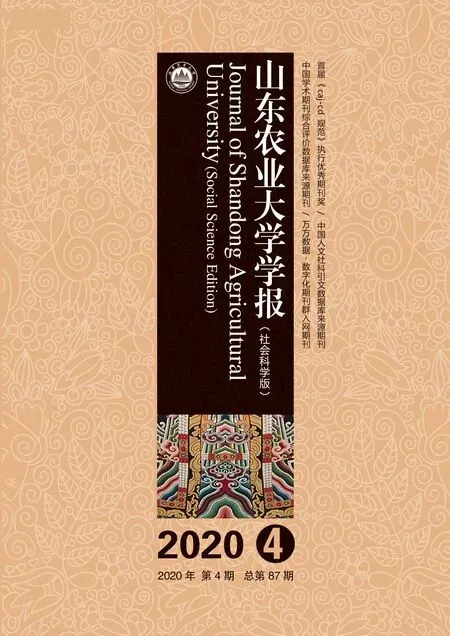从“鸽子视点”看《长恨歌》的电影化叙事
□刘 婧
[内容提要]王安忆在《长恨歌》的创作中运用了相当娴熟的“电影化”叙事手法。“鸽子视点”不只是一种别样的观看上海之方式,这种极富超越性的视角选择蕴含着作家的文化立场与情感态度。在“鸽子视点”的统摄下,“长镜头”和“空镜头”两种电影技法的交织运用及其表达效果成为《长恨歌》“电影化”叙事最为精妙和独特的部分。正是基于这“一个视点”“两种镜头”的独到运用,王安忆的《长恨歌》完成了对于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代表“新感觉派”及张爱玲的小说“电影化”叙事的突破,体现出作家对于文学表达独立性的坚守与对于上海民间更为深沉的文化内省。
“影像化”叙事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所谓‘影像(image)’,按照辞源学的说法,应和词根imitari即摹仿和类比有关”[1]。《影像的修辞学》对此有准确的定义,即“类比式再现”[2]。按照“模仿论”的观点,“影像”是一种虚拟的“再现”。所谓“影像化”叙事,意即使用更为直观、更具画面感、更有视觉冲击力和镜头意识的文本写作方式。所谓的“电影化”叙事,则与电影艺术的理论体系直接相关。其整体内含于“影像化”叙事的包围圈内,但在所指对象和理论阐说方面更加精确。
有着“东方巴黎”美称的上海与电影艺术渊源极深。中国现代小说的“电影化”叙事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第二代海派——“新感觉派”作家群手中发轫。经由四十年代海派文学的承继者和突破者张爱玲的发展,这一手法的运用日渐成熟。而今进入“读图”时代,电影与文学则愈发难舍难分。
被王德威誉为“海派文学,又见传人”[3]的王安忆早已有意识地在其小说创作中实践独具个性的当代“电影化”叙事。相关研究虽不甚丰硕,但已有论者论及其《小鲍庄》《启蒙时代》《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及《长恨歌》等作品中体现出的蒙太奇剪辑手法、光影流动中的诗意表达、淡雅的色彩造型等一系列“电影化”叙事技法。研究者们也多少触及其特殊的“鸽子视点”和长镜头的使用,但并未深入。本文试图说明《长恨歌》对于传统海派“电影化”叙事的突破之要义就在于“一个视点”“两种镜头”的独特选择与运用。
一、“鸽子视点”的选择
“简单来说,视点(Point of view)是摄影机的位置。”[4]57是指“镜头所模拟的观察者的视野。”[5]33在电影拍摄中,视点是最基本的画面造型语言之一,一般分为“客观镜头”“主观镜头”以及“正、反打镜头”等。而“角度”,作为镜头运用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一般又可分为“平视镜头”“俯视镜头”和“仰视镜头”。它们和“景别”“焦距”“运动”一同作为镜头运用的基本可变元素,相互交织配合,扬长避短,构建最恰当的镜头方式。
《长恨歌》第一部中,在王琦瑶的故事正式拉开序幕之前,王安忆出人意料地用一整章的篇幅细致描绘了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王琦瑶”。它们共同演绎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情态,以表现“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6]“街道,作为一种典型的城市景观,体现了城市的流动性、匿名性、混乱性特征”[7],它是现代城市最为典型的空间系统。“弄堂”即是上海独具个性的“街道”。“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8]3作者先引导读者观看宏观的上海弄堂全景。接着“还是要站一个至高点,再找一个好角度”[8]5来观看微观的弄堂。至于“流言”和“闺阁”,那都是隐匿在弄堂里的复杂因子。就在这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细节的流动中,上海最具特色的街道——弄堂的本质面貌一览无遗。
忽上忽下、忽近忽远的视野流动,并非常人所能触及。作者有意识地选择了“鸽子”这个意象,以其之眼,观此之城。“前边说的制高点,其实指的就是它们的视点。”[8]15“鸽子”是“惟一的俯瞰这城市的活物”[8]15,它们有着超越人类视野和行动的能力,观察这座城市的远近东西、犄角旮旯,更是城市秘密的洞察者、“无头案”的见证者。
“鸽子视点”是一种明显的“主观镜头”。飞越在城市上空的鸽子本身就是城市的一份子,它们是天然的、灵活的摄影机。鸽子成群结队,极富超越性,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自由姿态,生生不息地为城市留影。“主观镜头”模拟鸽子的形态与轨迹,引导读者接受主观镜头,无形中自然地介入场景,逐渐构建出关于上海的情景视野并主动产生情感倾向。同时作者在角度上选择了“俯视镜头”,不仅试图全览整个上海,更试图建构一种宏大的观看城市的方式。
但“鸽子视点”最绝妙处还在于作者因选择了“鸽子”这个天生的“摄影机”,同时通过其自然特性消除了视点选择的刻意性和人工雕琢之痕迹,达到了其使用“鸽子视点”这一“主观镜头”的终极用意——以“热肠挂住”之姿态进行客观的城市观察与文化内省。
鸽子与人类共为灵性动物,所以当流动的摄影视点与鸽子眼睛重合时,读者能够自然而然地参与到镜头的流动之中。又因鸽子本身是城市母体的一部分,是与人类血脉相连的活物,“他者”之“隔”便在此处自然消解了。“从通常的意义上讲,这种视点是以摄影机的运用为特征的,迫使观众去看场景中的人物正在看的,从而成为这个角色。”[4]59但当读者以和作者同样的“热肠挂住”之心态开始趁“鸽子视点”之便浏览镜头移动下的上海时,另一方面却又因明确自己和鸽子的各种差别,产生类似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从而将主观参与和客观审视适度地结合起来,转向更有深度的理解和阐释。也即读者能够通过“鸽子视点”的引导,并在作者所呈现出的弄堂意象和景观之中产生选择、分析和批判的自觉性,对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历史等进行严肃、冷静、理性的思考。在更宏观的意义上看,便是在接受层面引导读者集体开展一场关于上海的文化内省。“浮现在对城市的回忆中的,不只是对城市景观的纯粹感受(perception),更是通过联想之网而出现的对城市的复杂观念(conception)。”[9]
可见,“鸽子”在这里并非是“他者”,而是与观者融为一体并进行自我反观的一种对象,其包容性与延续性的确超越了其他意象及视点。事实上,张爱玲常用的“月亮”意象,也可被看作是一种固定的俯视镜头,但因缺乏流动性和与城市的母体联系,难免显得有些“苍凉”。可以想见,若将“鸽子”换作任何无生命的机械摄影镜头,或者与城市联系不深且缺乏指向性的其他视点,都不会产生“鸽子视点”的绝佳效果。
“鸽子视点”贯穿了《长恨歌》的始终,仿佛一台自由运转的摄影机,始终携带着作者浇灌于其中的客观立场与文化审视的自觉。而作者在“鸽子视点”统摄下对于“长镜头”和“空镜头”的独到使用更进一步地凸显了“鸽子视点”选择的精妙性与整个《长恨歌》“电影化”叙事的突破倾向。
二、“空镜头”和“长镜头”的交织运用
电影理论中的“长镜头”“是指较长时值的镜头画面。”[5]89它与传统的蒙太奇剪辑有所对立,“长镜头”“是在一个镜头内通过演员调度和镜头运动(推、拉、摇、移等视角和视距的变化),在画面上形成各种不同的景别和构图。”[5]89而“空镜头”则与远景画面有关。“远景——主要用于介绍环境、表现与环境有关的剧情内容。有的远景画面中没有人物,称为‘空镜头’。”[5]29
“长镜头”具有写实主义电影的美学特征。与编排镜头画面、声音和造型色彩等元素从而创造含义的蒙太奇不同,“长镜头”往往平稳、连贯、真实。而“空镜头”除渲染气氛外,常用没有人物的景观画面与人物的性格、心绪或电影的主题形成某种隐喻关系。
王安忆《长恨歌》的“电影化”叙事在“空镜头”和“长镜头”的交织运用方面独具一格。两种镜头的巧妙运用使《长恨歌》的表达具备含蓄性、多义性、深邃性、停滞性等多种特点,而此中对应折射出的历史化、客观化和宏大化叙事无疑显示了作者的历史观与对城市文化的深度开掘。
为表现“爱丽丝公寓”的旖旎奇景,作者选择了俯拍空镜头与运动长镜头结合的方式,将“爱丽丝公寓”的明艳奢华之感和盘托出。
“假如能揭开‘爱丽丝’的屋顶,……这是个绫罗和流苏织成的世界……”[8]91作者先运用“顶摄”手法,用一个俯拍角度的空镜头进入“爱丽丝公寓”的内部世界。接着用一个悠长舒缓的运动长镜头和空镜头相结合,一点点地将公寓中的细节展现出来。“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8]91通过运动镜头和焦距的调整,兼顾到公寓里的大小细节,顺序上又有一定的随意性。“迎门是镜子,关上门还是镜子。床前有一面,橱里边有一面,浴间里是梳头的镜子,梳妆台上是化妆的镜子,粉盒里的小镜子是补妆用的,枕头边还有一面,是照墙上的影子玩的。”[8]91这种极富随意性和流动性的镜头运动显得非常灵活和自由,从某种角度看,这同样可算作是一种俯拍角度的“鸽子视点”。通过俯视镜头下运动长镜头和空镜头的交叠与移动,“爱丽丝公寓”给读者呈现出既可参与又有距离感的双重属性。作者通过较为客观的镜头运转表现“爱丽丝公寓”的隐秘意味,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描写李主任和王琦瑶确定关系的过程时,作者采用的是固定长镜头与空镜头交相切换的方式。“王琦瑶偎在李主任的怀里,心是落了地的,很踏实的感觉。”[8]86为表现二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此处采取的是中近景的景别,在这样的景别中,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更加密切。固定长镜头对准李主任和王琦瑶,人物在其中调度。“两人相拥了一会儿,李主任推开她一些,托起她下巴注视着她的脸……李主任再次把王琦瑶拥进怀里……李主任把她又搂得紧一些……”[8]86两人之间的微妙情绪和关系的推动是由一段空镜头来进行辅助性言说的。“四川路上的夜晚是要平凡和实惠得多,灯光是有一处照一处,过日子的灯光。那酒楼的饭也是家常的……玻璃窗上蒙了人的哈气……”[8]86镜头再回到人物身上时李主任借租公寓一事进一步推进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为后文二人“名不正言不顺”的男女关系埋下了伏笔。两人缱绻的互动中插入的空镜头一方面使得人景互相隐喻,所谓“过日子的光”大抵是暖光,酒楼的家常菜等,皆是喻示着这对男女你来我往中的那点真情。另一方面,固定长镜头与空镜头的切换与呼应不仅延长了镜头的时间,更使得情节发展呈现出一种缓慢乃至停滞的状态,人物的心绪与场景的氛围变得朦胧多义,也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可能性,故而体现出一种延续性的情感体验与客观的距离审视。
当然,固定长镜头在《长恨歌》中并不是唯一的一种“长镜头”使用方式。更多的时候,在表现人与人、人与景之关系时,王安忆常恰如其分地运用运动长镜头来表现人物心理的波折与踟躇,并辅以空镜头,以期达到更为紧密和多义的表意效果。作者写主人公王琦瑶准备独自出门做流产手术时,就运用了主观镜头,以王琦瑶的主观视角引导读者揣摩她复杂微妙的心绪变化。从她打伞出门开始写起,一直到她犹豫过后最终回到家,运用了一个时值很长的运动长镜头,使读者跟着她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动产生同样的内心颠簸。其中还适当辅以对于雨、涟漪、天空、树等意象的“空镜头”展现,与活动中的主人公的表情、心绪等相互映衬,呈现出王琦瑶对于怀孕的复杂态度及其细腻的情感变化。
作者倾向于在两种镜头的交织运用中凸显“长镜头”的表现作用。在“祸起萧墙”一章中,作者先是用一个时值较长的“空镜头”和叠化手法来表现上海弄堂所面临的时间的压力。“风穿街过巷,窸窸窣窣地响,将落叶扫成一小撮一小撮……后弄里的那些门扇关严了,窗也关严了。夹竹桃谢了,一些将说未说的故事都收回肚里去了……”[8]334这里的空镜头表现了时光的积淀,也暗示着王琦瑶的老去。但“传奇”的王琦瑶怎会受时光之限,她的家里又聚集起了年轻的朋友。在表达这种反差时,虽然直接表述也未尝不可,但作者却运用了一个别有深意的运动长镜头。
“现在,让我们透过窗口,看一看平安里的内景。先是弄口过街楼上……楼下披屋的一家……再往里去,灶间的后窗里,两个女人窃窃私语……沿着门牌号码过去……隔壁的夫妇正反目……再隔壁的窗是黑着的……十八号里退休自己干的裁缝……我们终于看到了王琦瑶的窗口……”[8]334-335
作者引导着读者主动选择观看平安里内景的角度,采用了主观参与式的景深长镜头,一镜到底,按照空间的顺序,掠过窗口和内景,呈现出上海平安里的世情百态。在此基础上,再托出王琦瑶家里的热闹。为什么不直接写王琦瑶家里的热闹“派推”呢?一方面,王琦瑶是上海弄堂的女儿,她一生几乎都生活在弄堂这个民间文化的体系内,她也是城市中普通的生存者和参与者。另一方面,作者借这样的铺垫既强调了王琦瑶的与众不同,又含蓄地传达着王琦瑶不过只是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言人。作者自始至终想呈现的,还是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
总的来说,在《长恨歌》中,作者以“鸽子视点”为统领,贯穿整个“电影化”叙事的终始,常用主观参与式的长镜头、运动长镜头及叙事性长镜头,并辅以空镜头的运用,来展现人与人或人与景的关系。这样的镜头运用常形成延展性的影像叙事。“所谓延展性,即指影像叙事在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叙事点上所引发的向内或向外的扩展存在方式,而原点的意义则在影像叙事的扩展中得到升华和加强。”[10]其中尤其是延展性对白段落和延展性情绪段落,共同增强了叙事和情感的张力。
《长恨歌》中的“长镜头”和“空镜头”运用往往一箭双雕,潜移默化地表达出作者的立场和态度,同时引导读者独立思考。而所有的“长镜头”和“空镜头”运用都处于“鸽子视点”的统摄之下。在这座城市上空,只有鸽子才有如此灵动的飞行能力和自由的观察能力。城市中的每一个罅隙,都被鸽子尽收眼底。在王安忆之前,似乎还没有哪个海派作家能建构出如此宏大的观看视角、驾驭如此成熟的镜头转换,并同时在其中寄寓对于城市文化与历史的理性审视和深度理解,进而扩充文本的表现力与读者接受的可能性。
三、《长恨歌》“电影化”叙事的突破性
以王安忆为代表的新海派(以九十年代上海作家为主,包括程乃珊、唐颖、陈丹燕等)与传统海派(以“新感觉派”与张爱玲为代表)在小说“电影化”叙事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视角的选择与文化思索的落脚点。
就表现上海的都市景观与文化气质而言,“新感觉派”作家最常用的“电影化”叙事手法是蒙太奇剪辑。“蒙太奇是法文MONTAGE的译音,本是建筑学的用语,原义为构成、装配,借用到电影中有构成、组接的意思。”[11]蒙太奇手法通过镜头的剪接和组合,能够创造时空、含义与节奏,是影视艺术的基础。“新感觉派”作家最常选择的意象包括咖啡馆、跑马场、电影院、交易所、百货店、汽车、洋酒等。通过使用意识流般的回忆、想象、幻想和闪回等手法,讲究以快速的切换剪辑来表义。在文本中,他们常用短句、省略号、破折号来表现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与丰富性,并运用摇、移、跟镜头的方式,将都市景观符号进行快速的交叠,给人以眼花缭乱之感。
“亚历山大鞋店,约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
回旋着,永远回旋着的年红灯——
忽然年红灯固定了:
‘皇后夜总会’”[12]
在电影方面颇有创见的“新感觉派”小说家,有意识地实践了两种媒介的互构与互释,但他们的作品却还未展现出深层次的都市体验,往往还停留在都市景观的表面化呈现,在技法上也是较为单纯地移植、嫁接和模仿西方的电影表现手法。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化”叙事则比较娴熟。除蒙太奇外,她还善于运用长镜头尤其是固定长镜头以及慢镜头等手法。她将电影技法与文学表达作了有益的结合,其小说隐喻频发、寓意深远,精雕细刻、环环相扣,往往能够生动细腻地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历史中悄然流动的文化特质与人的生存体验。
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戏”感。小说中的画面分镜头感突出,常用蒙太奇剪辑、镜头的变化、具体的空间设置、多义的意象选择、精致的民俗描绘、明艳强烈的色彩以及具体可感的人物行动,给读者一种连续的、紧凑的画面转换体验。有一种“类似电影假定性的画面感、动态感和立体感”[13]。
比较而言,张爱玲的小说大多是可直观化的故事,情节往往一波三折,极富戏剧性。她在小说镜头化的尝试中好用近景和特写,以写人为主,细腻地表现人生际遇、人际往来以及人与文化的矛盾冲突等。其好用主观视角,聚焦人物个性,强有力地介入文本。其小说分镜感强烈,镜头连接性强,且场景集中完整。而王安忆之写《长恨歌》则好用远景和全景,以环境为重点对象,先造景再置人。其常用客观视角,镜头连接感不强,视觉冲击力亦不甚突出。
这样的创作特点使得二人作品的影视化实践效益也天差地别。王安忆著作虽丰,但其作却似乎很难被改编成叫好又叫座的电影。迄今为止,市面上只有《长恨歌》、《米尼》以及小说《流逝》改编的《张家少奶奶》三部。而张爱玲的电影改编在数量和质量上则明显更甚一筹。(如《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王安忆小说“电影化”叙事的失败,但实则却恰巧是她的突破所在。
首先,相较于张爱玲常用固定长镜头表现对于文化的关照和人性的体悟,王安忆更倾向于角度和景别多变的运动长镜头与空镜头的交织使用,并独创了“鸽子视点”,选取上海最具民间特色的弄堂为背景,将其对于上海的理解蕴藏在灵活移动的画面之中。运动镜头和场面调度并行,可以兼顾到人物情感的细微变化和人物关系的微妙传达,更要紧处在于加深都市气质的可感性、都市体验的深刻性以及现实的无限多义性。不动声色地传达作者的隐含情感的同时,又造成更为强烈的间离效果,总体上表现出一种宏大包容的文化姿态。
《长恨歌》体现出作者的城市观。她以都市之眼观人,展现二者的紧密联系,以含蓄的态度探索上海隐性的文化之根,将不稳定的、流动的、藏污纳垢的“民间”文化更为妥帖地展现出来,揭示出“民间”的多层次状态。《长恨歌》也折射出作者的历史观。“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14]如果说张爱玲认为“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到处都是传奇……”[15]王安忆就戳破了这座五光十色、传奇迭起的城市的表皮,揭示了所谓“传奇”的本质,将现代都市的“虚拟性”与人生际遇的无常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她将王琦瑶背后宏大的上海文化与历史浇筑为一个类型化的所谓“传奇”的人物“王琦瑶”。但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表述。当王琦瑶的传奇个性最终消融在千千万万个“王琦瑶”的共性之中,她的经验不但不足为奇,更是这种文化“虚拟性”的最好诠释。因此,所谓的“传奇”就被消解了。剥去华丽的外壳,“传奇”的王琦瑶不过是最终湮没在“传奇”的虚幻泡沫中的无名人,这背后是作家对于城市文化的驻足深思。“电影化”的表现方式,则以更直观的图像化营构表现都市的气质与都市人的生存经验,能够更具冲击性地展现大文化内质与小生存体验的绞合与互动。
其次,繁复的句式和多义性的词汇系统与电影要求的分镜头形式、叙事的片段性以及鲜明的造型元素相去甚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是文学表达独立性的展现。“长镜头”和“空镜头”的高频使用意味着画面冲击力弱、叙事节奏慢。但“空镜头”隐喻迭起的同时,却可将人物心绪的微妙与复杂层层深化;细致的“长镜头”运用恰如其分,则能在抽象化的美学营造与诗学传达中悄然蕴藏作者的文化思索。《长恨歌》难拍并非是因其叙事有瑕疵,而是因为作家写作的重点和目的不在于写“传奇”的人或情节,而是要表现一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其镜头连接性不强的缘由在于:作家有意识的镜头化表达大都被其同样有意识的文学化表达隔离开了。例如作者写蒋丽莉死前一周与王琦瑶的互动时有意识地将之镜头化,但之后再回到情节中时叙事时间已然过去一周,蒋丽莉最终死亡。这其中的空隙是由一段作者关于“歌哭”的叙述填充的,这种细密繁复的语汇表达是难以被转换成镜头的。正因为此,王安忆的《长恨歌》将“电影化”技法与文学语言的独立表达良好地结合在一起。既能保证文学表达免于被“电影化”表达过度侵蚀,又能通过巧妙的视点选择与“长镜头”和“空镜头”的交织运用等独特的“电影化”手法达成图像与表意的良性互动。
四、结语
就“电影化”叙事而言,王安忆的《长恨歌》以“鸽子视点”统摄全文,展现出上海恢宏且包容的文化之姿。而“长镜头”和“空镜头”的交织运用则不仅暗含着作者审视城市文化的客观倾向,也实践了这两种镜头表达写实美学的特征,营造出真实可感的“上海气象”。相比于传统海派作家的作品,《长恨歌》在文化深思、城市体验开掘以及保持文学表达独立性等方面有所突破,开辟了新海派的方向,表现出对于上海的城市文化更为冷静、理性乃至决绝的内省及判断。
——笔画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