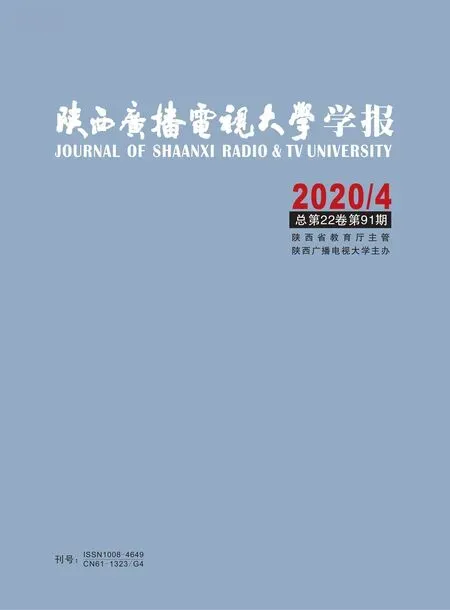论孔子的政治教化思想在教育上的成就
——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中心
薛 媛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开放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8)
孔子思想中时常透出强烈的政治关怀。当然此所谓政治不是现代意义的狭义政治。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分工越来越细,连学术也日趋分化细化。但先秦时代并不像今天这样区分出哲学、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美学等等诸多门类。那时候的共同关注是根本之“道”,虽然这种关注有旨趣、侧重、方向之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定位为一种“整全式”的关注。当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他很可能并不是专对政治而言,或专对道德或教育而言。孔子时代还没有“政治”、“道德”、“教育”这些具有现代学科指向的概念。从领导学角度去解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并不等于说这句话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解读;而是说,这句话与孔子所说的大多数话一样,包含着极为精深的道理。本文意在探究道理,并择其于领导之道有所启示者而开掘之,不等于指认其道即是领导之道也。
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断句疑窦
这句话出自《论语·泰伯》,是单列的一句话,没有上下文。原文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表明是孔子所说,但这一说并不是回答谁的问题,原文没有问答的语境和前后文。这使“子曰”后面的内容颇为费解。事实上,这句话历来岐解纷出,莫衷一是。到近现代,人们受新思潮的影响,更容易形成以今度古的思维模式,用现代的一些知见去推揣古人。这就更增加了正本清源的难度。至少从语法上看,这句话可以有五种断句方式(甚至更多):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五种断句法都能成立,没有语法问题,意义也说得过去。可是,不同的断句构成的意义的不同和深浅却是迥然有别的。第一种断句最为通行,获得较广泛的接受。但究竟哪一种才是孔子的本义?按说,这句话中的两个关键字,“由”和“知”,处于对列地位,可以也必须视为动词。“由”的意思可理解为“顺随,遵从”,与“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之“由”意义相同。至于“知”的意义,人们第一感觉就是“知道,明白”。这样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出现了疑难。
先搁下第一种断句,且看后几种断句的意义。第二种断句始自康有为和梁启超,把“可”理解为“认可”,把“使”理解为“让”,句意为:老百姓认为可行的,就让他们如此干下去;老百姓认为不可行的,就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才是对的。第三种断句把“可”当成“可以”,把“使”当成“指使”,大意是:老百姓可以指使的,就让他们遵从;不可以指使的,就要晓谕他们,让他们明白。第四种断句意思为: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不可遵从的话,就要晓谕他们,让他们知道。第五种断句意义与第四种差不多,只是改成了设问语气。
可以看出,这四种断句语法上都没问题,可是句意却毫无深意,几乎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训诫而已,与废话等同。难道孔子只是想表达一些常识性的废话?众所公认,《论语》记载的孔子的话,是以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深邃的人生反思作为基础的,极富学理意义。是不是真如黑格尔所说,孔子只不过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说出的不过是一些“毫无出色之点”的“常识道德”?毋庸讳言,《论语》确实没有多少“思辨”特色,但能说它没有什么深邃的道理吗?一部影响中国几千年的经典就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词句之堆积?这是说不过去的。事实上,这四种断句都不可能是孔子的本义,只不过是后人以今度古玩弄出来的语言游戏而已。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包含不少儒家和道家的珍贵文献。其中有一篇《尊德义》,文中一段话为后人理解孔子那句话提供了重要线索,可以算是一把打开疑难的钥匙。摘录如下:
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
很明显,《尊德义》这段话就是在阐释孔子的话,句式结构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而”字,“由”变成了“道”(同“导”)。按此,孔子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至少从第一直觉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意思是:老百姓可以顺导他们而行,不可让他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后世很多人就是从这种意义去理解的,并因此给孔子戴上了愚民主义的帽子。如郭沫若谓:
孔子说:对于老百姓,只能让他们照着(统治者的)命令去做,不能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是孔老二献给奴隶主贵族的愚民政策。(《论语批注》,1974)
郭沫若把“民可使由之”的“之”理解为代词,指代“统治者”。可是“不可使知之”的“之”他却不作同样处理。这种理解当否,容后详论。
事实上,不仅现代人倾向这样理解,更早时候的人们也是这样理解的,尽管当时并没有“愚民政策”的称谓。朱熹《论语集注》有两条意见可参考,一是朱熹自注,一是引用程子注:
朱熹云: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圣人设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户晓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尔。若曰圣人不使民知,则是后世朝四暮三之术也,岂圣人之心乎?”
《孟子·尽心上》也有一句话,似乎就是在解释孔子的话:“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对此,朱熹注云:“著者,知之明。察者,识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以然,既习矣而犹不识其所以然,所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钱穆在解释孔子的话时引用《孟子》这段话,并引《中庸》相互参证: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
钱穆认为“民性皆善,故可使由”,这是非常精到的见解。他认为在上者不能在使民由之之前使其知,这样不仅无效,而且会荡惑其心思,导致天下多故。通常说,能感觉的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能理解的就能更好地感觉。按钱穆之意,“由之”之前,不宜“知之”,此固然在理;但“由之”之后,何故还不能“知之”?这是说不过去的。钱穆接着说:“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这就是说,最终还是会知的。既然最终还是会知的,为什么“不可使知之”?这不禁让人纳闷:此间究竟有什么玄奥,只能让老百姓“由之”,而不能“知之”?
面临这些疑难,现代人无可解释,于是只能归之于“古今有不同之是非”。如李泽厚所云:
这两句当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大诟病。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如所引注,这在古代并不奇怪。古代的“民主”正是“为民作主”,“民为贵”也只是这种意思,而并非人民作主的现代民主。(中略)古语亦有“民可与乐成,未可与虑始”,均同一经验,不足为怪,不足为病。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是今日的是非。
李泽厚区分了“为民作主”(中国式)与“人民作主”(西方式)的根本区别,可谓击中要害。但问题是,以“民主”为讨论中心,并把这一切归结为古今有不同之是非,这等于把孔子原本意蕴丰盈的话降低为一种浅层理解。“民主”不是一个中国经验,至少不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经验,而是一个源自古希腊的西方经验。孔子原话不可能只是在谈论一种治民之术,而是关乎根本之“道”的。
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义探究
上述理解方式之所以出现不可解之疑难,原因很可能是人们对“知”字的望文生义,第一感觉就错了。事实上,“不可使知之”的“知”不是“知道”,而是别有意义。“知”在《论语》里确有“知道”之意,如“知我者其天乎?”(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此外,“知”还有“知遇,优遇”之意,如“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卫灵公)。可是在“不可使知之”中,“知”不可能是“知道”,因为这面临不可解的疑难,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那“知”该作何理解?
在孔子原话中,“知”与“由”相对而言,故解“知”需结合“由”。“由”并不费解。《尔雅》训“由”为自:“遹、遵、率、循、由、从,自也。遹、遵、率,循也。”郭璞注:“自,犹从也。”《诗·小雅·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郑樵笺亦同:“自,从也。……善言从女(汝)口出,恶言亦从女(汝)口出。女口一尔,善也恶也,同出其中。”据此,“由”可理解为“自从,顺从”。《尔雅》训“知”为匹配:“仇、讎、敌、妃、知、仪,匹也。”《诗·桧风·隰有苌楚》云:“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郑樵笺:“知,匹也。”许慎《说文解字》训“知”为词:“词也。从口,从矢。”“词”当然是名词;而孔子原话中“由”与“知”均为动词。综合义理、逻辑、语法等考虑,结合孔子整句话看,“民可使由之”与“不可使知之”当为分别指向两种不同的教化方式:前者指向“身教”,后者指向“言教”。“不可使知之”之“知”即由“词”引申而来,作为“言教”之旨,可训为“主持,执掌”,亦含有“干预”之义(详后)。
“知”之作为“主持,执掌”,见于《易经·系辞上》:“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大始”之知相当于“为”,与下句“作”意近互文。《经义述闻》引王念孙曰:“知,犹‘为’也,‘为’亦‘作’也。‘乾为大始’,万物资始也;‘坤作成物’,万物资生也。”《左传》襄公二六年:“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此“知”亦为“主持,执掌”。《国语》有“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之句,亦为此意。由“主持,执掌”之意,可引申出“干预,过问”之意,如《世说新语》:“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即为此意。按孔子原话,“不可使知之”之“知”作为言教,可解为“干预”。这可结合郭店楚简获得圆满解释。《尊德义》“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前一句是对孔子原话的重述,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解释,即“不可强也”是对“不可使知之”的进一步解释。由此可知,“不可使知之”之“知”即近于“不可强”之“强”,意近“干预”。如是一解,意义豁然贯通,朗然无碍,一切愚民专制之说皆可免谈。
应该指出,从古汉语“之”字语法看,原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之”字应视为动词缀语,补充音节,并无实意。“之”不是代词,既不是指代“民”,也不是指代某个施动者(王、统治者、在上者)。孔子原话可以省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意义不变。如是,“知”为“干预”(言教),则孔子原话意义甚明,亦不违背常理,其意无非是:民可顺导,不可干预。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顺其自然去引导他们,不可以强力去干预他们。前者是身教之感化,后者是言教之灌输。
三、“政者正也”与教化政治
孔子之所以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内在根据是以“仁”为核心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从义理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然结论。梁启超说“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可谓确论。孔子之“仁”,虽不可定义,却可体悟自得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子贡问仁,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的意义起点是孝悌,但不限于家庭伦理,而是推己及人,辐射整个社会。“孔子言仁,实已冶道德、人伦、政治于一炉,致人、己、家、国于一贯。”
基于仁治理想,孔子偏重教化,也就十分自然。教化不同于治术。治术在某种意义上脱不了干预性(知之),而教化则以体验为内在原则,以感化塑造为根本指向(由之)。所以,在上者以身作则显得尤为重要。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还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孔子还用风与草来譬喻上行下效之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在上者均能修身以正人,就能达到“不令而行”,“无为而治”的状态。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盛赞尧舜,认为二人达到了无为而治的境界。其赞舜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其赞尧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孔子认为,舜所做的无非是“恭己正南面”罢了,尧所做的无非是遵循天道(“则天”)罢了。尧舜所做,其精神实质正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上者只需依天道而行,由上及下,自然风化。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专门论及教化导民之方,与孔子之意恰可互证。其言曰:
君子之于教也,其道民也不浸,则其淳也弗深矣。是故君子亡乎其身而存乎其辞,虽厚其命,民弗从之矣。是故威服刑罚之屡行也,由上之弗身也。昔者君子有言曰:战与刑,人君之坠德也。是故上苟身服之,则民必有甚焉者。
这里说,君子之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身”(以身作则),一种是“辞”(停留于口头)。如果仅停留于辞(“言教”),而不去身体力行(“身教”),那么道民就达不到“浸”的状态(近于“润物细无声”)。威服刑罚之所以避免不了,屡屡见用,就因为在上者不能身体力行,施行身教;如果在上者施行身教,身体力行,在下者必会效仿,且会过之而无不及(有甚焉)。
那么,在上者如何身教呢?答曰:不能停留在末流之上,而要返本穷源。而“本”、“源”安在哉?即在民之所“由”也。《成之闻之》下一段说:
是故君子之于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返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也者。(中略)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入矣。
从其所由也就是反其所本,此即“民可使由之”之谓也。如果不从其所由,不反其所本,就不会见效,“虽强之弗入”,此即“不可使知之”之谓也。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民之所“由”就一定是“本”之所在?这是因为,民之所由即来自民之存在,换言之,民之存在即是民之生存意义之来源和根据。伽达默尔在论“教化”概念时说:“对于‘教化’这词我们所熟悉的内容来说,首先要注意到的是‘自然造就’这个古老的概念——它意指外在现象(肢体的形成,臻于完美的形式),并且一般意指自然所造成的形式(例如‘山脉形成’)……教化后来与修养概念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首先意指人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的特有方式。”既然教化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造就”,这就说明,民之生存意义与生存德性并非来自外铄,而就来自民之生存本身:民如何存在于世,民就有如何的生存结构和意义结构。此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深层根据所在。
由此,可以总结出两种教化模式:一种是“知之”:滞留于言辞的外在的干预和灌输,其本质是说教性的,谓之言教;另一种是“由之”:顺随“自然造就”原则,发掘民之内有本性而顺从之引导之,其本质是以熏陶感化为指向的“人文化成”精神,可谓之身教。
四、人治与法治的互补
“由之”指向身教,“知之”指向言教。通过身教“由之”而来的,是“君子”人格之养成。君子人格是孔子仁本政治的自然要求。这使孔子的政治旨趣与西方自柏拉图“哲人王”以来的政治旨趣殊为不同。后者强调以智治国,前者强调以德化人;后者倾向于法治,前者倾向于德治。“近代论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与治事之二端。孔子则持‘政者正也’之主张,认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与教育同功,君长与师傅共职。……而政治社会之本身实不异一培养人格之伟大组织。”在西方,政治与社会有一比较分明之界限,藉此而构造国家单位;而在孔子那里,政治与社会被“德”化成一片,经教化而养成文化单位。
主张德治,其实质就是主张仁治,归根到底是主张人治。仁治是第一大端,人治是其第二要义。德治必须也只能通过人治来落实,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君子”人格之重要性,屡屡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以彰著君子之意义。“君子”是孔子人治思想之结晶和直接表露。但须知,孔子“人治”始终与“仁治”内在勾连,无分彼此。按孔子之理路,人心不违仁乃是政治之起点和前提。《中庸》“哀公问政”一节是孔子人治思想最集中之表达:“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如是,人、身、道、仁贯通,人与仁浑然一贯,不可割裂。
当然,孔子并不完全否定法律制度之作用,但他始终认为刑罚之用有限,仅以补教化之不逮。一谈到刑罚体制,孔子即露不足之意。如季康子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论听讼,孔子则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最明显是这一段:“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萧公权谓:“孔子之治术倾向于扩大教化之效用,缩小政刑之范围。其对道德之态度至为积极,而对政治之态度殆略近于消极。”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仁道(仁治、人治、德治)只能“由之”,而不能“知之”。仁道诉诸内在本性之开掘(由之),而无法以外力强为烁予(知之)。
总之,就为政言,孔子的根本观点是“为政在人”,一切取决于人。人之教化实亦人之德化,只能“由之”,不可“知之”。孔子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对周礼心向往之,表明他既重德,亦不废制(礼),且要在制中注入“仁”。此“注入”唯可“由之”,不可“知之”。孔子屡言“君子”,其用意自是凸显人治,然非以人治代替法治,而是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如辅车之相依,如心身之共运”。后人喜欢把人治与法治对举,视为两不相容,是因为这种对举剥离了“人治”所固有的“仁治”内涵,从而肢解并误解了孔子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