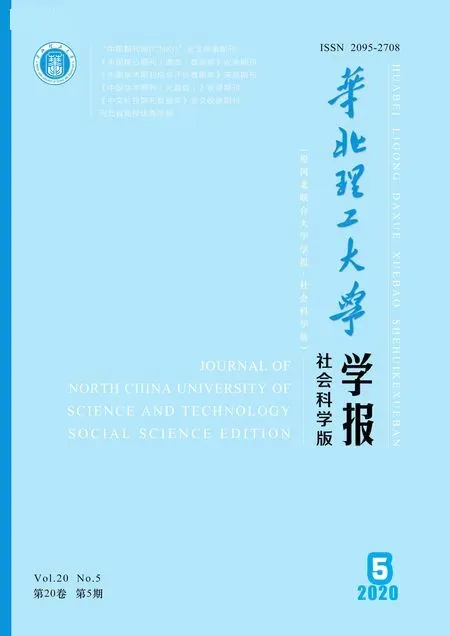语法隐喻视角下的汉日新闻翻译
——以人民网日语版的翻译为例
刘亚燕
(龙岩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龙岩 364000)
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人们了解世界的重要认知方式和途径。Halliday拓展了隐喻的研究维度,从语言的表现形式入手率先提出语法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体现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不仅限于词汇概念,还常常表现在语法结构上,是一种“意义表达变异”的语言现象。Halliday最初根据元功能将语法隐喻划分为概念语法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后经发展和完善,肯定了语篇语法隐喻的构建功能。概念语法隐喻表现为词汇语法和关系过程的隐喻化,通过名词化和动词化等实现。人际隐喻是增强意义协商潜势,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手段,分为情态隐喻和语气隐喻。[1]隐喻源自于重新构建经验现实(概念隐喻)和激活主体关系(人际隐喻)的需求。[2]语篇隐喻强调语法隐喻的语篇效用,体现为元信息关系、文本照应、内部连接和协商语篇组织。[3]Halliday和Matthiessen之后对语法隐喻重新进行归类,有过程、关系向实体的转换,环境向过程的转换、连接成份向实体的转换等13类。[4]语法隐喻认为“一致式”的表达方式与外部世界的事态较为接近,而语法隐喻则是指该“词汇语法”形式与其通常所表达的意义不同。[5]言语主体与外部和内在现实世界进行交涉产生了意义,语法隐喻则是从意义层自上而下对词汇语法层的表达形式做出选择。[6]国外学者对语法隐喻的概念界定,类型及判断标准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国内学者长期以来也做了详细的引介和研究,其中有语法隐喻的理论阐释和模式体现研究(如胡壮麟2000;朱永生2006;严世清2003;范文芳2007;姜望琪2014)、语法隐喻理据构建和识解机制(如丛迎旭,王红阳2013;陈新仁2014;林正军,杨忠2016)、认知理论等的借鉴分析(杨延宁,2016;林正军2017;邹智勇,程晓龙2015)等。由是观之,国内外对语法隐喻的研究日益丰富,著述颇丰,主要集中于介绍、阐释以及修补、完善等方面。然而,“现有的语法隐喻研究大多只探讨同一种语言内部语言表达式之间的隐喻性关系,”[7]运作机制的实际应用性还较为缺乏,从跨语言的角度,特别是语法隐喻与翻译的应用研究涉及不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隐喻是一种内在的语言机制,与思维的联系密不可分。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植根于人类经验,我们借助语言为自己建构经验现实。[4]语言作为意义符号系统的核心,包括内容和表达两个层面,两者相互依赖,构建人类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隐喻普遍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生活和行为当中。语法隐喻是一种语法手段的转换,实现形式不同,核心意义不变,反映了同一命题意义在表述方式上的可选择性和多样化。语法隐喻中,一致式与隐喻式之间表达方式和过程的变体,体现了不同的经验现实与重塑功能。人类经验的隐喻性受到社会文化和语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语言具有社会和认知双重属性,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或种族的语言对同一事件和情境的描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语言结构是对认知的直接映射,源语与译语之间认知方式的改变决定了翻译过程中对语言结构的重组必不可少。翻译中的语言转换体现了一种动态的,符号不断更新的过程。[8]语言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和使用,语言是人类经验的基础,在语码的转换过程中,翻译者需要进行多种语言形式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经验的重塑过程。由此可见,语法隐喻的运作机制与翻译过程的认知操作不谋而合,为其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认知阐释。语法隐喻在翻译方面的研究还很有限,黄国文(2009)、邓玉荣,曹志希(2010)从句子层面分析源语与译语之间可能存在的语法隐喻关系。肖英,吕晶晶(2007)、邓玉荣(2013)、齐佳宁(2014)等探讨了语法隐喻在不同语篇类型中的指导作用。语法隐喻作为一个普通语言学理论,应该更广泛地用于其他语言的研究。[9]翻译实践离不开语法隐喻理论的指导,语法隐喻理论研究翻译中不同表达的选择问题,是一种新探索。[10]此外,从译者可视性方面来看,翻译过程中的语法隐喻现象有助于探索译者主体性的思维轨迹。[11]以汉日新闻翻译语料为分析对象,进一步考察“语法隐喻”概念在不同语言转换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和表现方式,从微观上进行探讨,总结应用规律,为翻译操作提供新的认知视角和理据阐释,增强理论的适用性。
翻译过程中源语和目标语之间并非存在形式与意义的一一对应关系,而是需要利用所在语言系统的表达潜势,进行不同“等价物”的选择,实现语言间意义的有效对等。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常常必须在可以、可能表达原文意义的多个目的语法结构、句型中选择自己认为准确、合适的结构。[12]语法隐喻在翻译过程中的操作表现为源语与目标语在层级之间的重组,或者语法结构上的再映射。隐喻式和一致式在语言中是并存的竞争关系,一致式和隐喻式都具有理据性,其建构都需要付出认知努力。[13]语法隐喻的变异发生在语法层,是不同的语法表达形式转换使用的结果,语法形式或者说语法范畴发生了转换,这就是语法隐喻。语法隐喻通过语义与语法的表达错位,对现实经验进行重新建构,它不仅发生在一种语言内部,也出现在不同语言之间,在翻译活动中体现为语法域之间的相互转移,源语中的语法关系在目标语中常常会发生一些变化。在识解同一个经验时,由于汉日语言类型、思维方式以及译者主体因素等原因,汉日语言的形态各具特点,翻译过程中也经常出现“相同的所指,不同的能指”的现象,译者需要经过不同的选择,在目标语中采用不同的语法结构表达与源语相同或类似的意义。译者对过程的不同选择,必然导致概念语法隐喻的产生。[14]
一、概念语法隐喻的运用
及物性系统的概念语法隐喻成为语法隐喻研究的核心,使其能在理论内部解释更多语言事实。概念隐喻产生的工作机制指小句的成分、小句和小句复合体相互之间的级转移。[4]转换既包括不同语法类别之间的同级转换,也包括不同层次语法结构之间的异级转换,如表达序列、句子组合、小句和小句成分的转换。这种级转移通常会引起及物性系统的选择、词序的重新排列、主位结构和信息结构的调整等一系列连锁反应。汉日新闻翻译语料中,“名物化”是创造概念隐喻最有力的方法,由于动作被静态化,动作实施者被隐化,行文的客观性进一步增强。
(一)汉日新闻翻译中的“名物化”及连锁反应
Halliday认为名词化是实现语法隐喻的途径之一。翻译过程中的语法隐喻映射与汉日语言类型特征的不同关系密切。汉语在句子构建中动词的出现频率较高,动词集结的特征尤为突出。日语倾向于多用名词,使用静态方式进行叙述。“名物化”是创造概念隐喻最重要的手段,汉日翻译中的名物化语法隐喻机制可以将源语中的动态过程变为译语中的静态实体与事物。同时,翻译中语法隐喻的映射过程同时也是信息变化的过程,名词范畴化后作为参与者被重组,各成分所充当的功能角色发生了改变,成分之间可以相互隐喻化。名词化消解显性过程和倾向于主观化的描述,把焦点置于对象或结果上。经过翻译,目标语句子的语体显得更客观、正式,从而使译文更加符合译入语的认知习惯和要求,使表达合乎译语读者的阅读需要。
例1.“身轻如燕”的无人机更可以方便地装入记者的“口袋里”。
译文1.「燕のように身軽」な無人機であれば記者の携行にも便利である。
例2.但这个法宝却不利于苹果支付的推广
译文2.この宝刀が逆にアップルペイの普及拡大にはマイナスとなっていた。
例3.2010年,《云南映像》第二次来到日本,依然大受欢迎。
译文3.10年にも日本公演を行い、相変わらずの大人気となった。
语义、范畴在汉日两种不同语言系统中实例化后,呈现出语法性状的差异。例句中动态范畴向静态范畴的转变构成了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标域之间的语法隐喻映射关系。同时伴随着环境成分等其他成分的级转移,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和作用,语义潜势也随之共现。例1中“装入记者的‘口袋里’”的动词词组在译文中转移为名词词组“記者の携行”,意义凝缩,作为环境成分使用,构成后者的评价对象。而源语中表伴随着环境成份的副词“方便地”在译文中则转为形容动词“便利”,以谓语成分出现,成为命题的焦点。例2中“不利于”的动词转为“マイナス”的名词,例3中的动词词组“大受欢迎”转为名词成分“大人気”,通过语法手段构建,在语义方面,从过程转化为物,将其对象化。同时表环境成分的加强型副词修饰语“依然”则转移为属性成分,即译语中的“相変わらずの”。以上翻译在语法隐喻的认知机制下,发生了词类语法成分的级转移与重组,动态过程名词化后转为静态。同时,例2和例3中还进一步进行语义拓展,增加信息量,于句末附加了“となった”和“となっていた”,体现了名词化后的伸缩弹性,谈论的内容成为话语主题和有界的实体,使实体的变化过程更加自然、外部阐释更具客观性,由于源语中的物质过程变为译语中的关系过程,语篇更显客观、简洁和庄重。
(二)汉日新闻翻译中的“过程变体”:级阶-性状
在语义层面,由过程、参与者和环境的配置组成的一系列言辞能够形成言辞序列。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人类的经验建构在语义层依据复杂程度可分为三个等级,即言辞列、言辞和成分。三者在形式上分别体现为小句复合体、小句和词组。当三个等级之间出现错位,发生级转移时,就构成了语法隐喻。[4]语义层和语法层之间张力的存在和作用导致了语法隐喻的产生。[15]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民族主体之间认知方式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同一命题意义的表达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形式差异。汉日在对同一事件进行描述时,倾向采用不同的扫描模式,汉语在表达概念时多趋向使用多个动词的连动形式,以动态连续的顺序进行扫描,凸显前后的时间关系和过程,而日语则习惯于把握核心动词,以此为中心,突出空间关系的扩展和延伸。因此,在翻译中经常出现语法隐喻现象,修饰成分、核心过程、环境成分等在功能形式上发生变化,由体现级阶的小句复合体向表示性状的词组转变,从顺序扫描到综合扫描的识解切换。
例4.有网友拍下了照片发到了网上,引发网民关注。
译文4.あるネットユーザーが撮影した写真がネットに投稿され、ネットユーザー達の間で注目が集まった。
例5.她有着很多令人瞩目的头衔:日中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前理事长,日本中华书画艺术研究院理事长……她旅居日本20年,一直致力于中日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译文5.日中文化交流センターの理事長、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の元理事長、日本中華書画芸術研究院の理事長など、数々の肩書を持つ呂社長は日本に来て20年になり、中日の文化の発展や交流に力を注いできた。
例6.猪在遛弯儿时很不老实,……。
译文6.散歩中の豚は行儀が悪く、…。
名词强调的是整体事件,突出整体扫描;而动词着眼的是一维时间的过程关系,突出的是过程扫描。[16]语法隐喻是语义系统单位“言辞列”到“言辞”、“言辞”到“成分”、或“成分”中的“过程”到“事物”之间的转换过程。以上例句中,译文将源语中的信息进行重组,通过语法隐喻机制,发生语法结构的变化。例4源语中,表达序列的三个小句“拍下照片”、“发到了网上”、“引发网民关注”是按照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组织排列,译文对其进行“打包”,实现了从经验到逻辑,从过程向事物的转变,短暂的发生识解为稳定的现象,以顺应译者和目标语的心理感知过程,采用偏离源语思维常规语序的结构,时间关系在名词词组内部通过从属的依存关系实现,过程之一的“拍下照片”重构为属性的修饰语“撮影した”。与此同时,“引发”的致使过程被省略,导致部分功能和经验语义的丢失,最终转换为结果的“注目が集まった”。例4的翻译经由及物系统的选择,由行为过程转变为存在过程。例5中两个主语“她”在翻译过程中经过语法隐喻操作,将小句向下级转移为名词短语,浓缩为一个主语“呂社長”,将一段序列向复合句转换,体验由过程变为整体,促成了隐喻式表达。同时,句子内部结构更加严密、紧凑,逻辑关系更为明确。而相较于动词性状,名词性状更具稳定性。例6源语小句中的部分述位在译文中被背景化,与主语结合为名词词组形式,环境转为主位的属性,纳入已知信息,将其余核心述位凸显,通过语法隐喻,译文从零散转向严谨,让文本语义趋于静态和浓缩,实质中心概念更为清晰和突出。
二、人际语法隐喻的运用
级转移是语法隐喻产生的充分条件,但并非必要条件,不是所有的语法隐喻都存在级转移。级阶的阐释范围仅限于经验元功能。人际隐喻和语篇隐喻既没有经历句法结构的重新组合,也没有产生级转移,无法从级阶理论中寻求解释。[17]它们主要体现为网络选择的心理表征,通过不同语法形式的选择表达主观情感,属于纵聚合型语法隐喻。人际隐喻的策略是提升从词组到小句级阶的人际评价。[4]语言的运用以实现交际为目的,翻译过程中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人际语法隐喻操作,反映了不同言语背景下,主观判断与人际关系在语言层面的不同表征,需要通过合理调整和配置语法资源,以达到准确和顺利交流的意图。由于语言中表现人际意义的主要手段是语气和情态,因此人际语法隐喻包括语气隐喻和情态隐喻。Halliday认为,言语功能在交际过程中可以归纳出陈述、疑问、命令和提供四种。不同的语气系统对应一定的言语功能,实现不同的交际目的。例如,陈述语气功能语法对应“陈述”功能,疑问语气对应“提问”功能。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将情态定义为“情态系统的作用是阐述和构建肯定与否定之间存在的不确定领域的意义”。[2]
不同语言中语气隐喻的体现方式各异,对语言系统环境有着强烈的依存性。汉语还根据认知语法的原型范畴理论界定汉语语气副词的范围,将语气副词纳入语气系统。[18]日语属于黏着语,词尾非常发达,变化丰富,在终结句子的同时还可以显化叙述者的心理态度。因此,一种言语功能在跨语言中的语气表现形式常常有所区别。语气语法隐喻是指不同语气域之间的转移和变异现象。在翻译过程中,语气隐喻机制的应用体现在源语的一种语气域向译文中的另一种语气域的转换,译者对语气表达手段的选择带来言语行为效力和语用力量的变化,以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语气类别,促使跨语言的交流顺利进行。情态是通过语法形式反映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19]语言资源不仅可以用于表达命题,还能对所述内容做出评价,在确定性、承诺度等方面进行选择。[20]情态系统有主客观之分,前者表达说话者对事物的主观判断和态度,后者表现在事物存在的可能性评价程度。情态意义的表达形式主要有情态副词、情态动词、谓语的扩展部分和小句形式等。翻译过程中的情态隐喻体现在不同情态意义和取向之间的转换,由此,交互意义也随之增强或减弱。
例7.没想到这台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电动麻将桌“不堪重负”,竟然短路、烧了起来。
译文7.中古で買ったこの麻雀卓が、「使い過ぎた」のか、ショートして、燃えた。
例8.无人机将为新闻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译文8.無人機はメディア業界に新たな発展のチャンスを与えてくれるだろう。
例9.高昂的设备成本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译文9.巨額の設備コストがかかることが、その重要な原因の一つといえる。
例10.萌宠也可美甲?时尚美甲走红宠物界。
译文10.可愛いペットにネイル、ペット界でファッションネイルが人気。
以上例句译法灵活,富有弹性,译语与源语之间的基本语义保持不变,源语与译语之间发生了语气和情态的变异表达,呈现出主观与客观,显性与隐性的转换。例7中的语气副词“竟然”与附加小句“没想到”相呼应,表明作者针对命题事件的态度和评价,反映了主体对事件的预期与结果之间强烈的对比关系,体现出明显的主观性。而对应的译文对经验进行重新识解,不同的思维图式被激活,在语气上仅使用“か”将之前的陈述句转换为疑问句式,增加互动的语义潜势,态度缓和,使表达的内容具有外部客观性。例8体现了不同认知域在意义相似基础上的映射。源语使用的是肯定陈述,主体的控制力强,而译文中的句末则添加了推量句式“だろう”,融入了叙述者主观猜测的协商语义潜势,控制力减弱,其中的判断和态度成为该句突显的部分,利用人际关系的调整影响读者的评价和态度。例9中译文在源语的基础上将谓语部分延伸,添加了“といえる”,在认知情态上进行调和,事物命题随之由必然性转向可能性,趋向客观化,使语言在不同语境下更具说服力。此外,语调作为语气表达的标记之一,表明了主体在特定语境中的态度和情感。体现了译者处理信息的心智活动,经验的识解资源得以扩展。例10的源语中,疑问符号“?”是语气语调的辅助工具,与前文中的“也可”共现,目的不在于获取信息,而是发挥感叹功能,融入主体的情绪,表明其对萌宠美甲感到不可思议的惊讶看法,同时还可引起读者的共鸣和阅读兴趣,而对应译文的语气范畴发生了改变,原有的疑问语气不复存在,陈述语气取而代之,由主观性评价转换为客观叙述事实的陈述功能。译文中的结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效果,体现了译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对事物的认知态度通过跨域映射前景化。可以说翻译过程中人际隐喻的操作扩展了语言的意义潜势,通过确定性的极性表达与交流可能性的惰性表达之间的转换,在情态系统的显隐纬度,主客观的取向间进行选择,从而达到更加深层的交际目的。
三、语篇语法隐喻的运用
语法隐喻是一种语法形式的偏离,其中语篇隐喻具有语篇衔接的特征最为突出。[21]语法隐喻具有语篇促成性。根据隐喻发生的范围和体现方式,可区分“语篇语法隐喻”,即发生在小句内部、由语法结构变化体现的语篇隐喻和“织篇隐喻”,即跨越小句范围、发生在语义层面、由非语法结构性的衔接机制体现的语篇隐喻。[22]语言的演变源自语义层与语法层的张力,语义引力体现了语义与语境的关联程度。翻译中源语与目标语的语义虽然具有相似的同源性,但在表达方式等语法结构上存在语义密度和引力强弱的差异,体现出相同所指、不同能指的形式变体,即语法隐喻。语篇概念中,衔接的特征最为突出。[23]衔接反映了语义上的联系,语篇中的某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理解至关重要,那么这两者之间就具有衔接的关系。[23]语篇语法隐喻主要通过衔接系统体现出来,具体表现为篇章内部句子信息之间的语义连接。语言的衔接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照应、省略和替代、连接词和词汇衔接四种形式。翻译过程中,语篇语法隐喻运作表现为源语与目标语之间跨越语法和词汇层次,通过小句之间有机组合方式的变异,进行衔接方式上的转换。连接词是反映语篇中信息之间关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将语篇组织原则概念化为语义码显现出来。汉语中语言的语境依赖性较强,意合特征决定了其语篇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常常表现为零形式,语义引力较强,压缩的语法结构较多。而日语的形合特征要求使用外显的连接手段将语句概念间的关联性明朗化,语义引力较弱,语法结构压缩的较少。
例11.手动将iOS设备的日期设置到1970年5月或之前时间,你的iOS设备将无法重启。
译文11.システムの日付を1970年5月以前にするとiOSが再起動しなくなる可能性がある。
例12.园林专家邬志星在接收采访时表示,郁金香确实不宜种在室内或教室内,因为郁金香花中含有有害物质,……。
译文12.園芸専門家の鄔志星さんは取材に対して、チューリップを室内や教室内に置くのはすすめられないとした。その理由は、チューリップの花は、有害物質を含んでおり、…。
例13.李瑜在大会现场表示,“全球闺蜜联盟大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集合了全领域多维度角色的闺蜜经济生态圈。希望把全球闺蜜联盟大会打造成一张全球闺蜜的名片,每一届大会都将是全球闺蜜的盛宴,同时全球闺蜜也将携手共同探讨闺蜜生态圈更好的发展方向”。
译文13.李瑜氏は、大会において、次の通り述べた。世界女性の親友連盟大会は、開放的なプラットフォームであり、各分野で多角的な役割を発揮する女性の親友経済生態圏が一同に会する場となっている。同大会が、世界女性の親友の名刺代わりとなり、各期の大会が女性の親友経済の盛会となると同時に、女性の親友生態圏がより良い方向に発展するよう世界中の親友が共に探索を続けるよう期待している。
语篇隐喻关注小句的衔接与连贯。一种语言在语域或语类上常倾向于某种特定表达,而其他表达就不容易被接受。翻译中,目标语和源语的语义内涵和概念内容相同,但认知和编码方式经常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通过对源语进行语法隐喻衔接的操作,实现了目标语语篇的连贯和流畅。汉语一般通过词序体现事理逻辑,而日语则需要采用更多的编码,以实现语篇内在的统一。例11中源语的前后两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处于较弱的隐性状态,而译语则将其中的内涵以表层形式“と”显性化,凸显语篇的层次井然与整体性,表达具体,便于目标读者理解。例12的源语中使用连接词“因为”体现前后信息的衔接,而相应的译文则通过语法隐喻,将源语中的逻辑语义由名词性词组的经验语义来表现。名词词汇衔接“その理由”将前文的述位结构继续转化为下文的主位,指示语“その”上指“すすめられない”的整个事件行为,衔接语篇上下文,承载了与前文相照应的语篇功能,结构更加紧凑,为后面的语篇提供了基础,实现更深层次的语义连贯。语篇中的照应还可以发生在长篇的段落上,例13中的译文相比源文增加了名词词组“次の通り”,与后指信息构成详述关系,它在译文中作为一个实体指代其后的整个文章段落,语篇之间的联系由前者省略的内隐转化为显性的连贯,逻辑分明,使得语篇中的信息衔接更为紧凑。翻译过程中,通过语篇层面的隐喻思维操作,汉语源语中的内隐逻辑内涵关系转换为了表层显化形式,以顺应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表达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内容,它体现人们对主客观世界的经验。隐喻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认知能力,语法隐喻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语言翻译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翻译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经验的重塑过程,语法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各有差异,常常体现为一种倾向性。新闻语篇的汉日翻译过程在语法隐喻的认知机制操作下,语法符号被重新编码,语言中的经验意义和知识结构被重建。从译例分析来看,相较于源语汉语,目标语日语的主观印记强弱,主客意识的显隐,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性均出现了变化。而在语篇的展开过程中,译语的衔接和连贯更加高度化,逻辑关系显得更加严密。此外,译语的信息结构被提炼和浓缩,凸显了重点信息。不同语言间既存在共性规律又蕴含个性特征,翻译中语法隐喻的认知运作赢得译文读者在认知层面上的认可,在经验和知识结构上的接受,从而促进跨语言交际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