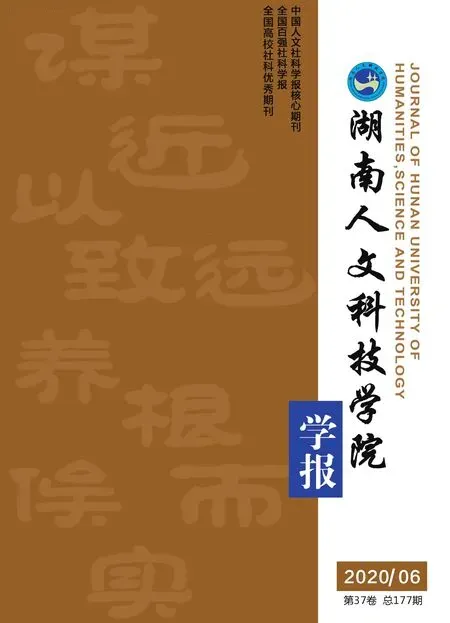梅山民俗文化翻译的可接受性分析
万正发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中国民俗文化乃中国特色文化之精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外国游客迅速增加,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凭借独特的民族风格、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正逐渐迈向国际舞台。梅山民俗文化作为民俗文化之瑰宝,以其得天独厚的地域风格和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多姿的民族风情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旅游因其满足了域外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多种心理需求,而被视为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现已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来华的外籍游客中只有少部分人旨在游览风景名胜,更多的人是被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和民间艺术所吸引,猎奇异己的异域文化心态是其来华旅游的重要原因。在“文化走出去”的方针指引下,我们既需要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又要把外国游客引进来进行文化交流,在跨文化交际的民俗文化互识、互证和互补进程中,文化的外宣翻译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民俗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个性与共性
在对外宣传和传播的中国文化内容中,民俗文化因其独具特色的异国韵味容易引起域外读者的目光和兴趣。影视文化和国际旅游业的发展,社交网络和多模态媒体的助力,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流,不同国家、民族充满生活气息的民俗文化成为文化互识和思想交流的主要内容。
《汉书》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同一国家、民族因地域差异也会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更何况是漂洋过海、跨越国界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是人类凭借其独有的思维方式创造的,不同民俗文化之间因为地域种族的不同存在着一定差异性。民俗文化的个性与共性密不可分。民俗文化离不开共性,没有共性,不同民族的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其他民族的民俗,民俗文化也离不开差异,没有差异性的特征,民俗文化就失去了独特的魅力和吸引力[1]。因此,越是奇特的异域民俗,便更加具有吸引受众的优势。
民俗文化的共性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它存在于各民族的民俗个性中,需要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进行挖掘。文化比较就是一个互识、互证和互存的过程,既符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发展要求,也是建立文化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民俗文化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在相互理解、相互证明、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保持和彰显本民族的鲜明文化艺术特色。
翻译是传播民俗文化最根本、最直接的方式,无论是展示各国风俗文化的文学作品,还是多模态文化样式,其展示内容最终的转化手段都离不开翻译。翻译作为一种最直接有效的媒介,帮助不同文化、语言的读者感受异国民俗的魅力。精准得体的翻译有助于跨文化交际者对于不同民俗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
二、梅山民俗文化的可译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民族的语言都存在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语言又是思维和认知的工具,人们通过语言来认知世界。语言的文化功能和思维功能使语言形成一个中间的认知世界,从而使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展开交际,以完成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即交际功能。人类作为生活在统一世界的大集体,必然拥有一定的共享知识,正是这部分共享知识,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随着跨文化交际的频繁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人类共享知识将越来越多,从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更加容易交流。奈达认为,世界上各种语言的基本结构至少有90%是相似的,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有足够的想象力和经验来理解另一民族在行为与价值观念方面与自己的不同之处[2]119。
跨文化交际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采用同一语言进行交际。正如不同文化背景的运动员可以在统一的国际比赛规则系统下同场竞技一样,不同国家的人也可以使用同一语言进行文化交流,这就使民俗文化翻译具有可行性。鉴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频繁地进行跨文化交际和源源不断的信息交换,人类共享知识将无限增加,使一种语言文化中所特有的事物,最终都能被另一种语言文化吸纳、表达。由此可见,一种语言承载的文化是可以通过另一种语言进行表达的。民俗文化就具有了可译性[3]。
然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维度、共享知识范围以及信息交换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再加上文化意象的空缺和语言形式的巨大差异,使民俗文化的翻译具有可译性限度,需要译者努力消除语言文化差异的障碍,通过翻译向目的语受众传播丰富多彩、绮丽多姿的民俗文化。
梅山民俗文化涉及领域十分广阔,涵盖民间神话、民间叙事长诗和民间故事、梅山民间歌谣、民间小戏、民间曲艺、民间寓言、民间谚语等。例如梅山民间幻想故事(或称“梅山民间童话”)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的民间故事就有很多相通之处,其中的狼外婆型故事、狗耕田型故事等主题故事在世界流传甚广。具有独特民族和地域风格的民俗在国外甚至是在国内几乎不可见,例如梅山民俗中的“舞春牛”是上梅山冷水江市东南一带土著族群的迎新春文化习俗,在这一文化活动过程中,有一组原始朴素的舞蹈动作:犁田、耙田、播种、插秧等,是古梅山土著族群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生活步入到农耕稻作生活阶段的历史进程记实。有过跨文化交际基础的外国友人可能见过中国的舞龙舞狮(dragon and lion dances),但肯定没有见过舞牛。同样,梅山民俗文化中丰富的民谣和梅山傩戏(Nuo dance: an ancient ritual performance to dispel evil and pray for good luck)在对外翻译传播时也具有可译性限度。在翻译这类民俗的时候,只是表达字面意思肯定不够,还需要通过文内注和脚注等方式呈现民俗的历史发展、活动方式和文化内涵。
要实现民俗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语际转换、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的确存在很大障碍,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需要在不同民俗文化的个性之中寻找共性,在可译性限度和可接受性之间实现平衡。
三、梅山民俗文化旅游翻译的可接受性
梅山民俗文化是至今仍存在于湖南中部的远古文化遗存,既包括紫鹊界梯田、茶马古道等物质文明,也包括梅山武术、滩头年画等非遗产品。梅山文化承载了湘中地区丰富的民俗文化精神,是湘中文化旅游的灵魂[4]。
曾有学者质疑梅山民俗文化汉英外宣翻译的价值。1980年,在法国发现了瑶族移民的手抄汉字巫术,其中有内容表述瑶人死后灵魂需回梅山认祖归宗。法国远东学院和中国学者联手,在梅山峒区展开瑶传道教的调查,该学者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汉法翻译,而不是汉英翻译。这种观点将梅山民俗文化局限于认祖归宗,难免有失偏颇,严重缩小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范围和功能。众所周知,英语的使用早就不限于英美等国。英语乃是一门世界语言,世界各地旅游目的地的信息基本都用英语表达,而且梅山民俗文化对外国游客的魅力和吸引力毋庸置疑,梅山民俗文化汉英旅游翻译研究的价值远远大于其他语种。
翻译是跨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桥梁。功能派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的可接受性作为功能翻译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评判翻译成败的一个重要指标。译文的可接受性指译文接受者对译文能否完全理解,以及译文是否明白易懂,可接受性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翻译的效果[5]61。翻译的可接受性并不意味着为了迎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而盲目采用归化翻译策略,例如将梅山民俗文化中的“角抵戏”翻译成“acrobatics”,或者是把“傩戏”翻译成“sorcery”,这样会失去梅山民俗的独特文化内涵。再如,梅山民俗中的“三朝礼”(又称“洗三朝”“打三朝”“吃三朝饭”)历史悠久,文化内涵非常丰富,且不同乡镇的民俗又各有不同,相同点是庆祝新生婴儿的出生,因此可以译成“new-born ceremony”。有的译者为了迎合西方的文化心理,认为“洗三朝”有给新生婴儿洗澡的习俗,与西方基督教的洗礼文化类同,故而将“洗三朝”翻译成“baptism”,这是不可取的。不明事实的外国读者还会以为中国人有信仰基督教的传统。
另一方面,单纯的直译、音译等异化的翻译方法又会让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如果简单地把“梅山傩戏”“滩头年画”“珠梅抬故事”译成“Meishan Nuo Opera”“Tantou New Year Painting”“Zhumei Story-lifting”,外国读者看到后肯定是一头雾水,无法接受。这里必须要加上注释,并辅助以图片,甚至是相关视频链接等多媒体载体才有可能让域外读者明白并接受。为了有效解决梅山民俗文化翻译问题,准确地传达梅山民俗文化的魅力和文化内涵,可以遵循民俗考察与体验、节译、异化为主、适度归化和多模态载体等翻译策略,采用音译+文化补偿、直译+文化补偿、使用脚注、直接描述等翻译方法[6]。
文化内涵丰富且可接受性强的译品,对目的读者会产生很大的吸引力。民俗文化的翻译对于现代旅游具有深远意义。民俗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好的梅山民俗文化翻译作品能使外国游客在游览隆回花瑶、紫鹊界梯田、茶马古道等物质文明景点的同时,领略梅山傩戏、梅山武术、滩头年画、珠梅抬故事等非遗文化的风采,使他们乘兴而来,满意而归,留下美好回忆。此外,梅山文化圈所属各地方政府及部门应改变以往各自为政的做法,充分整合政府部门与科技、文化、旅游、高校和媒介等领域的优势资源,集中统筹优质民俗文化展示,并组织文化翻译方面的优秀人才,像中国古代开办佛经译场一样合力翻译梅山民俗文化,通过立体综合的传播形式将梅山民俗文化的精髓客观地展示给海外受众。
译者在翻译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更重要的是肩负文化交流和传播重任,要有一种民族文化责任感,不能一味迎合国外读者的思想倾向,而要有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身份认同,传播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我们在对外传播民俗文化的过程中,也不乏存在迎合西方的现象,例如同样是对封建社会进行猛烈批判的电影,为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能获得这么多奖项,得到“国际认可”?在缺乏充分的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一国民族对异国异族的印象往往是社会想象力参与创造的结果,其本身就带有对异国民族倾向性看法和偏见。尤其是当一些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优于其他国家时,其国内的文学文化作品会出现对其他国家民族形象的虚构,甚至是贬斥,国民的集体意识和审美趣味往往也会带有这样的倾向性。西方世界最喜欢以探讨人性为借口去看“第三世界国家愚昧落后”话题的电影,西方世界多少年来盛赞过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基本都是战争、独裁、贫穷等题材。《大红灯笼高高挂》描述的是中国旧社会的一种妻妾成群的现象,似乎带着西方窥探了后院里的众生相,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从鲜明的“婚姻民俗”中窥视中国男性绝对权力的糟粕。事实上,我国众多民族民俗文化中存在很多优秀的婚姻民俗,各种嫁娶风俗异彩纷呈,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激励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明教化的水平。在文化传承中,要不断革除陈旧的、过时的旧文化,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在传播传统民俗文化时,我们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四、结语
民俗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差异与共性使梅山民俗文化具有可译性和译文的可接受性。独具特色的梅山民俗文化决定其在与目的语受众进行交流和传播时存在可译性限度和可接受性限度。限度的大小取决于译者和传播者在翻译和传播时运用的策略、方法和渠道途径。旅游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方净土,承担着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而且,多模态载体也可以在旅游文本中充分发挥作用,促进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