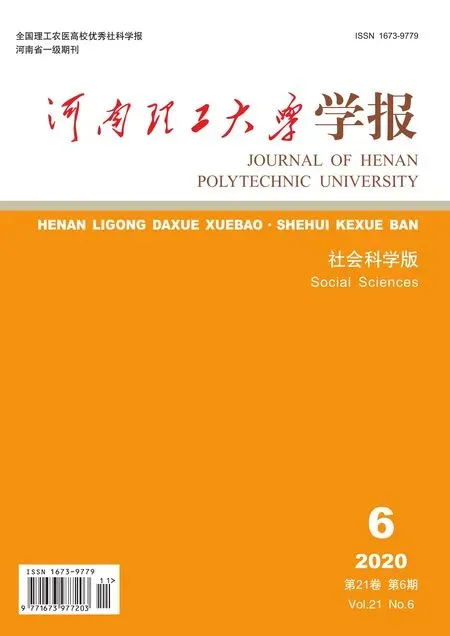跨界视域下的威廉·卡洛斯· 威廉斯医学小说
朱丽田,宋 涛
(1.东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2.东南大学 成贤学院,江苏 南京 210088)
“学科的‘跨界研究’,又称‘学科互涉’‘跨学科研究’‘学科交叉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据考证,社会科学的‘学科互涉’发轫于1926年出版的一部谈‘整体论与进化论’的著作,20世纪70年代渐渐波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1]20世纪中叶以来,不同学科间的交叉、交流日益增多,学科互涉和边界跨越逐渐成为一种知识发展的新特性。学科的跨界研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研究范式。文学研究也不例外,2003年,美国批评界权威期刊Critical Inquiry召开了一次关于理论未来和文学研究动态的研讨会,与会者认为,战争、经济、国家、学科、政治、学术机构同诗歌、宗教、科学、媒体、技术及哲学发生碰撞,是令人兴奋的跨学科混合。可以说,这种文学跨学科转型,已经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
“文学与医学”这一学科正式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学者们认为,随着医学知识的迅猛增长和技术的发展,医生会更加关注疾病与诊疗技术问题而忽视病人,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加强凸显医学的人文性成为必然,医学院校必须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与医学的关系被广泛讨论,文学即是人学,要加强医学的人文性,文学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医学与文学有着天然的纽带——医学关注人的身体,文学关注人的精神,而身体和精神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在古今中外,医学和文学的相互融合,都有迹可循。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既是医学之神又是诗歌之神,仿佛预见了医学和文学的深度跨界融合。
“医生作家”是文学与医学这一学科的一门课程,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国外学界对其医学小说的研究已有不少,如Marjorie Perloff的论文“爱女人的男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医学小说”以及Coles R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个写作的医生”,相对而言,国内的研究稍显不足。本论文的探讨基于三个原因。其一,鉴于威廉斯在诗歌上的巨大成就,国内学界对其诗歌研究热忱不减,但对于其小说研究不足。其二,威廉斯实际上是一名具有跨界思维的作家,他的诗中有画,这一点被广为论述。然而威廉斯是一名行医四十几年的经验丰富的医生,同时他将其毕生的医学生涯寓于小说创作之中,但这样的从医生到作家的跨界却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足够的重视。其三,“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医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医学所采用的科学性语言、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把疾病而非病人置于医疗实践的中心地位,人本身的价值被贬低,医患交流被削弱——这已经成为美国人文医学界对医学的经典批评。”[2]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即是医生又是小说家的威廉斯的关注是十分必要的。通读威廉斯的医学小说,可以发现其医学小说的中心是病人,而非冷冰冰的医疗器械或者是疾病本身,表达了医生对病人高度的共情、移情、同情,再现了医生对病人极具个性化的诊断、对生命伦理的反思,这正是人文医学界所高度重视的。因而,威廉斯的医学小说是文学与医学跨界研究的理想范本。可以说威廉斯的医学小说,恰恰凸显了他对现代医学重视医疗技术、忽略人的价值这一弊端的拨乱反正,值得当今的医学和文学研究者关注。
本文拟从威廉斯的《医生故事》中摘取《一张石头一样的脸》《心灵与身体》以及《动用武力》作为分析文本,探讨威廉斯医学小说中的医学人文、疾病叙事和伦理反思。
一、威廉斯医学小说的人文性
如上所述,医学与人文学科的建立正是基于医学人文的需要。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人文学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的医学。医学人文关怀强调用“人文理论认识患者的疾病与健康,将人置于医疗实践的中心,关注人类情感,反映人类价值,软化技术医学坚硬的外壳,唤回医生心底的柔软”[2],这一主张与威廉斯的医学小说所表现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威廉斯在其自传中写道:“行医的真正满足感在于它的单调,每日进来,每日出去,每日工作, 四十余年的出诊填满了他的生命。……人们对我的需求,不管是什么时间,什么情况,总是对我有着吸引力。亲密接触他们的生活,看着当他们出生,看着他们濒临死亡,看着他们死去,看着他们康复。”[3]在其行医生涯中, 威廉斯关注的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病人的生老病死,并且将这种关注体现在他的医学故事里。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从未觉得行医干扰了我,而是我的食粮与水,恰恰是行医让我有写作的可能性。”[3]
《一张石头般的脸》充分表现了这种威廉斯的人文的医学。《一张石头般的脸》记述了一对犹太人夫妻请医生“我”为几个月大的孩子看病,后来因为妻子右腿疼痛,又请“我”看病的故事。故事短小,并不复杂,一开始医患关系并不和谐,随着故事的发展,医生了解到妻子的疾病真相,对病人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和人文关怀,治愈了病人的身体并且抚慰了病人的心灵,使得这篇小说闪现着人性的温度。
“人文学科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疾病和疗愈问题的理解能力。至少在文学领域,这种作用体现在检验医学话语——尤其是有关疯狂、焦虑和其他心里紊乱现象的话语。”[4]在《一张石头般的脸》中,妻子是存在着心理紊乱的,正如小说标题一样,她有着一张面无表情的“石头般的脸”,“那是一种动物般的不信任,而非羞涩。她不是害羞而是像是嗅到了危险,而她正在预防这种危险”[5]。在为孩子两次的问诊中,她表现出了焦虑、不信任、极度的神经质,甚至疯狂。当医生靠近孩子、孩子发出叫声的时候,女子立即惊慌地将孩子护在胸前,朝门口跑去。而她的丈夫似乎也不太正常,在整个问诊过程中,他特别容易脸红。这对夫妻最开始就引起了医生的不满和讨厌,他们对孩子的关注似乎太过急迫,从来不管医生的作息时间。五个月之后,这对夫妻又来找医生,在为孩子检查的时候,女子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紧张。检查的时候,她就在“我”后面,“我”每做一步检查,她都紧张地看着孩子;而其丈夫也说,她要孩子一直在她身边,以便她能时时感受到孩子的存在。实际上这位母亲对于孩子的安全存在着极大的焦虑,她一直以为孩子快要死了,但实际上孩子并无任何异样,“看起来很聪明,它那完美的、快乐的、鲜嫩的微笑让我自己也情不自禁笑起来”[5],威廉斯通过细致的医学话语,描述了女子虽木然、呆滞对孩子却极度敏感的反常表现,为后来医生对其疾病的理解和治疗埋下了伏笔。
实际上,医学的本源就是人文关怀。“人类对于损伤或者疾病的最初帮助,是同情、关怀和尽力救护,反之,技术的方法是原始的,甚至是野蛮的。”[6]针对这对夫妻的表现,一开始医生表现出了厌烦。在检查过孩子之后,男子要求为其妻检查,因为她的右腿一直疼痛。“我”检查后发现女子的腿有明显的弯曲,整个腿部变形,显得丑陋不堪。“我”判断她有软骨病及静默曲张,但疼痛并非由静默曲张引起,而是因为她的O型腿承担了过多的压力。
在后来的问诊中,医生“我”得知,女子24岁,来自波兰。“我”据此猜到了女子的文化背景,“她是那一种特别的犹太人,在五、六岁的时候经过了大屠杀”[5]。后来女子的丈夫告诉“我”,女子丧失了所有亲人。所以女子的一切反常,包括她病痛的缘由,都有了解释。“我”对这位女子的嫌厌已经变成同情。“看着她神经质地、极度地关注着她的孩子,看着它,以一种说不出的方式和它说着话,对我完全置之不理,我暗自思忖,这就是原因了。考虑到她在被入侵的祖国所经历的一切,她这个样子并不奇怪。”[5]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医学人文关怀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协调患者的人际关系,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满足患者的个性需要,表达对患者的关爱感情等”[7],而理解患者的文化背景尤为重要。在了解到女子的文化背景之后,“我”的心立即柔软下来,对他们的态度也缓和下来,开始耐心尽力对女子进行救治,“我”建议她不要手术,而是采用弹性的绷带。“我”开始尽力去吸引女子的注意力,问她是否可以吞咽药片。“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关怀,也引发了女子的回应,她开始看着“我”,问“我”要服用多大的药片。她的丈夫替她回答,他的脸又红了,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她带着些许羞耻的爱,以及她对他全然的依赖。我被感动了”[5]。医生的温暖、耐心、关爱,让这个脸庞如同石头一般毫无表情的女子,卸下了防备,一改之前的木讷、冷漠、麻木,开始了与“我”的语言交流。到故事的最后,“我”第一次看到了她脸上的灿烂笑容,并且她终于可以和“我”顺畅交流了,答应服用药片,对“我”说:“好的,我会吞了它。”[5]
医学人文学帮助医生们“培养观念观察力、同情心和自我反省的能力”[4],在这个故事里,威廉斯细致描写了医生的细致观察、同情心,而“我”最初对这对夫妇的误解也能够引发医疗从事者的反省:病人的无礼,也许有其不得已的原因,而这种原因可能与其过往的经历有关,因而了解病人的背景,对于治疗是至关重要的。
二、威廉斯医学小说里的疾病叙事
疾病叙事是现代医学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哈佛大学精神病学家及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最早使用了“疾病叙事”这一说法,并区分了disease 和illness,“他认为前者是当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方式,是脱离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客体”[2],illness是指病人对疾病的感受、经历,是具有心理和社会性的主观体验”[2];疾病叙事“则是关于疾病的非小说性的第一人称叙述(口头叙述的疾病经历)”[2]。疾病叙事对于病人和医生都要重要意义。
对病人来说,叙述自己的疾病经历是一种宣泄,因此具有治疗意义,这在威廉斯的短篇小说《心灵与身体》中表露无遗。《心灵与身体》几乎通篇都是疾病叙事。小说叙述了42岁的英格丽腹部疼痛,因而来见医生“我 ”。从小说的第一句 “我们自己难道不是宇宙的中心吗”[5]开始,除了文中的医生,也就是“我”偶尔的回答或者提问,一直都是英格丽的口述。英格丽从自己幼时的癫痫病谈起,谈到医生对自己的误诊、医生对医疗技术和医疗器械的依赖、她的病史、她因为腹痛被医生错做了手术、她对宗教的疑惑、她对学校教育的质疑、她的第一次精神崩溃。她几乎将一生的重要经历和盘托出,倾诉着对自己境遇的疑惑、思考和苦恼。在此期间,她不止一次地表示,她需要有人倾听。她说:“我们需要可以向其告知我们困惑的人。我想今日我所说的一定让你烦扰,但是我必须说出来,你一定认为我疯了。”[5]实际上,英格丽这样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一会儿谈及其生活,一会儿谈及其疾病,一会儿谈及其心理状况, 应该归于疾病叙事的范畴。“对病人来说,疾病叙事是诠释自我的方式之一,经历了精神痛苦或濒临死亡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叙事来理解现在的我,以及疾病对他们的意义。”[2]在《心灵与身体》中,在英格丽倾诉完她想倾诉的一切并经过“我”的观察、倾听、共情和临床检查后,被“我”告知,她并没有罹患癌症。英格丽放下了包袱,说:“我想活着,是因为我发现了我在生活中的位置……”[5],“我们必须为别人活着,我们在这世界上并不孤单,我们也不能孤单地活着”[5]。此时的她,已经不似刚来的时候那样焦虑,而是轻松,并且有了信心。她的疾病叙事不仅宣泄了她的痛苦,也帮助了医生做出了诊断,是非常有价值的。
对医生而言,疾病叙事提供了了解病人精神状况的工具,“科室医生了解病人内心的伤痛、绝望、希望、道德上的痛苦,这些因素既可能是疾病的结果,也可能是疾病的原因,病人的叙事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病人疾病的框架,可以为正确的诊断治疗提供一定的信息”[2]。在《心灵与身体》中,作为医生的“我”,态度是极为审慎的,“我”仔细地倾听,小心地引导, “壮着胆子去问她有没有服用阿品脱和鲁米那去治疗她的结肠炎”[5],鼓励英格丽不加限制地倾诉。通过倾听英格丽的病史,分析她的家族病史和表现出来的心理状况,以及对其身体的检查,“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从你的叙述、症状所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你并未消瘦,你红润且健康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的痛苦来自黏液性结肠炎,这是一种大肠痉挛所引起的疾病。”[5]
在这篇故事里,正如小说标题所说的那样,“我”不仅关注病人的身体,更关注病人的心灵,英格丽的疾病与她的心灵,显然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英格丽在其疾病叙述中,谈及之前误诊她的医生是这样给她看病的:“我试试这个,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就试试别的什么。 如果有什么奏效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个病人究竟是怎么了。”[5]这类医生显然是将医疗器械置于医疗实践的中心、而非病人本身,他们只遵守医学客观、标准化的原则,但并没有兼顾个性化,他们眼里的疾病正是凯博文所说的“disease”。威廉斯更关注病人的经历对于病人疾病的价值,突出了疾病诊断的个人化。当英格丽问及她为何如此容易紧张时,医生认为这是她们家族性的动脉和静脉之间的环线过于纤长的缘故。这些环线非常脆弱,伸展和伸缩都极其容易,是所有不稳定的紧张现象的缘由,这一富有个性的身体特质影响了英格丽的心灵。英格丽的疾病叙事为医生提供了一个从心灵和身体两方面了解其极具个性化疾病的框架。这一点符合“文学既是人学”的价值观,体现了医学和文学的天然纽带:关注人本身。其结果是“我”愿意见证病人的痛苦,采取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建立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也为作出正确的诊断打下了基础。
三、威廉斯医学小说的伦理反思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科尔斯主张文学要为医学提供伦理反思的机会。他认为文学作品创造了一个个探索伦理选择的机会,使从业者可以明白伦理选择不仅仅是治疗的问题,而是医生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个个关于生命的决定,这些决定最终会决定病人的命运。威廉斯的《动用武力》提供了这样的一个伦理反思。
在《动用武力》中,医生“我”被一个发烧的女孩——马蒂尔德的父母请至家中,为马蒂尔德治病。因为马蒂尔德所在学校已经发生了好几例白喉病情,所以“我”最开始的问题就是女孩有没有咽喉痛。“我”的问诊力度是逐步升级的。先是孩子的母亲询问,孩子否认。然后“我”带着最好的职业性的微笑引导孩子张开嘴巴,“我”说:“马蒂尔德,你张开嘴巴,我们看看你的喉咙吧!”[5]但还是被拒绝。“我”又进行了态度更为温和的诱导:“我的手上什么也没有,你就是张开嘴,让我看看。”[5]孩子仍然无动于衷。于是“我”小声劝着这孩子,并慢慢靠近她,却遭到了她的激烈反抗,她抓了我的眼睛,“我”的眼镜随之掉落。“我”于是比较严肃地再次要求孩子张开嘴巴接受检查,否则就会强制执行,孩子依然故我。在此,威廉姆斯写道:“为了保护她,我必须检查她的喉咙。但是首先我得告诉这对父母,检查完全取决于他们。我向他们解释了危险性,但是说只要他们能够负责,我不会坚持检查喉咙。”[5]孩子的父母了解了事态的严重性,在他们的帮助下,医生将压舌板强制塞入孩子口中,却被孩子吐出来,孩子更为激烈地反抗,甚至嘴巴已经出血了。此时,医生想:“也许此时我该放手,一个小时或者再长一些的时间后再来。毫无疑问,到那时候,情况会好很多,但是我已经看到至少有两个孩子因为忽视这种病,在床上躺着死去了,所以感到要么现在就拿到诊断结果,要么再也不去管了。但是这件事的最坏一部分是我自己已经失去了理智。在我的愤怒中,我会将这个孩子撕裂,但我很开心。攻击她让我快乐。我的脸因为有此想法发烧。”[5]“我”强行用汤匙压住孩子的舌头,发现孩子患白喉至少已经有三天了,她对检查的激烈反抗,只是因为不敢面对这样的结果。
在这个故事中,“我”的决定,从结果上看显然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决定挽救了马蒂尔德的生命,体现了医疗行业救死扶伤的伦理道德。 但是“我”的选择显然也带着非理性的因素,“我”动用武力,强制玛蒂尔达配合检查,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不满孩子的反抗,在这一点上,“我”呈现了“控制欲强烈,典型的父权式医生形象”[2]。这种形象显然不利于医患关系,对病人和医生都产生了压力,从而对诊断和治疗起到了负面作用。“人际关系是医学实践中的一个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文理性正是将人类‘伦理’寓于人际交往之中的一种哲学思考。”[8]然而,在“我”诊断马蒂尔德的时候,在“我”的循循善诱并不起作用的情况下,除了动用武力拯救孩子的性命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伦理选择呢?是否可以以某种新的方式来对待问题、做出决定、解决个人和职业的冲突、避免恶化医患关系?这个故事是引人深思的,值得医务工作者研究。
四、结 语
1996年,美国学者宣布,美国已经进入了“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时代,人文医学已是大势所趋,而“医疗题材文学由于和诊疗行为密切相关,有着天然‘血缘’关系,因此也就成了医学教育首当其冲应当重视的人文学科”[9]。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死于医学人文学方兴未艾的1963年,但是在他的医学小说中,已经实现了他“以病人为中心”的主张,他以文学的形式再现了他坚持了四十几年的“根据个人做出不同诊断”[3]的医学实践。威廉斯在其自传中写道:行医与写作“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根本就不是两种工作,而是一个让他疲倦的时候,而另一个则让他休息”[3]。这正是医学和文学的真正关系所在:文学以柔性弥补医学作为科学的客观理性,共同为人类的健康做出贡献,这种关系也是威廉斯从医生到作家跨界思维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