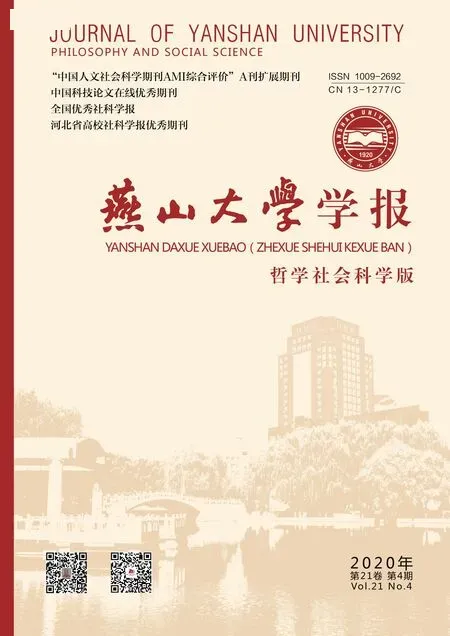《孟子集注》引杨时语辑考
马慧娟
(中山大学 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1130—1200)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是其“竭毕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者。[1]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先后学于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宋元学案》称:“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其最。”[2]杨时对二程理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对朱熹的《孟子集注》的编撰起了重要作用。
《孟子集注》对杨时以“杨氏”称之,书中所引学者共47位,杨时引文共有27条,位居第4。此次对于《孟子集注》引杨时语的辑考工作,所用书为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及林海权点校、2018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杨时集》。
1. 《孟子集注·孟子序说》:
杨氏曰:“《孟子》一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欧阳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谓误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 (《四书章句集注》,第199—200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2《余杭所闻二》:
《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
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尽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更说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杨时集》第2册,第327页)
按:朱熹于欧阳永叔之言后加“可谓误矣”四字,省去“永叔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尽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更说不行”一句,直言欧阳永叔言性之说为误。欧阳永叔即欧阳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提出儒家学者首先应当关注的是修己治人,而不应该过多关注心性之学。杨时和朱熹的反对表明儒家学者的关注重点已经由价值和制度规范层面向本体论、心性论方面转变。
2. 《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1·3:
杨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废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焉,则末矣。”(《四书章句集注》,第203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移民转粟,荒政之所不废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为尽心,宜孟子之不与也。(《杨时集》第1册,第173页)
按:朱熹将杨时所说“宜孟子之不与也”改为“则末矣”,将结论由孟子个人的判断扩大到本末方面的讨论。
3. 《孟子集注》卷1《梁惠王章句上》1·7:
杨氏曰:“为天下者,举斯心加诸彼而已。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产告之。”(《四书章句集注》,第212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为天下,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其王也,孰御焉?然虽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产告之,使民不饥不寒,而后曰:“不王者,未之有也。”(《杨时集》第1册,第174页)
按:朱熹省去“其王也,孰御焉?”“使民不饥不寒,而后曰:‘不王者,未之有也’”两条关于成王的论述。
4. 《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2·1:
杨氏曰:“乐以和为主,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而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濩》,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齐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四书章句集注》,第214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而孟子之言如此者,盖乐者,天地之和也。而乐以和为主。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使人闻钟鼓管弦之音,举疾首蹙頞,则虽奏以《咸英》《韶濩》,无补于治也。故孟子告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杨时集》第1册,第175页)
按:朱熹省去“而孟子之言如此者,盖乐者,天地之和也”“人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矣”。申淑华:“于乐和语句之后,略去人和、气和语句,专言乐。”[3]416
5. 《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2·5:
杨氏曰:“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论事。若使为人臣者,论事每如此,岂不能尧、舜其君乎?”(《四书章句集注》,第220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孟子与人君言,皆所以扩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论事。如论齐王之爱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论王之好乐,而使之“与百姓同乐”;论王之好货、好色、好勇,而陈周之先王之事。若使为人臣者论事毎如此,而其君肯听,岂不能尧、舜其君?(《杨时集》第1册,第248页)
按:朱熹将杨时的“革其非”改为”格其非心”,并略去“如论齐王之爱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论王之好乐,而使之‘与百姓同乐’;论王之好货、好色、好勇,而陈周之先王之事”三个具体事例。朱熹解释“格”为“正”,“格其非心”出自于《尚书·冏命》:“绳愆纪缪,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4]他将“革其非”改为“格其非心”,是因为“‘格其非心’,是说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说得浅者”[5]2061。在朱熹看来,两者只有程度的差别,而非本质不同。
6. 《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2·15:
杨氏曰:“孟子之于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礼之正也。至其甚恐,则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无大王之德而去,则民或不从而遂至于亡,则又不若效死之为愈。故又请择于斯二者。”(《四书章句集注》,第226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国君死社稷,故告之以效死勿去,正也。至其甚恐,则以太王去邠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亦在强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从之如归市。不知为善而去国,则民将适彼乐土矣,尚谁从之哉?然滕文公未必能如太王也。使其去国而遂亡,则不若效死勿去之为愈也,故又请择于斯二者。(《杨时集》第1册,第179页)
按:朱熹将“正也”改为“礼之正也”,省去“然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亦在强为善而已。故太王去邠,民从之如归市”一句,并将杨时所说的“善”改为“德”。
7. 《孟子集注》卷2《梁惠王章句下》2·15:
又曰:“孟子所论,自世俗观之,则可谓无谋矣。然理之可为者,不过如此。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26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2《余杭所闻二》: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齐人筑薛为恐,问救之之术,而对以“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国,则不得免”。问安之之道,而对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而继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观之,可谓无谋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说。舍此则必为仪、秦之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于智谋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贤之道也。天理即所谓命。(《杨时集》第2册,第351页)
按:朱熹省去“天理即所谓命”一句,也没有提及杨时所说“孟子直是知命”,表明朱熹并不同意杨时将天理与命等同。因为在朱熹看来,命可分为气质与义理两者,“‘死生有命’之‘命’是带气言之,气便有禀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谓性’之‘命’,是纯乎理言之。然天之生命,毕竟皆不离乎气”[6]77。
8. 《孟子集注》卷3《公孙丑章句上》3·1:
杨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使其见于施为,如是而已。其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则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则范我驰驱而不获者也;管仲之功,诡遇而获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四书章句集注》,第228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孔子谓:“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称管仲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则管仲之功,非子路所能也。而曾西谓子路孰贤?则曰:“吾先子之所畏也”;问管仲,则艴然不说曰:“尔何曾比予于是!”何也?
曰:昔者王良与嬖奚乘,为之范我驰驱,终日而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若子路者,为之范也,虽不获一而不为歉。管仲诡遇也,虽得禽若丘陵,射者弗为也。仲尼之门,羞称管、晏,亦犹是耳。(《杨时集》第1册,第179—180页)
按:朱熹此句,乃合他人所问与杨时之答而成。
9. 《孟子集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4·8:
杨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齐王能诛其君,吊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杀其父兄,虏其子弟,而后燕人畔之。乃以是归咎孟子之言,则误矣。”(《四书章句集注》,第248—249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4《答胡德辉问》:
答:“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齐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诛其君而吊其民,何不可之有?而其虐至于系累其子弟,而后燕人叛之,以是而归罪孟子之言,非也。”(《杨时集》第2册,第419页)
按:朱熹在此省去“使齐王因孟子之言而遂伐之”,将“其虐至于系累其子弟”改为“杀其父兄,虏其子弟”。
10. 《孟子集注》卷4《公孙丑章句下》4·12:
杨氏曰:“齐王天资朴实,如好勇、好货、好色、好世俗之乐,皆以直告而不隐于孟子,故足以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谬为大言以欺人,是人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何善之能为?”(《四书章句集注》,第252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先生尝夜梦人问:“王由足用为善,何以见?”语之曰:“齐王只是朴实,故足以为善。如好货、好色、好勇与夫好世俗之乐,皆以直告而不隐于孟子,其朴实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谬为大言以欺人,是人终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何善之能为?”(《杨时集》第1册,第239页)
按:朱熹将“齐王只是朴实”改为“齐王天资朴实”,将“其朴实可知”改为“故足以为善”,并且改变了原文顺序,从而使天资朴实到足以为善形成递进关系。
11. 《孟子集注》卷6《滕文公章句下》6·1:
杨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是以孔、孟虽在春秋战国之时,而进必以正,以至终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四书章句集注》,第269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宁道之不行,而不轻其去就。如孔、孟虽在战国之时,其进必以正,以至终于不得行而死是矣。顾今之世,独不如战国之时乎?使不恤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当先为之矣,孔、孟岂不欲道之行哉?”(《杨时集》第1册,第250页)
按:朱熹在此省去“顾今之世,独不如战国之时乎?”
12. 《孟子集注》卷7《离娄章句上》7·12:
杨氏曰:“动便是验处,若获乎上、信乎友、悦于亲之类是也。”(《四书章句集注》,第287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1《余杭所闻一》:
“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弗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弗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说于亲矣。”
今之君子欲行道以成天下之务,反不知诚其身。岂知一不诚,它日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乎?故曰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夫以事上则上疑,以交朋友则朋友疑,至于无往而不为人所疑,道何可行哉?盖忘机,则非其类可亲;机心一萌,鸥鸟舞而不下矣,则其所能所为可谓高矣。(《杨时集》第2册,第304页)
按:朱熹增加了“动便是验处”一句,杨时强调“诚其身”,朱熹则认为“获乎上”“顺乎亲”“信乎友”本就是“诚”的证验。
13. 《孟子集注》卷8《离娄章句下》8·3:
杨氏曰:“君臣以义合者也。故孟子为齐王深言报施之道,使知为君者不可不以礼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处,则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盖如此。”(《四书章句集注》,第295—296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雠”,以为君言之也。为君言,则施报之道,此固有之。若君子之自处,岂处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心盖如此。(《杨时集》第1册,第271页)
按:朱熹将“孟子所谓‘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雠’,以为君言之也”改为“君臣以义合者也”,从而削弱了两者的对抗性。并且朱熹将“君子之心”改为“君子之言”,以契合孟子之语。
14. 《孟子集注》卷8《离娄章句下》8·10:
杨氏曰:“言圣人所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称之。”(《四书章句集注》,第296—297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1《京师所闻》:
圣人作处,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以孔子之圣,孟子止言其“不为已甚”而已。(《杨时集》第2册,第297页)
按:朱熹将“故以孔子之圣,孟子止言其‘不为已甚’而已”改为“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称之”。申淑华:“盖朱子以‘不为已甚’为符合中庸之道,故难能,而杨氏之言,却有易为之弊,故朱子改之。”[3]489而另一方面,也是表达圣人之心同然之理。
15. 《孟子集注》卷8《离娄章句下》8·22:
杨氏曰:“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服穷则遗泽寖微,故五世而斩。”(《四书章句集注》,第300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26《跋邹公送子诗》: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盖人之于亲,四世而缌服穷,六世而亲属竭。服穷则遗泽浸微矣,故五世而斩,此古今之常理也。(《杨时集》第3册,第709页)
按:朱熹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改为“五世袒免,杀同姓也”,置于“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之后,并省去最后一句“此古今之常理也”。
16. 《孟子集注》卷8《离娄章句下》8·30:
杨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四书章句集注》,第305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7《答吴仲敢》:
章子之不孝,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与之绝耳,而仲敢乃独责其反于舜。(《杨时集》第2册,第477页)
按: 朱熹将“章子之不孝”改为“章子之行”,改变了原文中的贬义。
17. 《孟子集注》卷9《万章章句上》9·1:
杨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为此言。盖舜惟恐不顺于父母,未尝自以为孝也;若自以为孝,则非孝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07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据舜惟患不顺于父母,不谓其尽孝也。《凯风》之诗曰:“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孝子之事亲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为能,则失之矣。(《杨时集》第1册,第254页)
按:在此朱熹将“不能及此”改为“不能为此言”,“不谓其尽孝也”改为“未尝自以为孝也”,省去杨时所引《凯风》之诗、孔子之言,又将“若乃自以为能,则失之矣”改为“若自以为孝,则非孝矣”,从而突出孝道应有之义。
18. 《孟子集注》卷9《万章章句上》9·6:
杨氏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可以见尧、舜、禹之心,皆无一毫私意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14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21《答学者》:
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唐虞禅,夏后、商、周继,皆天也,圣人何容心哉?奉天而已。(《杨时集》第2册,第564页)
按:朱熹在此增加“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一句。另外,杨时将尧舜之禅让、夏商周几朝的更替归结为顺应天的变化,注重的是天的作用,朱熹则强调的是尧、舜、禹之心无私意,这便弱化乃至消解了外在的“天”的力量和作用,将去除人的私心、欲望视为首要。
19. 《孟子集注》卷10《万章章句下》10·1:
杨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迟迟其行也。膰肉不至,则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税冕而行,非速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20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曰:孔子之欲去鲁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故迟迟其行也。燔肉不至,则得以微罪行矣。过此,复无辞以去,故不税冕而行,非速也。(《杨时集》第1册,第185页)
《杨时集》卷13《萧山所闻》:
曰:“孔子欲去之意盖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为苟去,乃所谓‘迟迟’。若他国,则君不用便当去,岂待燔肉之不至然后行?”(《杨时集》第2册,第400页)
按:此条引文同时出现于《孟子解》与《萧山所闻》,但从文本上看,则与《孟子解》中更为相似。与《孟子解》相比,引文省去“欲以微罪行”“过此,复无辞以去”。
20.《孟子集注》卷12《告子章句下》12·2:
杨氏曰:“尧、舜之道大矣,而所以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百姓盖日用而不知耳。”(《四书章句集注》,第345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尧、舜之道,岂远乎哉?孝弟而已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间,人病不求耳。伊尹乐尧、舜之道,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也。孔子之相师,亦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则无适而非道也。(《杨时集》第1册,第189—190页)
《杨时集》卷13《萧山所闻》:
孟子所言,皆精粗兼备,其言甚近,而妙义在焉。如庞居士云:“神通并妙用,运水与搬柴。”此自得者之言,最为达理。若孟子之言,则无适不然,如许大尧、舜之道,只于行止疾徐之间教人做了。(《杨时集》第2册,第401页)
《杨时集》卷14《答胡德辉问》:
夫道若大路,行之则至。故孟子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其为孝悌,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间,非有甚高难行之事,皆夫妇之愚所与知者。虽舜、颜不能离此而为圣贤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杨时集》第2册,第413页)
《杨时集》卷18《答李杭》:
尧、舜之道曰孝弟,不过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日出而作,晦而息,无非道也。(《杨时集》第2册,第494页)
《杨时集》卷20《答胡康侯》:
夫盈天地之间,孰非道乎?道而可离,则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适东则离乎西,适南则离乎北,斯则可离也。若夫无适而非道,则乌得而离耶?故寒而衣,饥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视听,手足之举履,无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以乐尧、舜之道。”夫尧、舜之道,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伊尹之乐有在乎是。若伊尹,所谓知之者也。(《杨时集》第2册,第536页)
《杨时集》卷21《答练质夫》:
夫道,岂难知难行哉?虽行止、疾徐之间,有尧、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所以难知难行也。(《杨时集》第2册,第581页)
按:此条引文同时见于《孟子解》《萧山所闻》《答胡德辉问》《答李杭》《答胡康侯》《答练质夫》几处,从文本上看与《答胡德辉问》更为相似,朱熹省去“行之则至”、孟子之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以及“皆夫妇之愚所与知者”“虽舜、颜不能离此而为圣贤也”。从此段引文见于多处可知这是杨时天道观的代表性思想,在杨时看来,尧舜之道为孝、悌,道不可离,就在于百姓日用常行之间。然而在朱熹那里,物与道是有严格区分的,“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7]1496,因此杨时此说是混淆了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若便谓食饮作息者是道,则不可。与庞居士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之颂一般,亦是此病。”[7]1496-1497两者虽然不可混淆,但是道与器却又不可分割:“道不离乎器,器不遗乎道。”[5]1936所以朱熹认为龟山之说,乃是佛教的“作用是性”的观点:“龟山举庞居士云: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不知徐行后长乃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如运水与搬柴即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可谓之弟耶。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便是如此。”[7]557
21. 《孟子集注》卷12《告子章句下》12·6:
杨氏曰:“伊尹之就汤,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进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过迁善而已。伊尹既就汤,则以汤之心为心矣;及其终也,人归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四书章句集注》,第348—349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问:“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汤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汤进之也。”“然则何为事桀?”曰:“既就汤,则当以汤之心为心,汤岂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归之,天命之耳。方其进伊尹以事桀也,盖欲其悔过迁善而已;苟悔过迁善,则吾北面而臣之,固所愿也。若汤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为心也,以取天下为心,岂圣人之心哉?”(《杨时集》第1册,第246页)
按:朱熹对原文顺序进行了调整,省去“苟悔过迁善,则吾北面而臣之,固所愿也”,将“伐桀之意”改为“伐桀之心”。
22. 《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13·13:
杨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违道干誉之事;若王者则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四书章句集注》,第359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2《余杭所闻二》:
又言“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乐,有甚不得?但如所谓皞皞如也,则气象便与霸者之世不同。盖彼所以致人驩虞,必有违道干誉之事。若王者则如天,亦不教人喜,亦不教人怒。(《杨时集》第2册,第329页)
按:朱熹将“教”字改为“令”字。
23. 《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13·25:
杨氏曰:“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间而已,是岂可以不谨?然讲之不熟,见之不明,未有不以利为义者,又学者所当深察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64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8《答李杭》:
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间。则为尧、舜者,亦力于为善而已。颜子曰:“舜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论颜子之学,则曰:“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杨时集》第2册,第494页)
《杨时集》卷20《答胡康侯》:
舜、跖之相去远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间。故颜渊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其学为舜,亦曰“择善而固执之”而已。舜、文之圣,若合符节。则潜心乎文王者,亦岂外是乎?(《杨时集》第2册,第538页)
按:此条引文同时见于《答李杭》和《答胡康侯》。申淑华以为从“然讲之不熟”之后当为朱子之言,中华书局将其误加入括号中。[3]557从《杨时集》两处文本来看,应可从其说。“是岂可以不谨”一句为概括原文而成。
24. 《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13·25:
杨氏曰:“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颜子在陋巷,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无异。子莫执为我兼爱之中而无权,乡邻有斗而不知闭户,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犹执一耳,故孟子以为贼道。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以其有权也;不然,则是亦杨、墨而已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64—365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8《孟子解》:
禹思天下之溺犹己溺之,稷思天下之饥犹己饥之,至于股无胈,胫无毛,不当其可,与墨子摩顶放踵,无以异也。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未尝仕也。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氏之为我,亦无以异也。子莫执中,执为我,兼爱之中也。执中而无权,犹执一也。乡人有斗而不知闭户,室中有斗而不知救,是亦犹执一耳。故孟子以为贼道。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以其有权也。权犹权衡之权,量轻重而取中也。不能易地则皆然,是亦杨、墨而已矣。(《杨时集》第1册,第190页)
按:杨时将原文首句改为“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省去“人不堪其忧”“未尝仕也”“权犹权衡之权,量轻重而取中也”。
25. 《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13·38:
杨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者,形色也。则者,性也。各尽其则,则可以践形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68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3《南都所闻》:
“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履也,体性故也。盖形色必有所以为形色者,是圣人之所履也。谓形色为天性,亦犹所谓“色即是空”。(《杨时集》第2册,第388页)
《杨时集》卷18《答李杭》: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凡形色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反而求之,则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其则不远矣。(《杨时集》第2册,第494—495页)
《杨时集》卷26《题萧欲仁大学篇后》: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凡形色之具于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杨时集》第3册,第693页)
按: 此条引文同时见于《南都所闻》《答李杭》《题萧欲仁大学篇后》,从这几处文本对比可知朱熹与杨时思想的差异:首先杨时将“形色”“物”与“天性”“则”等同,并认为这与佛教的“色即是空”是一样的。朱熹则认为“物”为“形色”,“则”为“天性”,也即是“理”,其中有严格的区分。其次,杨时认为天下之理具于吾身,因此只需反身而诚,便可“通天下之志,类万物之情,参天地之化”[8]。但是在朱熹那里,理即物而存在,因此穷理必须格物,“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后会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这便是理之一本处。”[6]286因此他反对杨时之说:“龟山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甚么。”[7]1489
26. 《孟子集注》卷13《尽心章句上》13·45:
杨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所谓理一而分殊者也。”(《四书章句集注》,第370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1《京师所闻》:
论《西铭》,曰:“河南先生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杨时集》第2册,第297页)
按:杨时曾质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有流于墨家“兼爱”之弊,程颐回以“理一分殊”之说,杨时始悟。他以“理一”为“仁”,以“分殊”为“义”,将理一分殊与儒家的亲亲、仁民、爱物之说相联系,认为“理一”就是儒家所讲的仁爱,“分殊”就是亲疏远近之差等,从而给等级秩序和伦理规范以合理性说明。朱熹虽然受到杨时理一分殊说的影响,但他没有将理一分殊之说限于伦理规范,而是认为其中包括天理、物理、伦理多个方面,丰富了“理一分殊”的内涵:
本只是一太极(理),而万物各有禀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9]
如这片板,只是一个道理,这一路子恁地去,那一路子恁地去。如一所屋,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如草木,只是一个道理,有桃,有李。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6]102
理只是这一个。道理则同,其分不同。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6]99
27.《 孟子集注》卷14《尽心章句下》14·34:
杨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孔子则无此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82页)
此条见《杨时集》卷10《荆州所闻》:
孟子言:“说大人,则藐之。”至于以己之长方人之短,犹有此等气象在。若孔子,则无此矣。(《杨时集》第1册,第239页)
按:朱熹将原文中孟子之言改为“《孟子》此章”。
从以上逐条辑考可以看出杨时和朱熹的孟学思想的三个特点:第一,杨时和朱熹将孟子思想的重点放在了“心性论”,并将“正心诚意”作为孟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主题。第二,虽然杨时指出儒学与佛学不同,其孟学思想却不可避免地印有佛教思想的印记。朱熹的思想同样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他唯恐儒家学者误入佛学,因此对儒、佛的区分更为严谨和细致。第三,杨时的孟学思想中隐藏着与王安石新学的直接对立,到了朱熹,这种对立明显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