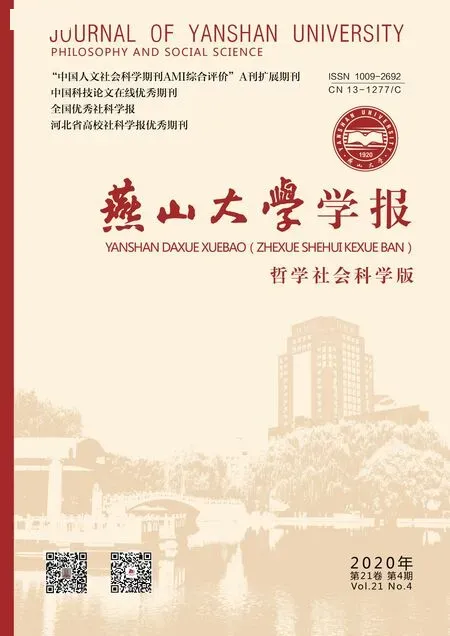赵南星《学庸正说》思想探析
许 卉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赵南星(1550—1627),直隶真定府高邑(今河北省高邑县)人,在晚明动荡的政局中有突出的政治表现,与邹元标、顾宪成并称“三君”,被视为东林党领袖,后人望之如“泰山北斗”。四库馆臣称:“盖南星为一代名臣,守正不阿,出其天性,故当狂禅横溢之时,能卓然有以自立,虽不以讲学名,而所言笃实过于讲学者多矣,未可以其近而忽之也。”[1]357近些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文学思想,此外,他的理学思想亦有其独特之处,本文以《学庸正说》来管窥其理学思想的倾向。
一、 《学庸正说》成书缘起及版本
(一) 缘起
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赵南星六十六岁,著《学庸正说》三卷,其中《大学正说》一卷,《中庸正说》两卷。著《大学正说》的缘起有三:
第一,王门后学的流弊横肆。在万历年间,王学大盛,其后学中有流入“狂禅”之弊,不仅对传统儒家的正统礼制秩序和人伦造成冲击和破坏,而且对儒家经典亦持有不尊和轻视态度,“明自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2]赵南星对于这一现象,亦持指责态度,称:“其谈空说幻欲超出吾圣贤之上,试与之以近代诸大儒之书,略观辄弃去,曰是不足知。然实未尝知也。彼以部试选举,故读孔孟之书,不然则亦弃去之矣。”[3]172不仅王学末流轻视经典,不主张工夫修为,且任心驰骋,陷入狂肆,赵南星对此指责道:“夫语圣学之要则,一敬尽之矣。即‘致良知’之说,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无弊也。后之讲学者,又过为玄妙,舍所戴之天而言九天之上,又言无天之天;舍所履之地而言九地之下,又言无地之地,此与白马非马之辩何异?”[3]163可见,赵南星时期,王学末流的弊端已经凸显,成为思想界共同批评的对象,在当时,很多儒家学者认为世运之兴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面对于此,作为有识之士的赵南星作《学庸正说》,试图从思想根源和学理上寻找解决的方法。
第二,三教合一思潮对正统儒家思想的冲击和解构。晚明时期,三教合一思潮蔚然成风,佛老之学也在士大夫之间颇受欢迎,有“南方多好佛,北方多好仙”之说。张履祥指出:“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释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4]如与赵南星当时的袁黄、李贽等人都援佛入儒,稀释了儒学的内纯性和正统性。对此,赵南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直指这种怪现象,“吁嗟!可忧哉。天下其乱矣乎,何举世皆妖怪也。经义,发明吾儒之道者也,今所言者,非吾儒之道而释氏之道也。”[3]207他认为这种明儒阴释的做法直接背离了圣学,“圣人之学,固非示人以难,亦何至若是之易,近在目前,而其所见者非也,甚至取释氏之余食,穿凿而强传之。其失愈远矣。夫学何可不讲也。”[3]175他著《大学正说》《中庸正说》,试图以儒家经典扶正人心,与当时流行的杂糅佛老的“异说”相抗衡。他称:“余少时,先大夫命之习浅说,至于今三四十年矣。而世道大变,士皆喜为异说,欲高出前辈之上,且浸淫于佛老之说。余甚惧焉,命儿辈仍守浅说之学。”[1]358
第三,燕赵文风的颓变引起的忧患。赵南星称:“夫燕赵之人,自古少文,其文率正大明,白如其人,今亦随俗为邪僻,不类燕赵之产矣。世道人心之坏,此其章章者也。余不自量力,而以正文体为己任,故从昌期之请,刻之江南,然固宜自吾乡始也。”[3]168在赵南星看来,当时之文盛,士人作文皆求怪异,以不合经义为见识超远,以远于时制为词胜,这种风气亦在燕赵之地流行,改变了燕赵本来平实、朴素的文风。这种变异求奇的文风直接导致了人心不古,因而亟需救正。又称:“今天下之文盛,不患其不巧,而患其离于法。夫法也者,非独结构脉络之谓也。贪美者恶锐往者踬,故妍之过也俗,新之过也臆,析之过也脞,邃之过也黭,雄之过也忿,疏之过也缦,奇之过也谬,皆不可以为法。”[3]169他作《大学正说》《中庸正说》,“词旨醇正,诠释详明”,不求怪异,亦可以说是对当时文风的一种反动。
第四,《大学》和《中庸》等书虽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但官方主流的意识形态对于其诠释造成了一定的局限,且赵南星认为,明中期之前,对于《大学》《中庸》的诠释以平实、朴素为主,不作深度诠释,因而难以透彻其精深奥义,他作《大学正说》和《中庸正说》,可以起到导路之用,“然往时风气浑朴,学士家于圣贤之书,仅求通晓,未甚精核,其解多在廊庑之间,鲜窥窔奥。余乃以浅说为主,参以近日名家之说,会萃折衷,昼夜思索,偶有所得,亦颇有先儒之所未发者,然自谓不害其为同。他日视之,殆有可以解颐,令儿辈习之知吾道之滋腴无穷,无庸求异为也。”[1]358-359
(二) 版本及体例
《高邑县志》卷八《著述志·赵南星》称:“《学庸正说》序:于万历乙卯乃就闽中陈恩献公浅说删润以成之。一本程朱,间或参以己见。所云明命即天命之性,新民即修道之教,综括两编,归纳于一。其深悟独到之处,荟萃折衷,务斥异说之义,抑又具矣。学者宗而师之庶乎?易所难,难所易,而得入学之门。版存赵忠毅公家祠内。”[5]按县志所言,《学庸正说》的底本是以陈恩献的本子为基础,加以删节、润色而称,有万历版本存。
通过“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查询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的版本收录情况,如下:
(1) 《学庸正说》清光绪六年(1880)赵氏刻本,线装,存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2) 《学庸正说》,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线装,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3) 《学庸正说》,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刻本(补刻),线装,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4) 《学庸正说》,民国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线装,存于南开大学图书馆。
(5) 《学庸正说详解》3卷,民国二十一年(1932)石印本,线装, 1册,11行23字,白口,四周单边,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首页有榆园业刻之一标注,题有“明高邑赵忠毅公原著,佚名朱墨涂乙增删稿,后学宁津李浚之述刊”。
(6) 《学庸正说》,直隶总督采进本。
(7) 《学庸正说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册号207,隶属于经部·四书类。
《学庸正说》的体例是以《大学》经文和《中庸》经文为主,分章进行讲论、诠释。四库馆臣称:“《大学》一卷、《中庸》二卷,每节衍为口义,逐句阐发,而又以不尽之意附载于后,略如近世讲章。然词旨醇正,诠释详明,其说《大学》不从姚江之知本,而仍从朱子之格物,并《补传》一章亦为训解。其说《中庸》不以无声无臭虚拟性天,而始终归本于慎独,皆确然守先儒之旧。”[1]357概括来看,在诠释内容上,赵南星以朱子的诠释为本,但同时杂以王门后学如罗汝芳等人的思想,并对王学后学的流弊进行修正,显示出融汇朱王的倾向。所谓“确然守先儒之旧” 应该说总结得并不完全准确。
二、 《学庸正说》思想的渊源
通观《学庸正说》,可以看出其思想的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程朱理学。由于程朱理学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的标准,作为士大夫的赵南星无论是在治学和授业过程中,必定不可抛弃程朱理学。在《学庸正说》中,他以朱子对《大学》《中庸》的阐解为主,其在推阐经典大义时,多以程朱之观点作为自身阐解的基础,如“朱子说,明徳自天命之唤做明命。人多鹘鹘突突,一似无这个明命。若常见其在前,则凛凛然不敢放肆,最说的透切”[1]363。同时,对于王门末流弊端的救正,赵南星采取尊朱的策略,因而四库馆臣称“确然守先儒之旧”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是概括正确。
其次,通观《学庸正说》,其受王学后学思想的影响亦鲜明可见。《明史·儒林传》载“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6],可窥王学的流行之盛。虽然在万历十二年张居正病逝之后,以王阳明从祀孔庙为王学解禁、流行无碍的标识,而赵南星明确接触到王学则是在万历十七年,通过杨起元接触到罗汝芳的思想。赵南星自述:“己丑之春,余与杨复所先生同事礼闱。余睹其人,似有道者……与余具言近溪先生之学。余于是乃知吾身之大也,为圣贤若此之易也。……欣喜之深,不可为比。既而出闱,先生悉以近溪先生之书示余,读之,日与先生谈。时过先生。……自是而余读孔孟之书乃稍知其旨趣,读诸子之书,乃能辨其是非,则感杨先生已。”[3]158可见,赵南星对于王学后学尤其是罗汝芳之学还是很有共鸣。此外,据《刻罗近溪先生语录抄序》,赵南星不仅诵习罗汝芳之书,而且还抄其语录,“余诵习罗先生之书既久,录其直接简易者”[3]158,且由乡人进行刻录传诵。在《大学正说》中,赵南星也多处引用罗汝芳的言语,如对《大学》之道的诠释,他称:“罗近溪云:此书既名《大学》,则看之者须要大眼孔,受之者须要大襟怀,读之者亦须大口气,而为之者亦须大手段也。此语甚妙。”[1]361除了罗汝芳的思想影响外,其弟子杨起元亦对赵南星有影响。赵南星在《刻圣学启关臆说序》中,提到杨起元对他的影响:“有谈道学者,不曰迂,则曰伪。余初年亦未脱于斯见。自乙丑春,奉教于杨复所先生,乃稍从事于圣贤之学。然自惟道不足以化俗,虑学者至诞而不信也。归隐以来,惟以经义授徒而稍抒其一得也。”[3]159可见杨起元的思想对于赵南星著《学庸正说》也有一定影响。所以,赵南星对于王门后学并不是持有一味反对的意见,而是试图折衷朱王,去短合长,寻找一条综合之路。
第三,艾穆、刘侯作为业师对赵南星的影响。艾穆和刘侯思想都尊以朱为主,在这种授业环境下,赵南星很容易亲朱、尊朱。《重修恒阳书院记》载:“己巳之岁,余读书恒阳书院,当道者聘请阜平广文艾纯卿先生为之师。艾先生,楚平江人也,博学能古文,平生慕李献吉之文章气节,数向余道之。”[3]326-327艾穆所钦慕的李献吉,即李梦阳。艾穆不仅向赵南星讲述李梦阳文章事迹,自身也是不畏强权,气节炳著朝野。赵南星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磊落耿介、守正不阿可以说是深受艾穆的教诲和影响。此外,刘侯对赵南星亦爱之甚渥,且寄予厚望。赵南星自称:“隆庆中,我庆泉先生以楚名士来高令,余得师事之。先生教之甚严,爱之甚渥,无异于子弟。余受知最早。……先生才德俱高,问学渊雅,其设行自与俗吏迥绝,民浸于实惠而士变于勤教。好若兰芝,爱若父母。”[3]235在《与刘乐城》中,赵南星回忆称:“昔者老师之莅敝邑也,星方弱冠,为诸生。老师爱之之至深,不啻亲子弟。星其时少年愚昧轻脱,虽感恩不浅而犹未知知己之难遇也。迨今五十有四矣,发种种矣。所交天下之人多矣。所见天下之为守令者不少矣,孰有如老师之爱星者乎?”[3]694师生之间的感情之深厚不仅仅在于赵南星的聪慧好学,也建立在赵南星对其思想和理念的领受上。
三、 《学庸正说》思想倾向
《学庸正说》成书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乙卯,赵南星主要用来教习子弟。此著作他曾寄高攀龙相阅,“向得手教,望以商量学位,仆未敢废学,恨不得与足下诸贤朝夕讲论,以祛习气耳。年来为小儿著《学庸正说》,亦足以知其中之所存。足下试取而观之,为我指其舛谬,则仆之受益多矣。”[3]700虽未见高攀龙的回复,但《学庸正说》的思想与高攀龙对于《大学》《中庸》的观点有相仿的取向。 关于《大学》《中庸》,朱熹和王阳明都持有“《学》《庸》一体”的观点。朱熹将《大学》《中庸》两者一体,互相发明,承载一以贯之的道统真理,成为构建“四书体系”的组成部分。王阳明亦认为两书内在一体,“子思括《大学》一书之义,为《中庸》首章”[7]。对于《大学》《中庸》两书,赵南星亦认为认为两者一体,相互贯通,互为表里。他在序言中称:“《论语》者,编次仲尼及弟子之言也。《孟子》者,孟子之所著也。惟曾子、子思之所为书,以《大学》《中庸》名。《大学》者,言其道之大也;《中庸》者,言其道之中正而平常也。二书之大旨具矣。初学率苦二书之难通,而尤以《中庸》为难。夫大者反易,庸者反难,二贤岂欺我哉。夫道一而已矣。言语文字则有详略隠显之异焉,犹厥之与其旃之与之也。且以二书之首章言之明徳,则天命之性也,率之而为道,不待言矣。新民则修道之教也,慎独所以诚意而正心也,中和在其中矣。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即天地位万物育也。曾有一之弗合者乎?”[1]358他指出,《大学》和《中庸》所言“道”相同,切入点不同,前者言道之大,后者言道之中正平常。虽然两书诠释道的角度不同,但两者互相映照发明,《大学》的明德即《中庸》的天命之性,《大学》的新民即《中庸》的修道之教,《大学》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即《中庸》的天地位、万物育。
概括而讲,《学庸正说》以朱学为本,杂糅王门后学,呈现出调和样态。
(一) 以朱学为本
首先,在诠释上以朱子为本。赵南星在推阐经典大义时,多以程朱观点作为阐解的基础。如在对“明德”的阐释上,赵南星称:“夫德而谓之明者,以其虚而且灵,具仁义礼智之性于中,而足以应夫万事也。既曰明德,则本无不明也,而犹有待于明之者,盖人钟二五之气以生,不能皆值其清而粹者,故耳目口鼻之欲,得以因其气禀之拘而蔽之而明者昏矣,然其明犹未尝息也,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审理欲之几,致克复之决,务使偏者以正,蔽者以开,而本明之体得以复其初也然。”[1]359这种阐释基本上就是顺着朱子的观点展开,指出“明德”的性质有三:一,虚灵;二,具有仁义礼智之性;三,足应万事。可见,“明德”具有体用,虚灵为其“体”,应万事为其“用”。天赋“明德”,“盖人之所得乎天而无少不明者,德也,人皆有之。”[1]363“吾之与民,同受明德于天。”[1]366“明德”保证了行为的道德必然性。赵南星承朱子观点,认为明德虽然是天赋于人且纯粹,但由于气禀的缘故、物欲的遮蔽、工夫的松懈,导致明德丧失,因而,要复归本然之明德,就需要格物和慎独工夫。此外,在《学庸正说》中多处引用王樵的《绍闻编》作为推衍材料。王樵深受朱学影响,对于王学多持有批判态度,可以说赵南星对他观点的引用亦是尊朱的一个体现。
其次,以客观的道或者太极为最终本原。赵南星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盈天地之所生所化,无物非道也。然历历而数之无一非物,无一物名为道者,盖道藏乎物之中矣。穷世运之既往方来,无事非道也。然缕缕而析之,无一非事、无一事名为道者,盖道潜乎事之内矣。是其有也,天下之富有也,亦天下之妙有也。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者也。”[1]389不仅无物非道,无事非道,而且他认为道体无物不包,无物不体,“君子语道之大,至于天地,圣人之所不能尽,可见此道无物不包而其大无外,凡载物者必大于其所载者也,而道乘乎器之表,不可得而限也,岂有能出于其外而载之者乎。语道之小,至于愚夫愚妇之所能知能行,可见此道无物不体而其小无内,凡破物者必小于其所破者也,而道贯乎形之中,不可得而析也,岂有能入于其内而破之者乎。”[1]390在本体的认定上,虽赵南星并没有取朱子之“理”,但是他的“道”与“理”并无二致。
第三,在认识论上肯定格物。赵南星批评王学舍物求心之弊,称:“仆见今之讲学者,至宋人‘即物穷理’之说,判以为非,欲一切求之于心。嗟乎!我,物也;道既有名,亦物也。故‘良知’者,阳明之障也。”[3]671他肯定朱子的格物论。如“格物致知”一节,他肯定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之功,对朱子的补传进行阐释。赵南星称:“朱子补格物致知传意,谓大学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然格物致知,乃学者最初用力之地,于此不用其力,则如醉不醒,如梦未觉,而诚正修齐治平,举无自而用力矣。然则此传,诚有不可缺者,故二程夫子始为之说,以开圣学之源,间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1]366-367
对于格物致知,朱子称:“《大学》所谓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穷得本来自然、当然之理,而本心知觉之体光明洞达、无所不照耳,非是回头向壁隙间窥取一霎时间己心光影,便为天命全体也。”[8]朱子肯定心的能动、知觉功能。赵南星对心的认知,一方面肯定朱熹对心的观点,肯定心的认知功能,称“人心之灵,所以妙众理而宰万物,莫不有知也”[1]367;另一方面,将朱熹心的“无所不照”的功能发展为“人心物理,相为流通”[1]361-362。在物之理和人之心的关系上,赵南星认为,从认知角度来看,内存于主体的心之理和外在客体的物之理两者之间不存在隔碍,内外贯通,因而“知在心,而实周于物;理在物,而实具于心”[1]367。两者之间没有隔碍之前提,为格物致知、物格知至提供了保证。如果说朱子的格物论强调了穷理,而赵南星的格物观则更加突出了心的地位。他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虽散在万物,实管于人之一心。人心物理,相为流通。理有未穷,知必有蔽。欲致知者,又在即事即物,穷其所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而物无不格可也。诚能于理之在物者,有以诣其极而无余,则一真内融,万境俱彻,而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至矣。”[1]361-362又称:“是以大学始教之初,必使后学自一身以至于万物,莫不因吾心本然所知之理,而益加学问思辨之功。……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则万殊一本,而为吾心之体之全者,有以极其全;一本万殊,而为吾心之用之大者,有以充其大,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1]367格物穷理是本于心之本然所知之理,在此基础上,推至心体之全和扩充心体之大,这就是知至,是客体与主体同一,是物理与心理合一的最高境界,是“一真内融,万境俱彻”通透圆融境界。可见,赵南星一方面尊朱,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对朱子的观点进行了创发,丰富了格物思想。
第四,在功夫论上主敬。赵南星反对王学不重功夫,认为王学不主张工夫,是释氏之说的改头换面,“学者亦遵圣贤之遗训而防简于身心之间,沉潜体究以俟时至而自悟耳。若夙无涵养而奇之以直透性体,不假修习,遂能目下领会终身无过,则夫子之圣,尚言三畏九思,择友改过,亦好劳甚矣。夫学以尽性谓之无所增益,则可安得云无所修习乎?乍听之则可喜,而徐择之则甚谬。盖释氏之邪说而昧者窃之以为至宝者也。”[3]164-165面对王学不主张修为的做法,他提倡主敬,指出,“欲修身者,必敬以直内,虚以应物而先正其心。”[1]361“人心只有动静二样,静时主敬,以培植根本,将动又提防私欲,用功不过如此。”[1]381在他看来,“敬”之工夫最为切实、完善,“夫语圣学之要则,一敬尽之矣。即‘致良知’之说,未若敬之一言正大而无弊也。”[3]163君子主敬,“一敬常存,以立万变之主宰,则天载之神,湛然常存于虚眀之中,而物交自不能引矣。”[1]380“君子主敬以立中,必使心之所存一,天命之密藏,而纎毫之偏私不得以杂之,真能立天下之大本,而致吾之中焉。”[1]381可见,赵南星非常推崇“主敬”工夫。
(二) 杂糅王门后学思想
虽赵南星尊朱,但并不意味着他全然承袭朱子之说。他的理学思想中对于王学后学多有借鉴和吸收,合会朱王之意亦鲜明可见,体现出燕赵士人兼容并蓄的治学之方。赵南星自述接触到罗汝芳之学,“自是而余读孔孟之书乃稍知其旨趣,读诸子之书,乃能辨其是非,则感杨先生已。”[3]158可见赵南星对罗汝芳、杨起元等人思想的欣赏以及后者对他思想起了启悟之用。赵南星的《大学正说》中融入了罗汝芳的“孝弟慈”思想,如在诠释“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章中,赵南星通篇以“孝弟慈”进行解说齐家治国,称“盖家国同一理,齐治无二机,是故孝者,所以事亲也。然国之有君,犹家之有亲,所以事君之道,宁有外于孝乎。弟者,所以事兄也,然国之有长,亦犹家之有兄,所以事长之道,宁有外于弟乎。慈者,所以畜幼,也然国之有众,亦犹家之有幼,所以使众之道宁有外于慈乎。然是孝弟慈也者,根诸人,心之固有,而非由外铄。发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强为,故康诰曰,如保赤子。诚以赤子有欲,不能自言为之,母者惟其中心爱之,是以心诚求之,虽或不中,亦不远矣。然此皆自然而能,世岂有学养子而后嫁者哉。慈幼之道既不待于强为,则孝弟亦岂待于强为哉。”[1]370并在结尾大段引用其言,如:“罗近溪曰‘孔子此书,却被孟子一句道尽。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孝弟慈,原人人不虑而自知,人人不学而自能,亦天下万世人人不约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为知,以所自能者而为能,则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于天下。此三件事,从造化中流出,从母胎中带来,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试看此时,薄海内外风俗气候,万万不齐,而家家户户,谁不是以此三件事过日子也。只尧舜禹汤文武,便皆晓的以此三件事,修诸己,而率乎人。以后却尽乱做,不晓的以此修己率人,故纵有作为,亦是小道,纵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学术也’。”[1]372在诠释“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二节”中称:“此章说平天下不外乎孝弟慈。罗近溪所谓大学术也。”[1]373此外,赵南星对于杨起元的思想亦有一定的接受,他称:“乙丑之岁,过杨复所先生于长安,闻其言,乃读宋儒及近日道学先生之书,略窥孔孟之旨,能修志意,不絯于富贵声名,有以自乐,身亦无病。”[3]176除此两人之外,《学庸正说》中亦多处引用王门后学中的唐顺之、邓以赞的观点,如在《大学正说》中关于义利之说,赵南星称:“以义为利,犹云以不贪为宝耳。享其利,只可带说。荆川之文至矣。”[1]377-378在《中庸正说》中对“鲜能知味”一句的诠释称:“邓定宇云,道无不在,而在口则能知味,此是元解。”[1]384除了上述王门后学人物外,赵南星与王门中的其他人物亦有交流,对他们著作也都加以搜寻、阅读,如与邹元标书信中称:“门下别久,所著述必多,幸从养冲处寄我,以当提诲,无遐遗也。”[3]697与汤显祖书信中称其“聪明绝世,言语至妙,今所著作,复得几百种,可悉示我阅。闻郎君之才,不亚乃翁,年来贤父子所为四书书经,乞寄下,小儿学书经,愿得而读之”。[3]697对于王门后学中的管东溟,赵南星亦是称赞,对于管志道的书,称“得之甚奇,仰见知己”[3]683,称自己“独于《易》了不能解,以为《易》者,圣人之所用也,非所谈也。不遇真师口授不能用,不能用亦不能谈,断非如程朱所解,断非可以臆测,想足下必有真得,不肖安得一闻玄秘,以不虚此生乎”[3]683,希望能在管志道那里得到指点。可见,赵南星并不是一味地批判王门后学,而是不拘于门户之见,兼容并蓄,试图通过融汇朱陆的方式重新整顿多元、激变的思想秩序,体现出晚明时期思想界试图以程朱收束王学的学术倾向。
概括而言,赵南星的《学庸正说》在尊朱的取向下,亦融摄王门后学的思想,试图调和朱王。这种调和表现在:一是以“道”为本体论根据,调和朱王。他既不取朱子之“理”,也不取阳明之“良知”,而是以“道”来融通朱王。二是,赵南星既强调格物致知,同时注重王学所强调的良知、心的主宰作用,以天赋的道德意识萌芽为发端,以后天的涵养、扩充为功夫,避免了王门后学蹈虚履空、好高骛远的学风,又避免了朱学末流读书穷理、皓首穷经的弊端。赵南星的学庸思想虽具有浓厚的朱学色彩,在当时学风之下,他对朱学的复归、对王学的批判无疑契合了明清之际的学术发展脉络。他的思想虽然不能和孙奇逢、黄宗羲等比肩,但是亦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在燕赵地域之学传承和发扬今天,他的思想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