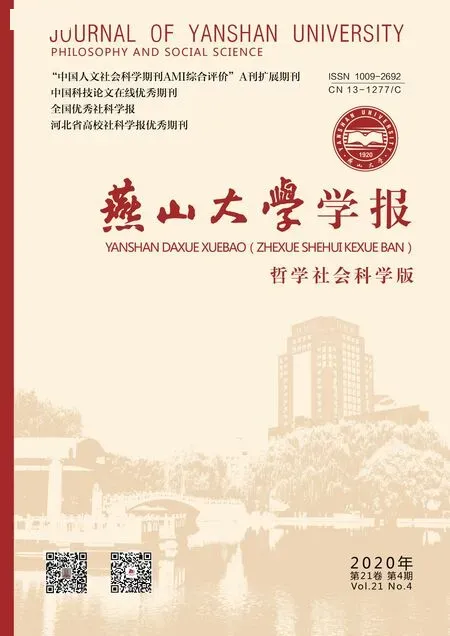皮尔士符号学视阈下的旗帜研究
徐结平, 贾艳贤
(1. 巢湖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巢湖 238000;2. 泰国西那瓦大学 人文学院, 泰国 曼谷 12160)
一、 引言
在欧美,旗帜研究业已成为一门学科。现代旗帜学的奠基者惠特尼·史密斯(1975)将其定义为关于旗帜历史、象征意义与使用的科学研究。广义来讲,一切关于旗帜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统称为旗帜学。[1]旗帜学的英文名称为Vexillology,词根取自拉丁词Vexillum,Vexillum为古罗马军旗,形态已具备今天的旗帜的雏形——由旗杆与绘有特定图案的布料组成。该学科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60年代,成立了世界旗帜学协会联盟(FIAV),召开了每两年一次的世界旗帜学大会(ICV)。几十年来,欧美学者对旗帜的历史、当今世界旗帜现状做了系统且细致的研究,但可能源于文化的隔阂,特别是中国古文的相对艰涩难懂,他们的许多研究结论出现了偏差,甚至是明显的错误。其实,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旗帜的国家,研究表明在商代的甲骨文,以及后来的金文中都能找到与旗帜相关的汉字:事、旗、旅、斿、祈等,旗帜的实物已荡然无存,但在先秦的古文字中尚可见旗的象形,通过这些字迹,可窥测中国古代旗帜的一些最初的形态。[2]中国旗帜不但历史悠久,其运用也相当系统与发达,先秦的许多经典中就有对旗帜使用的详细记载,比如《周礼》《墨子》《孙子兵法》等,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学界对旗帜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意指过程的理论[3],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作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与另外一位符号学先驱索绪尔的最大不同,就是他挣脱了机械的二元论而引进了动态的三元观,特别是在符号(sign)与对象(object)之间加入了解释项(interpretant)的概念,能诠释如下现象:不同符号主体对同一符号使用会有所不同;同一符号主体在不同的语境中对符号的解读也不一样。这无疑为我们分析旗帜的符号效应在符指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便利。
二、 西方旗帜史研究概况与局限
关于旗帜的起源,我们得从旗帜使用的最初用途中找寻答案。人类学家涂尔干与莫斯合著的《原始分类》(2009),研究了原始人类的图腾[4],指出旗帜的起源可能与人类的原始图腾有关。在原始社会,图腾物寄托的不但是某特定群体的集体崇拜,也能传达身份认同,相互责任和区别其他氏族的作用,这与旗帜的基本功能类似。[5]欧美学者将旗帜史分为三个阶段: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国旗时代。[5]
按照惠特尼·史密斯的说法,今天的旗帜的基本形态源自于古罗马的军旗,在欧美学界已成共识。但在古罗马战场上的作用远不及vexilloid,“一种与旗帜功能相似但通常外观有一定的差异,圆杆顶部常见一雕塑的动物形状”[1]。Vexilloid在形态上类似权杖,使用中包括了旗帜的功能。它没有布料的设计与今天的旗帜相去甚远。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覆灭,西欧大一统的时代基本结束,中世纪西方封建主义得以发展且形成地主阶级,西欧形成了大小不一的封建政权割据一方的态势,这促使骑士阶层的兴起。战乱频发,每个贵族领主都为自己的保卫者——骑士设计了代表自己的独特符号,帮助这些身披甲胄、头戴重盔的骑士在战斗中区分敌友。这使得纹章设计大为发展,战旗的重要性让位于更具实用性的盾牌等战场工具的纹饰。这些精心设计的图案因战场识别的需要,日益成为身份的象征。但在这段时期,旗帜随着纹章的设计有了新的发展,旗帜的图案与古罗马时期相比,不再以猛兽为主,特别是经历了十字军东征之后,十字架之类宗教性质图案汇入了旗帜的设计,使得旗帜增添了信仰的厚重,从异教徒中夺回属于他们的圣地,十字图案的旗帜昭示全体基督教徒他们是为上帝而战,为信仰而战的骑士,符号为他们的杀戮披上了所谓正义的外衣,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今天的丹麦、英国、挪威、瑞典等国家的国旗就是追随这一传统。
旗帜发展到近代,也就是第三个阶段,呈现了两大特征:其一,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特别法国大革命之后,为了冲破本国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外来势力的重重阻挠,以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带有浓重资产阶级色彩的平等与民主思想被大肆宣传,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诞生,国旗成为其象征,作为政治符号被提升到了重要位置。其二,旗帜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行会、社会团体、后来的国际组织、球迷俱乐部等都可以拥有代表自己的旗帜,可以这么说,从那时起旗帜的使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普遍。
欧美学者对旗帜的专门研究成果卓著且研究细致,但遗憾的是以欧洲旗帜为研究对象,未能全面观照世界其他文明(特别是古代中国)对旗帜的设计与运用,更为遗憾的是,有许多明显误判。
首先,认为最先将旗帜分为不同颜色的是古代阿拉伯人,不同的颜色代表相应的时代与领导者,先知穆罕穆德用黑色旗帜,他的传人Abu Bakr用白色旗帜,Umar则是用红色旗帜[1],这种设计在现代欧美三色国旗中的设计依旧普遍。其实,早在阿拉伯人一千年前的中国先秦《墨子》旗帜篇中早有旗帜不同颜色的记载:苍赤黄白黑,并阐述在守城中的不同用途:“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6]
其次,认为18世纪欧洲人在海上贸易首先发明了“旗语”。 18世纪海上船只的旗帜在设计与使用方法上经历了重大变革,随着海上争霸的进一步白热化,舰队协同作战需要指挥,旗语第一次在海战中被使用,在随后的百余年信号旗的使用成为海上通讯的基本手段,直到19世纪才被无线电通讯所取代[1]。其实,旗帜作为信息传递工具在中国古代战场已经非常完备了,戚继光(2001)的《纪效新书》卷十六《旌旗金鼓图说篇》有详细的图文记载,88种旗帜具有不同的信号传递功能[7],说明旗语在中国古代战场运用普遍,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加详述。
第三,旗帜在战场上的实际用途并非局限于区分敌我。[1]这也与古代欧洲战争规模相对较小有关,投入战场的人数不多,统一调度相对简单,不需要专门的指挥系统。中国古代战争则不然,规模大,人数多,且多为步兵,机动性相对较弱,将领需要旗帜、锣鼓等指令调度,士兵也需要信号的指引,《孙子兵法》云:“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8]在中国古代,为实现全军协同作战,古人创造了传递前方地形信息的联络旗、用于指挥士兵杀敌并能鼓舞士气的号旗、适用于特定行军阵法的阵旗、象征军队最高统帅的牙旗、各部将领的将旗、扎营标志的营旗、传递战时命令的令旗、战败投降时降旗、指示方位的四方旗等。
三、 对象—符号—解释项:三元观视阈下的旗帜符号
皮尔士一生著作颇丰,据后世学者统计,他写作生涯持续近半个世纪,平均每天2000字以上[9],但面世的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多是尚未整理发表的手稿。在皮尔士的符号理论中,三元观(triad)是其核心。他将符号定义为“连接符号对象(Object)与解释项(interpretant)的中间媒介(medium),对象决定符号,符号又决定它的解释项”。[10]但符号与对象之间并非直接关联,虽然符号由对象决定,但这种决定关系依靠解释项来完成(如图1)。皮尔士的解释项是其符号三元项中的必不可少的一环,皮尔士(1896)举例解释:“因此,(当你)看一幅地图时,地图本身就是载体,地图所再现的国家就是对象,而思维中的想法就是解释项。”[11]其中,符号载体就是符号本身。解释项的存在使符号表意过程进入三元互动,而非索绪尔能指所指机械的二元体系,在这里解释项是符号的延伸,继而成为新的符号。“符号的三元概念表明意指过程的另一特点,即一枚符号并非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它需与其他符号相关,因为从定义上看,每一枚符号必须具备可阐释性,这就需要至少另一枚符号的预先存在。”[12]这种动态的延伸就是皮尔士的无限衍义(semiosis ad infinitum)。
皮尔士将对象划分了直接对象(immediate object)与动态对象(dynamic or dynamical object),解释项又分为直接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动态解释项(dynamic interpretant)和最终解释项(final interpretent)[13]。
在1906年给韦尔比夫人的信中,皮尔士又添加了意图解释项(intentional interpretant)、效应解释项(effectual interpretant)、交际解释项(communicational interpretant)或共同解释项(cominterpretant)的三分类,但国内外对此三元的研究并不多见。“意图解释项,决定符号发出者思想;效应解释项,则决定着符号接收者思想;为了交流的顺利,交际解释项或者说共同解释项是它决定着发出者与接收者思想的融合,这种思想可以称为共有项,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交际)一开始就共同理解,其目的是为了符号交际功能的实现。”[10]依皮尔士的观点,我们可以做如下理解:
首先,在1868—1869年的三篇系列论文中,皮尔士提出了自己的符号学认识论——“一切思想都是在符号中”[14]卷5:253,意为我们所有的知识不是凭空而来,都是传承前人果实而来,就像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符号一样,而语言或其他符号系统是我们思维的载体,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思想的呈现。依此而言,存在于思维中的解释项在某种程度上能决定符号主体的思维。
其次,意图解释项是存在于发出者思想中的,带有明显主观意图的思维符号,它意在将发出者的意图与愿望强加给符号的接收者;效应解释项是接收者在对传输而来的符号在自己的思维中自我解读,从而可能产生有违发送者本意的解释。
第三,共同解释项(为便于理解,下文统一采用此名称,而非交际解释项)是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交际发生前就存在的思维共有项(commens),即相互的默契。需要指出的是,皮尔士此处所言的共有项不是指交际结果,并非指双方同意彼此观点或达成一致看法,而是存在于他们思维中能影响他们沟通的某种共有的经历(common experience)[10],它是交际的前提,是符号发送者与接受者思想能否融合的决定因素,它的在场与否决定了交际是否成功。
因此,皮尔士将解释项放在动态的交际(communication)语境中,并将发出者意图、接收者对符号的反应、交流前提条件都纳入其中,这使得交际存在如下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就是共同解释项在场,意图解释项与效应解释项出现融合,从而实现符号效应的顺利传输,这样交流也就顺利进行(如图2)。
第二种可能性是共同解释项缺场,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思维(commind)[10],他们不在一个思维层面上,不存在默契,那么意图解释项就仅停留在发送者一段,无法与效应解释项相融合,导致发送者与接受者无法交流(如图3)。
依据皮尔士的对象—符号—解释项的三元观,旗帜作为符号,它所代替的对象是某一团体、组织、族群或国家,他们对旗帜设计与使用有决定作用,即旗帜的对象决定了旗帜符号。旗帜的直接对象是符号主体思维中旗帜所代表的对象,它可能和动态对象之间存在偏差,如中国古代仪仗队中的大纛,其图案的直接对象是龙,是想象中的动物,不存在动态对象,象征的是真龙天子,即皇帝。解释项的概念能为我们对于旗帜作为符号在符指过程(semiosis)中出现的各种现象提供解释。旗帜的直接解释项就是指旗帜的意义,符号主体会对旗帜的直接解释项有一定的认同,这里的主体宏观上指某个国家,中观指同一社会或组织,微观指个人,认同感使得旗帜成为他们情感联系的纽带。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它也会受到主体间性的影响。符号主体的不同对同一旗帜的阐释会呈现巨大差异,国人对本国国旗的意义阐释和他国人一定不同,球队的队旗对于己方球迷群体与对方球迷也会以不同的感受呈现。即使是同一符号主体对旗帜的解释项也会存在差异,在异域他乡见到一面飘扬的本国国旗可能与在国内不一样;平时的升旗仪式与灾难时民众手中摇晃的国旗的实际效应也不一样,这是因为相同的符号主体,对于旗帜的动态解释项会不一样。针对旗帜的不同符号行为,作为符号本身或者载体,解释项会千差万别。因此,现在的许多国家,为了规范关于旗帜的符号行为与避免不同群体的因旗帜而引起的冲突,通过树规立法的方式做出必要的规范,如《国旗法》的实施就是通过保护旗帜这一符号来维护它的对象,其目的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引导本群体所有成员指向旗帜的最终解释项——也就是旗帜符号存在的“目的”[14]卷2:305。
旗帜的符号效应在于接收者对旗帜的阐释,也就是旗帜符号的效应解释项,但作为群体的指称,旗帜的意义是群体强加于个人,它不同于其他符号之处为它的发出者力量强大,换言之,它的最终解释项会受到发出者的强力干预来达到集体的认同,形成一定的共识后才最终成为个体的工具。因此,旗帜最终解释项是旗帜的符号效应的条件,也是旗帜的目的所在。其效应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旗帜的标记效应
人类具有寻求意义与创造意义的天性,自古以来我们一直在创造与使用符号来表意,在古代,社会群体中一直存在着某些人或团体通过特别设计的符号来表达自我与他者的不同,用旗帜来外化社会地位的高低,建立一套严格的旗帜使用的等级制度以彰显身份的不同,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州官县令,统治阶层利用旗帜的规格标记出自己高人一等,他们都有代表自己身份的旗号。海上船只所悬挂的旗帜标记归属,某种特殊符号还能为船只的停泊提供方便,某面特殊的旗帜能为船只提供庇佑,这都是符号的标记作用。
2. 旗帜信息传递效应
这在战场上表现尤为明显,无论是地面部队还是海上舰队,旗帜一度是指挥者了解敌情与指挥战斗的重要工具。中国古代士兵通过飘扬的己方旗帜得知战况,指挥者依靠旗帜符号传达相应的作战指令。中国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特别是发生在白昼的战斗,旗语的作用不可替代。《左传》有云:“师之耳目,在吾旗鼓。”[15]但是在各个地方,旗帜的信号功能的使用程度有异。在古代西方,战争中旗帜的主要作用还是区分敌我,传递信号功能并不发达。在中世纪的欧洲战场,旗帜实际用途不比士兵的服饰、盾牌纹章等在区分敌我方面的实用性。据记载,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中,诺曼公爵威廉为了鼓舞士气,需要在战斗的同时,向自己的士兵的脱下头盔以示自己依然在战斗而非殒命。[16]这无疑暴露了服饰无法迅速识别的弱势,而在中国古战场上,帅有牙旗,将有将旗,一目了然。
3. 旗帜的情感效应
旗帜能激发是某个群体内成员的某种情感共鸣,成为彼此间的情感纽带,而这种情感的共鸣能跨越成员间诸如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而且这种情感联系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群体内的成员才能建立这种情感,群外人士对此感受不到。比如,看到奥运会赛场升起的本国国旗会热泪盈眶,球场上球迷看到本方球队的队旗而心潮澎湃。旗帜如果引起不了这种情感上的共鸣,那它和一块普通的布毫无两样。
4. 旗帜的说谎效应
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1976)指出:“符号虽说是一物代另一物,但此另一物并不一定非得存在或者确实在某处,因此符号学从原则上说是一门研究可以用来撒谎的一切。如果某物不能用做撒谎,相反它也不能用做述真。”[17]在另一著作中,他(1984)从逻辑学的角度分析谎言:“符号可以用来说谎因为前件(表达层)并不要求后件为之必需或动力因。”[18]在这里艾柯是将逻辑学中的前件与后件对应语言学中的表达层与内容层。其实,在皮尔士后期的意图解释项—效应解释项—共同解释项的分类中,我们可以初见符号谎言生成的端倪,即当共同解释项在场的情况下,目的解释项与效应解释项出现融合,符号发出者成功操纵了接受者的符号解释项,以一种利己的方式实现了符号效应。这在战场上表现尤为明显,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战场就是两方或多方对符号的争夺。如果一方能占据有利的符号,有效地控制有利符号,正确地解读对方所传来的各种信号,甚至操控战场符号就能做到孙子所说的“致人而非致于人”[8]。作为战场上的重要符号——旗帜历来就是兵家关注的重点对象,古今中外不乏操控旗帜赢得胜利的战争。正如孙子云:“兵者,诡道也。”[8]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以旗帜为的道具,设计围绕旗帜的战术。古罗马将领故意将己方的军旗投掷于敌方阵营,使得本方士兵奋勇拼杀。中世纪军营中常见的火龙旗配上恐怖的呼啸发声器,犹如恶龙从天而降,让敌方士兵瑟瑟发抖,军心大乱。灵活运用军旗以实现作战意图在中国古典的军事理论中早有记载,《六韬》中就有“白昼如昏,数更旌旗,变易衣服,其军可克”,“多设旌旗,杂以强弩;或击其两旁,或绝其前后,敌将可虏”[19]的作战策略。《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中记录唐太宗李世民运用旗帜骗过突厥人以解雁门之围:炀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太宗谓定兴曰:“必赍旗鼓以设疑兵,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20]
李世民通过绵延几十里的军旗与连天的鼓声,营造了百万勤王之师到来的假象,成功骗过突厥的围军,计谋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共同解释项在场,此处的共同解释项为旗帜的数量指示军队的多寡,在共同解释项的作用下,旗帜的意图解释项成功地与效应解释项融合,实现了李世民的退敌之策。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21]中详细记载了韩信“背水一战”的经过,旗帜的运用更为精彩。作为符号的发出者,韩信的意图解释项有二:其一,尽量以弱示人,这里的弱有两层意义,一是本方兵力单薄, 二是主帅毫无指挥经验,让敌人掉以轻心,目的是让对方倾巢而出;其二,退无可退,决一死战,激发本方士兵的斗志。要想实现此二意图,韩信做起了旗帜的文章。具体说来,他分三步走:首先,在大战未开始,将自己的弱势完全暴露,“背水陈”,“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接收者(赵军)的效应解释项为:兵力与本方悬殊,且主帅现阵中,可生擒。背水而战的符号效应对赵军而言为韩信不懂战,必败无疑,因为他违背了“右背山林左前水泽”的对阵常识。第二步为“佯弃鼓旗”与“走水上军”,丢弃旗鼓的效应解释项有二:一是汉军已经一败涂地,二是延缓敌军的行军速度,因为赵军士兵势必争夺丢弃一地的汉军旗帜,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战利品势必为日后的奖励的凭证;二是对于己方士兵而言,背水一战,已经丧失了任何逃跑的路径,除非死战,也就是韩信说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第三步,派两千骑兵绕道敌人后方军营,“拔赵帜,立汉赤帜”。这一步尤为重要,拔掉对方的旗帜,插上汉营的红色旗帜,赵军前方遇到了汉军的顽强抵抗,根本进无可进,见到后方一片赤红的汉军旗帜,它的效应解释项为“汉皆得赵王将”,于是军心大乱,作鸟兽散。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韩信以自己超高的军事指挥才能,通过对旗、鼓、河流等符号的运用与操控,赢得了胜利。
四、 旗帜的符号类型
依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皮尔士将符号分为像似符(icon)、 指示符(index)与象征符(symbol)[14]卷2:307,像似符是通过相似性(similarity)与对象之间建立联系,但这里的像似性并非局限于视觉感官。指示符与对象的关系为一种邻接(contiguity)关系,为了区分皮尔士认为从三方面特点将它与其他符号加以区分:“第一,他与对象之间没有明显的像似性; 第二, 他们指称的是一些个人、单一单元、单一单元集或者单一连续体;第三,它通过某种隐蔽的强制力将关注点指向其对象。 ”[14]卷2:305象征符的构成仅是或主要是一种因自然或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
由以上三类符号可总结出两点:第一,皮尔士符号学是以逻辑学为基点。符号的三元关系依托于其普通范畴的第一范畴(firstness),第二范畴(secondness)与第三范畴(thirdness),范畴论的三元关系为:第三范畴包含第一范畴或第二范畴,第二范畴包含第一范畴,第一范畴为存在(being),它是独立之存在,第二范畴为依蛮力(brute force)而建立的事物关联,是一种相关关系,第三范畴将第一范畴的存在与第二范畴的关联依据调停(mediate)手段纳入其中[14]卷1:356,据此将像似符拟定为一级符号,指示符为二级符号,象征符为三级符号[22]。象征符可能依然保存着某些像似或指示的成分,也就是说三级符号可以包含一级或二级符号。第二,符号类型的三分并非相互排斥。对符号表意过程主要特征的描述,这种分类不是绝对,正如皮尔士所说:“没有绝对纯粹的指示符,或者某个符号完全没有指示特征,(只是)从心理上讲,此类型的符号行为取决于其邻接关系,而不是其像似性或思考。”[14]卷2:305
从旗帜与对象关系的视阈我们可以观照到旗帜的进化史,总体说来,旗帜史遵循了符号从一级到三级的转化历程。前文提及旗帜可能起源于原始部落的图腾,人类的原始图腾可能是对某种自然现象的恐惧,惊叹大自然的力量,这种恐惧继而发展成为一种崇拜,比如雷电、飓风、山崩地裂,或者某种凶猛动物(诸如猛虎、群狼、 野牛、毒蛇),又如供奉自己祖先,为他们塑像,将他们供上高台,或将这份敬畏画在布料上,从实物崇拜转为符号崇拜,即从具体有形到抽象有形的转化。[23]此时的旗帜还是像似符。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图腾不一样,图腾符号成了特有的标记,标识着本部落的领地、成员与物品等,完成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邻接(congruity),这也是旗帜成为指示符的由来。如古代中国皇帝仪仗中特有的旗帜可以指示皇帝的所在;在战场上,通过特定的令旗传达作战指令,令旗指示主帅。在这里旗帜的像似性脱落,指示性形成,一级符号上升为二级符号。到后来旗帜的使用发展成为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章甚至系统,其用途不仅是指示,如《周礼》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载大常,诸侯载旂,军吏载旗,师都载旜,乡遂载物,郊野载旐,百官载旟。”[24]古代中国皇帝有专属卤簿,大纛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符号。这些符号随着品级的不同有严格的制度限制,形成了一套符号制度。在戒律森严的古代中国,皇帝仪仗符号中旗帜的大小、颜色、图案、数量是决不允许与他人共享,僭越是一项不可饶恕的重罪。各级贵族官员也拥有属于本品级的旗号。在古代中国战场上,军旗的名目多达88种, 因此认旗,熟悉旗帜所传达的号令是古代军人的必修课。这些旗帜的使用,任何人都不能随便改变,这时的旗帜就成了象征符,发展成三级符号。
前文论述皮尔士的对象—符号—解释项三元观中提到,对象决定符号,符号决定解释项,至于对象如何决定符号,类似的问题在语言学领域一直存在争议,即语言作为符号到底是任意性还是理据性。笔者认为旗帜作为符号的一种,当它还是处在一级或二级符号阶段时,像似性与指示性应该是以理据性为主,当它成为三级符号即象征符会渐渐失去前两级的理据性,转而任意性占主导。虽然人类远古时期的旗帜实物无法找到,但是今天依然能找到的许多旗帜保留了像似性的特点。比如,日本国旗基于大和民族对太阳的崇拜;十字架本是古代欧洲的刑具,由于耶稣的受难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十字图形成为基督教的标志,象征着爱与救赎。再如,今天许多西方国家的军旗采用鹰为主要图案,就是继承了古罗马军团的鹰徽,鹰作为凶猛的掠食者,这与军队的形象像似。联合国旗的图案是一副以北极为中心的世界地图被橄榄枝环绕,地图遵循的是抽象像似,而橄榄枝代表和平来自《圣经》,指示洪水已退,绿洲存在。今天的旗帜象征意义多以任意性为基础,比如我们常见的受法国国旗设计影响的以颜色条纹组合的国旗样式,任意性更加占据主动,法国的蓝白红三色在今天被解释为象征自由、平等与博爱,在其形成之初代表的是国王与市民;国际红十字会符号在穆斯林国家变成星月;美国星条旗的颜色构成的象征意义,其设计者解释为白色代表纯洁与清白,蓝色象征警惕、坚韧和正义,而红色象征勇敢与顽强。人们习惯在某种色彩上添加意义,但某种色彩是否一定代表相关意义,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心理学上看并无定论,特别是当颜色与意识形态或政治等相联系时,其理据性一定是让位于任意性的。
五、 结语
欧美人研究旗帜,要想囊括世界上各民族的旗帜历史与人文信息实无可能,中国旗帜的设计与运用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一部分,旗帜在我们的过去与现在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代学者对于中国旗帜的研究尚处起步阶段。旗帜符号的表意现象相当复杂,因为它不仅受到了发送者与接收者的主体间性,解释项所处的时空、传送方式的左右,更受到社会意识形态、国家集体意志等方面的影响。旗帜还具有战术价值,在左右战场走势方面旗帜一直扮演着或大或小的角色。旗帜谎言在古代战场更是司空见惯,或为激励本方士气,或为诱骗敌人。在分析旗帜的符号类型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将旗帜教条地归类为像似符、指示符或象征符其中之一,其类型取决于现实的运用,其价值在于它的使用。
注释:
① 国内学者有将communication翻译为“传播”,详见赵星植《皮尔斯的三元模式在传播学中的意义》。
② 国内学界有将symbol翻译为“规约符号”,笔者认为此译不妥,原因有二:其一,英文symbol与“规约”很难对等;其二,按皮尔士本人的一级符号、二级符号与三级符号划分, 三级符号可以包含一级,“规约”并不包含“像似”,而 “象征”指“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辞海》,1999年,第2338页), 切合皮尔士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