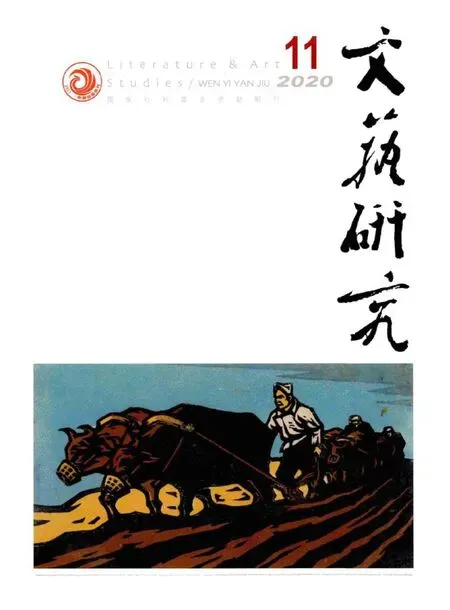批校本的层次类型及梳理方法刍议
——以清人批校本《文选》为例
南江涛
批校本作为一种古籍版本形态,虽然历来受到收藏家的重视,但进入研究视野相对较晚①。近年来,随着文献研究的深入和评点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批校本受到学界青睐,或被征引利用,或被个案考证,或被辑录整理②。与此同时,收藏机构公布的古籍影像和出版界影印出版的图书中,批校本也随处可见。然而,在研究和整理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将批校和过录混淆、把批校者张冠李戴等等。这与研究者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本文拟以笔者调查到的82种清人批校本《文选》中的典型个案为例,探讨批校本的基本层次类型,并对如何辨别和厘清批校本的复杂层次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批校中的圈点、标抹符号等暂不涉及;批校与过录所用底本不同造成的文本差异十分复杂,亦暂不讨论。
一、批校本的层次类型
此处所言批校本,包括名家手批本与过录本,不含刻印的评点之本③。过录本是抄者阅读的产物,通常保存了手批本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在手批原本不存的情况下,其价值更为凸显。过录本有一人专录一家批校者,也有一人录多家批校者,更有多个过录者录于一本之上的情况。有时,过录者还会施加自己的按断。过录本的存在,对手批本的传播和批校内容的丰富起了重要作用,是手批本得以保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当然,也正是由于过录者的存在,增加了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下面拟以清人批校本《文选》为例,从“人”的维度着眼,将批校本分为三大类六小类,分别举例分析其层次构成。
(一)同一家的不同批校本
即同一家批校在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副本之上。读书活动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由于目的、时间、载体的变化,同一家进行多次批校的情况时有发生。这造成了批校本在“源头”上的差异。通过这些差异,可以反窥批校者不同时期的批校特点。正如杰克森所云,读者的批校不仅可以反映其私人生活、读者的社会功能和他们所觉知的自己的社会功能,而且可以展示读者阅读时的学习、思维过程和心理状态④。清初钱陆灿集录明末清初孙月峰等诸家批校,又间出己意加以按断,形成了他自己的批校本《文选》,影响深远。上海图书馆藏有筠山录钱陆灿批校本《文选》,目录末录有钱氏跋语:“余第一阅本为邓生木上取去,第二阅本则杨生凫令临一副本见还,此本则孙生天士所临也。”⑤(图1)卷二三前衬叶又录钱氏跋语。据此可知,钱陆灿从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二十四年间,至少批校《文选》四次。他先后赠给邓木上、杨凫令、孙天士,最后自藏一本。这三人均为钱氏学生,邓木上为金陵万竹园主邓旭之子邓焮,钱陆灿曾馆于邓旭金陵万竹园。杨凫令即杨乔年,武进人,工书,名列常州书法“后四家”。孙天士,即孙闳达,字天士,号逊庵,江苏南通人。清康熙三年进士,官太原知县,著有《逊庵诗稿》《自知编》等。钱陆灿没有写过《文选》专著,其选学研究心得仅以批校形式传世。这四个本子,批校内容最多、传播最为广泛的是孙天士本。这一点从存世本批校内容多据孙本传录可以得到印证。钱陆灿批校《文选》,有因子女早丧而以读书纾痛的动因,更有教学的实际需要。他为孙天士批校之时,已经见过《文选瀹注》等书,掌握资料更为丰富,所以此本批校内容明显多于其他三本。这体现了钱氏掌握材料的变化与心境的不同。
除了钱陆灿、潘耒等人外,清人中批阅《文选》次数较多的还有许巽行。巽行字密斋,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数十年以校勘《文选》为业,校订异文,申说字义。光绪五年(1879),其玄孙许嘉德复加按语,整理刊刻成《文选笔记》一书。卷前有嘉德识语云,“高祖密斋公校雠《文选》凡十三次,痛削五臣沿习之旧,悉还李氏原有之文”,并且“皆有更正之文,而多未加载笔记”⑥。此外,俞正燮的两次批校本、顾广圻的不同校勘本、梁章钜的两个批校本,也都属于这类情况。批校者因为时过境迁思想变化、掌握材料不同、批校目的差异,进行了两次以上的批校。正如程章灿所云:“对流传版本进行校订,正讹补缺,从而制作某一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种新的文献……衍生文献虽然有所依傍,但它绝非没有原创性,相反,其原创性恰是隐藏于对原典的依附之中。”⑦同一家陆续在不同本子上进行批校,成为清代新的《文选》学著作生成的基本范式。

图1 筠山录钱陆灿批校《文选》 上海图书馆藏
(二)同一人(家)的汇校汇评本
同一人(家)不断将新获得的资料和心得汇集于一本之上,逐步形成了汇校汇评本。这种情况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批校者长期批阅一书,所见材料不断变化,阅读感受逐渐深化,于不同时间批校于一本之上;二是过录者痴迷一家,将名家不同时期的批校本汇集于一个底本之上。
1.批校者不同时期批校于一本
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梁章钜批校本《文选》,是此种批校本的典型。梁章钜是清代著名的选学大家,著有《文选旁证》。他在《文选旁证自序》中说:“束发受书,即好萧《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北往来,钻研不废。岁月迄兹,遂有所积。”⑧此序作于道光十四年(1834),距其“束发”(约1795),整整四十年。梁氏批校本《文选》,至少明确记载了两个不同的批阅时间。卷六首有朱笔“嘉庆甲子(1804)二月初旬校”的识语⑨,是卷内最早的时间节点;卷五五末用朱笔写有“嘉庆乙丑正月初六日,章钜手录并识”一句,则是接近此次校读尾声时所记。虽然不是每一卷的识语都得以完整保留,但这些简短的记录非常清晰地表明,1804—1805年间,梁章钜曾以朱笔校读此书。而各卷保存的墨笔识语,是梁章钜数年后又一次批校的证据。卷一有墨笔记“戊辰(嘉庆十三年)初冬校于赛月亭之背树轩”,卷三〇记“庚午重阳后三日,补校于赛月亭”,卷三五记“庚午八月十六日,重校于补萝山馆”,卷五八记“庚午九月七日重校于赛月亭”等等。上述几条识语,既明确记载了校读的时间和地点,而且说明校读是不断累积进行的。从内容来看,梁氏在这两次批校中主要利用的资料有孙月峰《文选瀹注》、何焯评点《文选》、于光华《文选集评》、方廷珪《文选集成》、林茂春《文选补注》、段玉裁《校文选》等。将其与梁氏所著《文选旁证·凡例》所举诸家比对,会发现批校本已具《文选旁证》之雏形。又以批校所引林茂春语与《文选旁证》比勘,会发现有诸多差异⑩,于此可看出梁氏不同时期的取舍倾向。当然,梁章钜这样标注批校年月的做法一目了然,非常容易看清批校层次和材料来源。如果没有标注,就需要从内容去寻绎并辨析批校层次。
2.过录者将同一家不同时期的批校录于一本
同一家不同时期的批校被过录于一本之上的情况,以名家何焯最为典型。当然,随着书籍的流转,单纯录一家而又显示出源自不同时期批校的本子,已经非常罕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佚名录何焯批校本《文选》,未见他处著录,最为接近此种类型。此本卷中有过录者识语五处。卷一首记:“从《义门读书记》中补入,以后凡云‘何云’者据本此。”卷一末记:“以上四篇评语旧曾借相传何义门先生本录出。近得杨耑木先生本,更为详密,因为增入,而以杨云别之。以后悉照杨本,故不复别署云。”卷四首记:“以下悉照杨本,其有从他本附入者,以〇别之。”卷一六首记:“此卷旧从别本批阅,兹将杨本评语增入,不复别署,而以〇别之。”卷二四首记:“以下评阅俱从吴阊本增入,故不复以△别之。”⑪据此,此人所录至少包括《义门读书记》、相传何义门本、杨本、吴阊本等四种不同来源的何焯批校,内容互有差异,当分别源自何氏不同时期的批校传本。过录者将其陆续录于一本之上,虽然中间杂有他人评语,但其目的乃是集录何批。此外,于光华在《文选集评》刊刻之后,也发现了何焯的初评本,并且增补到《重订文选集评》一书中⑫。虽然后者不属于专录一家者,但也可从侧面证明此类情形的存在。
(三)不同家的同一批校本
这种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的汇评汇校本;二是过录者在汇评汇校的基础上,还施加了自己的按语;三是收藏者得到的本子上已经有前人批校,他又在其上增录了他人批校或者记下了自己的按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流传、层累,形成了不同人的同一批校本。这样的一人或多人参与的汇评汇校本,是批校本中层次最为复杂的,其中大多数并未标注批校者姓氏,需要仔细辨析内容源流、辨别笔迹同异,进行综合梳理。
1.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
汇集诸家批校于一本,往往是过录者(也即阅读者)充分理解内容的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批校本的价值。这样的本子从内容来源讲,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本于一本;二是过录者节录汇评本内容而成。第一种情况有的卷前会清楚交代,比较容易识别。第二种则一般不留痕迹,需要仔细辨析。国家图书馆藏阮元录冯武、陆贻典、顾广圻校并跋本《文选》⑬,属于第一种情形。阮元在过录前辈、时贤校勘时,亦步亦趋,非常严谨。除了分别用不同颜色的笔校改文字,还过录了冯武、顾广圻的识语,乃至冯本的涂改、顾本的签条也都一一过录,并标明叶数,而且细致记录了冯武、顾广圻和自己批阅《文选》的具体时间。此外,王同愈批校本《文选》也是此类中比较典型的例子⑭。过录者的重点是汇集前人、时贤的批校内容,较少或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发挥按断,属于比较纯粹的学习,而非深入的研究。
明末,已经有《文选瀹注》《文选尤》等汇录数家评点于一本的刻本问世。南京图书馆藏佚名录俞、何焯批点《文选》,过录何焯康熙辛巳秋日识语后,又有朱笔识语云:“余幼时最爱《文选》,十二三岁时,每于师案窃取俞批《文选》抄录。甲申年意欲补全,值冀北之游中止。直至庚寅夏,始借友人本以竟龆龀之志,并借义门何师批本校录,可称二美具矣。”(图2)在卷二九末又有朱笔识语一行:“乾隆己丑二月花生日前一日点阅毕。”⑮可见,至迟在乾隆中期,俞与何焯二人的批校已经出现了汇集本,且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其后的很多批校本,多是俞、何合璧本。随着于光华《文选集评》的刊刻,初学者纷纷过录或节录此书内容到一个本子之上,促成了第二种类型的汇评本的大量问世。从乾隆年间的诸多佚名过录者到晚清的曾国藩,无不受惠于此。这些批校本第一眼给人以朱墨灿然之感,最易使人误以为诸家手批本,只有比勘批校内容,才能 正本清源。

图2 佚名录俞、何焯批点《文选》 南京图书馆藏
2.过录者汇集诸家批校并加有按语
有时,过录者在汇集诸家批校内容的同时,也会加入自己的按语。上海图书馆藏谭献批校本《文选》即属此类中的典型。卷中数十条跋语,记述了谭氏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十四年间数次用力于此本。从具体时间到所用参校本,都翔实记录,绝非一般阅读目的的批阅所能比拟。跋语与《谭献日记》中的记载⑯相互印证了谭献曾计划撰写一部《文选注疏》的事实。谭氏主要参考了余萧客《文选音义》、胡克家《文选考异》、梁章钜《文选旁证》、王念孙《读书杂志·余志·文选》等书⑰。他不是长篇累牍地过录前贤批校,而是在底本上标注相关符号,简明扼要地注出是“胡校”还是“何校”,是“梁曰”还是“余云”。遇有心得时,则加上自己的按语。通过卷二《西京赋》中的13条按语,可以看出谭献在这个本子上所作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充分利用梁章钜《文选旁证》、胡克家《文选考异》的校勘成果,并予以补充、完善。有意见不同者,也予以标出。如他认为有的胡校有些武断,保留异文比较好。有时他还根据文意等推测原本情况,得出与胡校不同的结论。二是不厌其烦地校何校、胡校未及之处,列出校记。三是根据校勘及文义,辨析李善注之真伪,进行适当考证。这显然是在为计划撰著的《文选注疏》做准备。
3.不同批校者(或过录者)的层层累加
有时,批校者(或过录者)所用底本上已有他人批校,他在此基础上又加了批校。从书籍再生产的角度看,也就是读者阅读使书的内容有了新的增值,正如程章灿所言:“读书是中心,抄书、校书、藏书、刻书等,既是读书的准备,也是读书的方式;而编书、著书、注书等既是读书的延伸,更是对书的利用和再生产,也是书的传播流通的另一种方式。”⑱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任侠、高步瀛批校本《文选》。此书原有清任侠父子墨笔批校,卷前高步瀛跋云:“是书原有评点,不知出何人手,向读时□□误处,而评尤谬妄可恨也。今迻录吴挚甫先生评点,只好用绿色笔以别之。而旧评之尤诞者,亦间乙去,俾初学知所去取焉。戊午二月,阆仙识。”⑲翻检可知,高步瀛对清人任侠批校进行了大量勾抹涂改,并添入了吴汝纶集成的桐城派评点。高氏对任侠评点进行否定与驳斥,又将桐城派历代名家评语集于一本,最终形成了多重的批校层次。
有前人题跋或“凡例”固然给人以指引,但有时候也要仔细辨析。因为有的题识文字已经产生误会,会以讹传讹。如上海图书馆藏王帆洲录诸家批校本《文选》,卷前有王帆洲朱笔跋语。他直言买到此书时即有部分“丁屺山批评”,但不全。于是他十多年间四处借阅,节录诸家评注于其上⑳。之后,书归藏书家张玉山,张又作题识以表看重。审卷内批语,墨笔乃据汪由敦本系统过录,但已经失去“汪由敦按”及卷三后面的识语。朱笔内容多有标“邵子湘云”者,均与何焯、俞评语相合,却与《重订文选集评》等书所录“邵云”不同。故而笔者颇疑其或是过录自邵子湘的过录本,或因邵氏过录时未标批校者姓氏,故二次过录者误将邵氏过录的何焯、俞评语当作邵氏自己的批语。
二、梳理批校本层次的方法
正是因为批校本的层次纷繁复杂,故常常会发生利用者误判的情形。有时,研究者欣喜若狂地发表论文,认为辑录出了新的材料,然通盘细审,却可能是价值不大的过录内容。利用批校内容时张冠李戴的情形更是时有发生。要想摆脱这种状况,需要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高度警惕,多维度地对其进行观照、梳理。下面就此谈一点笔者的浅见。
首先,批校本的传播有一定规律,即通常是自内而外、由师门授受的过录到友朋间的转录流播,由本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循此脉络,由众多的“流”上溯至“源”,可以厘清一些重要的名家批校本之基本面貌。如上文所说的何焯批校本,由于传播最为广泛,成为有清一代《文选》批校本中最为复杂的一个“族群”。存世的过录本何批中,单纯的何批极少,更多的是杂糅了俞、钱陆灿等人批校的本子。尤其是俞批,与何批彼此混杂,难以分清,却往往被称为“何义门”评本。《义门读书记》《何评文选》和《文选集评》的先后刊刻,对何评《文选》的广泛传播起了极大推动作用。其后的很多过录“何焯批校本”,大多由这三种转录而来。与此同时,何批本旧貌也越发模糊。因为这三种刻本不但所辑的何评本不同,还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削或增改。如海录轩本《何评文选》卷八扬子云《羽猎赋》下,何批云:“《按子云奏此赋得为郎给事黄门漫题一绝》:‘待诏承明四十余,客言词丽似相如。《上林》《羽猎》方驰骋,可得雕虫悔壮时。’”㉑而在较早的过录本何批中,却保留了“康熙冬壬午,书以自嘲”㉒的时间落款。汪由敦录何批之外,偶有所见,加以按语,与何焯批校形成互补或对话(图3)。用混杂了诸家批校的“何批”本,与比较严谨的汪由敦本对照,既可总结出汪氏对《文选》的用力之处,也有助于复原何批旧貌。此外,汪氏过录何焯批校本《文选》,有着由内而外、由族人到佚名者的传播过程,在清代有着比较广泛的转抄传播经历。我们可以汪氏过录本及转录本为中心,反推寻绎,探究、复原何焯批校本《文选》的原貌。
其次,将批校本置于古代阅读史的大背景下,对批校内容进行系统参照、整体比勘,梳理其层次及源流关系。在不断转录的过程中,过录者作为批校内容和形式的传播者,往往会因学识所限,造成批校内容的张冠李戴。比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影印了《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天头有佚名录“邵二云曰”批校。范子烨在《前言》中云:“‘邵曰’为邵长蘅之批语,而‘邵二云曰’则为邵晋涵之批语。两家的批语约计有三万余言。”㉓这些批语后来被赵俊玲收录到《文选汇评》中,也是列于“邵氏”名下。细翻《集成》一书,卷内很多的“邵曰”“邵二云曰”被人涂去,表明此前的收藏者发现了些许疑点。

图3 汪由敦批校 《文选》上海图书馆藏

图4 金守正录潘耒等批校《文选》 浙江图书馆藏
笔者发现,浙江图书馆藏金守正录潘耒等批校《文选》(图4)等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准确的答案。浙江图书馆藏本过录潘耒识语后,有金守正跋语,非常清楚地介绍了潘耒批校本的来源,并且发现了其中有何义门评语羼入的现象。此本最大的价值,是非常完整地过录了潘耒为其子潘其炳批校的内容,包括文辞赏玩、篇章结构的分析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很多叶韵切音,正是潘氏《类音》一书的重要资料来源。此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不属于同次批本,与兰州大学图书馆所藏同源,但批校内容保留得更全。将之与“邵晋涵”批校本《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邵曰”“邵二云曰”对比,可发现评语几乎99%相同,只有少数用语略异。这是《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批语过录自潘耒批校的铁证。潘耒曾代柯维桢撰《文选瀹注序》,又被张之洞《书目答问》所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入“《文选》学家”㉔,足见其在清代《文选》学界举足轻重之地位。邵晋涵主要成就在史学和小学方面。当然,从其所作《拟鲍照舞鹤赋》来看,他也肯定是熟读《文选》之人,但与其同时的人所录比他长一百多岁的潘稼堂评语与“邵二云曰”内容相同,显然潘氏才是真正的作者。
既然批语源自潘耒,那《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这个本子又如何有了“邵曰”“邵二云曰”的标注呢?这说明邵二云确实是批阅过《文选》的,而他过录的对象当系潘耒批点本。在他抄录评语过程中,除了个别地方,绝大多数没有逐条标明是潘稼堂语。后来,《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转录其批校本,误以为是他本人手批。可见,我们不能轻信批校本中的“某曰”“某案”等字眼,而应系统比勘批校内容,这样才能厘清批校层次及源流关系。
再次,重视批校本中的“互文”信息,发掘批校本所展现的对话线索。就批校内容而言,后者对前人有时会有回应,或赞同申说,或反驳考证,这也有助于厘清批校本的层次。如上文提到的《文选》卷八扬子云《羽猎赋》末有何焯题诗,在苏州图书馆藏赵豹三批校本上,其后又有墨笔一则,当是赵氏笔意:“是年冬十二月,圣庙召先生暨海宁查初白慎行、武进钱庵名世、休宁汪紫沧灏于南书房,试诗文,赐先生与灏癸未科一体会试。明年,又赐先生、灏、蒋文肃一体,殿试改翰林吉士,特达之,知子云远不逮矣。”㉕针对何氏自题绝句,赵氏征引史实,道明何焯相比于扬雄的幸运之处,表达了自己对扬雄与何焯不同命运的感慨。又如上文所言高步瀛录吴汝纶集评本,所用底本上有名为“任侠”的评语。高氏在跋语中就多有诋毁,并且对很多任侠的评语都进行了涂抹,甚至将其斥责为一介腐儒㉖。又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孙尔周批校本,也是汪由敦过录本系统的一个传抄本。孙氏在过录何义门、钱陆灿、汪由敦等人批校时,并非单纯抄录,而是偶发己见,其中颇为重要的,是对文章段落划分、主旨把握的“总评”,足见他精通文章结构和章法。如卷一二在总结何义门所云“畦径分明”后,笔锋一转云,“然浩淼离陆,变化错综,观者已茫乎不知其畔岸矣”㉗,与何氏的品评形成对照。这些不同批校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有助于厘清批校本的层次,而且可以使我们鲜活地感知古代文学批评的语境、氛围,值得关注。
《文选》自身版本的复杂性,为其批校本的复杂性已然做了铺垫。撇开这一点不论,批校者的多次叠加,过录者各取所需的转录,由一人之本到多人参与的汇评汇校,都令文本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不过,只要我们对批校本层次的复杂性有高度警惕,多维审视,通盘分析,认真细致地进行比勘,还是可以大致做出区辨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期望更多的学人加入讨论,共同深化批校本的研究。
①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章第三节《批校本》开列专节介绍,韦力《批校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为第一部研究专著。
② 目前对批校本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个案考证,仅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3期)、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袁媛《批校本研究的困境与尝试》(《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论文集》上,北京大学2019年)等少数几篇论文,简要分析了批校本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路径。
③ 韦胤宗总结道:“批校最本质并起决定性作用的特征有两个:其一是它永久地附着于事先存在的文本上,是一种回应性的书写材料;其二它必须是手写的。”(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
④ 转引自韦胤宗《阅读史:材料与方法》。
⑤ 张凤翼纂注:《文选纂注》目录,明万历十四年(1586)刻本,筠山录钱陆灿批校并跋,上海图书馆藏。
⑥ 宋志英、南江涛选编:《〈文选〉研究文献辑刊》第4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7—9页。
⑦ 程章灿:《中国古代文献的衍生性及其他》。
⑧ 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⑨ 萧统辑,梁章钜批校:《梁章钜批校昭明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本段所引识语均据此本。
⑩ 详参南江涛《梁章钜批校翻刻汲古阁本〈文选〉及其价值——以〈魏都赋〉为例》(杜泽逊主编:《国学季刊》第3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和《林茂春〈文选·赋〉简端记》(《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版)。
⑪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佚名录何焯批校,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⑫ 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重订凡例》云:“义门先生《文选》评本,凡三易稿,故或纪年或用又曰以别之。世所传写,皆晚年所定,初次则支分节解,于初学尤宜。华幼时所受业于家泉庄先生琰,亦系晚年定本。丙戌春,晤宜兴吴丈怀雍振鹭于羊场旅邸,得见初次评本,另抄一帙,藏诸箧笥。”(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⑬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乾隆二十七年杨氏儒缨堂重修本,阮元跋并录冯武、陆贻典、顾广圻批校并跋,国家图书馆藏。
⑭ 南江涛:《王同愈批校〈文选〉述略》,《国学学刊》2018年第3期。
⑮ 萧统辑:《文选》,清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佚名录何义门批,南京图书馆藏。
⑯ 范旭仑、牟小朋整理:《谭献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9—40页。
⑰ 萧统辑:《文选》,清乾隆间云林周氏怀德堂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谭献批校并跋,上海图书馆藏。
⑱ 程章灿:《教化有根 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江苏地方志》2019年第2期。
⑲ 萧统辑:《文选》,明潘惟时、潘惟德刻本,高步瀛录吴汝纶评点并题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⑳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王帆洲汇评,张玉山题识,上海图书馆藏。
㉑ 萧统辑,何焯评:《文选》卷八,清海录轩刻本。
㉒ 萧统辑,何焯评:《文选》卷八,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汪由敦批校,上海图书馆藏。
㉓ 范子烨撰:《〈昭明文选〉邵氏批语迻录稿》,《文史》2006年第1期;后作为《前言》收入《增订昭明文选集成详注》一书(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引文见该书第1册《前言》第3页。
㉔ 范希曾编,瞿凤起校点:《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㉕ 萧统辑:《文选》,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清康熙二十五年钱士谧重校本,赵豹三跋并录钱陆灿批校并跋,汪昉跋,苏州图书馆藏。
㉖ 赵俊玲编著:《文选汇评》,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㉗ 萧统辑:《文选》,清乾隆间云林周氏怀德堂翻刻明崇祯间汲古阁刻本,孙尔周批校,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