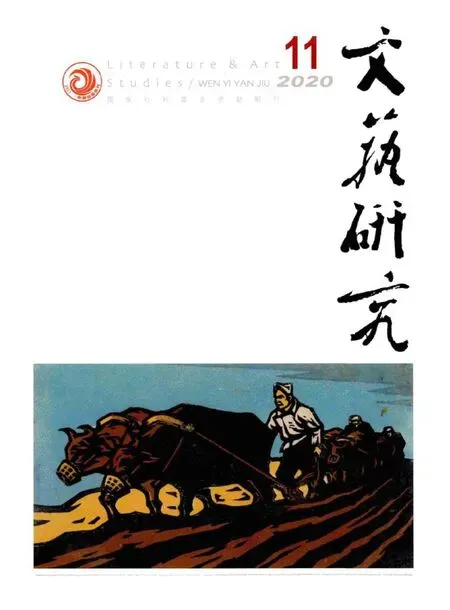《英雄儿女》解读:新中国电影英雄形象生产的内在逻辑
朴 婕
一、从《团圆》到《英雄儿女》
1961年,巴金以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所见所感为基础,创作了中篇小说《团圆》,讲述因革命斗争而失散的父女在朝鲜战场上重逢的故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对该作赞许有加,指示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导演武兆堤接下这一摄制任务,与编剧毛烽一起充实情节。1964年,影片登上银幕,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英雄儿女》。
电影的基本情节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士王成在保卫无名高地时牺牲,全军发起纪念并宣传王成精神的活动,过程中师政委王文清认出王成的妹妹王芳竟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英雄父亲、王芳的养父王复标来前线慰问时,认出了王文清,两人回忆以往共同斗争的历史,也让亲生父女相认。该片上映后引起轰动,王成牺牲前喊出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成为体现英雄舍生忘死精神的名句,为代代人津津乐道。《英雄儿女》堪称抗美援朝题材乃至现代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中的经典。
对比电影与小说,电影显著强化了对王成的表现和歌颂,且随着王成形象的丰满,影片的主题也悄然发生偏转,歌颂英雄的目的盖过了原作讲述家庭团圆和工农兵团结的主旨,以致当时的观众评论认为“父女相认”的故事干扰了电影的主题,甚至要求删去①。这就引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小说已经将王文清作为英雄来歌颂,刻画他顾全大局而压抑自己的情感,具有英雄式的牺牲精神,何以电影主创还要强化王成的英雄形象?第二,在同时存在两个英雄时,何以战斗英雄又格外受到瞩目?现有研究②虽然分析了从《团圆》到《英雄儿女》的改编所反映出的意识形态状况,但较少触及电影的生产性特征;而对于电影生产性问题的研究,又大都集中于体制、资本、市场等问题上,对于这种生产机制如何影响文本表意,学界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应该说,王成形象的强化体现出此时电影在英雄形象生产上存在着某种特定程式,而观众对英雄形象的接受也形成了某种文化惯习。
相对于其他时期,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电影生产有其独特之处。当时,电影制作作为一种工业生产模式,表现为制片厂体制下从生产到上映的一条龙管理,这凸显出其与文学活动以个人为创作主体不同的、有众多人员参与其中、也因此更注重遵循一定规范的特点。这种规范化的制作,对资本和市场的依赖程度低,商品属性不明显,无市场竞争压力,意识形态可以直接作用于从生产到上映的全过程,最终作用于电影的呈现,并影响观众对电影及其背后话语的接受。要理解新中国电影如何参与新中国英雄形象的构建,就要充分考察这种生产方式对文本产生影响的范围和可能。因此,本文强调这一时期电影作为流水线生产的现代工业特征,探讨它所遵照的特定规律,它的规范与程式对形成新时代艺术呈现方式的影响。
针对这一时期电影的生产特性,本文尝试以《英雄儿女》中英雄形象的塑造为着眼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电影作为一种备受重视的宣传手段,承担着思想传播的重要使命,因此需要先厘清小说创作与电影改编的语境,明确英雄形象是在怎样的时代需求下被塑造出来的;第二,分析电影制作内容与形式上的程式,探讨这些程式构造了怎样的英雄形象标准,这样的标准可以传达出怎样的意义、达成怎样的目标;第三,从电影如何建构观众的期待视野入手,分析新中国电影如何构造影片呈现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英雄意义的有效传达;第四,新中国电影既是遵照政策和时代话语的要求进行生产,其产出也会反过来推进话语的发展和变革,因此需要剖析英雄形象生产对新中国整体建设的参与,理解其现实意义。

《英雄儿女》海报

小说《团圆》
二、凸显英雄形象:时代需求与电影生产
王成在小说中的作用是让王文清“听他口音,看他相貌,觉得很熟”,而后想起他是“后楼王家的儿子”③,以此作为找到失散的女儿的线索。对他本人的描述只有短短几句话:“他一再要求到前面去,最后团政委也同意了。这个人叫王成,年纪不过三十多点,来到朝鲜,水土不服,身体不大好。”“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它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④武兆堤与毛烽几经研读原作后,认为电影可以在王成形象上进行扩充。当时,毛烽读到《志愿军一日》中记录的英雄事迹,决定汇集更多的英雄事迹来充实王成形象,于是,在王成身上可以看到坚守阵地的赵先友和杨根思、喊出“向我开炮”的通讯员于树昌和蒋庆泉等一系列真实的人物事迹⑤,而影片主创有意识地将塑造英雄形象和体现英雄精神作为影片的一个亮点。
突出英雄形象,可谓时代性诉求。毛烽所参考的《志愿军一日》是抗美援朝战争后,由志愿军党委和政治部动员全军写作并编选出的作品汇编,其间筛选了一万三千六百多篇文章,最终整理为一百万字的四卷本,收录了从五次战役到停战协定签订的整个过程中每个战线上的人物形象。同一时期,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成立编委会,收集专业作家和参加了战争的指挥员、干部等的作品,以通讯和特写的方式记述了64位英雄的事迹,树立起黄继光、邱少云、张渭良、杨根思等一批经典的英雄形象。这还是仅就抗美援朝题材下的书写而论,若考虑到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书写,则英雄形象更是不胜枚举。
大量的英雄形象承载起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叙述。《志愿军一日》在编选时被期待既可以作为文学作品,又“能是志愿军战史的旁编”⑥。这种“一日型”汇编形式本就是建立共同体认同的手段。它源于高尔基在1936年编纂的《世界的一日》。高尔基通过向社会公开征集有关日常生活片段的书写,试图展现一个时代的切面。邹韬奋受此活动启发,邀请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茅盾随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征文启事,选定1936年5月21日这一时间点,征集这一天“中国范围内海陆空的大小事故和现象”⑦。这一活动获得了积极响应,也刺激了此后《苏区的一日》《上海一日》《冀中一日》等一系列征文活动的开展。这类作品固然建立在每个人对于自身生活的真实描述的基础上,但最终成书却要经过一定的整理和编排,实质上是基于特定话语去建构一种共同体想象;又因为它建立在个体对自身生活描述的基础上,很容易询唤参与者认同于这个共同体。在这条线索上延续的《志愿军一日》,以英雄形象塑造为载体,书写英雄主义的战争精神,并通过文字汇集来建构对中国革命历程的认同。

《志愿军一日》内封
值得注意的是,据组织编写《志愿军一日》的陈沂介绍,在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有的单位把写作‘志愿军一日’和语文课结合进行”⑧,这意味着文化工作者介入了战士们对战争的记述。知识分子和文化宣教工作者“热情地帮助工农同志写作,给他们开回忆斗争生活的座谈会,帮助他们选择题材,剪裁故事,给他们修改稿子”⑨。战士们书写战争历史的过程就是他们重新习得历史的过程。陈沂以“热情”“帮助”这类正面词汇评价这种教导活动,意味着这样的活动形式得到肯定。因此,“集体创作”相当于将一定的书写规范和意识形态诉求灌注到战士的意识中,让他们再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记忆把战斗故事讲述出来,最后形成既有血有肉又合乎标准的历史叙述。
由此追溯有关抗美援朝战争叙述的发展过程可知,先是战争爆发初期涌现出大量的新闻报道和报告文学,以最迅速的方式反映战争前线的状况,展现将士英勇奋战的精神;而后中国文联三次组织作家前往朝鲜半岛慰问及访问志愿军,巴金、老舍、胡风、路翎、魏巍、刘白羽、杨朔等作家和记者亲历战地,发表所见所感,创作出《坚强战士》《风雪东线》《上甘岭》《三千里江山》等一系列歌颂志愿军英雄的作品。组织力度之大、动员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创作数量之多,都反映出英雄形象塑造是新中国文化政治工程构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电影作为一种工业生产方式,既有利于生产大量的人物形象,又具有突出的传播能力,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民众⑩。因此,电影局一再提出要“创造新的英雄典型”⑪、刻画“鲜明的英雄人物”⑫,并且在历次题材规划中都将战争题材放在首要的位置⑬。在此政策引导下,1949年党所领导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投入生产不久,就涌现出《钢铁战士》《赵一曼》《刘胡兰》《白衣战士》等作品,此后随着北京、八一、上海等几大电影制片厂投入生产,《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柳堡的故事》《董存瑞》《铁道卫士》《烈火中永生》《自有后来人》《独立大队》《兵临城下》《三进山城》《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战争题材作品陆续出现在银幕上。这类题材不仅在数量上占据影片制作总额的近半数乃至半数以上⑭,也因情节冲突明显、人物形象鲜明,在观众中引起热烈的反响。
不同时期电影塑造的英雄形象,都在积极回应所在时代的需求。从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多以赵一曼、刘胡兰这样的个体为蓝本来塑造英雄形象,情节上突出英雄的气节,展现共产党人的精神意志,呼唤观众对共产党和新中国产生信仰与认同;进入50年代中期,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注重其与中国革命史发展的联系,如董存瑞、李向阳等英雄形象,不仅闪耀着舍生忘死的英雄气质,而且他们的斗争经历也能够引出中国近代以来的斗争历史,从而满足当时新中国建构自身革命历史叙述的需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仍处于经济复苏期,电影产量较少,加上电影制作需要一定的周期,无法像文学创作一样即时地回应抗美援朝的宣传需求,但有一些其他主题的作品在叙述中加入抗美援朝的要素,如讲述运输业发展的《英雄司机》(1954)将故事背景放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提示工业生产对前线战争的支援作用以及战争对于生产发展的保障,侧面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保家卫国意义以及英雄精神在全国的影响。战争结束后,《上甘岭》《烽火列车》《英雄儿女》等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作品陆续登上银幕,它们塑造出一批战斗在一线的英雄,体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和英雄性,完善了对这段历史的呈现。以英雄形象来凝聚时代精神,承载中国革命历史叙述,并最终找到可复制的、最为理想的英雄书写范型,可谓50至70年代电影生产中最为核心的使命。
三、英雄形象范型:标准化与拍摄程式
电影要呈现特定的人物,需要情节叙述与摄影机、灯光、演员表演以及后期剪辑、音效通力配合,所以当一种典范的英雄形象成型时,它往往代表着电影制作形成了一条稳定的生产线。生产线的出现,也反过来使得英雄形象按照一种标准模式生产出来。以王成最为高光的牺牲时刻来说,影片的处理方式是:英雄昂首挺胸慷慨赴死,镜头从全景或中景一直推到英雄特写,然后切镜头为空景,以枪声或炮声等暗示英雄牺牲的瞬间,此时雄壮的背景音乐响起,空镜头中地动山摇,卷起的硝烟、耸立的树木等场景体现出英雄的精神力量仍然震慑世间。类似的处理手法可见于《钢铁战士》《中华女儿》《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烈火中永生》《自有后来人》等一系列影片。片中镜头的运动轨迹、画面光影、过场方式、单位镜头的时长都相差无几,甚至应当具有相对自由度的演员表演也显得如出一辙:无论是面对首长时的积极争取作战机会,还是面对亲人与乡民时的和善笑容,以及面对敌人时的金刚怒目,英雄的表情与动作都如同标准照一般被复刻下来。
再进一步追溯,表现王成英雄品质的各个情节桥段,也都能找到源头。王成以从医院返回前线的伤员形象登场,头上的绷带还没拆掉,便软磨硬泡地向首长要求上战场。这种积极的表现,一如尚未足龄便要参军的董存瑞、小兵张嘎,以及疲病仍不下火线的白衣战士白求恩等;王成在返回前线的路上遭遇美军轰炸,于是忘我地帮助朝鲜百姓隐蔽,这可以对应到《钢铁战士》《刘胡兰》《铁道游击队》等一系列影片中八路军或解放军战士与群众的友好互助;王成在战友大都牺牲后,英勇地以一己之力攻击敌人,步话机传来他不雅的言语,这种略有些鲁莽但勇于斗争的性格,一如董存瑞等临危不惧的表现;王成的牺牲精神,更有上述大量的英雄形象作为先例。所以,王成无疑是汇集了各种英雄叙述而形成的。他身上反映出英雄形象的共同特征:自幼嫉恶如仇,成长为革命战士后具有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团结战友,善待民众,为了集体利益舍生忘死。还须指出的是,影片也会高度配合英雄形象的塑造设置情节,让这类英雄身影可以在各类战争题材作品中既体现个人成长的经历,又凸显英雄主义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此一时期的英雄生产已经具备了检验的标准,配置有标志性的形象和情节,形成了标识度极高的经典序列。
标准形态并不意味着一经成型便止步不前,王成本身也体现出这种英雄形象在不断加以改进。他那句震撼几代中国人心灵的“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激昂口号,突出的两个关键词——“胜利”和“我”,可以引出两方面意思:一是为了新中国翻身富强这一崇高目标,个人应当牺牲小“我”;另一是对比差不多十年前《董存瑞》中同样经典的“为了新中国,前进”,喊出“向我开炮”的英雄显然表现出更明确的自觉牺牲精神。电影镜头充分配合了这一自觉理想的宣誓,特写了英雄手持爆破筒冲上去的瞬间,让观众充分感受到“我”献出自身生命的实在重量。“我”的力量与随即而来的援军的炮火融在一起,营造出个体化身于群体的崇高氛围。当然,这种意义的传达从电影拍摄技术角度看并不容易,因为镜头画面很难同时凸显英雄的超越性和英雄隶属于集体的集体性。受镜头自身单点透视的限制,若采用现代透视法上的纵深视角,则只能凸显一个个英雄的崇高,比如20世纪30年代电影《风云儿女》,其中逐一特写了投身战争的人物,这实际上很难表现他们已化作一个不分彼此的群体。至于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中国电影,善于以多人全景来呈现平等、和睦的人物群像,某种程度上会透出集体性意涵,但又不易展现英雄精神的超越性。《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融合“我”的牺牲与集体的胜利,让英雄既以个体形象出现,又让人感到他是集体中可被复制的一员,这可谓当时电影表现上的一种有意识突破的尝试。当然,王成的这一突破是在英雄形象塑造的序列之中的突破,是在固定模式上的精进,并具有被标准化后复制的价值。比如后来在影片《战洪图》中,镜头近景仰拍抗洪英雄们站在洪水边以及丁胜河投身下水疏通拥堵的身姿,一如从山岗上冲向敌人、与之同归于尽的王成,而英雄们争先恐后要投身汹涌洪水的场景也凸显出英雄是集体的一员,集体中的每个人都是英雄。可见,电影制作通过不断累积和完善,集萃了塑造英雄人物的种种程式。
这种英雄序列也可以印证当时英雄人物形象塑造,往往会经过一个标准化的处理过程。比如,《英雄儿女》中把军政委王文清塑造为沉稳的首长形象,一如此前所有战争题材影片中出现的作为指引者的政委,这样的处理相应地削弱了他在小说原作中本有的英雄性。《团圆》中刻画王文清向“我”介绍王芳身世时这样写道:“我看见他收起了笑容。我看见他用力搔须根,把两边脸颊都搔红了。我看见他皱起两道浓眉。”⑮接连用了三个“我看见”,以“我”的眼睛为透视点,拉出了一个凝望王文清的镜头纵深,营造出层次感。再以他数次“搔须根”相配合,无声地显露出他对王芳炽烈的情感,而他对情感的压抑更体现了他以工农兵团结为重的大局观和自我牺牲精神。如果以这种方式去呈现王文清,也能让人感到王文清身上具有的崇高精神。但影片放弃了这样的呈现,完全以表现首长的镜头常规地表现王文清,他的牺牲精神被淡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在追溯王文清的革命经历时,影片在他因地下运动被捕的场景里,赋予他一个英雄赴死式的特写镜头,在某种意义上让王文清的英雄性转移到他此前经历的残酷的革命斗争上,英雄似乎只有通过斗争与牺牲才能呈现出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既定程式的排斥性。

王成站在山岗上,手持爆破筒(《英雄儿女》剧照)

镜头推进(《英雄儿女》剧照)

另一机位(《英雄儿女》剧照)
程式固然存在僵化的问题,但也确有其功能优势。李杨在分析《红灯记》时指出,现代京剧“要程式,不要程式化”的特点,它承袭了京剧艺术本有的象征性特征,形成固定的规范化符码,观众与其说是在欣赏京剧故事,不如说是在欣赏这样一套符码,每次观看演出都像是在仪式中经受洗礼⑯。这一分析同样可以启发对电影艺术的理解。不断重复的呈现方式如同大写的文字,会更有力度地冲击观众的神经,使呈现英雄形象的程式构成询唤观众认同的固定装置。观众以这样的方式辨识英雄、理解英雄周边发生的一切,将情感更集中、更强烈地投射于对象。从这一意义上说,程式更有利于达成当时电影所肩负的宣传任务以及新中国文化工程的建设任务。
英雄形象的程式亦无声地表明,英雄形象是可复制的,它的标准化生产模式尝试让英雄精神无损地传递下去。当银幕一遍遍地向观众呈现相似的英雄形象时,也将何为英雄的标准种植在观众心中了。这便形成中国战士都是英雄或都可以成为英雄的价值判断。在片中庆功会纪念王成的一幕上,画面叠映王成牺牲的形象与战士们歌颂他的形象,隐喻王成精神复制到其他战士身上。这奠定了讲述“英雄的中国”的基础,而英雄作为中国革命精神的一种表征,可以引导观众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因此,新中国文艺利用电影复制的再生产能力,不断产出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建构并巩固着观众对新中国的理解。
四、观众反应:家国一体与情感认同
电影作为一种观视媒介,有赖于观众对影片做出反应,这样才能够实现其价值。米尔佐夫指出,“政治身体”是在公民与共和国之间通过交换而得以成立的,“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它都不是一种封闭的或自我密封的再现”,“观看者的参与是政治身体再现得以成功的关键”⑰。英雄形象塑造的完成是影片与观众间媒介得以建构起来的时刻。观众对英雄形象的接受以及对英雄人物的歌颂,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必要条件。因此,分析英雄形象生产,就必须考虑这一生产是否同时“生产”了它的消费者,亦即需要考虑英雄形象的受众接受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英雄儿女》直接展现了调动观众的时刻。在王成牺牲后,王文清提出要“抓住这个典型”来“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⑱,并展开一系列歌颂英雄的活动。镜头随即带领观众以战士小刘的第一人称视角看到自己写下“坚决向王成同志学习”,而后镜头又汇入人群,带领观众观看宣传王成事迹的海报板、进到庆功会和誓师会现场聆听《英雄赞歌》。对比一下庆功会和此前祝捷会的场面调度:在祝捷会的场景中,影片平行剪切舞台上的舞者与舞台下的战士和朝鲜人民,此处镜头对准观众时是在体现他们观看舞台表演的喜悦,台上台下的界限十分清楚,镜头只是在全知的位置上冷静观照这一切;到庆功会时,镜头不断从舞台拉到观众、再从观众推回舞台,体现出歌颂英雄的声音在观众间的传播,当台下观众加入合唱“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的时候,舞台的界限最终消失,所有人都沉浸其中,这时镜头也站在人群中间,成为英雄精神的传递者之一。在消去舞台界限的时刻,镜头显然也有意消去屏幕的界限,让观众分享战士的位置,成为王成精神的继承者和歌颂者。
现代摄影技术本身固然会构造观察者,即单点透视建构了观察者的位置和视角,从而建构了观察者的主体,但这种建构过程通常会使自己透明化,刻意隐去建构的痕迹,让观察者误以为自己处于客观全知的位置,在不知不觉中为话语所询唤。值得注意的是,《英雄儿女》的处理是张扬的,它不啻一场“暴露摄影机”的行为,它让观看者意识到自己的观看行为,发觉英雄是需要“歌颂”的,而歌颂的氛围和格调是话语制造的结果。这样的拍摄手法,一旦处理不当,可能会引发解构英雄神话的危险。这显露出当时电影的一个特征:电影借由暴露话语的构造,呼唤观众成为自觉的参与者;而它所期待的理想观众,是在明知话语构造的情况下仍然响应呼唤的人。这让话语发出的动员声音更加精准、更加稳固。这种歌颂英雄的视角与场景的运用,在此前也曾出现。新中国电影起步于系列纪录片《民主东北》的拍摄,其时摄影机便经常汇入人群中,站在一个参与者的位置上观看解放军进城、群众扭秧歌等等。这固然是纪录片营造真实感的一种常见方法,但这样的拍摄视角也被吸收到后来的《赵一曼》《钢铁战士》《刘胡兰》等故事片的制作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群众围绕在英雄周围、仰望英雄的常规表达手法。这样的视角同时配合以群众为英雄所折服而向英雄致敬的场景,群众成为观众的范本。电影由此不仅规划了观众的位置,还精确地规划了英雄形象背后英雄/人民、群体/个体、国/家之间应有的关系,从而使观众站到自己所期待的位置上做出相应的反馈。《英雄儿女》在这种模式上推进一步。它将歌颂英雄处理为主要情节,强化它的作用。此时的电影成为话语的可见载体,它明确传递出自己的声音,也构成一种示范,向观众展示怎样的响应是合适的。
影片更进一步打造了理想的歌颂者,即王成的妹妹王芳,以此来体现每个个体与新中国之间应有的关系。王文清看了很多宣传材料均不满意,直到他见到王成的妹妹王芳,便鼓励王芳去回忆和歌颂自己的哥哥:“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⑲可见,王芳身为王成妹妹的身份成为“国”与“家”之间建构整一性关系的有力帮手,让“家”的亲和感融入对“国”的认同中,这种对亲人的回忆与歌颂成为“国”话语重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片中还特意表现了这一重构的时刻。王芳流着泪熬夜写出了歌词,交给王文清后,王文清认为“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对后半部分摇了摇头。当王芳表示她认为后半部分更好时,恰好战士小刘经过,王文清让小刘发表意见,于是发生了以下对话:
小刘:看到后面,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王芳:我觉得确实写出了我的真实感情。

庆功大会,镜头由观众席推向舞台(《英雄儿女》剧照)

庆功大会,镜头由舞台推向观众席(《英雄儿女》剧照)
小刘: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王芳: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王文清: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你写他,唱他,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⑳

王文清教导王芳修改歌词(《英雄儿女》剧照)
王芳因此领悟了王文清的意思,重新写出了歌颂英雄的歌词。经过这一番启发,王成对于王芳来说已经不只是从小疼爱她的哥哥,而首先是属于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英雄。影片由此制作了一个最完美的歌颂者:她既具有此前常规的歌颂英雄的视角,又有独特且切身的亲情,由此合情合理地完成了“家”情与“国”爱之间的联结。“家”成为“国”的载体,构成人们基于自身经验而认同于“国”的媒介;“国”则反过来升华了“家”的意义,让每个人都产生对“国”的认同感和神圣感。分享歌颂者身份的观众,也会受到这一完美歌颂者的指引,将自身的“家”经验提升为“国”认同。电影题目“英雄儿女”也昭示了“家”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结:“儿女”本是家族中的新一代,而“儿”奔赴前线为国捐躯,“女”将这种英雄精神传播给全国人民,“家”中的新一代人便都化作“国”的生力军,每个人都是“国- 家”的“儿/女”,继承并歌颂“英雄的中国”的精神。结合文本出现的时间来看,巴金是在抗美援朝军队全部回国之后筹备写作《团圆》的,而长春电影制片厂在抗美援朝胜利十周年开始筹备制作《英雄儿女》,这正是新中国迈进第二个十年的昂扬时刻。这样的呈现让影片之内的歌颂与现实中的歌颂化作一股力量,共同歌颂“英雄的中国”的胜利。
五、英雄形象生产的意义:平等精神与世界图景
在建构起观众对于新中国的认同之后,“国”更可以反过来以“家”为载体来完善自身的历史叙述。再来剖析一下“儿女”一词的意涵。尽管它通常泛指一代人,但《英雄儿女》中的“儿女”又确确实实是指具体的儿子与女儿,他们对应着“父”而存在。王成坚守阵地时,拿出了父亲的照片,读着父亲要为国家工业建设和支援前线做贡献的誓言,深受鼓舞。在这里,“父”就构成了王成的精神支撑。王文清的扮演者选择了当时已经53岁的田方,显然也意在强化父辈的印象。而小说里的王主任正当壮年,王成也已三十多岁,两代人的感觉并不显著。选择田方来扮演父亲,无疑从视觉上强化了“父”的观感,战士王成看起来则像一个毛头小伙子,这就突出了两代人的对话。考虑到故事情节发生的时间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可推算出早期王文清参与革命斗争的时间正值红色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30年代,因此,王成对上一代人的继承就意味着对30年代以来革命斗争的继承。由此,电影不只讲述了个体英雄,更以英雄为媒介讲述出一部现代中国革命斗争史,呈现了整个“英雄的中国”。同时,作为“女”的王芳兼具老革命的女儿、老工人的女儿以及英雄王成妹妹的身份,这将阶级身份与战士身份、党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这一“女”所体现的联合,与“儿”所聚焦的历史线索,构成中国革命史的横轴与纵轴,展示出现代以来中国人民团结斗争以摆脱外侮和内乱的历史。至此可以看到,英雄形象在响应话语要求宣传革命历史精神的同时,也参与了历史话语的构建。
当英雄形象具有构建历史的作用时,特别是像王成这种备受关注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时,这一跨国空间格外值得注意。电影特意强调了这一跨国空间。小说《团圆》已经借王芳之口叙述一户朝鲜人家在遭受苦难后仍然坚强快乐地生活㉑,勾勒出朝鲜民众的形象轮廓;电影在此基础上又加以丰富,如王文清奔赴前线时道路被炮火炸断,镜头展现了身穿民族服装、搬运石头参加修路的朝鲜民众,在纪念保卫高地的战役胜利时,还呈现了朝鲜歌舞。这些朝鲜人民的服饰、言语、举止和文化风情大量出现在影片中,显然是有意以另一种文化特色来激活对“中国”的自觉意识,帮助读者意识到中国此时是在舍生忘死地投入世界革命之中。英雄不仅是一个个活跃于战场上的个体,更是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中国”。生产英雄形象,实际上是在塑造“英雄的中国”形象。
朝鲜战场还从一个方面体现出中国参与世界舞台以及世界历史建构的独特意义。一方面,朝鲜和中国一样经历了近代以来被侵略的民族苦难,而朝鲜战争也会进一步唤醒中朝两国曾经的被压迫经验。片中王文清发现赵国瑞以王成精神来训练新兵时还未得要领,便启发他道:“你说说王成那种英雄气概是怎么来的?”赵国瑞回答了“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之后,王文清让他继续思考,通讯员小刘插话道:“恨美国鬼子呗!”赵国瑞顿悟,对新兵喊道:“前面就是屠杀朝鲜人民的美国鬼子,我们应该怎么办?”㉒于是新兵们群情激奋地练起刺刀。这与影片前文交代的日本鬼子对中国人民进行烧杀抢掠形成呼应。另一方面,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冷战”格局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到《英雄儿女》拍摄时,“冷战”关系下以往两大阵营的简单对立关系已经改变:中苏关系的破裂,迫使面对“冷战”对立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双重压力的中国,不能再简单地顺从苏联或抵抗美国,中国需要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找到独立的发展道路,建构一套自己的世界观。联系到《英雄儿女》的制作,这种对中朝关系的叙述更耐人寻味。它意味着中国在以两国近似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情感来重新组织两国关系叙述,以一种“第三世界”的眼光去面对世界。一如汪晖所说,如果将抗美援朝战争和在此前后的一系列世界运动联系起来看,“我们有理由断言抗美援朝以热战促和平的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的成立,世界人民的团结,东方集团的出现,以及在此背景下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打破了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格局”。它从长期效果来看,“包含了对冷战的霸权格局的解构”㉓。

朝鲜大爷金正泰,严寒中准备下河运送担架(《英雄儿女》剧照)

朴贞子帮王芳整理衣服并安慰王芳不用紧张,王芳抓住她的手摸自己心跳,两人相视而笑(《英雄儿女》剧照)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所展现的这种世界与历史中,中国在强调各国团结、共同奋斗的同时,也要保持相互平等和各自独立。此前研究多基于抗美援朝叙述中朝鲜男性角色少且中国军人相对于朝鲜民众具有解救性等方面,认为抗美援朝叙述将中国塑造成引导者形象,特别是当战士为中国男性而民众为朝鲜妇女时,更有男女性别结构中权力关系的类比,仿佛中国在暗示朝鲜是在自己的引导下获得解放㉔。这类观点显然有忽略历史事实之嫌。当时朝鲜人民军奔赴前线,志愿军容易接触到的主要是留在后方的女性或老幼,如果抗美援朝叙述大量写两国军队之间的合作,是缺乏真实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文艺创作已经尽最大的可能去体现中朝人民的平等。尽管片中塑造的是中国军人与朝鲜民众,在军民关系中仿佛中国更具有力量,但影片着重凸显了朝鲜民众的英雄举动,格外注意体现中朝两国的平等关系和共同斗争场景。影片塑造的朝鲜角色主要是金正泰,他在道路受阻之际动员大家帮忙将车抬过这段路,王文清才得以顺利赶到前线指挥作战;在王芳受伤时,他不顾寒冷和危险背着王芳渡河,让王芳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此时镜头对金正泰的特写方式与王成救助他时如出一辙,可见中朝军民都是同等的英雄。电影还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即相对于文学叙述受限于文字表达的时间性而难免有叙述先后和详略之差,电影作为一种平面语言,可以同时容纳群体在其中,能够让中朝两国人物形象平等地出现在画面中。如片中的祝捷会上,王芳穿上朝鲜妇女的衣服跳起朝鲜长鼓舞,朝鲜姑娘朴贞子抱住王芳来给她鼓励,这一刻两人均等地占据画面,体现出两国人民的平等和亲密无间。不仅是这部作品,影片《金玉姬》中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的朝鲜女战士金玉姬,《烽火列车》中共同战斗在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司机刘风与朝鲜司机金万吉等,都体现了两国共同的斗争历史和英雄精神㉕。可见,电影画面的均等构图也成为一种叙述程式,留在了当时的中国电影中,提供了一种各民族国家协作发展、平等互助的世界图景想象。
从这一意义上说,电影通过塑造一个置身于国际舞台的英雄,既体现了两国人民之间平等合作的关系,又潜在地讲出了中国对自身在世界版图上的定位,暗示了中国改进世界秩序的理想。尽管这一理想并未以明确的言语表述出来,但是它深藏在构图、场面调度等镜头语言中,长期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众对中国的理解。观看影片时动情的观众,便是“新中国”这个故事中的“入戏”者,参与到共同体建设之中。
① 参见长青藤编著:《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的台前幕后》,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② 参见陈娜:《不仅仅是故事的旅行:小说〈团圆〉与电影〈英雄儿女〉的改编研究》,《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李文甫:《从〈团圆〉到〈英雄儿女〉:断裂与承续》,《电影文学》2015年第16期。
③④⑮㉑ 巴金:《团圆》,《上海文学》1961年第8期。
⑤ 李春为、谭小龙:《寻找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党史文苑》2011年第1期。
⑥⑧⑨ 陈沂:《一个成功的群众性的创作运动》,《志愿军一日》第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第11—12页,第12页。
⑦ 文学社、《中国的一日》编委会:《〈中国的一日〉征稿启事》,《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5月15日。
⑩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除了电影本身有很强的传播能力之外,党和党的文艺工作者也有意识地利用电影的传播优势,进一步探索扩大电影传播能力的方法。党自20世纪30年代末在延安组建电影团,探索更适宜工农兵群众接受的形式,并建立流动放映队制度,以求电影突破城市放映的局限。“人民电影的奠基人”袁牧之在1948年提交的《关于电影事业的报告》中提出,“当最初阶段流动放映队还远远落后于新解放区的城市影院发行网时,(沪港的电影制片厂以其熟悉的表演对象而为工农兵利益的)这些出品可暂时占一定的比重”(袁牧之:《关于电影事业的报告(二)》,竹潜民、沈瑞龙主编:《人民电影的奠基者 宁波籍电影家袁牧之纪念文集》,宁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6页),表明中国要在此后建立一种影院放映与放映队并行的放映体制,并逐步加大放映队的比重。周扬在第一届文代会上也提出,“我们的电影,在条件许可下就应在农村大量放映”(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32页)。1952年初的统计中,放映队数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个队到去年底增加到一千五百个队”,“工厂农村部队的放映队观众约一亿四千万人”[文化部电影局:《1952年电影制片工作计划(草案)》,吴迪(启之)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城乡观影人数已很接近。再到新中国建立十周年之际,陈荒煤发表《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介绍“十年来全国放映单位从1949年的六百多个发展到今年年底将达到一万五千个,增长了二十三倍。这就完全改变了过去电影单位密集沿江沿海城市,分布不平衡,城乡之间不平衡的情况。工矿、农村、部队所拥有的放映单位占全部放映单位四分之三以上”(荒煤:《新中国电影事业的迅速发展》,《人民日报》1959年10月30日),可见放映队日渐成为重要的乃至主要的放映方式,电影也得以进入各阶层和各区域群众的生活。
⑪ 陈荒煤:《为创造新的英雄的典型而努力》,《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1期。
⑫ 夏衍:《一定要提高电影艺术的质量》(1960年12月29日),《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中卷,第309页。
⑬ 以1951年的规划为例。当时规划年制作18部影片,其中第一项为“反映战斗的”,要求“最好能有四个”,此外还要有“反美帝及世界和平问题的二个”,“反映国际主义的二个”(陈波儿:《关于1951年故事片创作计划草案及有关编导工作的意见》,《业务通讯》1950年8月15日,转引自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1954—1957年故事片规划中,也将题材规定为“反映党的革命斗争”“反映工业建设与工人生活方面”“反映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与农民生活”“抗美援朝、保卫和平斗争方面”“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方面”“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方面”“历史与历史人物传记”“文学名著、神话和民间传说改编”“其它”[参见《1954—1957年电影故事片主题、题材提示草案》(1953年10月1日),《中国电影研究资料1949—1979》上卷,第348—361页],可见战争题材在其中的比重。
⑭ 根据研究者分类标准的不同,比重会有所变化,比如部分“反特”题材作品将故事背景放在工农业生产中,这些作品亦可视为农村题材或工业题材,这会导致对战争英雄的统计数字有所降低。但总体而言,具有战争主题和英雄形象塑造的作品,仍占电影生产中的大比重。
⑯ 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265页。
⑰ 参见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萧易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3—140页。
⑱⑲⑳㉒ 电影《英雄儿女》台词,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
㉓ 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区域》第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㉔ 参见惠雁冰:《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常彬:《硝烟中的鲜花:抗美援朝文学叙事及史料整理》,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5页。
㉕ 电影因生产成本较高,成品数量相对有限,但彼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学创作体现两国人民的平等和英勇形象,如魏巍《朝鲜同志》塑造了一个曾经在延安参加抗日战争、而后回到朝鲜成为人民军师长的老金,他在“我”遭遇险境时提供了救助(魏巍:《朝鲜人》,《人民文学》1951年第3卷第4期);刘白羽在《雪夜》中也塑造了“五星红旗上也有咱们一滴血”的朝鲜“老战友”(刘白羽:《雪夜》,《刘白羽文集》第1卷,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可见中朝的帮助是相互的。另有《春在朝鲜》《风雪东线》《安玉姬》等大量作品体现朝鲜人民的英勇和乐观,可见抗美援朝叙述绝无制造中朝之间力量差序的目的。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本文不再做具体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