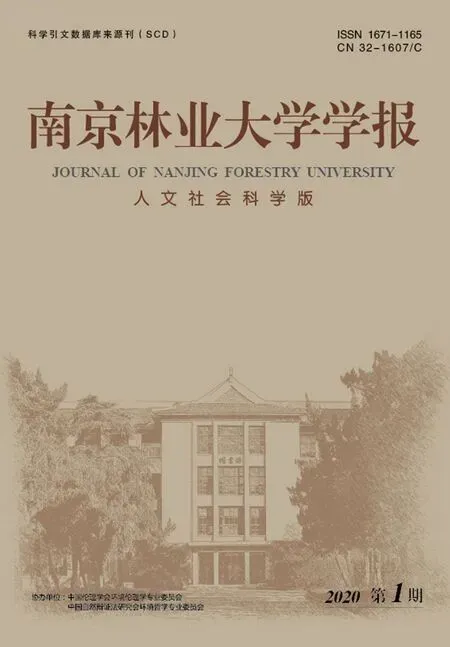西利亚·撒克斯特作品中灾难书写的美学意蕴*
杨嘉雯,李新德
(温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西利亚·撒克斯特(Celia Thaxter,1835—1894)是19世纪美国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散文、诗歌为主,记录了自己生活的多鱼群岛(The Isles of Shoals)上的风土人情与自然风光。尽管受到生活环境的种种限制,西利亚没有机会接受正统的学校教育,然而这并不能阻挡她在文学创作上所展露出的惊人天赋。自她的诗歌《汪洋中的孤土》(Land-locked,1861)被《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刊载之后,西利亚便开始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包括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内的许多文坛名流纷纷肯定了她的创作天分,后者还曾亲切地将她比作“海岛的米兰达”(Island Miranda)。[1]537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西利亚的作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之相反,国外学界较早地意识到了西利亚在美国自然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独特地位①目前,国内学界有关西利亚的研究相当有限,最早仅有程虹教授对其生平与作品作过相关评述,后来笔者也对她笔下的“非美自然”作过审美维度的研究,具体参阅:程虹,《宁静无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杨嘉雯、李新德,《撒克斯特作品中“非美自然”的审美诠释》,《鄱阳湖学刊》,2019(3):61-66。国外学界对此研究较为丰富,主要从作者的生平、宗教观、地方意识、生态女性主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在此列出一些文献以供参考:Jane Vallier,Poet on Demand:The Life,Letters and Works of Celia Thaxter(Portsmouth:Peter E.Randall Publisher,1994);Perry D.Westbrook,“Celia Thaxter's Controversy with Nature”,New England Quarterly:A Historical Review of New England Life and Letters,1947(4):492-515;Michael Buckley,“Reworking Nature Writing:Celia Thaxter’s‘Among the Isles of Shoals’”,in Writing the Land:John Burroughs and his Legacy;Essays from the John Burroughs Nature Writing Conference,ed.Daniel G.Payne(Newcastle: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8),98-111;Deborah B.Derrick,“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Place:Celia Thaxter and the Isles of Shoals”(MA.diss.,University of Nebraska at Omaha,2003);Leah Blatt Glasser,“‘The Sandpiper and I’:Landscape and Identity on Celia Thaxter’s Isles of Shoals”,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2003(1):1-21。,在他们看来,西利亚的作品兼具鲜明的时代性与创新性,既代表了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阅读品味,亦已初具现实主义色彩。[2]这种现实的态度显现于她对自然残酷面的真实描绘之中,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西利亚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存在于生活与创作两个层面,使她不得不在自然的残酷现实与牧歌式的田园愿景中作出抉择。[3]233-237然而,西利亚并未走向任何一种极端,而是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她不仅展现了自然那美好而令人愉悦的一面,也真实地记录了它那残酷而无偏私的另一面。目前,虽然学界已经认识到了西利亚的自然书写中所蕴含的两面性,但对于她在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的残酷面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这恰恰也是西利亚较之前人的不同之处,因而理应得到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结合当代环境美学家提出的“非美自然”(Unscenic Nature),参考康德(Immanuel Kant)的“纯粹审美判断”,意图从西利亚对于自然灾难的言说入手,从审美的维度对其进行剖析,以弥补这一研究的空白。
在西利亚的眼中,几乎一切的自然都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这其中也包括令人望而生畏的自然灾难。在当代美学家看来,自然灾难是无法被人类欣赏的,原因是其可能对他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此进行美学评价严重违背了伦理道德,超出了人类可欣赏范畴的界限。[4]238-253然而,早在19世纪末,西利亚就已为自然灾难的欣赏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她不仅验证了审美自然灾难的可行性,还使自然灾难审美脱离人类道德的束缚,拥有了被欣赏的可能。
一、“距离”产生“崇高”
成长于自然环境复杂多变的多鱼群岛,西利亚对自然的残酷与伟大深谙于心。纵观她的整个创作生涯,自然灾难不仅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也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面对这喜怒无常的自然,西利亚保持着逆来顺受的生活态度,始终在寻找一种理解残酷自然的方式,并试图领会其中蕴含的美学价值。西利亚毫不吝啬地将自己与自然灾难的每一次相遇过程详尽地付诸笔端,在她的作品中,有犹如《圣经》中的大洪水(The Deluge)那般猛烈的暴风骤雨①参见钦定版圣经(KJV)Genesis 7:6。,有吞噬无数生命的海上风暴,也有将岛上的灯塔几乎摧毁的狂风巨浪。这些关于自然灾难的记载为研究她的灾难审美观提供了诸多素材。
(一)“恐惧”与“崇高”的辨析
仔细分析书中关于自然灾难的描写,便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面对自然灾难时,西利亚对它的恐惧与赞美时常会相互切换,但两者从不同时出现。在《海岛花园》(An Island Garden)中,西利亚用生动的语言勾勒出这样一幅暴风雨来临时的图景。
闪电划破天际,从穹顶冲向天边,“一道凶猛的、似是寻仇般的横冲直撞的火焰”从北向南肆意穿梭,可怕的寂静随着每道闪电过后的霹雳声被打破了。又过了一会儿,几滴雨点像子弹一般砸在我们身上;接着被撕裂的天穹拽着几块如褴褛衣衫般的乌云飞了过来……它怒吼着、尖叫着、呼喊着,带着一丝洋洋得意的语调——洪水与飓风随心所欲地肆虐着。……在这场混战的间隙,一束奇怪的光线断断续续地照耀着海面和岩石,接着暴风雨又卷土重来,仿佛它已经吸了一口气,获取了新的力量。人的整颗心都因此肃然起敬,回应这场风暴带来的的美与荣光,并感激大雨为灵魂带来的洗涤。②作品中的引文均为笔者自译,原文参见:Celia Laighton Thaxter,An Island Garde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04),106-107。
在这段描述中,西利亚试图从听觉、视觉两个方面向读者还原当时的景象,她不仅使用了比喻、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并在形容天空中布满肆意穿梭的闪电的景象时,还引用了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诗句,形容它是“凶猛的、似是寻仇一般的火焰”[5]。此处的描写明显是具有审美性质的,这在后文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这场风暴中,为着这风暴所让她体会到的“美与荣光”,作者“整个心都肃然起敬”。但是,也许连作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她在这场风暴中体会到的所谓的“美”(beauty),实际上与审美意义上的“美的”(beautiful)所指的范畴有所不同。按照康德的说法,美应该是无利害而令人喜欢的,并且它广泛存在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共通感(common sense)之中[6]87,而西利亚笔下对于这场“凶猛的、似是寻仇般的”风暴,对多数人来说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这样的景观显然无法在人类普遍认同的共通感中找到立足点,事实上这种类似于“美”的体验是感官在受到崇高的自然景观刺激后而产生的愉悦(pleasure)。康德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一书中将愉悦分为四个范畴:快适(agreeable)、美丽(beautiful)、崇高(sublime)与善(good)①拉丁语原文依次为:iucundum,pulchrum,sublime,honestum。国内学者对此四个范畴的翻译主要有宗白华、邓晓芒两个版本,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sublime的翻译,宗白华翻译为壮美(崇高),而邓晓芒则直接译为崇高。根据康德对sublime与pulchrum的区分,本文倾向于参考邓晓芒的版本。本文下述所有术语的中文翻译皆以邓晓芒教授的翻译作为参考,不再赘述。。崇高的愉悦需要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被感知,他认为,自然界中被判断为“力学的崇高”(dynamically sublime)②对于dynamically sublime的翻译,英美文学领域的程虹教授译作“动感无穷的壮美”,哲学领域的邓晓芒教授则译成“力学的崇高”。必然是被表象激起恐惧的对象,它是欣赏者在感知到自然强力的前提下才能体会到的愉悦,但这也要求欣赏者在能够感知自然强力的同时,不会因这种强力而受到任何强制力的压迫。[6]119也就是说,欣赏者不能在自然强力面前处于精神被压迫的状态诸如紧张、恐惧等,因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人通常会出于本能而选择逃避,所以有意识地作出审美判断几乎是不可能的。
西利亚在上文提到的那场风暴中感受到愉悦与敬畏之后,恐惧的情绪转而控制了她,在这场风暴的后半程,她的文字中充满了对暴露在风暴中花儿的担忧与恐惧。
噢!但这风太强烈了!求你爱惜我的宝贝,噢,不要尽行杀戮我美丽的、挚爱的花儿们!……在这危险持续之时,我屏住呼吸,脑海中只想着这风的力量会伤害那些花儿……这大风让我为我的花儿们感到害怕,因为它们对此毫无防备。船在码头胡乱地颠簸,海水在岸边疯狂地翻腾,世界被淹没而逐渐消失,只剩下狂风暴雨的奔腾与咆哮。[7]
对于一生中爱花如命的西利亚来说,花儿们就如同她的骨肉至亲,它们的喜怒哀乐全都能使西利亚感同身受。在这场风暴中,花儿的命运与她紧紧地连在一起,她为花儿的安危而担惊受怕,脑海中充斥着“风的力量会伤害花儿”的想法,对于风暴本身的感知霎时间荡然无存。此处的西利亚将自我的灵魂寄居于屋外的花儿之中,风暴对于花儿的强制力也就转嫁到了她的身上,在这种紧张、焦虑、惊惧的状态下,方才在恢宏壮阔的暴风雨中感知到的几分愉悦早已不见踪影。这份崇高的愉悦,只有在欣赏者既能够感受到自然物体的强力,又对欣赏者没有强制力的状态下才会产生,康德认为这种强制力是恐惧产生的根源,它的消除必然依赖于审美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条件——适当的审美距离③康德在论述自然中“力学的崇高”时提出,在保证安全的状态下欣赏自然的强力,便能够感受到崇高的愉悦。详见Critique of Judgement 第28章。。
(二)“距离”之外的灾难书写
关于审美距离必要性的探讨可以追溯至18世纪,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在《崇高与美的哲学探索》(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Sublime and Beautiful)一书中提出:“当危险或痛苦太过接近时,它们便不能产生任何愉悦,仅仅只是恐惧;但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经过一定的修饰,它们便可能是愉悦的,正如我们每天所经历的那样。”[8]该理念继而引发了康德对于恐惧与崇高关系的思考:首先,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他认为在具有一定危险性的自然事物面前,恐惧与崇高是无法共存的;其次,人之所以能够感知崇高的愉悦,是因为他们发现自身有能力实现对于自然强力的领会(apprehension)与统摄(comprehension)①拉丁语原文分别为apprehensio与comprehensio aesthetica。。然而,实现这种领会与统摄不仅需要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还需要欣赏者的自身安全得到保证,否则审美评价根本无从谈起。[6]108时至今日,审美距离依旧在对自然灾难的欣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代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Yuriko Saito)②有关Yuriko Saito 的姓氏翻译在国内学界有“斋藤”与“齐藤”两个版本,通过向Saito教授求证得知,“斋藤”确为其家族姓氏,但她本人更倾向于使用“齐藤”,故本文尊重Saito教授的意愿,一律译为“齐藤”。也认为,在欣赏具有危险性的自然事物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要的,它能够保证审美评价的产生。[4]246
上述几位哲学家关于审美距离的探讨大多是形而上的,与他们不同的是,西利亚从未专门阐释过距离如何影响她对灾难的欣赏,对距离的领悟与运用仿佛是她的天赋,她总能与危险的自然景观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既不会因为太过亲密而令她感到紧张不堪,也不会由于太过疏远以致无法获得全面、立体的审美体验。比如她在《夏日的一天》(A Summer Day)中,就记录了自己随着雨势减弱,逐渐靠近并参与到这场暴雨之中的经历。
接着雷声大作,一声巨响
恢宏壮丽,划破天际,肆意冲撞;
狂风犹如暴怒的龙骨般,
刺向海面,溅起朵朵巨浪。
它带来大雨横扫陆地与海洋。
又是一阵骚动!闪电锐利且热望,
雷,风,雨——一场伟大的庆典在这苍穹之下,大地之上!
……
在那里,雨势渐缓,但我同样欢愉,
伫立于他的手心,
我加入了这场歌颂上帝的圣歌,全心全意,
带着一份不可名状的幸福,激动颤栗。[9]29
在暴风雨的开始与高潮阶段,站在岸边近距离的观察是极度危险的,作为岛民的西利亚深知这一点,因此她选择与愈演愈烈的暴风雨保持距离。在选文的前两节,她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了这场“伟大的庆典”,然而,随着雨势衰颓,西利亚的欣赏距离也随之拉近,她最终“加入”了这场“歌颂上帝的圣歌”,成为暴风雨的参与者。在诗的最后一节,作为参与者的西利亚不仅收获了感官的愉悦,也体会到心灵的感动与“颤栗”。柏林特就十分强调“参与”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10],认为它能够保证欣赏者获得“浸入式”的审美体验(fully engaging aesthetic appreciation)[11],他的观点在此处是部分合理的,西利亚在走近暴风雨后的确为自然的壮丽所触动,继而激起了灵魂深处的共鸣,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自然必须以欣赏者的安全作为首要前提,尤其是在她作品中所记载的那些大大小小的自然灾难中,倘若西利亚选择在“雷声大作”、闪电锐利横行、巨浪“不断拍打孤独的小岛”之时,以“参与者”的身份欣赏这场暴风雨,那么令她“颤栗”的也许就不再是那份“不可名状的幸福”,而是一份由于害怕被海浪卷走而本能产生的恐惧了。
西利亚对距离的领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特殊的成长环境。尽管西利亚笔下的多鱼群岛一年四季都绽放着无与伦比的美,但实际上这里的气候并不适宜人类生存。自四岁随父母迁居此处以来,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几乎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她见识过狂暴的大海几乎将小岛吞噬,冬日的严寒使小岛寸草不生,逼得岛民们不得不依靠屯粮过活,自然那残酷无情的一面时时刻刻警醒着她——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人类就如同那“附着在礁石上的小小鸟蛤”一般微不足道。[12]118这般独特的成长环境也使得她对自然有了与众不同的理解,在她看来,自然不是人类的附庸,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更加高级的范畴,当自然的强力在人类面前真正显露之时,“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束手无策”[12]138。这使得她与那些康科德(Concord)的超验主义者们在如何与自然相处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13],相比于西利亚居住的偏远海岛,以爱默生、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者大多生活在自然环境相对稳定、适宜人类居住的内陆地区,生活在此处的人们鲜有与自然灾难正面接触的机会,在他们的认知里,多鱼群岛上的暴风雪也许并不比吹灭壁炉火苗的大风更加凶猛,也不可能会把一艘大船无情地抛向坚硬的岩石,并吞没船上所有鲜活的生命。对他们来说,自然是平和的、可接近的,甚至是理应为人所用的,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对自然的态度保持着乐观的底色,他们相信自然,迫不及待地试图拉近与自然的距离。而西利亚与他们的看法有所不同,她曾在一封写给福克斯(Feroline Fox)的信中提到过自己与超验主义者在与自然相处方式上的差异,她认为爱默生和梭罗欣赏自然的方式属于积极主动型,他们愿意每天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自然中“享受散步这件事本身,用眼睛而耳朵积累财富”[1]54。劳伦斯·布伊尔(Laurence Buell)认为,西利亚在这封信中将爱默生与梭罗形容为“无忧无虑的漫步者”,暗示他们坚持“追寻”自然所传达的某种意义。[3]233-237西利亚则与他们不同,成长于自然环境复杂多变的多鱼群岛,见惯了自然的危险与残酷,她比爱默生等人更加了解自然中蕴藏着的强大力量。对她来说,盲目地深入自然是危险的、不理智的,对于未知的自然,西利亚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但敬畏也意味着疏离,这份潜意识里的疏离感也呈现于她对于自然灾难描写的字里行间。相比于暴风雨的亲历者,她更愿以旁观者的视角观察它的壮阔恢宏。正因如此,西利亚反对过度地参与自然,甚至批评爱默生等人是在“刻意地追求幸福;在自然中费尽心思地追逐幸福只会适得其反”,要想真正领悟自然的美与智慧就应该学会静观与等待,“任由它独自发展,它最终会来到你的面前”[14]。
实际上,尽管西利亚在作品中穷尽华丽词藻来美化自然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自然灾难的危险是麻木无知的。她也能像常人一样感知灾难所带来的强力,只不过在距离的帮助下,灾难加之于她的强制力发生了质性的转变,甚至直接参与到她的审美过程中来。换句话说,借助于距离,西利亚眼中的自然灾难已经不再令她“感到恐惧”(being afraid of it),而仅仅是一种“可恐惧的”(fearful)存在,这个转变看似细微,却使灾难之美在西利亚的眼中变得愈发迷人且深刻。前文已经提到,西利亚对自然的残酷与暴戾了如指掌,她深知人类在自然面前不堪一击,明白渺小的人类根本无法同伟大的自然相抗衡。力量上的悬殊差距使她意识到,人类在自然灾难面前所做的一切抵抗都是无意义的,在亲眼目睹了一场海难发生之后,她写道:“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真是惊魂一刻,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却什么也挽救不了。”[12]138于是西利亚作出了妥协,她选择放弃与自然抗争,以一种释然的姿态接受自然中发生的一切,这份释然令她甘愿成为自然的“旁观者”,站在安全的距离之外,灾难的强制力所带来的恐惧也随之被冲淡,取而代之的是对灾难本身强大力量的敬畏,换言之,随着作者与灾难之间的距离不断扩大,作者对恐惧的感知也就逐渐减弱,恐惧中令人精神压迫的成分被不断抽离,剩下的仅仅是一层看似“可恐惧的”空壳,它最终转化成为一种关于审美客体的客观判断,并再次参与到西利亚对自然灾难的欣赏中来。
同样地,我们并不畏惧,看着夏天的暴风雨,听着悠扬的雷声在雨后的海面上低吼。……风暴从海面呼啸而来,将我们在无助之时吞没,在灯塔中看着这景象真是极好的。[12]136
灯塔四周镶嵌着透明的玻璃,它既是保证西利亚安全的屏障,也成为了她全方位地感受暴风雨的最佳观测点。狂风卷起巨浪不停地拍打着坚固的玻璃,这真实的灾难看似与西利亚近在咫尺,眼看就要将她“吞没”,但正如她在引文的开头所说,这一切并不使她感到“畏惧”,因为她被灯塔保护着,无论窗外的巨浪如何汹涌澎湃,此刻的她都是安全的;这样,精神上的恐惧已经转化成了视觉上的“可恐惧”,而后者本身也是一种静观中产生的审美判断,在它的作用下,西利亚享受着那风暴“将我们在无助之时吞没”的愉悦。这份愉悦是在自然灾难中体会到的崇高的愉悦,它一方面产生于西利亚对自然伟大力量的敬佩与叹服,另一方面孕育于西利亚试图欣赏自然灾难的过程之中,是自然的强力对她灵魂的净化与升华。这也正如康德所说:“它们之所以被称为‘崇高’,是因为它们将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平庸。”[6]120
恐惧的确会阻碍审美判断的产生,但它是人类面对自然灾难时的本能反应,也是危险性自然景观区别于其他自然景观的独特之处,刻意回避恐惧的存在,也就难以领会自然灾难的美学价值。西利亚对灾难的理解是全面而客观的,借助于对距离的巧妙把握,她不仅克服了恐惧对审美活动的阻碍,更是将其进行转化,从而深化了对自然灾难审美价值的理解。得益于特殊的成长环境,西利亚相信距离在人与自然相处中的重要性,她不认同盲目乐观的“参与者”心态,主张以静观的方式感受自然带来的愉悦。与自然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的疏离与漠视,反而代表着西利亚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相比之下,盲目地走近未知的自然,却是人类无知与自负的体现。
二、泛化的“道德”与纯粹的“审美”
自然灾难几乎是贯穿西利亚整个写作生涯的主题之一,在她的笔下,不论是汹涌的海浪、猛烈的暴雨、无尽的白雪甚至是无情的飓风,都展现了各自独特的魅力。也许在西利亚看来,将它们定义为“自然灾难”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它们不过是自然规律运作的印证,尽管会对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一定的损害,但这绝非它们的本意,因为自然的运转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她看待自然的态度更具现实主义色彩,她不像爱默生那样,将自己看作大自然的“宠儿”,在西利亚的认知里,人类永远都是自然界的一份子,人类的命运也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命体一样,被牢牢地攥在大自然掌心之中,自然从不会偏袒她的任何一位子民。
(一)人类与自然语境下的“道德”辨析
出于对自然运行法则的清醒认知,不管是残酷无情的自然灾难,还是令人心旷神怡的乡野田园,都一视同仁地被纳入了西利亚的欣赏范围,成为了她体悟自然中的“美”与“崇高”之愉悦的来源。然而,当代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对审美自然灾难的道德性提出了质疑,她承认自然灾难存在美学价值,但因其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伤害,所以她认为,自然灾难超出了人类可欣赏的范围,审美自然灾难是有违道德的行为。[4]248-249然而,“道德”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内涵,自然灾难并不属于人本主义道德的受用语境;并且,将道德作为审美活动的前提或评判标准,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审美的初衷,所得出的审美判断也已失去了纯粹性与自由性。
“道德”指的是衡量行为是否正当的的观念准则,它的内涵会根据其所处语境的不同而发生转化。在人类社会中,人们会根据其特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关系以及生活状态逐渐自然地形成一套道德标准,尽管不同的社会所产生的道德标准各有不同,但它们本质上都以人的利益为价值导向,因此也可以被称为人本主义的道德标准。而在自然世界中,同样存在以自然界整体利益为导向的道德标准,它与前者的产生条件不尽相同,然而两者并行不悖,能够各自作用于其所属的范围之中,但两者之间绝不能相互置换,因为那样便会扰乱各自世界的运行规律,产生极大的相反局面。
长期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西利亚俨然把自己当作一位“自然的公民”,尽管她从未解释过何谓自然世界中的道德准则,却将对自然法则的领悟渗透于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有学者认为,西利亚·撒克斯特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意识到自然对人类“无偏私”(indifferent)的作家。[15]自然的神秘与伟大令她心怀敬畏,她相信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得以生存;在那座人迹罕至的孤岛上,西利亚始终恪守着这样的生存法则,也履行着一名“自然的公民”应尽的义务。19世纪上半叶,超验主义正在新英格兰的土地上蓬勃发展,这场被称作“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潮将人的主体性与优越性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西利亚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直至20 世纪中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才在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对自然世界的道德准则作出系统阐释,提出了“土地伦理”(Land Ethics)的概念①“土地伦理”中的“土地”概念泛指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在内的整个生物共同体。,强调人类在自然的共同体中与其他成员拥有平等的地位,自然永远有自己的运行法则,人类必须努力将自己与自然的发展轨迹融为一体,不能与之背道而驰。[16]
齐藤百合子之所以认为审美自然灾难是违反道德的行为,是因为她错误地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法则作用于对自然事物的审美范畴,且不论道德能否参与审美活动,即使它真的能够作为一种判定自然审美范围的标准,那么适用于此处的“道德”也应来源于自然范畴而非人类范畴。例如,某自然景观(包括人造的)是否有利于其所属的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或者某自然事物的存在是否会打破周边生态环境的平衡秩序。自然界的任何活动都可能对人类造成伤害,极为普通的闪电也可能致人死地,凶猛的野生动物亦不会对人类手下留情,若仍旧以人类的安危作为划定审美范围的标准,那么自然界“可欣赏的”(appreciable)事物便所剩无几了,这样一来,谈论“自然审美”也就犹如纸上谈兵一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西利亚坚信人类属于自然,因此她始终恪守着一名“自然的公民”应履行的职责,尊重自然规律,尝试理解它们可能对人类造成的伤害。不仅如此,她还在寸草不生的小岛上开垦出一片色彩斑斓的小花园,这片花园不只是小岛上唯一的一片“绿洲”,更是成了迁徙的候鸟暂时驻足的大本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态度赋予了她广阔的眼界与包容的胸襟,使她跳脱了人本主义道德的束缚,并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然多元之美的大门。
然而,尽管西利亚全然理解了自然的残酷,但这并不代表她对在那些灾难中逝去的生命置若罔闻。多鱼群岛上竖立着许多座无名的墓碑,这些墓碑的主人都因为无情的海难而失去了生命,西利亚时常会来看望这些“沉默的”朋友。她不仅对逝者的悲惨命运感到惋惜,也为在绝望中等待他们回家的家人们感到心痛。在《西班牙人的坟墓》(The Spaniard’s Graves)一诗中,西利亚看到数十年前死去的西班牙水手们的坟墓时,不禁联想起他们的妻子、母亲、女儿,想到她们在这几十年中,“年复一年,苦苦地守望着,直到青春与容颜逝去,直至如炬的目光熄灭,直至生命走到尽头,希望也最终陨灭”[9]25,想到这些,站在墓碑前的西利亚被泪水沁湿了眼眶。这泪水不仅是为被海难吞噬的生命,也为那些在大洋彼岸苦苦守候的“黑色眼睛的姐妹”。
(二)脱离“道德”的纯粹审美
西利亚对不幸的命运有着共情之心,她不仅为在自然灾难中逝去的生命悲痛不已,也对因灾难痛失挚爱之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但这份同情并未阻止她欣赏自然灾难的脚步。前文已经提到,特殊的成长环境赋予了西利亚广阔的审美视野与审美能力,对自然的敬畏又使她能够从自然的立场看待自然灾难,她是一位理智的欣赏者,在她的作品中,自然的残酷与魅力得到了完整且独立的呈现,对逝者的同情并未阻止她欣赏的脚步,也从未参与到她对灾难的审美中来,借用康德的话说,她向读者呈现了一种“纯粹的”“无利害的”审美体验。康德认为,审美活动应该是纯粹且自由的,如果审美判断被某种知性的概念所控制,那么审美就失去了纯粹性与自由性[6]131;“美”与“崇高”都是无关利害的审美体验,必须在没有概念束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6]127。尽管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利害”在当代受到了批判①柏林特就曾在他的《艺术与介入》一书中,否定了审美作为一种脱离概念与利害的无功利审美活动存在的可能性。具体参阅:Arnold Berleant,Art and Engagement(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然而审美经验的“无利害”在对自然的审美活动中还是有着无法忽视的意义,正如当代环境美学家埃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所说,无论是对美或是对崇高的鉴赏,都应该排除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以此避开自然欣赏中的主观性与人本主义倾向,因而才能如其本然地审美自然。[17]
西利亚是否阅读过康德的相关著作已经不得而知,但对于审美的“纯粹”追求的确在她的审美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不论是前文提到的诗歌《西班牙人的坟墓》,还是《波卡洪塔斯号的残骸》(The Wreck of the Pocahontas),亦或是她在散文作品《海岛生活》(Among the Isles of Shoals)中的相关描写,对逝者的同情始终被她置于审美之外,扮演着独立的角色。然而,齐藤百合子认为,对自然的审美判断是关乎人类道德的,这种道德应该指导人类对自然的欣赏,若是在审美过程中置同类的悲惨遭遇于不顾,那么这种审美行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实际上,尽管前文已经指出,她的观点错误地将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作用于自然世界,但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对事物的欣赏都不应受到道德的束缚,因为一旦如此,审美过程便不得不与利害相结合,因而失去了纯粹性,而审美判断最终就成了一种合目的性的智性判断,人们在此过程中会误以为自己体会到了“美”或“崇高”的愉悦,但实际上这种愉悦是“善”的愉悦①参见本文的第二部分,康德将感性的愉悦分为四个范畴,其中“快适”与“善”是关于利害的,而“美”与“崇高”必须是与利害无关的。,它与“美”或“崇高”有所不同,前者来源于一种纯粹智性的判断力,而后者才属于真正感性的(审美的)判断;也就是说,若是“道德”参与审美活动,那么所得出的审美判断便无非是一种合目的性的智性判断,这种判断与纯粹的感性判断有所不同,审美判断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其承载着主体的感性认知,这种感性认知必须是自由的、纯粹的,不能受到任何前提条件的限制,否则稍有不慎便会成为目的论的判断,从而失去了审美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西利亚是一名合格的“自然的公民”,她恪守自然的道德法则,为着自然的发展作出贡献;她也是一名出色的自然鉴赏者,她理解自然的残酷,同情人类的苦难,始终为自然之美坚守“纯粹”的底线,真正做到了以自然的名义欣赏自然。
三、结语
作为一名合格的“自然的公民”,西利亚相信距离在人与自然相处中的重要性,她不是盲目的“参与者”,而是理智的“静观者”,与自然保持距离,并不代表疏离、漠视自然,反而彰显了她对自然的尊重与敬畏。尊重自然便意味着遵循自然的道德,她从自然本身出发,以自然的整体利益为准则,为理解自然灾难找到了出口;同时,她坚守着审美自然的“纯粹”底色,真正做到了以自然的名义欣赏自然。
审美自然灾难固然不能在短期内被广泛接受,但审美灾难的意义的确是非比寻常的。自然拥有仁慈与残酷的两面性,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实际上都是自然规律的呈现。以人类的标尺衡量自然现象,我们便很容易陷入自我欲求的囹圄,进而只倾向于了解自然对人类有利的那一面,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理解自然。审美自然灾难并非仅仅为了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它更深层次的意义是为了帮助人们增强对于自然中的“他者”的领悟能力。我们在看待灾难时,不能只聚焦于灾难对人类造成的惨痛损失,更应看到自然的崇高与伟大,并由此反思人类自身的脆弱与渺小,进而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所应保持的关系。西利亚对于自然灾难的审美思考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她为人们积极地理解自然灾难提供了一种可能。在她看来,审美自然灾难的“距离”是必要的,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才可能克服恐惧来把握灾难中蕴含的崇高之美;而“道德”是必须舍弃的,审美是意识对于审美客体的主观投射,审美过程中掺杂道德评价势必会影响审美的纯粹性与自由性。她对于自然灾难的审美欣赏扩大了“非美自然”的审美疆域,对人们探索自然中的积极审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