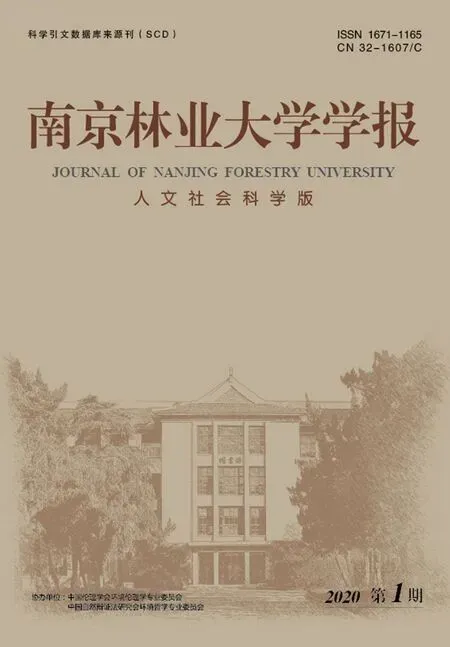“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试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
王云霞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
印度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和世界人口第二大国,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和能源,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淡水资源,但由于多年来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加之人口基数大、贫困程度高,印度大范围的环境破坏与环境退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其环境退化的经济成本约占全国GDP的3.5%~7.5%。迫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压力,印度虽一再加强了对本国环境可持续性的重视,但在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退化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这也由此催生了印度本土风起云涌的环境保护运动。从以妇女为主体发起的农民保护喜马拉雅森林的“抱树运动”,到不断爆发的民众抵制修建大坝运动,印度的环境运动已成为世界环境运动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印度的环境运动虽已引起学界关注,但相关研究成果并不多见。就国外而言,印度学者加吉尔和古哈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1]堪称印度环境发展史中的标志性著作。该书主要从宏观叙事的角度系统考察了印度次大陆的生态史,但对印度的环境运动并未给出详尽考察;还有学者①具体参见:P.P.Karan,“Environmental Society”, Geographical Review,1994,Vol.84,No.1,pp.32-41;Mukul,“Villages of Chipko Moveme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1993,Vol.28,No.15,pp.617-621;Martin J.Haigh,“Understanding‘Chipko:the Himalayan People’s Movement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Studies,1988,Vol.31,pp.99-110.拘泥于从实证角度概览印度的环境保护运动。我国学者张淑兰②具体参见:张淑兰所著的《印度的环境政治》(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印度的环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 年第5 期)、《印度的环境主义研究》(《南亚研究》2009 年第3 期)、《印度的环境非政府组织——拯救纳尔默达运动》(《南亚研究季刊》2007年第3期)。对印度环境运动有较多关注,并将其主要区分为保护森林运动和反坝运动。这些研究成果对我们了解印度的环境运动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共同缺陷是未对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进行甄别探究。事实上,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印度的环境运动非常别具一格。这体现在印度人民发起的保护环境运动并非仅仅出于对大自然的保护,而是基于“能够活下去”的日常生存需求,所以它不能简单划归于生态正义或环境主义的旗帜之下。另一方面,印度的环境运动与欧美的环境正义运动也有着显著区别,因为后者所指称的“环境”是人们居住之地、工作之境和玩耍之所,而非印度人民所指的森林、河流等外在的自然大环境。以此来看,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就成为一个十分有趣和值得关注的议题。本文尝试从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两个维度反观印度的环境运动实践,并对其正义指向进行研判,认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旨趣是环境正义与生态正义的奇妙混合体。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澄清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对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有着不同正义指向的两个概念。“生态正义”主要指认为人和自然之间存在正义关系的一种理论主张。它是伴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再反思的产物。生态正义的流行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环境伦理学不无关联,并以环境伦理学中的主潮——非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代言人。有鉴于自然已伤痕累累,并以各种方式如生物多样性消失、植被退化、土壤破坏等控诉着人类的暴行,“还我公平”[2]被非人类中心主义视为自然界发自内心的呼唤。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流派,史怀泽、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奈斯、利奥波德和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等,不遗余力地将生态危机的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认为正是其将人置于中心地位,而不考虑非人类生物的主体地位,特别是内在价值的错误做法,才招致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基于此,赋予动物、植物等以道德主体资格,承认其内在价值,并让人类对其讲义务和道德,就成为这些流派的理论旨趣,并希望以此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正义,以实现自然不被人类奴役和破坏的目的。
环境正义虽然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但它和生态正义在发端、源流以及价值取向上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环境正义诞生于美国,是由广大少数族裔、有色人种、低收入阶层组成的环境弱势群体,为追求环境平等权益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环境正义主张“在发展、环境法律、制度和政策的实施等方面,所有人,不论其种族、文化、收入以及教育水平如何,都应得到平等对待。平等对待意味着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缺乏政治或经济的力量而被迫承担不合比例的环境负担,如环境污染或环境危险物等”[3]。对环境善物与恶物的公平分配是环境正义追求的首要目标。此外,它还强调人们在环境事务中应拥有参与权和知情同意权(参与正义);主张社会应对人们的独特性,尤其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群体做到心理和文化上的承认认同(承认正义);以及认为社会应关注与环境有关的行为或决策是否促进了人们生活能力的改善和提高(能力正义)。也就是说,环境正义是集“分配正义、参与正义、承认正义和能力正义为一体的综合性框架”[4]。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关注的对象虽同为“环境”,但二者对“环境”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想象。生态正义意在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关心的是外在生态大环境的安全,也即荒野、湿地、国家公园和濒危物种不受人类的过度干预和破坏。环境正义旨在强调人类在环境事务上的公平公正,关注的是身边“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免遭环境不正义行为的侵害。
二、印度的环境运动
作为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印度的环境运动可追溯到被视为“生态分水岭的殖民主义”时期。在被英国殖民者侵占之前,印度人和大自然保持着较为和谐的关系,“对自然的敬畏,经过世代延续,已成为印度人灵魂和心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6]。在印度神话和民间信仰中,战神和女神将它们的家安置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河流被认为不单纯是运输的通道,而且是滋养印度人生命和丰饶的源泉,是神圣之所。森林及生活于其内的各种野生动植物,对印度人也有着独特的意义和重要性,是需要关心和保护的对象。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疯狂扩张,特别是在沦为英属殖民地之后,印度的生态系统就被扰乱,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被重新进行了塑造。“遍及世界的不列颠民族的破坏性能量迅速将森林变成了沙漠,对次大陆的森林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1]73英国在对印度树木进行大规模开采的同时,还不断将林业商业化,这些举措对世代以森林为生计的主要来源的印度人而言,无疑是一种严重的干涉,也因此遭致了他们的不满和抗议,甚至引发了起义和抗争。这可被视为印度早期环境运动的开始。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进行的抗争活动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基于夺取对森林资源的控制权这一目的,以便能够延续其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比如采集、狩猎、游耕等。因而,印度早期的环境运动更多的是源于自发,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也远未上升到自觉的程度。这种状况在印度获得独立后,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才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尤其是在经历了震惊世界的“博帕尔泄露事件”后,人们的环境意识更是得到大大增强。这些都将印度的环境运动带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就目前而言,印度有两类环境运动举世闻名,这就是著名的契普克和反坝运动。
(一)契普克:为保护森林而战
契普克(Chipko),又称“抱树运动”(the Tree Hugging Movement),是对印度妇女采用抱树的方法使其不被木材公司砍伐,从而有效保护森林的简称。在印度文化中,通过抱树使其不被砍伐的观念由来已久。但“契普克”这个词汇真正得到流行,则要归因于印度一位诗人在目睹了1972年喜马拉雅山的树木被大面积砍伐后,用诗歌对人们掀起的抗议活动的描述:“将树环抱,使其免于砍伐;它们是喜马拉雅山的财产,要拯救它们不被砍伐。”[6]而抱树运动也是印度人民对其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长期践行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继承和发扬。甘地的追随者和助手米拉·贝恩、莎拉拉·贝恩都是印度抱树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米拉曾连续几年居住在喜马拉雅山中,与森林为伴。她注意到该地区的洪灾一年比一年严重。经过调查研究,米拉发现洪水肆虐是森林中的喜马拉雅橡树被木材公司砍伐所致。她还注意到当地林业部门砍伐了橡树,种植了能带来高额利润的经济林。但这种短视行为给喜马拉雅山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也威胁到当地妇女的生存安全。在她的领导下,印度妇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抱树运动,这一运动也一直延续至今。在抱树运动中,妇女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1973年3月,高帕什渥村庄的300棵木岑树被林业官员划分给了运动物品制造商。不久,公司代理人来到村庄准备砍伐树木。愤怒的妇女们聚集在一起,列队步行,敲鼓齐唱传统歌曲。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将树团团围住,不让伐木工人靠近。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伐木公司不得不撤退。一年后,当林业部宣布拍卖雷尼森林的2 500 棵树,妇女在保护这片森林中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80 年8月,在丹戈瑞潘德利的一个村庄,由男人组成的村委会与园艺部门达成协议,打算用附近的橡树林进行一场交易,即用砍伐树木的手段来换取一条水泥路、一所高级中学、一家医院和向村庄供电。这个消息令环境主义行动分子不安和愤慨,她们试图劝说委员会改变立场,但遭到拒绝。被激怒的男人们警告妇女,如果敢反抗委员会的决定就把她们杀了。但女人们的勇气势不可当,她们举行了抱树示威集会,拯救了橡树林,并促使政府颁布了禁止在该地区砍树的法令。1997 年11 月,抱树运动在德尼伽惠尔的一个小村庄再次掀起。为阻止林业部门和木材商的伐木交易,妇女们将圣珠系在了即将被砍伐的树上(按印度教习惯,把圣珠系于某人身上就建立了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她们决心为拯救这些树而战,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妇女们的这一举动让试图说服其让步的林业官员气得大吼:“你们这些愚蠢的女人,你们知道森林意味着什么?树脂、木材和外汇!”一位妇女响亮地回应道:“是的,我们知道森林的含义,那是土壤、水和清洁空气。”[7]印度妇女之所以对抱树运动有如此高涨的热情,并将这种传统延续下来,是因为这关系到她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森林一旦遭到毁灭性砍伐,妇女们的日常活动,如汲水、拾柴和做饭等都会受到影响,这使得她们对树木的保护有着超乎寻常的关切度和积极性。说白了,印度的抱树运动是为生存而战。所以,“对土地、水、空气和能源的保护并不抽象,而是简单活下去的一部分”[10]。
(二)反坝运动:寻求可替代的发展
印度的“反坝运动”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民众对“静之谷”的保护中。静之谷是位于印度克拉拉邦仅存的未被干预过的原生态热带雨林区之一。由于远离城市中心和高速公路,静之谷的木材几乎不曾被大规模砍伐,土地也不曾被耕种过。然而,政府却在1968 年突然作出决定,要对其进行大规模开发。按照规划,从静之谷穿行而过的一条大河将要被拦腰切断,用来建造一座大坝,而众多木材公司也会被批准砍伐雨林中的树木。此举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的决定不仅会给静之谷产生环境负面影响,而且带来的社会负效应也不可小觑。一来切断河流修筑大坝,砍伐树木获得木材,会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给雨林中动植物的生存带来威胁;二来修建大坝和砍伐树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城市的消费,而不是使当地人受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静之谷的干预和破坏会给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因此,对静之谷的开发既是一种生态不正义(给植物动物带来灭绝性伤害),更是一种环境不正义(城市享受修建大坝带来的环境善物,却让农村承担由此产生的环境恶物)。在非政府组织和环保主义者的帮助下,人们发起了反坝运动,对静之谷的开发终被叫停,但由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对水力和电力的高涨需求,印度对通过开发大坝建设项目用于灌溉和发电的热情丝毫未减,而这也使“印度成为20世纪建坝排在首位的国家,印度的大多数河流要么已经完成建坝,要么正行进在被建坝的路上”[4]。这些工程多属大规模水利水电工程,而且被印度视为发展国民经济、帮助人民脱贫致富的有力杠杆。恰如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所言:“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圣堂。”然而,寄托着印度实现现代化理想的大坝工程是否如人所愿呢?真相远非如此。事实上,印度的大坝工程带来的经济效益远不敌其产生的生态负效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工程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自然也遭到了反对。例如印度最大的水电项目迪邦水坝自启动以来就饱受争议。按照政府计划,该水坝的作用不仅仅是用来发电,还能解决临近平原洪水泛滥的问题,但水坝修建将会使5 000 hm2左右的土地淹没在水下,而这些土地正是印度森林密集的地区。按照印度政府的评估报告,仅有301人可能因建造大坝受到影响,但在民众看来,这不啻于天方夜谭。他们认为,水坝的建造会使附近的牧场土地和渔场受到威胁,而这些恰恰是人们的生存之本。总之,“项目所需的生态环境及社会成本远大于大坝给印度带来的好处”①具体参见:http://www.cpnn.com.cn/sd/gj/201410/t20141031_751306.htm。。自该项目举行奠基仪式以来,反对之声几乎从未停止过,与之相关的抗议行动也常见报端。2011年发生的一次抗议活动中,警方突然向人群开火,造成10 人受伤。当地政府给抗议者扣上了反政府的帽子,更是激怒了民众。
较之迪邦水坝工程项目,纳尔默达水坝引发的争议与冲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该项目包括30个大型、135个中型和3 000个小型水坝。设计该项目的初衷是满足灌溉与饮用水的需求,但代价却是数万名居民迁移以及广泛的环境损害。纳尔默达水坝工程曾获世界银行巨额资助,但在项目实施不久就引发了争议。当地群众认为,在至少10 万人口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情况下,对大坝贸然动工的决定十分草率和冒险。他们在一个名为“拯救纳尔默达运动”[9](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NBA)的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和领导下,进行了小规模示威、静坐和绝食活动。在此举不奏效的情况下,NBA组织了大规模群众性环境抗议集会,并成立了印度第一个全国性的环境运动组织——“人民发展运动”。1991年初,有7名活动家举行了“绝食至死”运动。不久,人们提出了“我们的村庄我们统治”[10]的新口号,并向高等法院递交了停止修坝的申请。1996年,人们又向政府主张对大坝的“知情权”。此外,他们还向媒体呼吁,以引起广泛关注、同情和声援。1999年7月,人们打着“自由纳尔默达运动”的旗帜,发动了一场行程800 km、历时8天的沿河进军运动。在高等法院2000年宣布继续修建大坝的判决后,印度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大型集会以示抗议。2000 年6 月,NBA成员出席了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了纳尔默达工程中的人权问题。同时,他们还利用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及其监督机构向政府施压。NBA甚至把反坝运动与反对全球化和私有化联系起来,指认全球化就是把印度人民的土地、河流和森林转变成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而根本不在乎人民的福祉与环境的保护。[11]
三、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
通观印度的环境运动,似乎很难将其简单划归为生态正义或是环境正义。就生态正义这一层面而言,不难发现,无论抱树运动还是反坝运动,虽然从表面上看,印度人民发动抗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原始森林不受损害,但从根本上说,却并非是单纯地“为了大自然而保护大自然”,而是基于对自身生存安全,也即是为了延续传统的生产
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自觉”考量,并由此发起的对自然的“被动”性保护。例如生活在喜马拉雅的妇女们之所以会掀起抱树运动的浪潮,是因为森林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依靠着生态系统赐予的食物、水和燃料,妇女们的日常活动如砍柴、取薪、汲水等,才得以很好的维系。森林里的树木不仅是人们获取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天然的生态屏障。树木一旦遭到毁灭性砍伐,不仅会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更重要的是会使人们原本就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正是基于这些担忧,妇女们才义无反顾地与政府、尤其是伐木公司进行了坚决斗争。“我们从我们的土地上只得到一点点事物;当我们甚至不能取得做饭用的微不足道的薪柴时,我们不得不诉诸于一场运动。”[1]142而这和流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中产阶级以上的有闲阶层发起的对河流、荒野、森林等人类所处大环境的保护,也即“为了大自然本身而保护大自然”的运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概言之,印度人民所生发出的对大自然的保护,绝非是基于生态正义——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单纯想要维护其健康和完整,而是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印度的环境运动多由生活贫困的低收入阶层——农民发起,而他们对森林、河流的保护从根本上来讲,是基于对生计的关切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比如印度在试图建立国家公园时,就曾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在人们看来,国家公园一旦建立,就意味着放牧、获取燃料木材和林副产品等传统权利会被大大限制,而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由于所有山脉和那些被当做休耕地与牧场的连绵起伏的土地都处在林业部的控制之下,以至于穷苦农民的牲畜在地球表面连呼吸之处都没有。”[1]91这些都充分说明,印度草根群众对“环境”的想象主要还是聚焦于使其满足自身生存需要,而不是像欧美国家有闲阶层那样,对荒野、湿地等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情感。“纯粹的”和不那么接地气的自然保护或许并非风马牛不相及,但对印度人而言,它们还远未提上议事日程。所以,印度的环境运动不能被理解成是为了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因为它和生态正义的指向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属于“穷人的生态正义”,也即是草根群众基于自身生存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安全的被动维护。正如印度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古哈所说的那样:“北方国家的环境主义主要是一种荒野保护主义,是中产阶级的发明,与生活质量和个人需求的满足密不可分。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主义不是富裕的产物,而是贫穷的产物,是农民和其他社会下层群体为争取拥有土地、森林、牧地和水资源的控制权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生活而展开的斗争。它的关注点是人的权利,是社会正义的问题,是为了让穷人与特权阶层一样享有自然界的成果。而西方的环境主义的关注点不是人的权利,而是动植物和野生栖息地。”[12]
而用环境正义这一维度进行审视,似乎也很难将印度的环境运动归于其麾下。因为和环境正义的策源地美国不同,印度的环境运动并未聚焦于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场所”免遭环境不正义之侵害,而是直接指向了对大自然环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绝非是为了自然本身,而是基于维系日常生计之考虑。众所周知,美国的环境正义主要是因为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少数族裔和低收入群体,对有毒设施和废弃物安置在“自家后院”而发起的抵制和抗议。比如著名的“瓦伦抗议”和“爱河事件”。前者爆发于1978年,当时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当局打算在黑人比例最高和最贫穷的瓦伦县修建一个垃圾填埋场,用来储存含有PCB的渣土废料。此举遭到人们反对。在经历了诉讼失败之后,愤怒的人们用人墙和躺在马路中央的方式封锁了装载着有毒垃圾卡车的通道。在抗议中,有超过500 人被捕。这是非裔美国人反抗有毒物质PCB(多氯联化二苯)倾倒在自家后院的勇敢尝试。“爱河事件”则是因为蓝领工人的住处和孩子们就读的学校,被建在了化学公司废弃的填满场上,而填埋场下面全是剧毒化学物质,这给人们的健康和家园的安全构成了致命威胁。但反观印度,却并未出现类似情况。个中原因可能是印度的人口构成比较单一,所以并未出现针对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的环境种族主义歧视。加之印度人口过于庞大,多数人都在贫困线上挣扎,对于家园社区健康安全的意识还未被充分激发和唤醒。比如印度德里作为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曾出现过由环境非政府组织发起的反对空气污染的运动。迫于压力,政府不得不宣布关闭化肥厂、钢铁厂和造纸厂等污染性企业,但这一举动却遭到穷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自己被迫失业后就丧失了起码的生活保障。再比如印度虽发生过渔民反对工厂企业将垃圾倾倒入海的环保运动,一些渔民还因为政府鼓励大兴养虾业造成红树林减少和农业用地被占用破坏,以及自身生活受到恶劣影响,而发起过反对商业性养虾的运动。这其中虽不乏对环境利益和环境负担分配不公所表达的不满,以及对家园环境质量下降的抗议,但说到底,其实是建立在养虾业影响和威胁到日常生计,而希冀红树林、土地和大海得到保护,因而和通常意义上的环境正义斗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然也需注意到,印度人民在其环境运动实践中,正不断显示出他们对分配、承认、参与和能力等多维度的环境正义诉求。这体现为当政府在公布环境决策或实施与环境有关行为的过程中,人们将自己看成环境弱势群体,并积极主张和维护自身环境权益。从抱树运动、反坝运动以及反对养虾业等运动中,都不难发现这种影子。另外,对知情同意权的觉醒意识,希望自身的独特身份被承认和认同,以及认为政府的环境决策和行为影响和威胁到自身生存能力等,都无不显示出印度人民对承认正义、参与正义和能力正义的追求。只不过这种对正义的追求不是基于对居住社区或家园健康安全的维护上,而是建立在对森林、热带雨林以及河流的保护之上。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印度的环境运动是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奇妙混合体,属于另类意义上的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