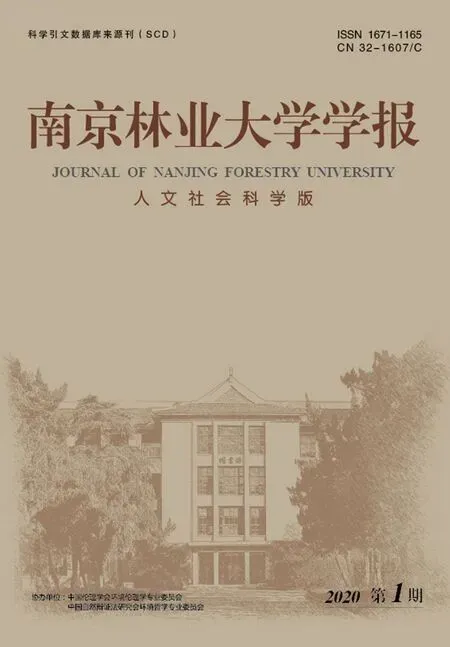以生命的独特性与稀缺性修正泰勒的生命中心主义*
王宝锋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提高,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其实践活动已经扩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范围。地球的陆地表面未被人类踏足和影响的地方越来越少,原本属于各种生命的生存场所在人类活动的挤压下范围大大缩小。人类活动造成了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并导致了大范围的物种灭绝,甚至人类自身亦受到环境问题的巨大影响。鉴于此,作为研究自然界价值与人类对自然界义务的环境伦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于西方哲学界。其中以泰勒(Paul Taylor)等人为代表的生命中心论以其严谨与完整的价值论阐明与实践体系的演绎在西方伦理学界被广泛地认同与接受。[1]泰勒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因具有内在价值而应该受到道德关怀,并给出了处理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关系的若干原则。泰勒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文试图发展和修正泰勒的论据,以完善其观点并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一、生命的独特性与稀缺性
生命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与非生命不同,但究竟区别生命与非生命的根本特点是什么,以及哪种特点能够成为被道德关怀的根据呢?对此,泰勒提出了“拥有自身善的实体”(entity having a good of its own)的概念。泰勒认为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包括单细胞原生动物、植物、动物、人乃至于某些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生命。对于这些生命来说,我们可以合理地讨论什么是有益于其自身善的,什么是对之有害的。而对于非生命来说,我们就无法应用这一概念。比如,对于沙子、石头、水坑等非生命来说,我们就不能说这堆沙子自身的善会被促进或被损毁,这是由于我们无法观察到任何有关这些非生命自身的善被损毁或被促进的现象。但对于所有生命,甚至最简单的单细胞原生动物来说,谈论什么对它们是有利或有害的就是可能的。[2]37-38在此,这种自身善还没有道德上的内涵,它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所指的不过是对生命的有利或有害。这种自身善的道德意义需要结合“以生命为中心的世界观”。
既然生命是拥有自身善的实体,那这些自身善的内容是什么呢?实际上,泰勒并没有对这种自身善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阐述。但是根据生命所具有的目的,可以对这种自身善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生命自身善的促进意味着生命目的的实现,正是在生命所具有的目的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知道生命的自身善是什么。假如生命的目的是保存自身,那对其自身善的促进就意味着避免对它造成伤害,阻止那些有利于其目的实现的东西的丧失等。因此,只要确定了生命的目的,就能够知道生命自身善的内容。
泰勒认为所有生命都是生命的目的论中心(teleological centers of life),“说它是生命的目的论中心,就是说它的外部活动和内部功能都是有目的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努力使自己活下去,并使自己能够成功地发挥生命功能,以此繁殖后代和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事件和环境条件”[2]76。泰勒这一观点的得出依赖于对生命是具有目的的假设。具目的性是生命具有自身善的前提。判断生命具有什么样的自身善需要根据生命所具有的目的,符合其目的的就是善的,违反其目的的就是恶的。而生命具有什么样的目的则是通过观察生命的行为倾向得出的。生命的行为倾向如果不是指向某种目的而具有合目的性的话,我们就无从得知其所倾向的是否就是对于生命是善的。因此,要想承认生命的自身善是存在的,我们必须假设生命的行为倾向是合乎其所具有的目的的。也就是说,对于生命自身善的得出,是从观察生命的行为倾向,假设生命的具目的性和行为的合目的性进行的。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具目的性与合目的性都是假设的生命特性,具目的性描述的是生命自身的性质,而合目的性描述的是生命行为的性质。在本文中笔者将根据不同的语境使用之。正是由于沙子、石头、水坑等没有可以被我们发现的行为倾向,也就不能假设它们是具有目的的,自然也就没有所谓自身善的说法。
尽管泰勒提出了生命的目的论中心的观点,却并没有对生命所具有的目的进行深入阐述,也没有对动物、植物生命的目的与人类生命的目的作出区分。[3]就笔者看来,生命所具有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所有生命都具有的自我保存的目的,这种目的为所有生命所具有。这种目的也是泰勒的生命的目的论中心观点所强调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着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两种自然客体,说某物质是有生命的,就是说它具有营养、欲望和思考这三者中的任何一种或多种生命行为。植物只具有营养的生命行为,这意味着植物只有摄取营养、生长和繁殖的特性;动物除了营养外还有欲望,它们的生命行为包括感觉、希望和感情;而人则具有营养、欲望和思维这三种生命行为。[4]其中为所有生命所共同具有的是营养的行为,这一行为体现了生命对自身的保存倾向。也就是说,生命将自身的存在作为目的,并以营养的方式来实现。由此可以看出,亚氏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不论是植物、动物还是人类,这一目的都内在于其自身,是作为生命的本能而存在,不因物种的差别而有所差异。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善,因为虽然我们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生命都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但保存自身的目的却并不必然是所有生命所具有的。虽然以微生物、植物、动物和人类为代表的生命往往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但是保存自身这一目的却不能成为生命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某种生命不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甚至以毁灭自身为目的的生命也是可以想象的。
第二种是为了实现保存自身目的的手段性目的。这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欲望的生命行为,如对快乐、避免痛苦、自身利益、幸福等的欲望。这种目的作为生命保存自身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自身的手段是朝向自身的,对之的追求往往是为了实现生命自身尚未达到的某种状态。这一点可以从大多数的生命行为中看出。当一只动物饥饿时,就会产生对进食快乐的欲望,在大快朵颐饱腹之后,再继续进食就将对自我保存的目的不利而不再进食。由此可以看出,快乐作为驱使生命去进行保存自身活动的动力,就是生命满足自我保存目的的手段。而诸如避免痛苦、自身利益、幸福等,也都与快乐的作用类似。尽管其为手段,却常常被生命视为目的。当动物在满足了保存自身目的之后所进行的嬉戏打闹,就可以看作将快乐作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通过嬉戏打闹以满足其他目的。对这些目的的追求,除了能够满足基本的保存自身的目的之外,还是生命发展自身、使自身繁荣兴盛的重要途径。
第三种目的主要是朝向自身之外的目的。其不同于自我保存目的,也不是作为实现自我保存目的的手段,而是将外在于自身的实体作为目标;这类目的包括理想、他者的利益、社会共同体、某种产品、某种对象等。对这些目的的追求可能有损于自身的利益,并且往往是具有强大自主意识的人类才能设定的。就人类而言,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目的都是可以被设定的。比如,人类可以将外在于自身的某种理想作为自身的目的,并以完全违反属于其本能的保存自身的目的来行动,就像通过绝食以捍卫某种信念、为了民族解放奉献自己的生命等。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能够设定完全不同于自身生存目的的能力是人类能够承担对生命的道德义务的必要条件。而泰勒所举的蜜蜂和蚂蚁这种所谓的社会性昆虫,虽然具有不是朝向自身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却并不是由它们所自主设定,而是与生俱来的。它们具有朝向其所在的共同体的目的,在其中行使着某种功能或作用,因此可能为了共同体而损毁自身。[2]76
就保存自身的目的而言,或许有人质疑生命虽然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但这一目的本身未见得就是善的。这个质疑是有意义的,因为事实上具有目的并不代表这一目的就是善的。但是生命保存自身的目的是善的,这是由于从生命的独特性来看,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在生命出现之后,原本没有目的的、被动的宇宙由于能够成为生命满足自身目的的工具而具有了工具价值。另外,只有在生存的基础上,生命才能实现其第二种及第三种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属于生命自身的价值。由于生命的脆弱性,假如生命不具有生存的目的,或者以死亡为目的,那生命可能早已消亡,而建基于生命之上的繁荣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生命的生存目的是一切价值产生的前提,是价值之源,而生命本身也由此而具有了道德上的重要性。
相对于完全被自然规律所支配的非生命的无目的性而言,生命的具目的性是极为独特的。但遗憾的是,这种独特性的存在却是极为稀缺的。生命是稀缺的,这在当下看来似乎是个伪命题,因为众所周知,地球上生命的数量已经很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生命的稀缺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生命在宇宙中的分布范围极小。就目前人类的探索能力之所能及的,尚未发现除地球以外存在生命的可靠证据,由此可见在地球上诞生的与非生命全然不同的生命之稀有。不用过多描述,只用想象在无垠的宇宙中,居然只在沧海一粟的地球上孕育出了不同于非生命的独特的生命,由此观之,生命的稀有已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相对于生命来说,非生命的分布则是极为广泛的,甚至于生命本身都是由非生命构成的。虽然某些非生命在人们看来是稀有的,得到人们的珍视,但比起生命来说,却远远不及。黄金虽然在地球上比较稀有,但在宇宙中却比比皆是,而当人掌握了黄金的物的规律后,甚至可以直接在微观层面合成黄金。
其次,生命的生产也是极其困难的。假如生命灭绝了,要由自然界再次生产出生命来,想来也是极为困难的。而且就算是在生命出现后,如何使生命大范围繁殖也是极不容易的,这需要极为苛刻的条件。人类如今已经可以登陆月球,但为什么不能去月球生活呢?这主要就是由于离开了地球,不用提生命的繁殖了,就是生命的存在都是极为棘手的问题。就目前来看,除了根据生命所现有的生殖系统来加速或扩大对生命的生产外,要想完全人工地从无机物直接制造生命却仍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另外,如今人们设计并制造了形形色色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可以进行逻辑上的演算,并且能够根据设计者所预先设计的目的进行合目的的运动,虽然其能否具有意识以及是否可以称之为生命仍然未有定论,但就以生命的具目的性与主动性来看,人工智能似乎具有这两种成为生命的条件。但即便将人类所制造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算作生命的话,生命的存在仍然是极度稀缺的。
最后,生命的产生是偶然的。我们甚至难以想象,在一个全部是无目的与被动的非生命的世界中,如何能够产生出具有自主性与目的性的存在来。而在人类目前所知的宇宙范围内,只有地球上出现了生命,在这个意义上,生命的出现也是偶然的,并且出现的概率是极低的。
总的来说,生命都是具目的性的存在,这种具目的性界定了生命的自身善。根据生命所具有的目的,人们对之的行为才能够具有对错之分,因而才能具有道德意义。而生命的稀缺性则表明对生命保护的必要性。生命的存在是价值的根源,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价值,生命的稀缺性使得这种价值更为凸显,使得保障生命存在的道德义务成为必要。
二、泰勒生命中心论的两个问题及其解决
由于生命与非生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生命的具目的性,从生命的具目的性可以得出所有生命都具有自身善,能够促进之的就是合于生命目的的,而损毁之的就是有损于生命目的的。但是,虽然生命所具有的目的能够作为判断人类对之行为的对错标准,但这种对错并不一定具有道德属性。因为即便根据生命所具有的目的,我们可以判断对之的行为是否在符合其目的的意义上的对与错,但我们仍然可以质问这种错误的行为何以是道德上不正确的。
泰勒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存在物拥有自身的善这一事实(一个“是”的陈述)与应该或不应该以某种方式对待它的主张(一个“应该”的陈述)之间存在着逻辑断层。[2]44为了连接这个“是”与“应该”的鸿沟,泰勒提出了所谓的“以生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的核心是四条信念:“一、人类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一员。二、人类与其他物种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每个生物的生存和福利的好坏不仅取决于其环境的物理条件,也取决于它与其他生物的关系。三、所有生物都把生命作为目的的中心,因此每个都是以自身方式追求自身善的独特的个体。四、人类并非天生地优于其他生物。”[2]62-63泰勒认为,这种以生命为中心的世界观是一种感受自然的方式,所有理性及真正有知识的人都该接受它。它是一种严肃的基于合理的科学证据的世界观,放弃这一世界观就要求我们放弃或必须修改已经得到的众多生态科学知识。当我们理解并接受泰勒的这一世界观的概念后,我们就完成了从描述性的论断说一个生命有其自身之善到规范的论断说它拥有固有价值的转变。接受这一世界观并认识到所有生物的固有价值就是接纳了尊重自然作为“最根本道德态度”,对生命和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负起道德责任。
从尊重自然出发,泰勒提出了四个一般性责任,它们是不伤害原则、不干涉原则、忠诚原则、补偿正义原则。如其字面意思,不伤害原则要求我们不伤害任何生物;不干涉原则要求人们不要试图操纵、控制、改变或“管理”自然生态系统,或介入其正常的功用,不去干涉个体生物的自由,也不去干涉生态系统或生物群落以免妨碍生物自由地追求其善,对于某些“自然”产生的环境问题甚至于环境灾难来说,人类也都不能干预;忠诚原则要求我们不欺骗或背叛野生动物;而补偿正义原则要求对伤害其他生物有机体的人对该有机体进行重构,当一个道德主体被伤害后,对该伤害负责的人必须对该伤害进行修复。[2]110-123
泰勒通过“以生命为中心的世界观”架起了“是”与“应该”的桥梁无疑是正确的,但其从生命具有自身善的事实与尊重自然的道德态度所推论出的“不干涉”这一规范性原则却存在着问题。泰勒之所以得出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于个体生命的侧重。[5]164对于泰勒来说,由于每个生命个体都追求其自身的目的,而作为整体的生命,如生态系统、物种则由于没有自身的善与目的,因而也就不能具有道德价值。而个体之间的冲突与竞争是生命正常的自然状态。基于这样的理解,泰勒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公正地解决这些冲突的原则,这就使得“不干涉”原则被合理化。基于不干涉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目的不能干涉,即使在其受到自然灾害损毁时,人类也不能进行积极的帮助。
另外,侧重于个体、尊重个体的善,使得人类的大部分实践活动都不能进行。[5]164-165几乎人类的所有实践活动,都会导致大范围生命的消亡,比如为了活着,人类将不得不吃掉无数的蔬菜和肉类,从而使无数的植物、动物、微生物的生命被损毁。那么,这样的行为能够被合理化吗?泰勒或许会认为,如果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保存自身这种基本目的的行为那就是可以被合理化的。但是如果这种实践活动不是为了保存自身这种基本目的,而是为了其他的目的呢?比如,砍掉树林以建立医疗中心,毁坏淡水系统以在湖岸建立旅游胜地,推平长满野花的草地以建立购物中心,为采矿而挖掉山的一边等。[2]163由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共同处于一个生态系统之中,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会有其他生命,生命作为一个整体,个体之间的行为也必定会互相影响。因此,除了保存自身这种基本目的之外,在人类按照第二种或第三种目的行动时,其中必定会出现对于其他生命的损毁。而根据泰勒的不伤害原则,这些行为都将是不道德的行为。实际上,泰勒也承认这一问题,他说:“然而,在每种情况下,要行使人类的权利,自然就要因此付出代价,地球的野生生物就要遭遇直接的不可避免的伤害。如果我们接受尊重自然的态度,这些行动对我们来说就构成了道德困境。”[2]163-164如果这样,那人类必将过上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或者迁居到没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地方去进行实践活动。
简言之,泰勒的理论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不干涉原则与生命保存自身目的的冲突。由于生命都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而在自然界中的环境灾难往往会损毁生命的这一目的,因此,当自然界中存在着损毁生命这些目的的灾难时,由于大多数生命并不具备对抗这些灾难的有效手段,从而导致生命的消亡。但是根据不干涉原则,在面对这些环境灾难对生命的目的损毁时,人类不能干预,而是任其自然而然。第二,人类的大多数实践活动会损毁其他生命的自身善,从而与不伤害原则相冲突,因而是不道德的,这也就导致了对人类大多数实践活动的否定。
第一个问题主要是由于泰勒没有考虑生命的独特性与稀缺性而导致的。结合这两个事实,可以推论出的应当是某种积极的道德责任,即帮助生命实现其保存自身的目的,或避免生命基本目的的损毁。这种积极的道德责任是有充分理由的,因而是可欲的,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支持这种积极责任的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生命这一完全不同于非生命的形态的出现,对于这个由非生命构成的宇宙来说意义重大。没有生命的宇宙是没有价值的,更是没有意义的,生命的出现赋予了宇宙以价值,使宇宙有了目的。没有生命的宇宙是必然性的存在,其自然而然且没有目的地运动着,而生命则具有目的。只有生命的出现,才能赋予非生命以价值,即作为生命实现其目的的工具价值。这一工具价值体现在:生命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和目的,将非生命作为工具。就较为简单的生命如微生物而言,其目的就是存活下去,不只是自己要存活,更要能够繁殖后代以将自身延续。在这一过程中,生命本身对于非生命的利用就是将非生命作为了工具,而这就赋予了非生命以工具价值,并进一步地使非生命的存在产生了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不仅仅是价值的主体,还是价值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生命也就没有价值。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不是人类的出现才使得整个宇宙具有了目的与意义,而是生命的出现使整个宇宙具有了目的与意义。在此,是否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一命题没有影响,所以即使是一个毫无认知能力的细菌,在这一点上所作出的贡献与一个人也是等同的。因此,生命的存在本身就使得宇宙具有了目的、意义和价值。而作为价值的主体,为了宇宙价值的持续展现,保障自身的存在本身就成了生命所应尽的义务。而生命的保存自身的目的也在这个意义上是善的,是有道德价值的。因而生命之间也就应当互相协助以实现彼此保存自身目的。作为目前已知的生命中最有能力保障生命存在的人类,在生命面临难以承受的自然灾难时,自然也就不能奉行“不干涉”原则,任由生命在自然灾难面前消亡,而是应当承担起协助生命实现其保存自身目的的义务。
其次,非生命的存在是普遍的,遍及整个宇宙,但生命则是稀缺的,其存在是偶然的。基于生命的稀缺性,假如地球上的生命由于其脆弱性而毁灭的话,对于宇宙来说,生命的消亡就是一种损失,损失的是一种极难再生且存在概率极低的可能性。虽然宇宙本身并不能意识到生命的这种稀缺性及其价值,甚至除了人类之外的大多数生命也不能意识到这种价值,但生命的这种稀缺性及其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基于人类对这种价值的认识与理解,人类也就更应当承担起保障生命存在的义务。
最后,人与所有生命都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这是所有生命所共享的。如果人类的自我保存的目的被损毁时,人们有义务去帮助他们,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同人类一样作为价值主体的其他生命不应当受到人类的帮助。因此,当生命的生存目的受到损毁时,帮助他们的道德义务也就显而易见了。
既然这种协助生命保存自身的义务是基于上述理由能够成立的,那这种义务是必要的吗?也就是说,如果生命完全能够以自身之力达到保存自身的目的,那这种义务虽然能够成立,却也是没有必要的。实际上,这种义务是必要的,这是由生命的脆弱性所决定的。生命是脆弱的和易消亡的,这也是生命稀缺性的重要原因。在很多人看来虽然生命在宇宙间的分布范围确实很小,但在地球上却有着数量庞大的生命群体。确实,地球上生存着难以计量的生命,从微生物到植物再到动物,生命在地球上似乎繁荣兴盛;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因为生命的存在需要极为复杂苛刻的环境条件,如温度、大气成分、地球环境、地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等。在这些影响生命生存的因素中,如人类的各式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工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人类的战争行为等已经使地球上的生命多样性减少,物种灭绝持续大范围地发生,而像小行星撞击、宇宙天体活动所产生的种种致命灾害等更是无时无刻地威胁着地球上的生命安全。生命在这些灾害面前往往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使生命就此消失殆尽。因此,基于生命在这些灾害面前的脆弱性,保障生命的生存目的这一义务也就是必要的和紧迫的。
如上所述,人类协助生命实现保存自身的目的是应当的,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因而是可欲的;且由于生命的脆弱性,这种义务也是必要的。因此,主张不干涉自然、任其自生自灭,实际上与由生命的独特性与稀缺性事实所得出的推论是相违背的。
第二个问题也可这样表述:在存在损毁其他生命的自我保存目的的实践活动中,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基于这种积极义务的必要性,如果不履行这一义务,那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将随时处于被各种灾难毁灭的可能性之中,届时,所有生命都将被损毁。相反,如果履行了这一义务,虽然某些生命可能被损毁,但生命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被保存下来。因此,就人类对这一义务的履行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就具有了正当理由。虽然这一理由并不能完全解决第二个问题,即对于除了履行这一义务之外的有损于其他生命的实践活动还需要理由和论据,但这种积极的义务实际上已经合理化了极大范围的人类实践活动。
三、积极义务的可行性
既然这种积极义务具有充分理由,因而是可欲的和必要的,那它是可行的吗?根据前文的论证,这一义务是具有充分理由的因而是可欲的和必要的,应当成为所有生命的道德理想。但根据“应该”蕴含“能够”的伦理原则,这一义务也应当是可行的。①可行性作为道德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由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首次系统论述,罗尔斯也将之称为“稳定性”。具体参见:罗尔斯的《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9 年第359页。这种可行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应当是生命有能力履行的。如果一个道德义务超出了生命的能力范围,或者要求太高而只能成为口号式的理想,那这种义务就没有可行性。其次,它应当能够成为生命的目的并产生按此义务行动的动机。如果生命没有充分的理由将这一义务设定为自己的目的并按之行动,那这种义务就由于不能实践而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基于前文所述的论据,生命之间赋有互相协助实现彼此保存自身或者阻止生命之间互相损毁的义务:这一方面要求生命之间互相协助;另一方面,这一义务要求制止生命之间的互相伤害。就其可欲性而言,由于这一义务是针对所有生命的,因此这一义务具有普遍性,是所有生命都应当承担的。所有生命都不应当损毁其他生命,并且应当制止生命之间所有互相损毁的行为。在世界之内,一般而言甚至在世界之外,只要是生命,就都应当被这一义务所约束,这是由于无论在何时何处,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前文所述的论据都成立。假如未来发现了外星生命,或许它们在形态上与地球生命完全不同,或许它们根本不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但只要是生命,那它们就都是价值的主体,并且相对于非生命来说都是稀缺的。
虽然这一义务的主体应当是所有的生命,但是基于这种可行性对行为主体能力的要求,以及生命之间履行这一义务的能力的差别,目前看来只有人类有这个能力。人类不仅能够根据自身所具有的保存自身的目的行动,还由于具有能够设定第三种目的的能力,使得人类能够承担起协助其他生命完成保存自身目的的义务。因此,笔者主要以人类为这一义务的主体进行展开。不过,假如还有任何一种生命有这种能力,那他们就也应当履行之。这里值得强调的是,除了人类之外的生命没有能力协助其他生命实现其自我保存目的的能力,也不能制止其他生命之间的互相损毁,但作为生命的基本目的,所有的生命都在尽其所能地保存自身。这种对自我保存目的的实现虽然不一定是生命意识到了保存自身义务的有意识的行为,但对于自身的保存却是生命的合于这种积极义务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生命的这种行为由于是合于义务的,也就应当被视为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种积极义务的可行性要求,生命能够在不损毁其他生命的前提下保存自身吗?这无疑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目的并不必然以损毁其他生命来实现。就大多数植物而言,它们只需要通过光合作用就可以实现保存自身的目的。另外,就数量庞大的家养宠物而言,在被人类驯养之前,它们往往需要捕猎其他生命作为保存自身的手段。但是在被驯养后,由于人类的饲养满足了它们保存自身的目的,它们就不需要再去捕猎;即便它们偶尔会尝试猎杀其他生命,这往往也是作为一种娱乐消遣,作为对第二种目的如快乐的追求,而不再是为了实现第一种目的。这种生活对于它们来说无疑更有利于其第二种目的的实现。宠物作为一个例子,说明生命之间的互相损毁完全可以在其保存自身的基本目的实现后而得以消除,并有利于它们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目的的发展。因此,在理想条件下,人类应当为所有生命提供帮助以实现其自我保存的目的,制止所有生命之间的互相损毁行为。
然而,实际上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生命数量极为庞大,人类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介入其中,以保证生命之间不通过损毁其他生命来实现保存自身的目的。根据“应该”蕴含“能够”的可行性原则,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人类去完全履行这一超出人类能力的义务。不过,由于所有生命都在根据自我保存的目的行动,并且这种表现为生命本能的求生欲望是如此的根本,以至于只要不出现不能承受的灾难,生命都能很好地实现其目的。并且,除了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往往并不会进行无端的杀戮,刻意以损毁其他生命为乐。它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努力地实现其保存自身的目的。因此对于自然界中生命之间为了保存自身而进行的彼此的损毁,在可行性的条件之下也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辩护。但是,假如生命之间出现了不是以保存自身为目的的而对其他生命的损毁,则人类就应当履行这种积极义务去制止之。这是由于不以保存自身为目的的对生命的损毁与这种积极义务相违背。比如人类为了追求美食、时尚等,而去猎杀生命、取其肉以食、取其皮以穿戴等,就由于超过了保存自身的基本目的且没有其他的正当理由而应当被禁止。
假如在人类的能力范围内,对某些生命或物种的救助并不损毁其他生命的生存目的,履行这一义务就具有了充分理由。比如对于某些濒危生命,如果对之的救助不会影响其他生命实现自我保存的目的,那人类就有义务协助之。实际上,如果某些生命或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时,对它们的救助往往并不会损毁其他生命保存自身的目的。这是因为如果某种生命或物种处于濒危状态,也就是它们的数量已经极为稀少时,以此生命或物种为满足其保存自身目的手段的生命必定也极为稀少。因此,由于可行性要求的限制,人类由于能力不足而不能对所有生命履行这种积极义务,但对濒危生命或物种的救助则由于并不会影响其他生命,并且完全在人类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时的积极义务就是应当的。
除了表现为对濒危生命的救助和制止生命之间不以自我保存为目的的损毁外,这种积极义务也体现在对于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所面对的灾难上。除了人类之外,目前所知的其他生命对于自身所生存的处境的了解并不多,而人类基于其卓越的认知能力,对于生命所面临的潜在危机和灾难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人类科学技术水平使得人类有能力在实现保存自身的目的之外,协助其他生命应对这些灾难和危机。就应对生命所面对的威胁而言,似乎有两种处理方式:首先,协助增强生命自身以免受威胁的侵扰,比如建立防护体系以防止生命之间的内部毁灭战争以及外来天体对地球的撞击等地外灾害等;其次,协助生命扩张其体量和分布范围,比如鼓励生育或星际殖民等。
基于可行性的第一个条件即道德责任应当是责任主体所能够履行的,由之确定的积极责任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一种负担;但应当看到,正是对这些积极责任的履行,人类获得的是进行某种有损于生命的实践活动的正当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解决了泰勒的第二个问题。另外,这种实践活动的正当性又能够激励人类按照这一积极责任去行动,使人类产生履行这种积极义务的心理动机,使这种积极责任的可行性的第二个条件即应当能够成为生命的目的并产生按此义务行动的动机得以满足。人类除了具有保存自身的目的之外,还具有另外两种目的。对于这些目的的追求作为人类发展自身善的必要内容,本来由于其实现往往需要以损毁其他生命为代价而不具有正当性;但由于协助生命保存自身这一积极义务的必要性,却使得为了履行这一积极义务而必然需要的诸如科技、经济、工业等实践活动具有了正当理由而具有道德价值,这就给予了人类强烈的心理动机来履行这一积极义务。由此可见,协助生命保存自身的积极义务能够满足可行性的两个条件,因而具有可行性。